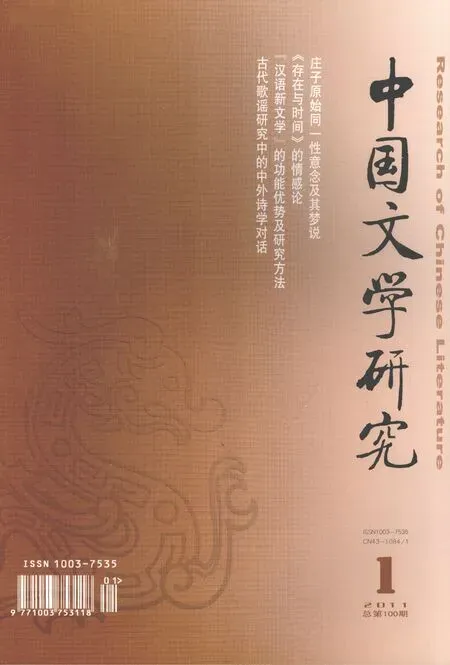“意义”的回溯与重构
——评吴康的《书写沉默:鲁迅存在的意义 》
张弛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邮编 100875)
探讨鲁迅存在的意义,历来已经是异常丰富而复杂的话题,吴康新出的著作《书写沉默:鲁迅存在的意义》(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版),还要探讨并追问些什么呢?用吴康在本书序言中的话说,本书要追问的是“鲁迅存在的意义”,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在柏拉图《智者篇》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当你们使用着‘存在着’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早就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然而我们虽相信懂得它,现在却茫然若失了。”〔1〕在我看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提及鲁迅的时候,似乎早就有一套我们从小就接受的关于鲁迅价值意义评判的标尺,但是当我们确信我们每个人都懂得鲁迅的时候,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否定、解构鲁迅的风潮面前,鲁迅作为“存在”的面孔似乎又模糊起来,而在神化与妖魔化鲁迅的两极之间,我们本来了然于心的“鲁迅存在的意义”这个问题,似乎又需要知识界重新去祛魅和证伪。
鉴于此,吴康提出:“必须将这些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种种命名搁置起来,径直走向鲁迅自身,睁了眼去看取他的在世生存,于言说中去倾听他从天地闭合般的寂寞的‘无声的中国’所发出的那个震世骇俗的声音,他书写沉默、打破沉默的声音。”(第8页)海德格尔曾经提到:“存在在思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2〕吴康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鲁迅在民族历史中的存在本身,以及他于这种存在的沉思中形成的言说:因为对于沉默无声的中国的国民来说,似乎很轻易地就会被权力阶层从历史中抹去,陷入到了无边的虚无当中而不能成为哲学范畴的“存在”,而此时鲁迅铁屋中的呐喊方才显出其意义价值,鲁迅在其存在之思中形成的语言,其为普通民众书写、代言的声音,这些成了吴康考察的重点。
一、对个体生存的关注
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观念悄然兴起,“民族被想象为拥有主权,因为这个概念诞生时,启蒙运动与大革命正在毁坏神谕的、阶层制的皇权的合法性。民族发展臻于成熟之时,人类史刚好步入一个阶段。”〔3〕“天朝上国”的子民开始成为世界意义范畴内的“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当时趋向激进的康梁改良派、孙中山的革命党人,他们积极推动西化、主张立宪和共和的启蒙呼声;还是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晚清国粹派,其偏于保守的反对贱古尊今、主张建立宗教、提倡国粹的民族主义主张,其存在的一个大时代背景便是,在西方列强虎视盘踞的时代,如何保国、保种、保教,于危机四伏中保住中国人在地球上的“球籍”,是摆在仁人志士面前的首要问题。民族、国家作为“群”的概念成为如梁启超这样的士人关心的重点,梁启超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主张新民,目的和手段都十分明确,其落脚点皆在于“群治”,“是在‘群’的统摄下去谈‘国民’、谈‘私人’、谈‘个人’”,“他们可以在不同的时期强调任何不同的思想内容,但他们思想深处的主题却永远是民族国家、是富国强兵”。〔4〕而恰恰是这一个看似不容置疑的具有绝对道德正义性的理想,成为了鲁迅警觉并且批判的对象。
“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缠始终如幽灵飘荡在近现代中国的上空,“五四”一代人以倡导个性自由解放的启蒙思想始,最终也转入“阶级”、“革命”的话语,重新回到民族、国家的重心中来,时至今日,同样会出现《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这样的民族主义呓语,诚然有其反对西方中心霸权的思考,但其对隐藏在“群治”之后个体生命差异、生存状况的遮蔽也不可小觑。这也是吴康在书中所突出并强调的鲁迅之为存在的第一个意义,早在20世纪初期,面对西化风潮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兴起,鲁迅不仅只有倾听的接受,并且已经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有了自己冷静的辨声,“由此生发的是鲁迅对中国现实最深刻也是最执着的生存体验,‘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在如此‘千万无赖’丛生的国度里,‘群治’的兴起必然以‘个人的供献’为代价,相对于封建的‘独夫’统治,‘千万无赖之尤’势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其压迫程度尤惨烈于专制暴君”。(第27页)
鲁迅这里所警觉的,是打着国家、民族的旗号,干着牺牲个体生命利益为自我或集团谋取利益的勾当和行为,毕竟“千万无赖丛生”的国度,极权的独夫固然可怕,但是多数人的暴政同样值得警惕,吴康便指出:“他们没有考虑到这样的理想学说是否可以遂行于当下的中国,他们并未就现实生存来追问:由谁来群治?无谁无我的群治只能是理想的滥用,犹如‘乞灵于不知之力,拜祷稽首于祝由之门者’,如此的理想只能破碎于中国残酷的现实。”(第28页)理想的滥用只会让在“群治”名义下个体生命消亡,让自由沉没,最终导致理想的毁灭,“无‘我’无‘谁’的社会仍只是一个荒漠萧条的社会。”(第70页)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基尔凯廓尔、尼采表达过相类似的观点,基尔凯廓尔便指出:“当个人什么也不是的时候,由这样一些个人所组成的公众就成了某种庞然大物,成了一个既是一切,但又什么都不是的、抽象的、被遗忘的虚空。”〔5〕而对鲁迅影响巨大的尼采在阐释他的超人思想时,有这样一段话:“我叫那为国家,那里无论善与恶,一切人都是饮鸩者;我叫那为国家,那里无论善与恶,一切人都丧失了自己;我们叫那为国家,那里一切缓慢的自杀叫做‘人生’。”〔6〕国家的“巨灵”无限膨胀,所到之处,不仅可以熔铸市民阶层,更可以消解个体存在,最后便是鲁迅所说的“以众虐独”、“灭裂个性”、“人丧其我”的可怕景象,鲁迅这里的思想与西方哲人相连通,但是他同样是依托自身存在的历史环境所作出的独立判断,要知道,在救亡保种为首要任务的晚清民国,在“群治”思想和民族国家观念急剧兴起的时代,要有这种超越的眼光做出这样的辨声是不易的,故吴康在书中强调:“鲁迅于‘举天下无违言’的近代维新之声中所倾听到的‘恶声’,仿若‘新声’,实为‘恶音’,只有慎思明辨者才会有这样的倾听,才会听出中国历史生存本质的弦外之音,才能去除深深的历史之蔽而将生存的真理呈现出来。”(第70页)
二、对“历史同一性”的批判
历史学家唐德刚曾经以“历史三峡”比喻中国近现代历史自1840年开始的转折,认为从独裁、专制走向法治、文明,至少需要200年方能透过惊涛骇浪的三峡,如果历史出现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将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中华民族的苦日子仍将持续。如果说唐德刚是以历史家的眼光来剖析中国历史的话,那么鲁迅则是以自身作为身处“历史三峡”中的存在,来实践走出历史迷局的求索之路。
鲁迅起初是相信进化论的,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曾经谈到:“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7〕近代中国受进化论思想影响深远,从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再到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改良和革命把成功的期望预设在将来,投射在年轻人身上,鲁迅最早期的论文便曾经热情洋溢地介绍了进化论的思想,并且热忱地信奉过它。然而无论是康梁主张的“虚君共和”,还是袁世凯的“君政复古时代”,再到“王道”与“霸道”的民国,关于现代民主、自由、文明的预设终于全部落空,过去是奴隶,如今之后成为了奴隶的奴隶。于是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沉思到了一部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中国历史,在这个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吴康在书中引用了阿多诺的话:“并非所有的历史都是从奴隶制走向人道主义,但是,有一种从弹弓时代走向百万吨级炸弹时代的历史。”并指出近代中国的变革史,“是中国人鉴于历次惨痛的失败向西方人学习的一条‘省悟’之路,学者名流视为一条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但鲁迅的看法恰恰相反,却是一条日益走向现代专制的道路。”(第371页)
吴康认为,关于历史同一性的判断,“都是鲁迅基于自身现象学的深刻言说,从自身的存在命运中展开的深广历史探寻,将中国沉重的历史生存置诸眼前,重叠在自己身上,从而能够于最近处直面它,‘肉薄’它,‘睁了眼看’它,以冷嘲热讽的笔墨解构它。或许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零度写作’,从此写作中呈现那个循环的历史同一性的幽灵,因为鲁迅自己就处在这幽灵笼罩一切的生存中。”(第297页)对于中国历史的同一性,作者自己在书中有比较精彩的论述:“中国历史生存的可怕同一性,不仅吞噬了民族的过去,而且还在和正在吞噬现在,呐喊无从置喙,于是便走向了孤独,终结于死一般的寂静和绝望。”(第169页)“如长在一个人脸上的‘艳若桃花’的疮瘤,但却实难以割去。由此‘国粹’与‘特别国情’便生长出历史的巨大同化力。中国倘有变革,也只是‘结合’之类,‘结合’者,同化之谓也,将‘他者’化为‘我’用,绝不会将‘他者’化而为‘他’的。这‘化’便造成了混杂,造成了社会生存的多重混杂现象,治者们便在这混杂中维系着他们的最高人生理想,历史同一性便在这混杂中长此永存。”(第292页)
柏杨先生曾讲到过这样一件事情,“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后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8〕这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满怀期望与热情的呼喊:“救救孩子”,然而面对暮霭沉沉的古国,“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9〕的执着信念最终变为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10〕的哀叹,进化论关于今胜于古的理想轰然崩塌,鲁迅对于投射到未来和彼岸世界产生了自己的怀疑:“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11〕
那么在这历史的漩涡中,鲁迅的选择是什么?吴康在书中做出了提炼,那便是“‘别种的战斗方法’,是鲁迅对中国后专制社会提出的抗争方式,他称作‘壕堑战’”,“战士深居壕堑中,一点点地向前推进,一块块地占据阵地”。(第308页)“‘壕堑战’作为破解历史同一性的现代轮回的唯一方法,乃是一种坚韧持久的立足于自身的生存搏斗。”(第308页)吴康认为,生命后期的鲁迅,已不仅仅局限于“睁了眼看”的文艺,而是自己整个进入到自己的生存状态之中,鲁迅所能具有的最终存在意义,“便是用自己的皮肉甚至生命给沉默的世人以警醒,给‘无声的中国’的人们以有趣的观看,或许能打破专制政治的一统天下”。(第342页)这里,鲁迅存在的意义不仅是作为一个文学家,更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中的存在,以个人的生命践履为民族国家走出“历史三峡”,摆脱他所批判的历史同一性提供了可能和价值意义的参照。
三、鲁迅的“学匪派”考古学
20世纪,米歇尔·福柯作为一个反知识理性、反对文明社会思潮主导的批评家的出现,几乎动摇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理性、启蒙思想的根基,福柯一生致力挖掘和发现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揭露医院、监狱等社会机构对于强化权力控制力的作用,“在理性和理性的他者(或非理性)之间的永恒对峙中,‘知识’一直情同手足地站在理性权力的一边”。〔12〕在《规训与惩罚》、《知识考古学》等著作中,福柯力图揭示的是理性、知识、规范对于现代人的压抑。
对于鲁迅而言,吴康在本书中的发现是,其实早于福柯,鲁迅也架构了一套自己的知识考古学,揭露的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对于普通民众的压抑,以及古老“儒学”、“经学”等知识背后所形成的知识权力和话语霸权,中国历史中“权力-知识”的二元体在鲁迅的笔下同样被发现。鲁迅自称为“学匪派”的考古学。植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体悟,鲁迅对这其中隐秘的关系的揭露有二:
1、中国晦涩难懂的文字,使得除去少数阶层外的中国人,丧失了言说的权力,数千年的汉字书写,越来越成为知识精英的游戏,乃至他们获取功名的手段,客观造成的却是一个“无声的中国”,而“与这种鬼魂附体精神上的隔膜相应,中国人便丧失了言说生存的方式,没有了声音,也没有了语言:‘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之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第95页)对这一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力主白话文运动的胡适同样有深切的体会:“那时的中国智识分子是困在重重矛盾之中的:1、他们明知汉文汉字太繁难,不配做教育工具,可是他们总不敢说汉字汉文应该废除。2、他们明知白话文可以作‘开通民智’的工具,可是他们自己总瞧不起白话文,总想白话文只可用于无知百姓,而不可用于上流社会。3、他们明白音标文字是最有效的教育工具,可是他们总不信这种音标文字是应该用来替代汉字汉文的。”〔13〕不言而喻,知识分子心中自然明了,语言是把他们和无知百姓分野于“上流社会”和“引车卖浆者之流”的最直接工具。在这里,鲁迅洞察到了“以众虐独”、“人丧其我”的社会乱象和可怕的历史同一性的根源,一切言说之声最终只能归属于‘圣人’或‘圣人之徒’,几千年不过是他们的道理和意见,这甚至导致为民众代言、“书写沉默”都会遭遇到极大的困境和吊诡:“古国的国民并没有自己言说的声音,他们是沉默的,你丧失了进入他们内在的世界唯一精神通道——语言,那么你怎么能真正理解他们呢?你又能用怎样的语言去书写言说呢?”(第95页)
2、从历史生存论的角度来考察“学匪派”的把戏,儒术经学作为敲门砖而非思想和信仰,士人作为“流氓”、“打手”而非“大儒”、“大侠”。鲁迅绕过了微言大义、阐释学说,直逼的是圣人之徒们的生存本身,从此来看待他们汗牛充栋的知识生产背后的真实效用和面目,“鲁迅追述的无异是一部‘儒术’的效用史,一部儒学如何成为普世有效的‘敲门砖’的历史,它敲开的不仅是权力之门,而且也是生存利禄之门。只是它教诲的不是思想和信仰,而是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和自私,儒士们怎样的‘做戏’。鲁迅曾将此绝妙地形容为‘吃教’,中国的儒道释之流的信者,‘吃教’才是他们的‘真精神’”。(第427页)
鲁迅少以主义、派别来界定、划分人,在中国的酱缸文化里,鲁迅更讲究的是真伪,是生存背后的本真,“鲁迅的考古学,即是还原历史的本原,直观孔夫子的生存现象,揭示其本原的悲剧命运。有意将其千百年来为圣人之徒们大加阐释、寻索其微言大义的思想学说悬搁起来,直溯其存在之源。因为那部记载其思想学说的演进史——古代称为‘经学史’、现代称为‘思想史’——已被圣贤之徒们涂饰太重,失去了原貌;而且也是一个预设的思想陷阱,进入其中是无法从中冲突出来的,只会成为俘虏甚至‘笨牛’,是鲁迅所不屑为之的……”(第421页)唯有拒绝做这些思想陷阱中的“笨牛”,才能从已被涂饰、阐发得面目全非的典籍中走出来,勘测冠冕堂皇的谎言,发现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规则:“由先前的以‘天’来压服‘人主’、至死不与人主合作,退落到周旋于王侯权贵之门的‘大侠’;又降等为打家劫舍的‘强盗’,等待招安,为君王效力;再沦落到充当豪门的保镳与打手,最终成为了只能横行社会、欺压平民的‘流氓’。”(第430页)
知识本无善恶,可当知识分子的正义与良知丧失,变为权力和市场的附庸,其如此堕落的过程在所难免,高深莫测的理论、冠冕堂皇的主义也会成为“学匪”们打家劫舍的工具与武器,这便是鲁迅考古学揭露的生存本真。鲁迅没有将知识与必然善恶联系起来,而是更加强调知识主体的作用,他说“无论什么都是有弊的。就是吃饭也是有弊的,它能滋养我们这方面是有利的;但是一方面使我们消化器官疲乏,那就不好而有弊了”。〔14〕与鲁迅同时代的左翼思想家葛兰西曾经批判在资本社会里,专家型的知识分子极易堕落成为全社会的中介,上层社会的活动家以及统治集团的管家,而鲁迅自身作为知识分子的存在有些趋近于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并非是职业革命家,但是须深入市民社会,促进社会变革,鲁迅在1927年的一篇演讲中就表明过自己对于正在形成的知识阶层的认识:“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15〕
吴康在《后记》里套用海德格尔的话:“惟当此在存在,才‘有’真理”,推论道:“惟当鲁迅存在,关于中国人生的生存真理才在,才能揭破中国自古以来的专制生存的遮蔽和隐秘,书写沉默,打破沉默,彰显出真正现代的意义来。”(第445页)鲁迅存在的意义始终在于两方面,它在于鲁迅本身,同时也存在于鲁迅之外,一方面鲁迅本身不是随着时代热潮变化,而是需要我们静下来思考的;另一方面鲁迅作为有着永恒意义的作家,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启发和价值,不仅仅是过去,对于民族的未来也有其价值。在这里,作者努力回溯到鲁迅作为存在本身,同时更有立足于历史乃至当下,重新建构鲁迅作为存在者价值的尝试,对于重启当下我们对于鲁迅存在的思考,是有很好的启示意义的。
〔1〕柏拉图.智者篇〔M〕.转引自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5:31.
〔2〕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A〕.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C〕.北京:三联书店,1996:358.
〔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
〔4〕程文超.1903:前夜的涌动〔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43.
〔5〕熊伟主编.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65.
〔6〕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M〕.楚图南译.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55.
〔7〕鲁迅.三闲集·序言〔A〕.鲁迅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
〔8〕柏杨.丑陋的中国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5.
〔9〕鲁迅.呐喊·狂人日记〔A〕.鲁迅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53.
〔10〕鲁迅.而已集·答有恒先生〔A〕.鲁迅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73.
〔11〕鲁迅.野草·影的告别〔A〕.鲁迅全集:第2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69.
〔12〕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C〕.张国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55.
〔13〕胡适.建设理论集·导言〔A〕.中国新文学大系〔C〕.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14.
〔14〕〔15〕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A〕.鲁迅全集:第8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89,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