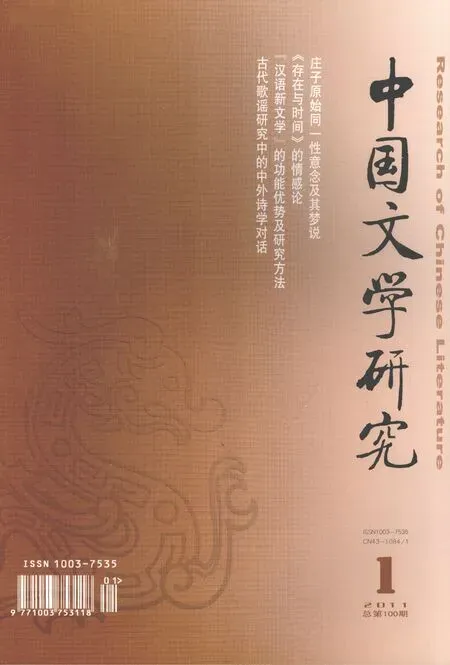对浩然文学“真实性”的理解与误区
——兼谈十七年文学评价问题
刘晓红 王富仁
(四川大学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37002;汕头大学文学院 广东 汕头 515062)
2008年2月作家浩然去世,一位红遍六七十年代的作家悄然离开这个时代。面对浩然,我们不仅仅是面对一个尽一身书写农民的作家,而是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他的创作横跨十七年、文革、新时期文学,创作轨迹遍布当代文学每个重要转折时期。研究浩然,是有效进入当代文学的渠道,是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农民形象的窗口,是理解工农兵文学方向的重要切口。然而时至今日,一个在当代文坛具有“样本”效应的作家的文学意义认定,至今模糊不清。其中,浩然文学里始终有一个欲说还休、道不清的问题,即怎样评说浩然小说的真实性。由始至终浩然创作引起的最大争议是小说与现实的纠结问题,真实性在此充当一个极其重要的评判准则。但事实上,什么是文学真实性?怎么理解文学真实性?以真实性作为唯一的尺度评价浩然,是否具有合理性?诸多混杂不清的问题,影响了我们对浩然文学的深入评说,对于这样一个样本意义的作家,解开浩然文学现象,对深入理解十七年主流文学也有一定益处。
在众说纷纭的文学真实性理论以及针对浩然文学真实评判的论争中,我认为不少研究者混杂或单一的使用“真实性”概念,对浩然文学评价存有一些误区,尤其对作家笔下“乌托邦”情结与局部细节真实的评价不一。事实上,无论是浩然或十七年时期的柳青等作家坚信自己所写的农村合作化小说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还是评论者据以历史事实质疑他们文学的真实性,我认为以文学真实性的含义和文学作品本身说话,才可避免评价中混杂的认识。“真实性”作为现实主义文学一个关键词,在十七年文学里有着强大的理论支持。近几年来,尽管“真实”已经得不到以往的尊崇,现实主义也作为陈旧的创作方法,但具体到在评价这段时期文学创作时,仍不可避免地落入把作品描述与现实进行比对。达成共识的是,农业化运动的历史和政策得失是不能作为文学优劣依据的,但是人们还是常会根据历史判断小说与现实的差距,并以现时代的价值观念作当时故事的评价尺度,然而,浩然的创作不是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著作,也不是供研究合作化运动的政治资料,它是小说,而且是只会出现在浩然笔下的小说故事。
一、“乌托邦”与“真实”
对于一个终其一生“为农民,写农民”,四十五年创作精力全部奉献给农村题材小说的农民作家,浩然从创作到行为都像一个地道的农夫。对农村农民有极深感情的他,执拗地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书写农村,尽管外界针对他的小说有真假质疑,甚至口诛笔伐他的“不忏悔”,晚年的浩然依然坚信自己的小说有存活的理由。回顾作家在前新时期文学里的作品,即使全部创作建构在农村合作化运动描述框架里,就算这样与政治话语靠拢、服务的作家,体验文本后,我们仍然有感小说里激起作家写作的根本欲望不是阶级表达,而是对农村未来的“希望”,是对心中理想农民集体精神的称赞,对美好人性的向往。对于这种农民在运动中的热情描写往往也是浩然受人针砭、质疑其真实性的理由之一。人们常会以现实政策制度的灾难否定那个时期农民在运动中的热情和积极,批评者的现实前提是客观的,但这些都无法作为否定文学作品的理由。事实上,从现实历史来讲,这个前提依然可以受到质疑,我们无法否认50年代新中国农民对共产党无比热情和信任的事实,也无法否认合作化带给过农村切实的改变和利益,所以用现实为尺度是有逻辑问题的,更何况身在其间的我们无法轻易对历史作简单评定。因此简单地就浩然作品歌颂了“失误”的政治、违背了生活而评价浩然,是极其粗浅和不识文学本质的。
那么什么是文学的真实性?文学真实性,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学思潮中有不同认知。大致说来,我们要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上考查浩然创作肩负的真实性。文学的真实,我们更强调的是“本质真实”,但严格地说来,就像没有完全客观的真实,完全本质的真实也是不可能的,由于创作者的主观性,任何作品都会出现作家经验之上的或真或假,或深或浅的反映部分生活的本质。另外,“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绝对不同于客观实录,除了事实本身的展示,它必须是渗透了作家深刻的思想的,包含着作家对生命、对人性、对生活事实的深沉思考——这一思考就凝结着对本质真实的深沉认识。所以,评价一部作品的真实性,不能只看它与外在现实表象是否完全一致,更应该看作家对深沉生活的渗透力、思考力和洞察力,看他透过生活表层、揭示生活本质的能力——只有作者的这一思想渗透力是强大而深刻的,揭示出了生活背后隐藏的、为一般人所忽略或难以理解的深层潜流的时候,它才具有真正的思想震撼力,才具备高度的真实性。”〔1〕对照以上对文学真实性的理解,浩然的文学无疑是有自己的思想认识的,问题就在于它不够深沉,没有达到超越时代深度的程度而已,但我们依然不能否认在文学本质真实里,浩然具备文学区别其他人文学科最大的特点,即它是以情动人,以人性书写和再现为基准的,即使这些与历史发展规律相违背的作品,只要具备了对生活和人性一面的描写,也有可能获得它独特的本质真实。所以浩然小说故事里隐现的乌托邦美好生活向往以及人性大公无私、集体精神追寻,足矣是一种能使文本生辉的独特力量。
围绕真实性问题,浩然小说里乌托邦美好生活的描写遭人诟病,而我的看法不同,正像上面提到的,尽管不够深层透过生活表层、揭示生活本质,但从文学个人阅读体验触动,浩然小说故事里隐现的乌托邦美好生活向往以及人性大公无私、集体精神追寻,依然足矣打动读者。评价浩然小说里的乌托邦问题,我认为与客观现实是否一致不能成为评价这个问题的尺度。“乌托邦”一词就是对完美理想人性、人境的追求,依照文学世界里对乌托邦的理解,我在此更多使用“乌托邦心态”一说,“当一种心灵状态与他在其中发生的那种实在状态不相称的时候,它就是一种乌托邦心态。”〔2〕“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虽然都包含着一些超越现存秩序的观念,但是,这些观念并没有作为乌托邦而发挥作用,……只有当某些社会群体通过他们的实际行为举止把这些充满希望的意象体现出来,并且为了实现它们而努力的时候,这些意识形态的心灵才会变成乌托邦心灵状态。”〔3〕显然浩然的文学里有着这样一群为之努力的人物。乌托邦作为人内在具有的对完美的渴望与追寻,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表现,至古中国就有此类文学期许,从老子、孔子到近代太平天国、梁启超的政治文学,再到毛泽东时代,浩然的文学在一定程度就是演绎着这个时代的乌托邦文学心态。既然是文学表述,那么进入文学的历史,虽然无法割断与历史事实的联系,却已不是历史现实的本身了,它打上了写作者的印迹。一旦历史的片断进入文学的修辞世界,那就是“想象”的世界。那么浩然的文学在这个想象世界中敞亮的是什么了?这是涉及如何评价浩然乌托邦写作、以及就此如何评价浩然文学真实性问题的关键。与评说浩然小说是“乌托邦祭坛”的论者意见不同,我认为不能简单结论。同样写农民的新生活奋斗,与同时代合作化小说《创业史》相比,柳青是农民物质欲望贯穿在集体创业之中的,而《艳阳天》、《金光大道》显然是轻视、抵制农民原始物质欲望的,姑且不论这样的表述符合人性现实与否,这里有一个矛盾:正如《艳阳天》、《金光大道》笔下的集体精神让人感染,然而小说在主人公们集体热情下,并没有充分讲述集体生产能量如何追求富足生活,那么小说究竟要在集体主义情怀下表达什么或者说由着这股热情带领着农民追求什么?这就是浩然小说的致命问题:从作者创作激情出发,他在一定层面带给了读者美好人性、未来生活的期待,但受认识生活深度局限,他所表达的乌托邦世界却不足以深刻。这就构成一定程度的艺术感染力与整体缺乏思想深度之下,呈现出的“有而不足”、遭人质疑的复杂局面。究其根本来说,浩然的小说实际表达的是“不患贫、患不均”的“乌托邦”农民梦想,萧长春、高大泉被赋予的集体带头人形象,实际演绎的还不像梁生宝式的个人理想光芒下的引领同伴实现财富梦,他们更像传统意义上桃花源境界中的武陵人,并不在乎能追求到的物质生活高度,相比之下,只要能在一片祥和、无矛盾的天地里,没有不平等、没有剥削,有田公耕,有饭共食即可。所以为了实现这个平等境界,在目前现状生活中,就要不断的发动阶级斗争,消灭阻碍这一目标的阶级敌人以及农民身上表现出来的个人自私小农意识,提倡并以身作则集体精神,这就是我们在浩然小说中看到的集体主义内核,然而这样不顾人性本质和现实中国情况的表达期待,注定只能是“乌托邦”。有限的思想深度在关键之中减销了浩然乌托邦表达的深度,加之小说里与现实不合的描写,大部分读者就会否认浩然作品的真实性,诟病他的“乌托邦情怀”。
谈及浩然小说的乌托邦表达,我并不想过多的涉及政治视野或现实,仅在文学表达里考查之于浩然个人意义的“乌托邦情怀”与文学“真实性”问题。我认为不能简单从政治或现实生活否定作品的真实性,从文学出发,在表层看似不顾客观生活写作下有一种个人内核理想的诉说,文学本质就是表达个人情感,虽然浩然要述说的情感没能以绝对的艺术力致胜,或者说无法企及思想的渗透深度,但是作为阅读,我们应该尊重作家真诚、努力想要表达的情感,这也是晚年浩然面对批评能保持沉默与坚守的作家之心。
二、细节真实的艺术与观念真实的误区
细节真实是评价一部优秀作品的指标,回顾十七年几部经典的主流小说,大致都有突出的细节描写,如同浩然小说被评价为细节真实、整体观念化,“在作品里,生趣盎然的形象与外加的观念,回肠荡气的人情与不时插入的冰冷说教,真是的血泪与人为的拔高,常常扭结在同一场景。”〔4〕浩然小说里局部细节真实和整体小说观念化构成的悖论,也是浩然现象中剪不断理还乱的争执问题。就作家而言,浩然坚持小说中农民都有真实人物原型,故事也是当时农村中真实发生过的,所以自己的小说具有真实性;研究者就历史现实而言,论证浩然小说是虚假的观念真实。那么究竟用什么来衡量作品的真实性?事实上,我们通常用模糊不清概念去判断,以致于纠结在对“真实”理解的误区中。
文学的“真实”与一般意义上的“真实”不完全相同,一般意义的“真实”是指“相符”,即观念、表达与客观事实符合。对文学真实而已,除了必要的与客观事实相符,文学还有虚构性,那么怎么理解文学真实性,虽然不同时代和文学流派有不同“真实”理解,大致说来,“文学真实包括两个维度,一是经验之真(体验之真),一是真理之真。所谓经验之真,是指通过感知和表象所直接把握到的人与世界之真切相遇,或者人的诚而不伪的内心状态——此为经验意义上的‘真实、真诚’。所谓真理之真,则是通过思维之归纳或演绎,或者径直通过直觉把握到的宇内万物抽象的运行规律或隐藏于其后的内在结构、秩序与动因——此为所谓的‘真理’,即潜藏于现象背后的‘本原、自身’(当然,所谓真理之真也常常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示,通往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性规定而非字面所指涉的‘真理’)。”〔5〕简单地说,文学真实性是经验之真和真理之真。而事实上,由于文学创作的主观性特质,在文学真理之真维度上,往往是一种意识形态化后的“真实”,是一种经意识形态“规定”表达下的真实,即所谓的被创作者吸收、接受了的“观念的真实”。凭着浩然对《讲话》精神的笃信,他深信不疑地认可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政党是最能够接近客观真实的政党,因此无产阶级文学服务于无产阶级政党,自然也是最符合客观真实的,由此认定文学真理和政治真理是同一的,政治的正确性就是文学的真实性。“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绝对相信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绝对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那么,我们歌颂社会主义的胜利,歌颂为夺取这一胜利的人民群众,大方向完全正确。”〔6〕这就是浩然的认识逻辑,换句话说,单一认知和忠实信仰使他真诚地认为自己所写颂歌文学“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代表了文学真实反映世界的客观性,这明显是一种驯化后的“观念真实”。这里可以解答问题了,很明显浩然主要依据“真理真实”维度上的“观念真实”写作,并真诚相信自己写作方向正确,实际上后来者在评价作品时最针砭的也就是他的观念性真实,而作为作家,浩然毕竟有着极好的文学天赋,他在生活体验之上又有符合实境的细节真实,即有一定“经验之真”,因此两种真实交织混同在一个文本中,形成驳杂、真假难辨的复杂局面。如果不避表达的简单化,则可以说,客观真理赋予文学现实功用,经验之真使文学富有血肉,而浩然在过分追求“真理之真”之观念真实的功用性之中,饱有的“经验之真”(有关生活的细节真实)在一定程度挽回了浩然小说观念写作造成的虚空性。这就是“写什么”和“写得怎样”的问题,“写什么”是浩然的“观念”决定的,而“写得怎样”是浩然“经验”之真到达的。也就是说,浩然在政治、阶级斗争路线框架里写作,但即使这个框架倒塌,内部充盈的生活故事依然可显现文本的生动真实性与文学魅力。这就是两种文学真实交织在浩然作品里呈现出的复杂面貌,因此不能用“真实”与否来笼统评说浩然的创作。再则,就“写的怎样”而言,浩然文本也是复杂难说的,虽然细节真实赋予文本艺术性,但观念之真的创作理念时常盖过作者的经验体会,事实上,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大部分作家都是被规定了“写什么”,被灌输意识形态中的真理之真,但是就文学而言,只有有着阅读质感的、有着体现作家艺术表现力的描写方能说明文学的“真实性”。
就文学细节真实表现力而言,相比柳青、赵树理,浩然的“观念之真”制约了他小说经验真实的发挥。以描写农民形象为例,柳青的《创业史》给人逼真的农民形象感,梁生宝、梁三老汉、徐改霞、高增福、素芳等人物的刻画除了带有柳青特有的知识分子情趣,可以说即使在强大的意识形态压力下,作者也少有让人物说不符合人物性格逻辑的话,这种对农民描写的细节真实性,正是《创业史》的文学价值所在。梁生宝,一个党在农村基层的干部,即使是这样集中意识形态的人物,柳青笔下梁生宝有生动的内心世界,在日益增长的个人威信过程中,有切实可寻的事件作逻辑对应,诸如在梁生宝个人“精神成长史”中,每取得一次精神进步,除了党组织给出指点,人物自身是经历动脑、切实分析作出决策的,比如买稻种、上终南山割竹,他用智慧和意志带领农民创业。相对而言,萧长春、高大泉的内心精神和情感世界显得匆忙而苍白,一出场,浩然笔下主人公就分外“成熟”,抓阶级斗争多于搞生产,过分强烈的阶级意识表达损伤了作品的生活气息。若说柳青心中,一部作品是否真实,要看艺术经验与主流意识形态是否相符合,赵树理则坚持,作品的真实来至艺术经验是否与日常生活经验相符合,诸如《三里湾》实际上就是以农民日常生活、心态做底,在合作化运动中展示农民生活的世俗情态的小说。文学作品,无论奉行什么主义,采用什么创作手法,或者企图传达什么意识意蕴,经生活经验之真展现的细节真实,最能体现作者艺术表现力,也是获取文学真实的重要指标,这一点不再更多做文本举例,可以说,浩然有突出的细节真实表达力,却因观念之真的理念更胜,常常在激烈的情感中为意识形态表达突然嵌入冰凉的说教,如小石子遇害一节,萧长春沉痛回到家里,看见孩子出生后的第一只枕头,坐在炕沿上,闻到一股子孩子的奶香味儿,联想到孩子幼稚的脸蛋时,刚强的硬汉子,压不住沉痛的感情,热泪直下,这一段细腻的心理刻画给我们展现了浓浓的亲骨思念悲痛之情,尤其是当革命恋人淑红走进来发现他的悲伤时,两人的心思是感人的。但作者忍不住跳出来,强行拔高人物阶级形象感,压抑人物的自然情感流露,把亲子之情,当作是英雄主人公不能具备的个人小我、自私、软弱的情绪。因此,面对淑红的伤心,萧长春反而安慰对方:“我一想到我为保卫群众不受大的损失,我自己遭一点小损失,遭了一点小损失,就保卫了大的利益的时候,我感到光荣啊!”〔7〕萧长春失去儿子却认为得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大利益,我们看到的也是人物褪下“人”的真实,最后走向“神化”。观念表达经常减销了作品带给读者的经验真实质感。
可以说浩然创作引起的最大争议就在文学的真实性上,这点也是如何评价浩然的关键疑难。浩然的问题在于,他认为“观念真实”远比“经验真实”重要,但作为一个有牢靠生活根基,有文学创作激情的写作者,创作者无意识会在文本中流露自我对生命、人性的文学表达,所以浩然作品出现“杂驳”情形,既有具体生活的生动场景,又有作者不自觉流露出的人性表达,同时又与因观念表达带来的与现实不吻合的“虚假”场景。“虚假”和“虚构”的区别何在?实际上,我认为,作者本人对此和评论者对此的认识还不完全相同。“虚构”在浩然眼里就是为“观念真”服务的文学手法,但因为大部分作品情节、主题的重复雷同写作,使读者阅读到最后愈发难以感受到文学本质虚构背后的艺术动心处,任凭作家如何自我真诚地认为小说是对时代的真实再写,可是时过境迁的读者并不“买账”,他们更多感受到的是“虚假”,而不是单一的艺术手法“虚构”。因此评价浩然文学真实性是不可简单一概而论的。
事实上,正因为多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难以对浩然以及十七年主流文学得出定论,研究浩然对十七年文学启发的意义也在此,作为一个典型性样本,透过浩然这个窗口,可观整体十七年主流文学样态。对于当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浩然确实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文学史解剖样本,他走上文学之途,他与时代亦步亦趋的紧跟,他笔下的独特农民书写,他被经典化,从文学写作内容到形式、从精神到实践都充分再现五、六十以及七十年代中国基本文学形态的变化。对于一个在每个历史转折点都留下一笔的作家,客观理解他的真实性,也是对这段当代文学史的正确看待。本质上说,文学研究是对文本的文学性研究,文学说到底是阅读体验的问题,我们不能过分用政治、经济、宗教等外在的体系代替文学感受。文学建筑楼里,感受是主体,而小说涉及到的相关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仅能作为主体建筑的外围门窗而已,透过门窗可以把楼里内部看得更清楚,但这些门窗却无法支撑或构筑起一幢大楼。因此在理清浩然文学真实性误区的时候,关键是个人阅读感受。抛开作品的研究,只是被外牵着鼻子走的外围研究,以致理解误区重重。我认为浩然是个复杂现象,他的文学里交织着时代观念和个人生命的双重表达,但由于观念表达的突显和作家单一的认知结构,致使精彩个人表诉的消减,作为作家本人极有文学天赋的才能,在特殊时代既得到极大施展也受到致命局限。整体来说,浩然以及他的文学是杂糅的混和体,以往的评价过于简化,只有回到阅读,在历史的辨析中才能相对客观理解浩然的真实性,作为一个样本启发我们看待十七年文学亦然。最后要说的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可供中国作家自由发挥、施展才华的空间是狭小的,客观地讲,即使这样,在那个特殊年代,在主流意识形态下写作农村小说的作家,也没能有几人的文学表达超过浩然的影响力。我相信,进行这样就算不够深刻的“真实性”研究,要比纠结浩然是否要“忏悔”的争执,有意义得多。
〔1〕贺仲明.真实的尺度——重评50年代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M〕.文学评论,2003(4).
〔2〕〔3〕〔德〕卡尔·曼海姆著,艾彦译.华夏出版社,2001:222,229.
〔4〕雷达.浩然,“十七年文学”的最后一个歌者〔M〕.北京文学,2008(4).
〔5〕姜飞.修辞立其诚—中国文学真实观念的历史和结构〔D〕.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01-16.
〔6〕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编.浩然作品研究资料〔G〕.1973:16.
〔7〕浩然.艳阳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