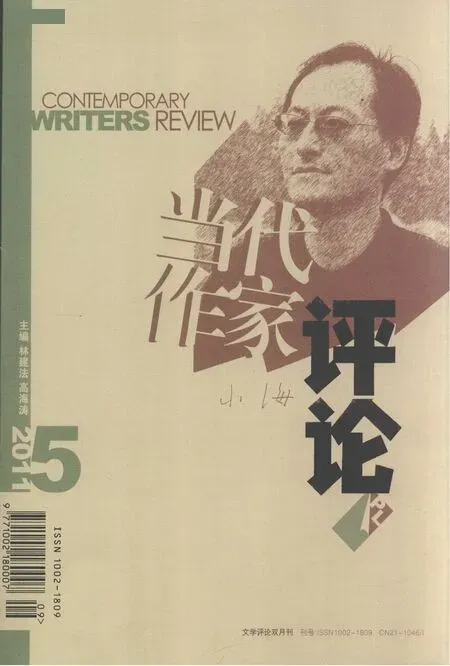逻辑的力量
张 红
王安忆为我们讲了三十余年的故事,同时,她也一直在思索如何讲故事,这思索首先是基于她自身创作的需要,除此之外,也基于对整个中国当代写作的整体境况的不满足。
不到二十七岁便结婚的王安忆曾在与文学批评家张新颖的对话中谈到,结婚之后,“就好像所有的经验都停滞了……这也是促使我写作必须要把出发点改变,把写作性质也改变。因为在这之前都是在宣泄……在表现自己的经验”。王安忆还认为,中国现代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作家很少,三十岁还没进入职业写作就退场了,终身写作者就更加难以找到。这导致我们现代以来的文学史缺乏继承性,而西方的文学史却都有源可溯。
在《故事和讲故事》的《我看长篇小说》一文中,王安忆讲述了“格林童话”里的一则故事。一个女孩子在她的订婚酒宴上到地窖去拿酒,久久不回来,母亲便下去找,却见她坐在酒窖里哭,问她哭什么,她指着酒窖壁上的一个桶说:“假如我结婚后生下了孩子,假如我的孩子到酒窖来拿酒,假如这个桶摔了下来,砸在孩子的头上,他就要死了!”母亲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便也和女儿一起哭。然后父亲再来找……王安忆极其赞赏这个故事所蕴含的“逻辑推理”,认为这种“冥顽不化的思维方式,却实在而有效,它可将一个极幼小孱弱的思想从出发地推至很远的地方,以达到一个遥远的目的地”。
这是王安忆一九八八年的看法,二○○七年,她在《写作课程宣言》中她再次提到了这个故事,并评价道“这是锁链式的,一环扣一环,而前提都是假设的,然后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就发生了”。到了二○一一年,王安忆在发表于《书城》六月号上的《短篇小说的物理》一文中,仍然认为,“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象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这自圆其说所依赖和仰仗的也正是逻辑。
逻辑,是王安忆所认为,并在自身实践中始终运用的,解决作家职业化问题的最佳路径。
逻辑是一个很“大”的词,有太过丰富的内涵,简单说来,逻辑的本质是寻找事物的相对关系,并用已知推断未知。具体到王安忆这里,逻辑被界定为一种自圆其说的思维方式,是作家在经验停滞的状况下,依靠对生活的观察和想象从已知推断未知,从而塑造人物,结构故事,丰富情节,完成作品,将人物从“此岸”渡到“彼岸”。她曾经说过,生活的逻辑无比强大,但同时,她对于类似上述格林童话这种纯粹的思维层面的逻辑游戏也有着旺盛的好奇心。
三十年,王安忆的作品在不断变化,从儿童文学到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再到如今的《富萍》、《天香》,但在这背后她始终有着清晰的、一以贯之的理论意识和追求,首先,王安忆以科学的态度,将自己置于文学工匠的位置,用逻辑的力量推动自己的作品,追求古典主义时代的人物在前台、作者在幕后的作品;其次,在这过程中,王安忆基于“做”也超前于“做”的“想”,也构成了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逻辑的魅力始终在魅惑着王安忆,诚如她在谈经典作品《百年孤独》时所传达的,如果艺术创作是一个游戏,那么她始终对这游戏的规则有着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
但不得不看到,她试图采取一种西方传统的哲思方式进行严丝密合的理论探索,却终究脱不掉中国人在理论探索时的实用和含混不清的命运。这体现为尽管在论述的过程中,她尽量一环紧扣一环,或判断,或推理,却在最初阶段——概念的选择和界定上过于随性。更令人不安的,还不止是随性,而是她在理论概念的运用上和她的写作同样地贪大,贪图那种丰盈的质感。因此,她选择了“逻辑”、“物质”、“思想”这类尤为难以掌控和界定的词汇,这带来的直接后果即是她的理论探索并不在任何一个理论体系之下,作为作家的王安忆在理论上始终处于并将永远处于童年阶段,喷发式地倾诉她走过的写作道路所获得的经验和感想。她认为《百年孤独》不仅是一本对拉丁美洲解释的小说,而且是一部有着独立存在意义的小说,小说所图解的对象(拉丁美洲,事实上用“所指”可能有着更少的歧义)和图示本身(《百年孤独》,能指)是相对独立的,图示本身可以脱离图解对象而独立存在,因此假设两者暂时断裂了关系,在图示的景象中,人的行为、事情的运动都有着自身的原则。借用这一说法,王安忆的理论所图解的对象(小说)与图示本身(理论)并非独立存在,她的理论倚赖小说,与小说创作协调一致,并不具备独立存在的品质。这孜孜不倦的探索终究有着明确的依附性的目的——作出更好的小说——整本书都在寻找做小说的“逻辑”。
但这正是一个迷恋表象的创作者的“理论”,正因了它的不能独立存在才避免了在概念内涵上的纠结,轻而易举地举步向前,寻找丰富的外延,倒也走到了一个有趣的境地,将理论做得如创作一般,不妨一读,而且为想成为作家的人如何做小说提供了一条王氏路径。
当然,这样走下去,王安忆的理论探索将是日益枯竭的,最终会简化为最为核心的一个东西。但作品却能够在这种简化之上日益丰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