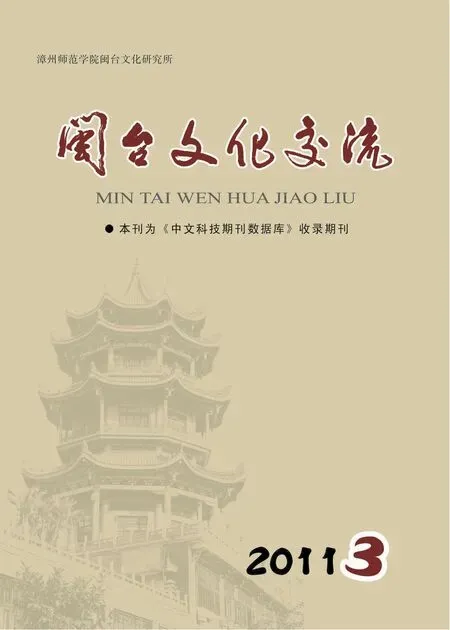从定光佛信仰看台湾汀州客与福佬人的族群关系
祁开龙庄林丽
从定光佛信仰看台湾汀州客与福佬人的族群关系
祁开龙庄林丽
在台湾客家族群中,有嘉应客、惠州客、漳州客、汀州客等,其中以嘉、惠二州客家占多数,汀州客、漳州客在台湾客家人中属于少数,所占比重不大。汀州客家人中又以永定人占绝大多数,台湾现存的两座较为完整的定光古佛庙均为永定客家人出资兴建和修缮的。可是,永定虽也存在上老庵、五公庙、镇龙塔、永封堂等奉祀定光佛的寺庙,可是与武平、长汀、连城、清流等地相比,永定的定光佛信仰相对要薄弱得多。在康熙、乾隆、道光、民国四个版本的《永定县志》中,并无定光佛的事迹与庙宇名录可寻。定光佛信仰在永定人中的信仰虽相对薄弱,但移台的永定人却仍以定光佛作为庇佑自己的地方神明,把淡水鄞山寺和彰化定光庵作为汀州人在台的“汀州会馆”。之所以会如此,与定光佛在闽西的地位有关,与台湾的移民环境及汀州客的族群意识有关,定光佛信仰是反映汀州客与福佬人族群关系的一面镜子。
一、汀州的“共神”——定光佛
定光古佛,又称定光佛、定公佛,俗姓郑名自严,泉州同安县人。生于五代闽国龙启二年(934),卒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开庆元年(1259),汀州知州胡太初主修的《临汀志》较为详细的记载定光佛生平以及定光佛在世具有的诸如除旱排涝、驱蛇伏虎、送子保赤、以及惩恶扬善、捍患御灾等带有神话色彩的功能。[1]
在赣闽粤边区,除了武平南安岩的定光佛,还有许多能为百姓提供祈雨、御寇、禳灾、祛病种种护佑功能的活佛、祖师,如汀州宁化县的伏虎大师、赣州雩都县的僧伽和尚等,何以定光佛信仰能脱颖而出成为闽西的公神呢?其原因大致有如下两个:
第一、定光佛信仰中蕴含丰富的内容,满足了各个族群现实的需要。广袤的闽粤赣边山区,自然环境十分恶劣。面对现实,定光禅师吸收和借鉴当地盛行的巫教和道教的某些宗教思想和做法,为百姓从事伏虎、除蛟、开井、治水、祈雨、御寇等活动,解决了百姓特别是北方移民的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所以百姓都信奉他为救苦救难之神明;其活动又含有当地土著原始宗教中的某些成分,如定光佛的形象是五只猫头鹰形状的怪鸟或五个檀香苞子。定光禅师吸收汉人宗教信仰与土著居民宗教信仰的有益成分,创造了各族群共同信仰的民俗佛教。
第二、官府对定光古佛信仰的大力表彰和鼓吹。定光佛虽有道法和巫术的表现形式,但又不同于道与巫。它是正统佛教与赣闽粤边带有巫教色彩的民间信仰的结合体,是南迁汉人宗教信仰与土著居民宗教信仰的结合体。这一改良的佛教,适应了官方对老百姓进行精神统治的需要。最初,由于定光大师的某些行事与巫道相似,有些官员将其视为左道。后来,随着定光佛影响的日益扩大,官员逐渐认识到其形式有利于王道的统治,开始对他进行大力表彰和宣传。如祥符四年和六年前后任太守的赵遂良曾请他“结庵州后,以便往来话次”。他与定光佛交往是为了请他做法兴利除害。据记载,赵遂良曾先后请定光佛出水、除蛟,结果都一一奏效,他便“表闻于朝,赐‘南安均庆院’额”[2]。继任者胡咸秩看到定光佛祈雨,解除旱情,使当年农业大丰收,对其佩服有加。卸任后,便“历言诸朝列”,由是“丞相王公钦若、参政赵公安仁、密学刘公师道皆寄诗美赠”[3]。嘉泰(1201—1204)年间汀州郡守陈公瑛,则将其抬升到汀州精神领袖的地位,说:“雨旸之应如响,是佛与守分治汀民也”[4]。为了与定光佛的民间地位相称,陈公瑛曾不惜财力大加扩建了定光庙。此后,各任郡县官都对扩建修缮庙宇和奏请加封定光赐号方面不遗余力。在官方介入后,定光佛崇拜由原先百姓自发的信仰行为,发展成为百姓与官方共同推动的信仰,定光佛在汀州成为普遍的信仰。
定光佛信仰集各族群宗教信仰之有益成分,充分适应了闽西社会的发展环境,也满足了各族群不同的现实需要和信仰需要,也有利于清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王道统治。故定光佛信仰在汀州社会有巨大的影响力,是汀州客向外移民中的精神领袖。
二、定光佛——汀州客团结的象征
“不同人群创造不同的文化存在差异,不同地域的文化风貌也不尽相同。人口在空间的流动,实质上是他们所负载的文化在空间的流动。所以说,移民运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迁移。”[5]定光古佛作为汀州客家最主要的神明信仰,也随着汀州移民入台播迁到台湾。
汀州客家移民之所以选择定光佛作为精神寄托,主要受两方面的因素影响:
其一,台湾特殊的社会环境。
汀州客家人渡台,首先要面临的是渡台过程中的海上威胁,在当时的航海技术条件下,出现海难的几率是很高的。因此,希望乡土神明能“济汀渡海”。到达台湾后,因为西部的平原地带早已为先到的漳泉人所占,他们只能穿越西部平原,到达丘陵或近山地区;或在中北部登陆,建立新定居点。这些地区往往是菁密林森、瘴气弥漫,虎蛇成群,疾病、旱涝、毒蛇猛兽等常常威胁着他们。除了自然的因素外,还面临着居住地复杂的族群冲突。在他们拓垦的地区,族群成分十分复杂主要来自漳泉的福佬人,也有其他地区的客家人,还有原先的原住民,其中包括为数不少的有“猎首”习性的“生番”。这些族群或为争地划界,或为水利,或为私仇引起了一系列或大或小的战祸,大致可分为漳州人与泉州人的械斗、客家人与福佬人的对抗,汉人与原住民的征战等。社会环境恶劣,而当时清政府在台的控制力又很弱,无法有效的维持正常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求助于神明,求助于在闽西客家人最崇拜的定光佛。而定光古佛所具有的除旱、排涝、驱蛇、伏虎解疾以及惩恶扬善、捍患御灾等功能,较好地满足在台拓垦的汀州客的现实需求,故定光佛信仰在台形成一定的规模。
其二,汀州客在台湾移民中所占比重很小。
闽西客家人迁台很早,在明郑时代,就有相当数量的汀州客家人渡台。随郑经经略台湾的大将刘国轩是汀州客家人,其部属多为客家子弟,清廷平定台湾后,有一定数量的客家子弟留在台湾拓垦开基。到康熙后期至雍正年间,汀州客在台往来渐众。黄俶敬《番俗六考》载:“罗汉内门、外门田,皆大杰岭社地也。康熙四十二年,台诸民人招汀州属县民垦治,自后往来渐众。耕种采樵,每被土番镖杀,或放火烧死,割去头颅。”[6]至于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汀州客家特别是永定客,以更大的规模迁台。关于这一点,地方史志、今人论述、族谱、寺庙等建筑的兴建等,都证实了这一问题。[7]汀州客家人移台一直持续到甲午战争后,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殖民当局禁止移民迁入台湾,历经两百多年的汀州客家迁台随之结束。
客家迁台时间很早,也形成一定的规模,但是与闽南人、粤东人相比,在台的汀州客数量有限,势力单薄。据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编印的《台湾在籍汉民族乡贯别调查》称,福建汀州府属《包括永定、上杭、长汀、宁化、武平等》的客家人最少,仅占十五分之一。[8]汀州客在台所占的人口比例偏低,其势力是无法与福佬人、与粤东客家人相比的,面对原住民的袭击,面对漳泉械斗或闽粤械斗,他们不能从清政府那里获得救助,只能求助于神明的庇佑,依靠群体的力量。
因此,与武平、长汀、连城、清流等县相比,永定定光佛信仰虽相对要薄弱,但永定客家人(台湾汀州客以永定客家人为主)仍选择了定光古佛作为汀州客的精神领袖,彰化定光庵和淡水鄞山寺作为台湾的汀州会馆,成为联系汀州八县客家人的中心。
三、定光佛信仰与福客关系
明清时期,漳泉闽南人、潮汕人、嘉应客、惠州客、汀州客、莆仙人、福州人等不同族群,纷纷移垦至台湾。在这三、四百年间,各族群经过长期的互动与融合,出现了文化的融合现象,其中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带地域性与族群性的地方神明,出现了地域性与族群性界限模糊的现象。如福佬人拜客家神、客家人拜福佬神、漳州人拜泉州神、泉州人拜漳州神、南安人拜同安神、惠安人拜南安人神……等信仰融合情况。这种信仰信仰交融造成现在的台湾人很少知道自己祖籍地所拜的神是什么神,因为现在地域神明完全没有族群之分,任何族群都可以成为任何庙宇的信徒。但是定光古佛庙却是例外,它的运作除了汀州八邑客家人之外,其他族群一概拒绝。可以这么说,定光佛庙对汀州客家人有较强的团结性,而对于其他族群的信众则有较强的排他性。[9]
在台湾复杂的族群关系关系中,汀州客作为弱势族群,为了族群的生存,在内部必须特别团结,对外则则带有较强的排他性。鄞山寺和定光庵的日常运作规程里,就特别规定定光佛寺庙是由汀人办理,大事是由汀众“集体决议”。鄞山寺的“善后章程条款”碑文云:“鄞山寺系台北汀众公建,所有本寺祀业,应由本地汀人办理。公议有事项商确(注:榷)之处,亦由本地汀众集合议决”;“公议鄞山寺对于各庙,本有互相庆贺之举,自应遵行。至于在地绅士实心办理,及实有与劳寺中善后各事宜,若有喜庆,应行恭贺,由董事闻众集议,妥筹办理”;“公议董事必由汀众公议遴选殷实老练之人,秉公办理。倘遇有应行改易者,仍由众议公举接办,以垂定章”;“公议每年春季祭典之时,各董事务宜整肃衣冠,早晨参拜,汀众亦然。”[10]彰化定光佛庙亦有类似的规定,该庙规定,“信徒是世袭的,也就是改创庙当时的士绅后代始能继承成为该庙信徒,委员会再由信徒产生,庙宇的运作由委员会操作,外人无法参与,热心的外人也只能称之为香客,没有任何庙宇运作参与权。”“一位住彰化七十多岁的吕川成先生说,他的祖籍也是永定人,但他的祖先没有参与创庙,所以他的祖先两百多年来,也只能当香客,不得当信徒。”[11]从这些日常活动管理章程可以看出,鄞山寺与定光庙的定光佛信仰完全是局限于汀州客家的,它通过日常活动把“汀众”联系在一起。
定光佛信仰除了维系汀州客以外,在与周围福佬族群的接触中,定光佛信仰也表现出较强的自我调适的特征,在福佬社区中传播。“如台北县板桥市的普陀山接云寺,以观音佛祖为本尊,挟持有善才、良女、从祀有韦陀、护法,配祀有定光古佛、注生娘娘、十八罗汉、山神、开漳圣王、马元帅、李元帅。例祭日各不相同,本尊的观音是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定光古佛是正月初六,开漳圣王是二月十五。”[12]桃园县大溪的福仁宫,俗称“大溪大庙”,兴建于嘉庆十八年(1813),“宫内正殿主祀开漳圣王,左龛祀定光古佛,右龛祀玄坛元帅;左厢祀巧圣先师,右厢祀财神爷;后殿祀天上圣母,配祀注生娘娘、池头娘娘。就庙宇的规制而言,左为龙边,其位阶高于右边的虎边。定光古佛位居正殿左龛,可知他在福仁宫的地位仅次于开漳圣王。”[13]定光佛与福佬人的祖籍神并列庙中,并共享香火,说明随着汀州客的对外交往,定光佛进行了自我调整,为福佬人所接受,定光佛具有跨族群整合的功能。
上述似乎说明定光佛信仰在台湾汀州客与福佬社区都有较大的影响力。但事实并非如此,汀州客与周围的福佬族群接触中,虽没有汀州客直接参与到福客械斗中,但汀州客作为后来者,难免会与先到的福佬人发生冲突。特别是林爽文事件之后,客家人与福佬人之间的矛盾加剧,福客械斗事件时常发生。虽然事件的主角是福佬人与粤东客家人,但是汀州客也未能幸免波及。有一则古老的风水传说曲折地反映了淡水鄞山寺建立时汀州客与邻近的草厝尾街居民(福佬人)发生的冲突,其大意如下:
传说鄞山寺的风水很好,是个“水蛙穴”,庙后面的两口水井相当于蛙眼,庙前面的半月池代表蛙口,在这种地点建庙必然特别灵验。然而草厝尾街的居民却十分紧张。原因是草厝尾街的风水恰是一条“蜈蚣”,如果让水蛙开始活动,这条街就会受到很大影响。于是,在严重抗议不果的情况下,当地居民请来了风水先生:在草厝尾街高高立起一根钓竿,每天夜里竿头点火作为诱饵,鼓乐齐奏,频频念咒。汀州人也十分恐惧,极力保卫,甚至举行盛大祭典,最终才保住水蛙的一只眼睛,另一只被对方攻破,井水变浊,于是水蛙也成了“病蛙”。由于鄞山寺的风水遭到破坏,因此据传该庙的管理人,即使不死也要罹患重病。[14]
这则故事一方面反映了汀州客与福佬客两个族群在台毗邻错居,他们往往会因利益之争而冲突不断,无法和睦相处。在福、客冲突中,鄞山寺对汀籍客家人利益起保护作用,实际上也就是定光佛信仰对汀籍客家人的团结、凝聚作用;另一方面则汀籍客家在当时是属于少数族群,在与其他族群的利益冲突时,汀州客一般采取较为温和的手段,避免与其他族群直接发生冲突。在发生冲突后,汀州客作为弱势群体,常常是迁往它方。
鄞山寺和定光庵作为汀州客团结的象征,始终由“汀众”负责寺庙的日常运作,汀州客也很顽强地保存着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特色。但是在台湾这个族群大熔炉中,面对强势的福佬文化,以定光佛信仰为中心的汀州客在与人数占绝对优势的福佬族群的互动中,渐渐忘却自己的语言,出现了福佬化现象。台湾学者林瑶琪曾对彰化定光庙做过调查,发现目前定光庙管委会的103位委员祖籍几乎都是世袭的永定人,“但是很多委员已不知道自己汀州府人,他们更不知道汀州府就是讲汀州客话”。一位祖籍永定的七十多岁的吕川成先生说,永定不是讲闽南话吗?[15]随着祖籍、语言这些表层文化的同化,宗教信仰等深层的文化事象也出现同化,鄞山寺里供奉的土地神被叫做“福德正神”,而“福德正神”是闽南人对土地神的称呼,汀州客家人把土地神称作“公王”或者“社公”等,如永定高头江氏就称土地神为“公王”,是当地最主要的神明。鄞山寺是汀州客的主要庙宇,在供奉定光佛的同时,却也接受了对土地神的“福德正神”称呼,二者和谐相处,没有人感到奇怪或提出异议。[16]
四、结论
在台湾移民社会中,闽粤移民对原乡的地方神祇的信仰,使得带有明显地域性和族群性的地方神,常常成为一种以祖籍认同为基础的地缘关系的象征。如粤东的客家移民信奉三山国王、漳州人信奉开漳圣王、厦门同安人信奉保生大帝、泉州安溪人信奉清水祖师,而来自闽西的汀州客则崇祀闽西的地域神明定光古佛。
在早期的从无到有的拓垦过程中,移民长期面临着许多未知的自然环境威胁,更因不同族群之间的争水、争地等利益冲突而随时有丧命的可能,定光佛信仰在汀州客心中扮演着庇佑与安定的重要角色,而在现实生活中定光佛信仰又发挥着凝聚和团结汀州客的作用。而在与福佬族群的接触过程中,汀州客与福佬人的信仰也逐渐融合,定光佛信仰为福佬人所接受,奉祀在福佬人的祖籍神庙中。汀州客也对自身文化做了某些适应性调整,接受福佬文化的某些成分,“福德正神”称呼和谐的出现在定光庙中。汀州客与福佬人的双向性调整,是客家文化与福佬文化在移民社会的环境下相互互动、融合的必然结果。
注释:
[1]《临汀志·仙佛》与《临汀志·山川》,转引自谢重光:《佛学研究》,2000年第9期,页:121。
[2]《临汀志·仙佛·敕赐定光圆应普慈通圣大师》,转引自谢重光:《闽台客家社会与文化》,页:76。
[3]《临汀志·仙佛·敕赐定光圆应普慈通圣大师》,转引自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页:127。
[4]《临汀志·寺观·定光院》,转引自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页:127。
[5]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页:586。
[6]黄俶敬:《台海使槎录》,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页:272。
[7]刘大可:《闽西客家人迁台与定光古佛信仰》,《台湾史研究》2003年第1期,页:86。
[8]转引自刘大可:《闽西客家人迁台与定光古佛信仰》,《台湾史研究》2003年第1期,页:89。
[9]参见林瑶琪:《汀州客的团结象征—以彰化定光庙为例》,《台湾源流》卷44,页:132-133。
[10]杨彦杰:《淡水鄞山寺与台湾的汀州客家移民》,《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页:43。
[11]林瑶琪:《汀州客的团结象征—以彰化定光庙为例》,《台湾源流》,卷44,页:136-137。
[12]引自刘大可:《闽西客家人迁台与定光佛信仰》,《台湾研究》,2003年第1期,页:91。
[13]蓝植铨:《大溪的诏安客—从福仁宫定光古佛谈创庙的两个家庙》,《客家文化研究通讯》,1996年第2期。
[14]铃木清一郎原著,高贤治冯作民编译:《台湾旧惯习俗信仰》,台湾众文出版公司,1978年,页:301-302。
[15]林瑶琪:《汀州客的团结象征—以彰化定光庙为例》,《台湾源流》,卷四十四,页:137。
[16]杨彦杰:《淡水鄞山寺与台湾的汀州客家移民》,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页:45。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编:吴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