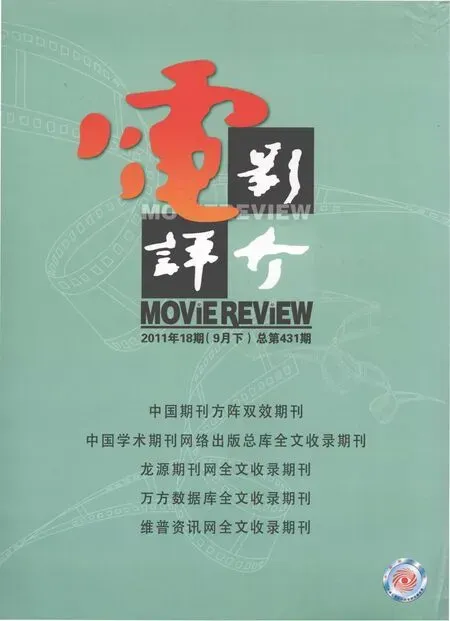只谈风月不谈魔术——电影《最爱》的症候与探因
一直盛传的以《魔术外传》[1]为名的顾长卫导演新作最终将片名更迭为《最爱》上映,一如既往的,影片试图将观众的视线从过分聚焦的都市拉回主流大众的乡村,配合艾滋病的敏感社会题材,讲述一个经典模式的“爱在瘟疫蔓延时”的故事。在顾长卫导演的创作序列中,他不止一次将人物置于不同层面的生存逆境里,竭力渲染绝处逢生的蓬勃生命力,配合摄影师出身的他对影像天生的敏感,《孔雀》和《立春》最终都取得了优异的口碑。新片《最爱》表面上遵循作者电影的一贯路线,将逆境从政治大环境与悲喜小个体过渡到新的领域——绝症,通过死亡宣判下的百姓对待余生的态度反衬出生命的美好和个体的不屈。但正如片名的变更一样,风格的传承在叙事与表意的双重过程中皆遇到了阻碍,一系列“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现象”[2]接二连三地出现在影片中,这究竟是创作者无意泄露的隐秘,还是在多重场域叠加作用下有意为之的合理规避,值得探讨。
在接受凤凰卫视[3]访谈时,顾长卫无不惋惜地表达了对《最爱》删节及其更名的失望,却在解释个中原因时略有含糊其辞。从他的表述中可以获知,《最爱》的原始版本长达两个半小时,原笔原意是描述濮存昕与郭富城所扮演的兄弟两人的故事,前者更为社会化(可以理解为与所谓艾滋病的故事关联更深),后者着重于渲染关乎爱情的情绪线索。根据顾长卫的说法,主要是“为了迎合影院放映的需求”而删减了将近一个小时时长,删除的依据在于濮存昕的线索过于“敏感”,而当下观众更乐意于在影院中享受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于是有关郭富城、章子怡的线索保留,与其无关的桥段被暴力地剔除。
这样的解释对于一位坚持且资深的导演来说显然站不住脚,选择“艾滋病村”的题材注定了导演的初衷在于揭示至少是呈现隐匿于边陲山村美妙景致之下令人耸动的社会性真相,而非谈论至少不是仅仅谈论所谓动人爱情。与此同时,顾长卫还多次强调原始片名《魔术外传》的合理性,并声称在被删除的一个小时时长中,关于魔幻的、富于想象力的内容可以为《魔术外传》正名,之后要力争让完整版“作为给观众的消遣”重见天日。因此,无论是不是无意识,在顾长卫这些的解释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亟待被更进一步阐释的意义,该意义在被阉割后的文本中依旧能够跟踪到蛛丝马迹。作为在2011年中国大陆上映的艺术电影的凤毛麟角,去探寻《最爱》这部几番波折的影片的完整样貌和分析其删改的终极原因,遂成为还艺术清白的极有意义之举。
一、叙事的断层与沉默
《最爱》最大的硬伤在于情节上无端的跳跃与莫名的抒情。与同期上映的国产影片《大太阳》[4]相同的是,中国大陆的导演们在处理攸关生死的凝重题材时,原本得以埋藏强烈戏剧冲突的机遇,最终都不约而同地成为似乎难于幸免的阿喀琉斯之踝,即一种浮于表面的想当然的被刻意捏造的情绪,成为了推动叙事进程的唯一主导力量,而勾连事件之间的线索屡次被毫无征兆地打碎,致使这些影片难于在原本就舒缓柔和的节奏中,吸引日益浮躁的影院观众。这种仿佛传染病一般流行于当下中国电影市场的硬伤对于手握柏林银熊以及《孔雀》《立春》两部优秀作品的顾长卫导演来说,似乎是一种不可推脱的罪责。但实际上,缺乏逻辑的情节并不是导演的随意所致,正如顾长卫在采访中所澄清的一样,如果从那些被遗弃的片段中找回可以与失落的情节相匹配的信息并完整转录,那么《最爱》或者说另一部叫做《魔术外传》的影片,最终的整体呈现大抵并非如此支离破碎。
顾长卫的所有电影,都以带有浓重乡音的画外旁白加大远景空镜头开场,《最爱》也不例外。唯一的不同是,该片的旁白是由一名已经死去的孩童赵小鑫念出,并且由这个声线稚嫩、口吻老成的画外音贯穿了整部影片。影片的开端部分匆匆交代了这位重要角色的死亡,然而由此开始,《最爱》的叙事就已经陷入了混乱的泥潭。导演将赵小鑫的死亡处理得十分暧昧,一方面旁白交代了全村感染热病(艾滋病),人们不断地死亡的事实,一方面用叔父郭富城与父亲濮存昕手拿菜刀冲出家门、作复仇状的升格镜头突兀地剪辑在赵小鑫的死亡戏份之前,这两个导向截然相异的构设,令观众无法辨知他的死亡究竟是身患艾滋病突然发病所致,还是被怀恨在心的相邻暗害所致(大部分观众在只看过影片后认同前者),而如果查阅影片上映之前流出的剧情梗概,赵小鑫的死亡原因是邻居给他吞食了经过下毒的西红柿[5]。这个至关重要的情节,可以解释此后濮存昕扮演的赵齐全对待一众村民的态度和行事作风何以至此,同时避免赵齐全的角色被过于平面地塑造成为利欲熏心的第一反派,但被导演十分刻意地略去,牺牲了整部影片的连贯逻辑。就连影片最重要的线索——章子怡扮演的商琴琴和郭富城扮演的赵得意之间的“爱情”——从本质上说是一段“搞破鞋”关系——都没能令人信服地叙述到位。在仅有一次的半推半就之后,两人就从有夫之妇与有妇之夫一跃成为相濡以沫的爱侣,他们的结合在有悖伦理的前提下,被导演强扭成具有合法性的争取自由的行为而争取或者说迫使观众认同。爱情(甚至只是孤枕难眠的寂寞芳心)在缺乏铺垫时突如其来,无疑削弱了逐层递进的真实性和合理性所本应带来的心灵震撼。更不必说那一整条给予濮存昕极大发挥余地的线索,最终仅仅依靠众人之口简单提及了事。
就像马歇雷在关于意识形态“症候式阅读”的理论中所表述的,“实际上,作品就是为这些沉默而生的,我们应该进一步探寻在那些沉默之中所没有或所不能表达的东西是什么”[6],《最爱》的“沉默”才是影片所真正倾向的描写重心。因此,这种急切到近乎盲目而最终造成硬伤的叙事,实际上是导演掩盖村中残忍真相的障眼法,戕毒幼童的行为、动物性结合的情节乃至赵齐全利用村民愚昧怂恿其卖血的前史,在这个从残酷时代写真退化成为柔美爱情小品的故事中,是如此的格格不入,哪怕导演愿意为这凄美的苦恋抹黑,影院方面也必然对繁冗的篇幅所影响到的排片而感到不满。但即便如此,对于最终呈现出的版本,顾长卫没能在九十分钟内圆润地叙述一个普通的爱情小品,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这个失误实际上来自顾长卫未泯的宏大叙事野心,他不愿放弃哪怕已经无力回天但仍能还原影片些许原貌的细节。于是,《最爱》给人的整体感觉是一块没有打磨光滑的璞玉,突显的毛刺就是那些属于《魔术外传》而并不属于《最爱》的桥段,可以说是顾长卫一半一半的坚守摧毁了原本简单的《最爱》,而给了两个半小时的《魔术外传》以悬念。
二、乌托邦梦泯灭和失语
《最爱》中的一大亮点,是顾长卫利用故事发生的背景精心构设了一个还原“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场景:即老柱柱将所有的艾滋病患者召集到停课的娘娘庙小学一同居住,意在使所有患者得到同病相怜的对方的关爱,免于遭到正常人的歧视,同时统一伙食也能避免浪费。但这个想象中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式的幻景,在现实的物质与精神基础都不具备的前提下,在人性的趋势下,只能演化为与历史雷同的悲剧:因为粮食的分配不均造成众口难调、校内的私人物品不断失窃、管理层与被管理者争权夺利的勾心斗角频频涌现。顾长卫原本想要借用这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生态圈反映某种阴暗的现实,加深影片中批判现实主义的力量,我们甚至可以据此推断出原始的《魔术外传》实际上寄托着顾长卫宏大叙事的史诗野心。根据粗剪版影片内部观摩提供的信息,郭富城与章子怡的戏份在《魔术外传》中只占百分之三十左右,而在《最爱》中蜻蜓点水出现的一众配角,在被顾长卫删减的部分中,组成了九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在中国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最真实最典型的一幅浮世绘。
事与愿违的是,最终呈现出的影片中,全明星班底的配角如同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每隔一定周期就无关痛痒的死去(这与艾滋病原本的症候截然不同),甚至由王宝强扮演的大嘴和蒋雯丽扮演的粮房姐的死亡仅仅是赵小鑫旁白中的两句话,仓促到连这两个较为重要的人物死去的镜头也并未给予。而另一位重要配角黄鼠狼在临死前看着家中厅堂上自己与一位莫名女子的合影,手握赵得意夫妇从围墙另一端抛洒进来的喜糖悲痛欲绝,也让人推测导演同样——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删去了一条原本重要的线索。此外,娘娘庙小学的公社也在一些小偷小骗中不知不觉的解散,导演放弃了进行众生相刻画的可能性,反倒是赵得意与商琴琴的“破鞋”关系越位地成为了重点叙述的对象,这种避重就轻的处理,让顾长卫试图营造的对乌托邦梦幻灭的描摹随着《最爱》的推出而土崩瓦解。作为影片的导演和题材的选定者,顾长卫对《魔术外传》的修缮显然带有极不情愿的让步妥协,这致使他在接受访谈时一方面对删改的原因三缄其口,一方面底气十足的宣称“影片从立项到投拍到上映都经过了广电总局的许可”。如果说选定爱情主线是市场需求的话,那么对于乌托邦之梦的鞭挞(至少是如实反映)的抛弃则令人浮想联翩。从“症候式阅读”要求批评家关注文本的无意识内容而非理性内容的层面上说,我们“沿着与其想要表达的含义相反的方向去阅读”,顾长卫对爱情唯美的不遗余力的刻画,实际上是对村民劣根性与共产乌托邦至少现阶段无可实现的慨叹。
三、魔幻现实之殇与禁区
在以《魔术外传》为名的影片中,相信顾长卫曾经设想过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来重构这个“取材于真实事件”的故事,而实际上《最爱》中零星的片段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世界影坛,前南斯拉夫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曾经凭借这种独特的风格,屡次摘取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的桂冠,足见魔幻现实主义的独特魅力。这种拉美文学爆棚时期流行的艺术手法似乎也是一部分中国导演追求的,特别是在他们的第三部电影中追求的一座里程碑。2007年姜文导演的《阳关灿烂的日子》以他第三部导演作品的身份亮相,影片以四段式的结构,颇具魔幻色彩的影像风格,和一系列神奇人物、超自然现象完成了魔幻现实主义这种起初仅限于拉美地区的艺术手段的中国化。然而,这种尝试的最终结果并不理想,过于超前的电影艺术语言对于仍然浸淫在好莱坞大片中的中国观众来说难于理解,姜文不计后果的个人表达也使得这次尝试从接受层面上痛饮失败的苦果。《最爱》同样作为第三部作品,在经历过写实主义的成功后,顾长卫试图赋予他的新作以魔幻现实的光环,至少在前期筹备阶段,从片名开始,影片就走向了又一条魔幻现实中国化的探索道路。
魔幻现实主义电影的一个重要表征,是一系列有灵性的动物成群出现,无论是库斯图里卡的《地下》《黑猫白买》《生命是个奇迹》还是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抑或是蒂姆.伯顿的《大鱼》,这种现象都成为了影片独特的风景线。在《最爱》中,戏份颇多的一头花脸猪担当起了这个重任,一方面,它是娘娘庙小学中唯一一个没有感染艾滋病毒的生命体,见证了人们渐次的离去;另一方面,它的贪吃直接造成了蒋雯丽扮演的粮房姐的死亡。《最爱》中另一处体现魔幻质感的桥段,是老柱柱梦中由赵齐全打造的一口真皮大棺材,这口棺材在极饱满色调的影像中有一种令人满足却又不寒而栗的感觉,与此同时硕大的棺材盖居然能够腾空而起。实际上随着镜头拉远,观众看到这是赵齐全手握遥控器对棺材进行升降控制。这个梦境流露出老柱柱对自己儿子操控村民生死的惊惧。除此之外,有看过《魔术外传》的内部人士表示,未删改影片的结尾处濮存昕掉入井中,而两只蝴蝶从中飞出,在所有人都死了以后,画面中闪现出两个看上去颇似章子怡和郭富城的小孩。这两个设计是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表征,不可思议的超自然事件背后寄托着导演对于这个没有生气的乡村未来的希望。由此观之,除却原始结尾遭到遗弃之外,甚显突兀的梦中棺材一段以及花脸猪的相关桥段实际上在原始影片中理应得到标准规格的放大延长,但也许是考虑到魔幻现实主义尤其是电影上的该种风格,对于影片的主要受众依旧是难于用常理理解的梦魇,因此在参考《太阳照常升起》频频被质疑看不懂的教训面前,顾长卫选择了部分放弃的策略,将《魔术外传》去魔术化,从而完成了《最爱》。
注释
[1]影片之前还被赋予过《魔术时代》《罪爱》等其他名称.
[2]蓝棣之.症候式分析:毛泽东的鲁迅论[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3]凤凰卫视作为为数不多获得中国大陆部分地区落地权的境外媒体,其言论和嘉宾言谈具有内地正牌媒体不具有的客观中立公正性.
[4]一部表现“五.一二”汶川地震周年祭的主旋律影片,导演杨亚洲.
[5]参见豆瓣网:《<最爱>剧情简介》,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4843637/
[6]Pierre Macherey.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M].trans.by Geoffrey Wall. Landon,Henley and Boston: Routledge&Kegan Paul,1978, 第 4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