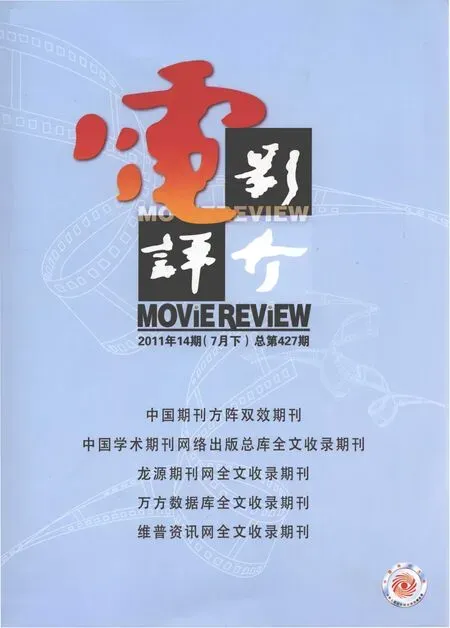从电影符号学角度分析电影《最爱》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刘玲玲
从电影符号学角度分析电影《最爱》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刘玲玲
电影符号学在影视批评的领域逐渐凸显其重要性。今年5月上映的顾长卫导演的电影《最爱》,不管是艺术上,还是商业上都获得了成功,从符号学角度看,电影《最爱》中间融汇了不少电影符号学的思想,多处能体现符号学的相关理论。
电影符号学 象征意义 《最爱》 道具
符号学出道之初,就被一些传统“正道的”人攻讦刻意的标新立异,甚至讽刺为“玩符弄咒”。符号学与当时的主流研究方向确实大相径庭,但是它的科学性经过时间的考验,已经被证实。符号学由一门新兴的学科发展至今,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多个方面。建筑、音乐、美术、舞蹈等各个领域都有了自己的符号学。电影也是如此,作为大众传媒的主要手段之一,电影符号学在影视批评的领域逐渐凸显其重要性,加之电影审美大众化的趋势,电影符号学已经由一门生僻的美学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首先,很多人对符号学的科学性提出质疑,或许是因为很多人对符号学并不了解,把电影符号学与一般符号学同而论之。“符号学”是由现代语言学之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提出的,他认为,符号学“是一门研究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符号生命的科学”。他的符号学理论集中在语言符号学。索绪尔还提出了著名的“符号的二重性”理论,他认为符号由“能指”与“所指”构成,分别体现符号本身的形式和意义(符号所表示的概念)。然而,“符号的二重性”理论并不适用于电影符号学。首先,电影没有最小的符号单位。电影符号显然不能以镜头为一个单位,因为一个镜头中囊括万千,时间空间的交错,人物与事物的重影,光线与音响的杂糅……电影艺术的综合性使电影的“格”也不能拆开化解。电影由多种艺术形式构成的,那么就不能指定电影的“能指”,更不能指向确切的“所指”。因此,电影符号学认为,电影符号的意指应该由电影符号的“内涵”与“外延”来构建。电影符号的“内涵”包含万象,一千个读者所给予的解读会产生一千个不同的含蓄意指层,“外延”一词来表述这个无限的集合更为恰当。
第二,符号学的研究者容易陷于语言学的框框中,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出发,以语言符号学的规律对电影符号学生搬硬套,易造成电影符号学四不像的结果,致使漏洞百出。以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没错,但将语言符号的规律来束缚电影符号,却犯了概念性的错误,语言和电影本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每一种艺术都有自身发展的规律和可循的程式,电影艺术也有它可循的规律。值得注意的是,语言和电影有些有限的相通点,那就是叙事功能,但并不能因此把电影看作语言学上的语言。电影语言不等于自然语言,我们所说的电影“语言”,是指传播学意义上的“语言”,一般的“语言”是我们平常交流的口语和书面语。语言符号和音响符号、画面符号、建筑符号等各种有效结合,才成全了电影符号的传达表意功能。
今年5月上映的顾长卫导演的电影《最爱》不管是艺术上,还是商业上都获得了成功,从符号学角度看,电影《最爱》中间融汇了不少电影符号学的思想,多处能体现符号学的相关理论。
一、对结构主义电影学原理的运用
结构主义的中心观念不是“结构”,而是“系统”。结构展示的是一个系统的特征,一个系统由若干组分构成,任何组分的变化都要引起其他组分的变化。应用到电影符号学当中,我们可以借此分析电影的线索、结构、技术及整个文本的特点。
故事的叙述角度很特别,是从一个已经死了的小孩口中讲述的。故事开端,他躺在他爹为他做的棺木中,棺盖徐徐关上。同时,小孩“我”去往了“另一个世界”。棺材盖上这个片段是镜头从三分之二处切入,以仰视的角度拍摄的,是以小孩为“第一人称”的手法。这样,其他角色由小孩的叙述串联起来,逐一介绍。故事的结局说道:“在你们那边,村人们在一起,在我们这边,我和叔婶还是一家,和到了这边的村人们在一起,我们也吃饭、种地、过日子,闲下来大家说笑,还讲故事……”小孩本来以讲故事的口吻叙事,但是故事一完,是“大家说笑还讲故事”。给人一种被所编的故事骗了的错觉,加深了“故事”整体的“符号性”。小孩的死没有把小孩剔除在故事之外,他不仅是叙述者,他也承担一个角色——他结婚了。小孩的爸爸赵齐全为他娶了个媳妇,是县长大人的千金,这个片段为整部片子的发展有意无意地突显故事主题。整部故事以出镜频率最高的“我”字方言化——这里,语言符号对电影符号的功能实现起到很大的作用,方言腔,不仅辅助性实现了语言符号在电影符号的传达作用,更造成类似文学上的“间离”效果。不熟的口音提醒观众你们是在看别人的戏,同时,这事情真实、可信,好像发生在身边。这种手法体现了第二符号学的运用原理,即与观众的思想参与其中,对观众思想进行干涉,增强影片的互动性。
“热病”——患病的人会被热死,就是艾滋病。“热病”是死神,对于得了“热病”的人来说,死是三朝两日的事情。它是线索之一,因为“热病”,大家去学校呆着,便于统一管理;几次盗窃事件;赵得意和商琴琴结婚;其中免不了接二连三的死亡。故事其实就是以死亡为开始,由死者叙述,拉二胡死了,老疙瘩死了,房粮姐死了,大嘴也死了,琴琴和得意也死了。在小孩叙述时,如果是大全景,镜头会从半空平行或俯拍拍摄,既体现出小孩是叙事者的视角,又能够反映出天色的变化:这种镜头里,天色总是变化诡异,让人想起:“天有不测风云”这句话。死亡并不是片子里最令人害怕的结局,每个得热病的人都平常地看待自己的病,不像我们日常理解的疯狂,甚至,他们中间有人知道自己快不行了。老疙瘩为了红袄袄,做错了事,事后向村长解释,然后没了;大嘴拿着他的标志性喇叭,晃了晃,然后笑着说:“我的喇叭没电了,我也快没电了”;得意快死前,梦到他娘了,也知道大限将至了……当然,死亡是片子的结束,却不是他们意识的结束。小孩赵鑫说了,“这边的人和你们那边的人一样吃饭、种地……还讲故事。”
爱情也是故事的线索。赵得意对商琴琴一见倾心,“热病”推波助澜,成全了这对恋人。也许一开始只是情欲的宣泄,到后来相互依靠、惺惺相惜,赴死。爱情的发展与其他线索结合,带来的不仅仅是故事性增强的效果,还有音响、画面色彩也随之明亮。
二、象征符号的应用
象征符号在电影中颇为常见,也是最容易让人接受的电影符号。象征符号可以体现在道具、色调、音乐、故事情节等的选择上。道具、色调等的合理应用能够利用时空的张力和符号的变量思维,使同一能指在不同的时空下有不同的意指,又能使不同的能指在关联下有相同的意指。在《最爱》里,象征符号的运用俯拾即是。
“结婚证”是宣传海报上显眼的道具。“我们结婚吧,趁活着……”促成了两个人的喜事。赵得意为了领到“结婚证”,卖掉了自家的老房子,让他哥哥搭上一口上等的棺木,说是为了爱情,是为了琴琴,也是为了全村人的认同,让他们可以堂堂是正正作做夫妻。“结婚证”代表的是法律的确认,让他们的爱情有一种归属感,在死了的路上也是夫妻;也是一种临死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为爱情,赵得意这个自私的小男人开始勇敢,甚至顶天立地起来。他改变了琴琴,把快乐和尊严带进她的生活。美好让他们有所追求,而首先追求的,就是那张红色的证书。
他们刚在一起的日子,电影的音乐突然变得欢快,让人从心里溢出喜悦之情,有闻之起舞的冲动;影片的色调也变得明朗,仿佛悲伤未曾来过,幸福会一直延续下去。但是,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一起生活的房子:那么小,灰白的大理石的颜色,方形的门,拱形的顶,像极了——一座坟。这里的符号的象征手法,起到了隐喻的作用,在轻快明亮的色彩里,暗灰色的房子不时提醒观众,“喜马拉雅山也会塌下来。”
“红色”在电影里,是一种民族性很强,也极能体现人物个性、体现影片风格的颜色,因此备受很多导演和编剧酷爱。像在片名中含有红字的电影如《红粉》、《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等,都充分利用了“红色”的爆发力,将其风格的独特性充分发挥出来。
在《最爱》这部影片里,红色,是琴琴的颜色,这个爱美丽的单纯的女人,为了一个牌子的洗发水去卖血而“卖了命”,对素色、粉红、大红色的痴爱也体现了商琴琴热爱生活,向往美好爱情的个性。红色是证书的颜色,是新郎官的领带、新娘的衣裳,是赵得意和商琴琴如火如荼的大胆奔放的爱情。红色,是命的颜色,是死神无时无刻的警醒,琴琴死后,得意自杀,醒目的殷红的血从蓝色的门槛里流出来,命就没了。
赵得意和商琴琴婚后搬进了老院,老院的房子是鲜艳的蓝色,这里的蓝色刚进银幕时占据镜头约三分之二,在这部除了红色之外都用偏于昏黄的色调里,房子的蓝色显得格外突兀。蓝色本是象征忧伤与梦想,婚后的得意和琴琴应该更加幸福,但是热病发作,幸福就成了明亮的幻想了,到片尾,蓝色更与流出门槛的鲜艳的血红形成鲜明的对比,暗示得意和琴琴两人美好生活的结束。
用电影符号学的方法分析电影能给影视鉴赏带来更多审美体验,同时,也给影视创作带来启示。
[1]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商务印书馆,1982
[2] 王志敏,《电影语言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 王志敏,《现代电影美学体系》[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0.3969/j.issn.1002-6916.2011.14.017
刘玲玲(1987—),女(汉),湖南娄底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09级,影视戏剧文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