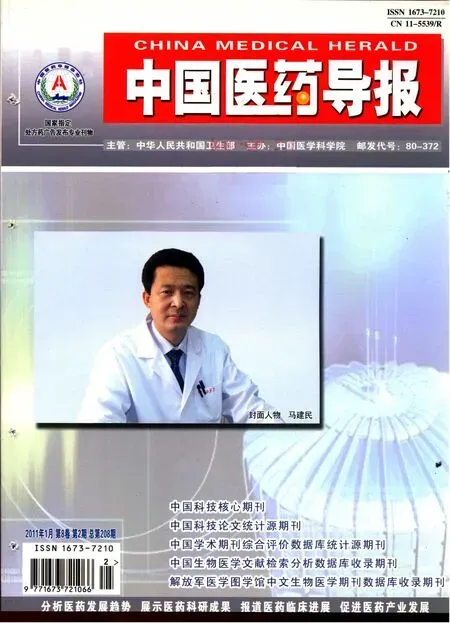马建民:做“学者型”的眼科医生
文图/《中国医药导报》记者 韩同伟
马建民:做“学者型”的眼科医生
文图/《中国医药导报》记者 韩同伟
记者见到马建民博士时,他刚刚从台湾参加“第十三届台北国际眼科专题演讲会”后回到北京。作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副主任医师的马建民,除了繁忙的临床医疗工作外,他还积极参与眼科学界的其他工作,教学、科研、会务交流、著书写作等,都是他的工作内容。
自2005年博士后出站至今,马建民先后参编了 《眼科临床指南》、《泪腺区实用解剖及手术操作实例》、《青光眼专家释疑》、《北京协和医院眼科诊疗规范》等多部著作;同时翻译了《眼和眼眶的超声诊断》、《神经眼科学图谱》等有代表性的眼科外文专著;参编了人民卫生出版社、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等出版的、供医学院校使用的《眼科学》教材。
近年来,马建民医师多次参加各种国内外眼科会议,并负责会议中一些具体的组织协调工作。据记者了解,2008年,马建民医师参加中国大陆和香港眼科界共同承办的世界眼科学术大会(WOC2008),并担任会议翻译团队的负责人。他带领着一支经全国知名眼科中心推荐,由32位眼科医生组建的敬业团队,承担了会议期间大量的翻译工作。翻译团队成员每天仅有三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他们以这种忘我的敬业精神,高质量的翻译工作,得到了所有参会人员的好评及香港眼科界的赞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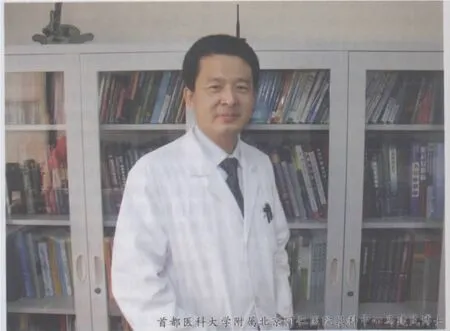
临床医疗:手术理念更加重要
记者:马博士,大学毕业后,您为什么选择眼科学作为您的专业方向呢?
马建民:人与外界接触,感受外界的信息,最主要靠的就是眼睛。在人的一生中,80%~90%的外界信息是通过眼睛获取的。人一旦丧失了视力,尤其对于有过视觉体验的人而言,无疑使他从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跌入一个暗无天日的深渊。可想而知,这对患者来讲,是多么的痛苦与无助。所以我觉得眼科工作十分重要,眼科医生的职业很有意义。我想用自己所学到的医学知识与技术来帮助那些患有眼疾的人,希望他们可以重获光明,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
记者:大家一般都认为眼睛结构比较精细,许多眼病需要手术治疗,那么眼科临床工作都有哪些要求?
马建民:眼睛作为我们的视觉器官,跟身体其他部位的组织器官一样,都会受到各种疾病的侵犯。就眼科疾病的治疗而言,最基本的治疗包括药物和手术两部分;其中许多眼部疾病就如您所讲的需要手术治疗。由于眼球及其附属器官解剖结构、位置及功能的特殊性,所有眼科手术均是非常精细的,这不仅要求眼科医师具有较为渊博的理论知识,而且要求眼科医师具有扎实稳健的手术操作基本功。就以我现在的主攻方向眼肿瘤领域为例,因为眼肿瘤累及范围非常广泛,眼球及眼附属器几乎所有的组织结构和部位都可以发生肿瘤,所以,眼科肿瘤病种繁多、病情变化多端。眼科肿瘤专业不仅涉及眼科学知识,还涉及肿瘤学知识、医学影像学知识、病理组织学知识等多个学科。它属于交叉性学科,要求这个学科的医师不仅要掌握专科理论知识,同时也应具备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系统的理论知识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准确地诊治疾病,减少漏诊误诊的发生几率。正确诊断病情是治疗的基础。眼科肿瘤手术方案的制定、手术方式的选择,也因肿瘤性质、大小、部位等不同而不同,这就对医生的综合技术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由于眼部组织结构的复杂性、精细性,手术操作时,过硬的手术操作基本功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圆满完成操作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更重要的是确立一个正确可行、科学严谨的手术理念。
记者:和手术操作相比,为什么说手术理念更重要呢?
马建民:手术操作是眼科医生应该掌握的最基本的技能之一。只要刻苦学习,反复训练,每位医生都可以掌握手术操作的具体方法;但手术理念的形成却远不止这些。它不仅要求医师具备完整的知识体系、系统的理论素养,还需要具备丰富的临床经验、精湛的手术操作技艺。术者手术理念的不同,有时也可导致治疗效果的迥异。如位于眶尖部的一个海绵状血管瘤,这是一种良性肿瘤,可以导致视力下降或失明,手术是治疗该病的唯一方法。如何去做?是全部切除,还是部分切除,还是局部减压?由于眶尖部有许多与眼有关的重要的神经、血管通过,手术稍有不妥,就会发生一些严重并发症,这时就需要术者做出慎重选择。由于该病是瘤体占位效应导致视神经受压,进而出现视力的损伤;再者,该病系良性病变,发展缓慢。那么,设计手术方案时,首先应该从保护患者现有视力,减弱或消除肿瘤的占位效应出发。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我们可以采用部分切除或眶尖部局部减压,以达到治疗的目的。如果医生一味地主观追求完全切除肿瘤,而实际操作难度又非常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冒险牺牲视力或引起某些严重并发症的可能,来追求对肿瘤的完整切除。手术理念就如盖楼房时的设计图纸,而手术操作就如具体施工。若仅停留在手术操作这一层次,再好也只是个“匠”,而非“师”。为此,只有在科学合理的手术理念指导下的手术操作,才能达到更为理想的手术效果。每当遇到疑难手术时,我都要经过反复的思考论证,查阅相关文献,权衡利弊,尽最大可能地设计一个完美的手术方案,尤其是手术细节的设计。当手术成功时,就会感到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欣慰和满足。
临床科研:追赶世界水平的“起步石”
记者:马博士,您经常参加眼科界的国际交流,您认为中国眼科水平和国外相比处于什么样的状况?
马建民:在改革开放这30多年的历程中,我国眼科界与国际眼科界交流日益增多,一些国际知名的眼科会议近年来也首次在中国举办,如WOC2008、ICER2008、APAO2010 等 ,说明我国眼科界的国际地位正在逐步提升。为了迎接2010年9月份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的第三届中日韩眼科学术会议和APAO2010,我曾经制作了一部泪腺区手术操作的英文版视听教材,目的就是让国际同行了解我国目前有关该病的一些治疗方法,只有通过交流,才会相互了解,才会相互认可。尽管我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眼科医生的临床诊治水准正在逐渐接近,但仍存在一定差距,如刚才我提到的手术理念和手术方式,往往是他们原创和提出的,而我们仅仅紧随其后而已;另外,在眼科高精尖医疗仪器领域中,我们往往是仪器的使用者,而非仪器的发明者。对于眼科领域的基础研究,我们目前的主要问题仍然是缺乏原始创新,很少能够提出被业界公认的新的学术观点和理论体系。科研的创新是一个缓慢的积累过程,只有通过不断地积累,不断地摸索,在量变的基础上才会发生质变;对于学术创新,也需要经历这样的过程。
记者:马博士,您参与过哪些课题研究,这些研究对临床水平的提高有什么样的帮助?
马建民:近年来,我主要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课题2项,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计划课题1项,卫生部资助课题1项,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科委课题2项,其他省市级联合课题2项。由于课题都是针对临床常见而又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所提出的,通过参加课题研究,尽管付出了许多辛苦,但同时也有很多收获,对所研究疾病的发病机理有了更深的认识,对疾病的治疗也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如在参加“眶炎性假瘤中胶原纤维异常增殖相关基因筛选及干预研究”课题中,我们采用基因芯片技术,首次筛选出与眶炎性假瘤发生相关的许多未见报道的基因,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眶炎性假瘤的发生机理提供了依据,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可能会为眶炎性假瘤的治疗提供新的方法。所以,参与课题研究会对临床水平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
记者:您参与了这么多的国家研究项目,是怎么处理好临床医疗和临床科研两项工作的?
马建民:作为一名眼科医师,最基本的工作就是看病和手术,这是医生的天职;但是为了更好地治病救人,提高医疗水平,有必要从临床实际需要出发,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就需要科学研究,临床和科研二者之间应该是互相促进的作用。至于实际工作中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我认为,应在完成临床工作的基础上,抽时间去做科研工作。这些年我把大量的晚上、节假日的时间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尽管牺牲了很多休息、娱乐时间,但想想我的那些老师、前辈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就无怨无悔了。任何事情有失必有得,看到已取得的点点成绩,也就觉得值得了。
临床教学:培养“学者型”眼科医生
记者:马博士,您除了临床医疗和科研工作,还负担了临床教学工作。您对医学人才培养有什么样的主张?
马建民:北京同仁医院是首都医科大学的教学医院,所以教学也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之一。我平常的教学工作主要是指导带教研究生,如指导研究生撰写课题申请书、撰写论文及实验设计等,同时每年也帮助一些下级医师、进修医师修改文章。尽管这些事务会耗费我的一些时间和精力,但看到学生和下级医师课题申报成功、论文得以发表时,我会为他们取得的成绩和进步而感到欣慰。我认为,国家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除了要培养基本人才外,还要大力培养高端人才,就是要培养出可以提出我们自己的学术观点、治疗理念,能够做出我们自己原创尖端科研成果的人才,这对提升我国整体医学水平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也体现了我国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目前全国许多医院已经提出了建设“学院型医院”的设想,培养“学者型医师”是建设学院型医院和科室的关键内容之一,这将会为我国整体医学水平的提高奠定基础。
记者:如何理解“学者型医生”?
马建民:关于“学者型医生”可以这样理解:作为一个医师首先要具备诊治疾病的能力,也应该具备针对临床实际需要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临床科研能力,同时具备丰富的教学经验。在实际工作中,以一种科学严谨的态度去诊治疾病,在诊治疾病中多问几个为什么,而不是“照葫芦画瓢”、按图索骥,应该追本溯源,掌握和探索疾病发生发展的奥秘和正确诊治的机理;在临床实践中,具备带教意识,对医学生和下级医师进行合理指导,履行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
记者:做“学者型眼科医生”,您本人正是这样的一个榜样。您是从哪里得到这样的启发?
马建民:我在大学毕业后,陆续经历并完成了硕士、博士、博士后阶段的教育和培养,这一培养过程,为我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跟随我的各位恩师学习的过程中,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对医生这一职业有了新的认识,对医生的标准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我认为,医疗、科研、教学应该是一位医生、尤其是在教学医院任职的医生的基本工作任务。后来有机会参加国际会议和参观访问时,我发现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等地的一些青年医生,也都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和工作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有些已经在国际眼科界的舞台上崭露头角,这让我不得不反思我们的年轻医生与他们之间产生差距的原因,这些正是我国医学发展欠缺的地方,也是一个医生有义务要提高、攻坚的领域。反过来,这也可以作为一种动力,激励着我们继续努力和进步。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打开我国医学界和医生在世界医学舞台上的通道。这是追赶世界水平的“起步石”。
[专家简介]
马建民,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副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会员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目前兼任《中华眼科杂志》、《中华实验眼科杂志》、《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武警医学》等杂志通讯编委或审稿专家。以主要研究者参加国家级课题3项,省部级课题2项,市级课题3项。参编参译著作14部,其中主编(译)3部,副主编(译)3部,参编全国医学院校眼科学教材4部;获得省、市级奖励3项。2009年荣获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颁发的“眼科学会奖”。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记陶瓷艺术大师张义
——旅美作曲家梁雷音乐作品学术研讨会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