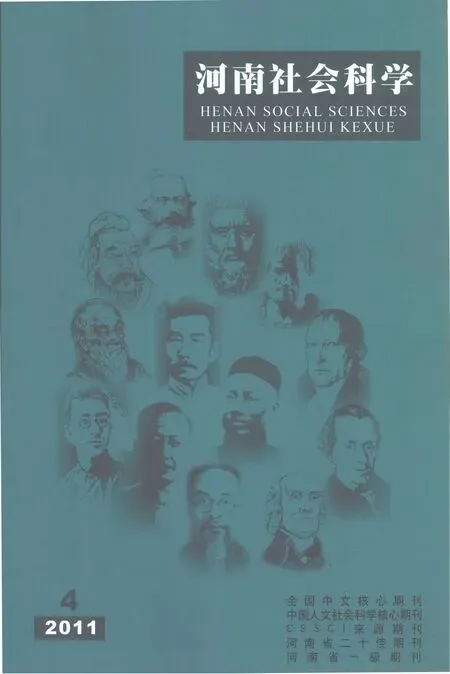“事实/价值”等于“现象/本体”吗?
——对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说”的一个检讨
卢 兴,吴 倩
(1.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071;2.天津外国语大学 涉外法政学院,天津 300204)
“事实/价值”等于“现象/本体”吗?
——对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说”的一个检讨
卢 兴1,吴 倩2
(1.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071;2.天津外国语大学 涉外法政学院,天津 300204)
“良知自我坎陷说”作为牟宗三哲学体系的核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该学说的根本症结在于牟氏将“事实/价值”的区分等同于“现象/本体”的区分,缺失了“事实性之本体”和“价值性之现象”两个重要的层面,由此造成了“知识上不去、道德下不来”的理论难题。因此,只有将平列性的“价值/事实”与立体性“本体/现象”区别开来,才能真正解决“坎陷说”的难题。
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说;事实/价值;现象/本体
一、引言
“良知自我坎陷说”是牟宗三一生哲学思考的核心主题,也是其“道德的形上学”体系建构的关键所在,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学说是牟氏思想体系中最具原创性同时也最受争议的学说。学界对于“坎陷说”莫衷一是、争讼不已,反对者们从实现条件、论证方式和深层心态等方面对此说进行质疑和批判,而认同者则从文化使命、价值取向等方面对此说予以捍卫和辩护。在学界关于“坎陷说”的讨论中,论者认识到牟氏沟通“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的努力,但对其沟通两个世界的具体方式以及其中存在的内在问题探讨得不够充分。本文试从“现代性哲学”的视角出发,在充分肯定牟氏“坎陷说”理论意义的同时,对其在根本思路上所存在的理论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检讨,以期推进对牟氏哲学的研究。
着眼于20世纪中国哲学的演进,“良知自我坎陷说”对于牟宗三哲学本身、对于现代新儒学以及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首先,“坎陷说”是牟氏自身的哲学体系的枢机,联结了其存有论和认识论思想,显示了其思想深层中西方哲学传统的会通和综合。其次,“坎陷说”代表了牟宗三立足于儒家价值系统打通“事实”和“价值”两个世界的基本立场,是现代新儒学思想进展的逻辑归结。再次,“坎陷说”既为儒学现代转化探索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也为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性精神的接榫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尽管“坎陷说”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但其中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理论问题,本文的重心在于对这些问题及其深层原因予以揭示。众所周知,关于“现象”与“本体”的划分(或者说“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的划分)是哲学思维成熟的重要标志,这对于东西方各个哲学系统具有普遍性;但关于“事实”与“价值”的划分则是“现代性”兴起之后的哲学观念,其产生是韦伯所揭示的“工具合理性”对世界进行“祛魅”的结果。以牟宗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力图克服由“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分化所带来的现代性危机,力图通过重建“价值本体”的方式安顿这两个世界,因此才需要“良知的自我坎陷”。值得注意的是,“坎陷说”的根本症结就在于牟宗三将本体世界“价值化”或者说将价值世界“本体化”,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将“事实/价值”的区分等同于“现象/本体”的区分。这种倾向突出表现为牟氏将康德的“理知世界”(本体界)与“感知世界”(现象界)的划分放在“价值/事实”二分的模式中理解,他明确地说:“依康德,自由意志所先验构成的(自律的)普遍的道德律是属于睿智界,用今话说,是属于价值界、当然界,而知性范畴所决定的自然因果律则是属于感觉界、经验界、实然或自然界。”[1]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牟氏的这种“等同”是自觉的、有意识的,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一方面确保了儒家之“德性”的本体地位,另一方面能够比较合理地说明由“价值”到“事实”的转变。然而,这种概念上的等同却在逻辑上取消了“事实性本体”和“价值性的现象”存在的可能性,这就在以下两方面存在着问题:一方面,在本体界并没有给“知识”和“认知活动”留下位置,这在牟氏的体系中的表现是“认识心”是一个“虚执”(“权用”),其无独立之自性而以经验界为其性,亦无独立之自体而借“德性心”为其体;另一方面,由于现象的“事实化”,在现象界并没有为创造价值的实践活动给予适当的位置,这使切入经验世界的“德性工夫”无以安顿,同时也使艺术创作、宗教生活等关联于价值的实践行为无以着落。以下本文就这两方面的缺失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检讨。
二、“事实性之本体”的缺失
就“事实性之本体”的缺失方面而言,尽管牟宗三建构了“现象界的存有论”,但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都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本体地位,因此整个认知活动以及事实世界都缺少形上根据,不免于“泛价值主义”的弊病。
牟氏对康德的“物自身”概念进行了儒家式的改造,肯断“物自身”是一个高度价值意味的概念,但这并不符合康德的原意,极大地弱化了“物自身”的认识论意义。细致地分析可以将这一过程分为“实体化”和“价值化”两个步骤。先看第一步“物自身的实体化”。康德所谓“物自身”的内涵是“3+X”,其中的“3”是指“意志自由”、“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三个纯粹理性的理念,而所谓“X”是“先验客体”,对于后者康德指出:“先验客体意味着一个等于X的某物,我们对它一无所知,而且一般说来(按照我们知性现有的构造)也不可能有所知,相反,它只能作为统觉的统一性的相关物而充当感性直观中杂多的统一,知性借助于这种统一而把杂多结合成一个对象的概念。”[2]“先验客体”既为外部现象奠定基础,又为内部直观奠定基础[2]。康德对“先验客体”的描述表明这是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术语,一方面刺激感官产生直观中的杂多,另一方面作为统觉的相对之物确保表象的统一性,这些对认识过程都有积极的作用。而牟宗三通过研读康德的著作,指出其所使用的“先验客体”与“本体”两术语容易引起混淆,“‘超越的对象’(即本文所谓‘先验客体’——引者注)一词实是不幸之名,亦即是措辞之不谛”[3],因而认为可以把康德“先验客体”之名取消。在牟氏看来,“物自体(即本文所谓‘本体’——引者注),假定预设一智的直觉时,它可以为一‘真正的对象’,然而超越的对象则又可转而实非一对象。物自体是实,超越对象是虚。这当是一个重要的区别点”[3]。牟宗三之所以取消了康德这个认识论上具有积极作用的概念,实质上是将虚指的“先验客体”收摄于实指的“本体”之中,这样就完成了“物自身”实体化的转变,这个实体性的“物自身”就是“智的直觉”所呈现的“物”,亦即“自由无限心”之“经用”。
再看第二步“物自身的价值化”,牟宗三进而证明这个实体性的“物自身”必然是价值意义上的实体而不能是事实意义上的实体。在解析康德关于“现象”与“物自身”之间先验的区分时,他曾多次引用康德《遗著》中的话:“物自身之概念与现象之概念间的区别不是客观的,但只是主观的。物自身不是另一个对象,但只是关于同一对象的表象之另一面相。”①康德在这里所谓“主观的”意思是说以上区分是对人的认识能力而言的,而其对人之外的存在是否依然有效是我们不得而知的,这更不意味着确定有一个“上帝”在人之外实存着。而牟宗三则将这里的“主观的”理解为对于两种不同的“直觉”而言,认为对于同一个“物”,以“智的直觉”观之为“物自身”,以“感触直觉”观之为“现象”,而康德只承认人具有“感触直觉”,将“智的直觉”交托给上帝,在这个意义上认定康德不能充分证成“现象”与“物自身”的先验区分。由于牟氏将“物自身”实体化了,因此必然实存着一个“智的直觉”去创造它,这样“上帝”就作为一个实体性概念被牟氏引入了康德的哲学框架中:“如果我们把上帝类比于本体,则依康德,上帝所面对的不是现象,乃是物自身。如是,这乃成上帝、物自身、现象之三分。这是客观的、笼统的说法。如果详细言之,同一物也,对上帝而言,为物自身,对人类而言,则为现象。”[4]在牟氏看来,康德为了保证两层的区分,必须请出一个实存的“上帝”来创造“物自身”,这就将“上帝造物”的神学问题引入康德的论述:“吾人根据神学知道上帝以智的直觉去觉一物即是创造地去实现一物。我们据此了解了智的直觉之创造性。”[4]就“上帝造物”而言,就出现了“无限”(“上帝”)如何创造“有限”(“被造物”)的问题,这里牟氏又将康德关于时空的观念性引入这个神学问题的解释中,指出上帝所造之物(“物自身”)不在时空之中(因为时空是人的先天直观形式),“如果真要肯定它无时空性,它之为有限物而在其自己决不是一个事实概念,而是一个价值意味的概念。只有在此一转上,它始可不是一决定的有限物,因此,始可于有限物上而说无限性或无限性之意义”[4]。这里,“有限物具有无限的意义”就是说物自身“无而能有、有而能无”,这就是牟氏所谓的“价值”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他得出了“物自身是一个价值意味的概念”的结论。接下来牟氏就比较顺利地将“智的直觉”归属于人之“自由无限心”,以此价值性之“心”呈现价值性之“物”,成就“本体界的存有论”。牟氏的基本理路如上所述,但论证过程颇为繁琐,在笔者看来至少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混淆不清:第一,牟宗三混淆了康德哲学的语境和神学的语境。在康德那里,上帝只是一个实践理性的“悬设”(“设准”),尽管有“上帝创造自在之物本身”的类似提法[5],但相关文本旨在说明:说上帝在“感知世界”中(遵从自然因果律)创造“物”(现象)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命题,而只有在“理知世界”中“上帝造物”才能够避免矛盾,但究竟这个上帝是否实存、如何造物等都是我们人类所不可能知道的;而在基督教正统神学(实在论传统)看来,“上帝造物”是创造物的个体之实存,不仅创造物的形式,也创造物的质料,并且是使其形式与质料结合的动力因,甚至于人心中关于“物”的观念也是上帝所赋予的,这也就是说康德意义上的“现象”也是上帝的创造物,这里由“无限”到“有限”的转变是上帝之“全能”的表现,不同于牟氏所谓“觉之即生之”的创造方式。因此可以说,“上帝造物”的问题不是康德哲学中的问题,而是一个神学中的问题;而牟宗三将这一神学问题改造为“上帝以智的直觉去觉一物即是创造地去实现一物”,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儒家道德形上学“本体之创生性(活动性)”的投影。第二,牟宗三混淆了“时空中之物”的有限性和“上帝所造之物”的有限性。在康德哲学中,前者是现象身份的物,其有限性来自人的感性直观形式;后者是物自身身份的物,其是否为“有限”或“无限”是我们人类所不得而知的,因为“限制性”是康德所谓12个知性“范畴”之一,其只能被用于感性直观所得的经验,而不被能用于物自身。因此,在康德那里,不仅不存在“上帝造物”的问题,而且不存在“无限”创造“有限”的问题,因此牟氏的以下说法就难以成立:“如果被造物决定是有限物,而定是有限物者又决定是事实概念,则此作为事实的有限存在物之在其自己,既不可以时空表象之(无时空性),亦不可以任何概念决定之,它必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无实义。如果它要有丰富的真实意义、价值性的意义,它必不是一个事实概念,那就是说,它必应不是一个决定性的有限物。”[4]在康德那里,“物自身”不存在“有限”或“无限”的问题,也不能确定是“事实概念”还是“价值概念”,说其“空洞”也可,说其“并无实义”也行,这正是康德“经验实在论”的本义。总之,牟宗三并未能成功地证明康德的“物自身”是一个价值意味的概念,尽管他处处依托康德的术语,但在根本精神上与康德背道而驰,甚至有回归于神学的取向,因此有的学者指出这种做法是对康德“物自身”概念的“去批判化”[6]。抛开康德哲学而不论,牟氏通过繁琐的论证而将“物自身”价值化的过程包含了许多混淆和臆断,不能真正使人信服。
由此我们可以确知,牟宗三所坚持的“价值优位”的立场无疑来自儒家传统,而不是康德哲学。牟氏将康德所讲的“实践理性”对“理论理性”在“先验人类学”意义上的优先性转变为在“存有论”意义上的优先性,力图证明康德也是一个“价值优位者”,这是对康德哲学的一种误读②。牟宗三所处的“后工业时代”与康德所处的“启蒙时代”已然有相当大的差别,18世纪的思想家力图达到“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并重双显与和谐统一,而“现代性”演进到20世纪却出现了“科学”意识形态化、“工具合理性”一方独大之势,“事实”与“价值”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对立。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说”具有为西方现代性补偏救弊的针对性,力图通过重建“价值之体”而为事实世界和科学知识奠基,其作为“科学一层论”、“事实一元论”的反话语出现,却以同样极端的方式予以表达。正如傅伟勋所指出的,这种“泛道德主义”与“唯科学主义”一样,同样具有“化约主义”的弊病[7]。同时应该看到,牟宗三“泛道德主义”的思想倾向根源于儒家传统本身,而这种“价值的泛化”只是在“现代性”之两个世界分化对立的语境中才成为问题的。易言之,就以关怀人之德性生命为根本特质的儒家系统自身而言,无所谓价值之“泛化”,只是一个“生生大化”之价值宇宙;而只有对以“工具合理性”为基本动力的“现代性”而言,“道德”或“价值”的独尊性才对知识的独立性产生了阻碍。就牟宗三的体系来看,所谓“泛道德主义”只是在“本体”层面的,而在“现象”层面却充分肯定了事实世界和科学知识的地位,这较之于传统儒家而言显示出鲜明的现代性特征,因此不能以“泛道德主义”一语对牟氏哲学盖棺定论,而应当以历史的和辩证的眼光对“坎陷说”进行细致的分析。
三、“价值性之现象”的缺失
就“价值性之现象”的缺失方面而言,牟宗三将道德活动之“体”与“用”都归入本体界,使其与经验世界产生了隔膜,造成了“道德实践”的概念化、抽象化,使“修养工夫”以及相关于价值的实践活动无以着落,难免有“虚玄蹈空”之弊。
传统儒家讲道德是“兼赅体用”,正所谓“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王阳明《别诸生》),其“用”真实地切入现实的伦常生活之中,与经验世界紧密联系。朱子在存有论上强调“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朱子语类》卷一),王阳明在工夫论上强调“致知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传习录》中),都将德性之“实践”置于关键的地位。这里的“实践”不仅仅是一个工夫论意义上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存有论意义上的概念,其相当于黑格尔所讲的“现实性”,是对德性之“理”的具体落实,是“本体”的发用流行,德性生命通过“实践”达到了其本真性的自我澄明。这里的“德性实践”无疑属于价值世界,但对于“本体/现象”的划分而言则可以“上下其讲”(这里借用了牟宗三的术语):一方面,“德性实践”的过程是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一种包含目的性的关系,主客双方都是经验世界的存在者,伦常关系是现实的人之间的关系,如父子分别构成了“孝”之行为的主体和对象。另一方面,与认识行为的主客体关系有所不同,“德性实践”关联于形上的本体世界。在儒家看来“孝”作为美德指向超越性的目的(“天道”、“本体”),因此“尽孝”的实践又不仅仅是一个经验行为,更重要的是一个展现“天道”的过程,也是一个呈现“人之为人”的本质的过程。因此,“德性实践”体现出儒家“即本体即工夫”、“即内在即超越”的理论特质。
尽管牟宗三在界定“道德的形上学”时强调了上述特质,同时以“随波逐浪”表征道德理性之实践义,但在“两层存有论”的体系中,“德性实践”被形上化为“本体界”的“心”与“物”(行为物)的关系,尽管“自由无限心”可以创生道德行为,但后者属于“物自身”,高踞于经验世界之上;而在“现象界”只剩下事实性的认识行为,将人的现实生活完全归之于“认识心”的活动,这显然是以偏赅全,本文称之为“现象世界的事实化”,其与“本体世界的价值化”一样,具有“约化主义”的弊病。这种“现象世界的事实化”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德性实践的概念化和抽象化,其被抽象为一个空洞的概念被安排在“无执的存有论”的框架内,与日用伦常相疏离,不能现实化为真实的生活常轨,使儒家整个道德学说只有“高明之维”而遗失“中庸之维”,成为一种“高调而空洞的理想主义”,难免重演王门后学“虚玄而荡”、“玩弄光景”之流弊。
另外,由于“价值领域”不仅仅包含“道德”这一个维度,至少还应包括“审美”和“宗教”等领域,因此“价值性的实践”还应当包含艺术创作、宗教生活等方面,因此这些也应当在“现象界”中有所安顿。当然我们不能苛求牟宗三一个人详尽考虑所有问题,但这些价值领域对于丰富完整的人类生活而言不容忽视。
综上所述,牟宗三的“坎陷说”将“价值/事实”的区分等同于“本体/现象”的区分,造成了“知识上不去,道德下不来”的理论难题。笔者认为,以上“价值/事实”区分是平列的(无所谓何者优先),“本体/现象”的区分是立体的,因此可以通过以下表格展现出这两种区分交叉的情况(针对牟氏的论域,“价值领域”只涉及“道德”方面):

本体现象价值德性本体(道德心)德性实践(工夫)事实认知本体(认识心)认知实践(知识)
注释:
①Kant:Opuspostumum,AA,Bd.XXII,S.26,这里引用的是牟宗三根据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英译本中引文的译文。
②在这一问题上牟宗三对康德的误读比较复杂,对此笔者将另撰专文予以详细考察。
[1]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
[4]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M].台北:学生书局,1975.
[5]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6]邓晓芒.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之三)——关于“物自身”[J].学习与探索,2006,(6):1—6.
[7]傅伟勋.“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
B2
A
1007-905X(2011)04-0071-04
2010-04-07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NKZXB10140)
1.卢兴(1981— ),男,陕西汉中人,哲学博士,南开大学哲学院讲师;2.吴倩(1983— ),女,河北邢台人,哲学博士,天津外国语大学涉外法政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吕学文
(E-mail:dalishi_sohu@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