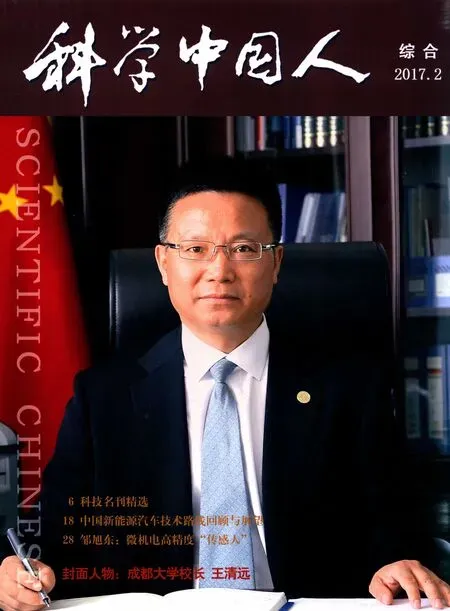大学教育该如何回答“钱学森世纪之问”
熊丙奇
大学教育该如何回答“钱学森世纪之问”
熊丙奇

人民科学家、“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2009年10月31日逝世。人们在追忆钱老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以及他的爱国精神、科学精神的同时,反复提到他晚年对发展中国教育、培养杰出人才的肺腑之言——2005年,他对温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钱老的话,温总理曾在多个场合提及。2006年,他在一次高等教育座谈会上,向参加座谈的几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转述了钱老的话,并说这是他“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这其实也是当下中国教育的焦虑,尤其在每年诺贝尔奖颁发之际,围绕大师人才的培养问题,各方都会来一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在各种讨论文本中,见得最多的字眼,就是“造就”大师。在笔者看来,要回答钱老的世纪之问,应该认真体味钱老所说的“冒”字,让人才自然地生长出来,而非对人才进行所谓的“造就”。进而根据这样的认识,为杰出人才“冒”出来提供良好的教育土壤和学术土壤。
一、人才评价的严重偏差
培养优秀人才,必须首先明白何为“优秀人才”,可令人遗憾的是,在恢复高考制度30多年之后的今天,整个社会的“人才观”,还极为落后,学校、家庭和社会都还用落后的“人才观”,去要求人才,最终,“人才”成长为大家所需要的模样,却离杰出越来越遥远。
具体说来,我国社会的“人才观”,最大的偏差,不是大家所熟知的“学历社会”中,以学历高低评价人才,而是对“全才”、“偏才”和“怪才”纠缠不清。近年来,在高校试点的自主招生中,无论高校还是社会舆论,都说要为“偏才”、“怪才”提供上大学的途径,而这种提法的存在,本身即表明我国社会对人才的评价进入严重的误区。
何为“全才”?在现今的学校教育中,中学指那些各门功课(主要是高考科目)总分高的学生,大学则指公共必修课、专业课学绩点高的同学。而与之对应,那些有某几门功课不及格的学生,则不是这样的“人才”,最多属于“偏才”和“怪才”。
我国的高考制度和大学教学管理,是为我们所理解的“人才”服务的。在高考中,依据学生的考分高低、结合志愿进行录取,单科分数再高、总分低一分也不能录取;在大学中,必修课占了所有课程的极大比例,只要有一门必修课程未通过,就拿不到学位和毕业证书;就是在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要通过笔试门槛进入复试,不但总分要过线,单科也要过线。
这样的人才评价体系,貌似很“全”,实则“单一”,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人才”是被“拔出来”,中小学教育普遍在“赢在起点”的理念指引下拔苗助长;“人才”是被“塑出来”,一出土,就给他们套一个“模子”,要求他们在这个模式里生长——中学教育追求高考科目的考分,一些单科跛脚的同学有可能在中考时就被淘汰,难进重点高中,很多学生为了获得高考高分,而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去弥补自己的薄弱学科,在弥补的过程中,个性和兴趣也逐渐丧失,这就是钱老所说的学生对学习知识不感兴趣;大学教育追求专业课、公共必修课过线;考研变为第二次高考。简言之,分数成为一个人成就为“人才”的不二法宝。大多数人都被赶进一条成才途径,所谓的高考独木桥由此形成。而针对这种现象,所做的“修补”调整,就被认为是也给偏才以成才机会。
再来看美国的人才评价体系,其与我国社会的人才评价完全不同,根本不存在偏才、怪才之说。以访美学者整理的美国名校招生评价体系为例。其基本评价公式为:综合素质总分=就读的高中(0~4分)+课程难度(0~21分)+年级排名(-1~3分)+平均成绩(0~16分)+SAT成绩(6~25分)+全国荣誉学者(0~3分)+申请论文(-3~5分)+推荐信(-2~4分)+课外活动(-5~30分)+种族多元化(-3~5分)+体育活动(8~40分)+超级录取(40分)+[体育教练点名(5~10分)+家住远处(3分)+父母因素(5~8分)+多元化(3~5分)],从中不难看到,任何一方面有特长的学生,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评价,事实上,一个SAT满分获得者,得到的评价,还不如一个课外活动表现优秀者或者体育活动表现优秀者。按照这样的体系,在我国教育体系中,被认为是偏才的学生,可以很自然的得到超级录取(40分)的评分,他不是人才是什么?
这样的多元评价体系,无疑引导中学生重视个性的发展,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因为这些都会在大学入学中被评价、被关注,在美国中学,大多推行分层教学,学生可按自己的兴趣和学科实力,选修不同难度的课程,比如,数学就有数学A、数学B、数学C可选,学生们不必花大量时间去弥补自己的弱项让其达到最高的水平,而只需使弱项达到最低要求即可,更多的时间用于发展自己的爱好;而大学从招生时,就有多元的人才评价视角,进而在大学教育里也为学生提供更充分的选科、选课的机会,低年级不分专业,推行完全学分制,选修课比例高达50%,这为杰出人才的涌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二、大学教育中的“两重两轻”
受单一人才评价观的影响,我国的大学教育也存在偏差。表现在两方面:
1、重知识教育轻人格教育
我国的教育,长期以来,以记忆能力代替了学习能力,以学习能力代替了观察能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创意能力。重在考核学生知识掌握程度的基础教育,已经被“填鸭式”的教育理念牢固占据,并由于老师易教(照本宣科)、学校易管(以升学率为目标、以分数为指标、以题海战术为手段),这种教育理念难以转变。而只知记忆、背诵的学生进入高等教育,也延续了以前的学习方法,要么以考研为目标,努力攻克几门考研课程;要么以专升本为学习目的,一进大学校门就准备“第二次”高考,而没有以上升学目标的学生,则很多时间在茫然中度日。这些学生到了毕业时,很难有兴趣导向的学术追求,最新的数据显示,一半博士毕业生选择进公务员队伍。
这样的教育考核与人才评价,都倾向于鼓励学生“听话”,鼓励人才“老实”、“本分”。听老师的话、听家长的话,按老师和家长的话去做的孩子,就是乖孩子,就会受到表扬。学生听到最多的,是“不准”,“不许”,“不能”,“不要”——上课不许“乱说话”,大人场合不能“乱插嘴”——久而久之,老师和家长的选择代替了学生的自主选择,老师和家长的管理代替了学生的自主管理,老师和家长的意志代替了学生的自我意识,学生们变得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主张。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中,个性发展是十分困难的事,个性人才,难以生存。不上大学、没有学历,生存都将困难,更谈何成为杰出人才;而上了大学,几乎都在长期来的共性要求和个性压抑下,没有了自己的个性,没有了自己的兴趣。
另外,总体而言,人才培养在大学中的地位并不高,《中国青年报》2009年12月曾以《高校教师上课过分依赖PPT课堂教学丢灵魂》为题报道大学教师的“PPT依赖症”,不少教师照“PPT”宣科,这一症状充分说明大学不重视教育教学。先进的教育技术,没有给课堂带来活力,反而更让课堂死气沉沉,这显然不是技术本身的错。客观上说,PPT依赖症,不过是大学不重视课堂教学的延续。如果教师重视教学,PPT是可以发挥其“先进”的功效的;而如果教师不重视教学,“先进”的技术,只会进一步反衬教师的教学方法“不先进”。在当前的大学教师评价体系中,教学处于极为次要的地位,影响教师考核、评价、晋升的,主要是论文发表数、课题经费数、发明专利数,教学评价主要体现为教学工作量,因此,怎样用最少的精力完成规定的教育工作量,必然成为教师的现实考量,PPT也就成了既让课堂现代化,也让教学轻松化的“双赢选择”。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能有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倒是很奇怪的事。
钱老在其最后一次谈话中说到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教育,“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拿国内的大学教育与其对比,相差实在太大。有不少研究生半年之内都见不到导师,何来与导师间的学术交流;而研究生们都是如此,又谈何本科学生呢?
不仅如此,近年来一些大学在迎接评估中的弄虚作假,以及统计毕业生就业率时严重注水,甚至去年曾曝出“被就业”丑闻,这给学生的不是教育,而是“反教育”,教育的尊严在学生心中荡然无存,与此同时,一些学生热衷学习灰色技能。
2、重技能教育轻通识教育
去年9月,中山大学推出博雅学院,首批35人,在中山大学8000名新生中,不到百分之一。但这一“四年不分专业、以培养‘做学问’人才为目标,以古代经典阅读为重点”的通识教育开创性举措,却受到教育界的广泛关注。而这种关注本身表明,我国高校中的通识教育极不乐观。
本来,选择一所进行学术性教育的大学,就是接受其通识教育,这将为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与长足的后劲。与之对应,期望在学校中习得就业技能,学生就应该选择职业教育学校。这样的教育与就业模式,是既符合教育的规律,又对人才发展十分有利的。但是,这样的基本道理,在今天的高等教育界和受教育者中,已经讲不通。近年来,政府部门和社会舆论,对所有大学的评价都采用统一的标准,具体到就业上,就是看毕业生离校之际的就业率的高低,教育部门甚至以就业率定学校专业的生死。而很多用人单位,纷纷对应聘求职的大学生,提出一到岗就能“上手”的要求,也就是说,如果大学不重视学生就业技能,将直接影响到就业。
于是,在大学中,通识教育被认为是无用课程,渐渐被学生抛弃,应用性、工具性课程对学生才有吸引力。一进大学,学生们就把主要精力用在读GRE、TOEFL,以及各种考证,到企业去实习之中,应该培养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观察能力,都让位于“社会大学”、就业技能与证书,大学已然是同一个模式的职业培训所。而用人单位也频频抱怨,大学生的质量为何如此之低,没有长远发展的底蕴,招到一个好大学生实在太难。大学教育与就业,走进“狠抓就业、围绕就业组织教育、学生综合质量降低、就业持续困难、继续很抓就业”的恶性循环。

三、重建教育土壤和学术土壤
要让杰出人才冒出来,对大学来说,应该努力重建教育土壤和学术土壤。而最为关键的,就是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我们注意到,从去年1月和10月,由新华社刊发的温家宝总理的两篇文章——《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到最近的座谈会中,温总理提到的四方面教育改革意见,都谈到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这一问题。这一问题,其实就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牛鼻子”。
推进教育体制改革,首先需要清晰界定政府、学校、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力(权利)和责任。近年来,我国教育出现行政化倾向,家校矛盾、师生矛盾加剧,教育质量下滑,都与政府和学校之间,学校与教育者之间,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没有理清有关,其中,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尤为关键。具体表现为政府部门将举办权、管理权、办学权、评价权独揽手中,造成学校对行政的严重依附,失去办学特色与个性。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月26日在听取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10位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时深有感触地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
诚如温总理所感慨,大学没有办学自主权,这被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最大弊端所在。10年前的《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高等教育学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包括制定招生方案、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制定教学计划、开展科学研究等方面。可从《高等教育法》颁布至今,上述办学自主权,基本上都没有落实。以自主招生为例,到2010年为止,全国范围内只有80所高校,有5%自主招生试点权,获得这些学校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还必须参加统一高考。而就是高校拥有这样少得可怜的自主权,也招来广泛质疑。大学由此陷入“办学自主权缺失、但实行自主权就被质疑”的双重尴尬。
大学办学自主权为何缺失?从《高等教育法》本身就可看出端倪,在这一部法律中,居然没有“法律责任”一章,也就是说,如果政府部门越权干涉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大学将无处获得救济。也于是,在过去10年间,纵有诸多大学校长在两会和各种论坛表达不满,但政府部门干涉大学办学自主权的事还是频频发生,最为著名的就是行政化的本科教学评估。与此同时,由于高校的财权、人事权被掌握在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手中,大学也逐渐习惯于对行政的依附。
保障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然选择。为此,需从法律保障与校内管理制度改革着手推进大学自主办学进程。2009年,新创的南方科技大学表示,要通过制订由深圳人大审议通过的《南方科技大学章程》,来确保大学依法自主办学。这值得所有高校借鉴。其实,我国《高等教育法》也早已规定大学必须有大学章程,可在我国2300所高等学校中,目前没有一所大学有具有宪章意义的大学章程。制订由学校举办者同级人大通过的大学章程,大学依据《大学章程》办学,是落实自主办学的第一步。
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其次需要落实、保障学校办学自主权、教育者教育自主权、受教育者评价、监督权的机制。

以大学办学自主权来说,相应的治理机构,应是大学理事会(或董事会),大学的校长应由理事会(或董事会)遴选,重大战略决策由董事会(或理事会)制订,这样才能确保校长对理事会负责,大学的办学能保持传统与特色。可我国大学,一直没有具有决策与遴选校长功能的理事会(董事会),那些号称有理事会(董事会)的学校,其功能主要是拓宽学校办学资源,用理事或董事的头衔去换取资源。
落实教师的教育自主权,在大学,相应的机构,应是教授委员会,教授委员会负责学校教育与学术事务的决策,负责教育质量监控,以及教师教学、学术评价。我国一些大学,虽设有教授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但基本上是摆设,由于学术共同体的缺位,导致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频发。
而保障受教育者的权益,则更是我国教育的最薄弱环节。从基本的制度设计上,我国教育给受教育者的选择空间十分有限,以“统一高考、集中录取”为最突出,学生在考大学时不能自由选择大学,进入大学之后对学校不适应、不满意,也不能申请转学,使学校间的竞争大大削弱。另外,大学中没有维护学生权益的学生自治组织,也使受教育者的权益一再受到侵占。因此,要保障受教育者权益,需要建立具有竞争性的考试制度和人才培养制度,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同时,需要在大学推进学生自治。
不调整教育观和人才观,不改变基本的教育土壤和学术土壤,却寄希望于开展某些人才培养工程,把大师造就出来,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其必然结果是,我们年复一年的期盼出现获得诺贝尔奖的大师,但大师总是无影无踪。与其这样幻想、期盼,不如脚踏实地地耕耘,当良好的土壤得以构建,杰出人才也就不期而至。
专家档案:熊丙奇,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