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学术环境不应鼓励泡沫
张怡:学术环境不应鼓励泡沫
我只是想给学生一个宽松的环境,那里没有禁锢,没有篱笆和高墙,也没有制约。

张怡:
祖籍上海市, 现任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财税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世界税法研究会(ITLA)理事;重庆市税务学会理事。
我们在学习上除了受到非常敬业、非常关爱我们的老师的教育之外,同学之间的相互学习帮助对彼此的成长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记者(以下简称“记”):首先请您谈谈您的求学经历,我们想知道您当初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法学研究的道路?
张怡(以下简称“张”):我是72级高中生,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也非常兴奋,在乡下挑灯夜战认真备考。由于我特别想学医,报考了理科,结果却因为物理成绩不佳,差了几分,与从医的职业生涯失之交臂。1978年我继续备考,在距高考仅两个月之际转向文科专业,等于一切从头做起,花了很多精力准备。好在我基础不错,最后总算顺利过关,选了当时的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
记: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报考西南政法大学呢?
张:我家住成都,祖籍上海,我父亲是上海人,1949年参加了西南服务团跟随刘邓大军解放西南一路进军来到重庆,就再也没有回上海。我自小在成都长大,不太愿意离家太远,而且西南政法大学专业也比较集中,所以成了首选。
记:您能给我们谈谈在西南政法大学期间的求学经历吗?
张:进校之后,我感觉西南政法大学像北大荒,完全是个大工地。我们上课要经过一段很深的泥地,很多同学有失足滑倒和深陷泥潭的经历。全校400多位同学都住在一幢楼里面,同学中,年龄大的已届三十,工作了很多年,也有高一高二就考进来的学生,这么些人拉到一块,彼此叫叔叔叫阿姨的都有。我在众人里面属年龄偏小的学生,很多事情我们总会跟在这些大孩子们后面。年长的同学在社会阅历、思维、学习方法等诸多方面,对我们是很有引导帮助的,我觉得他们在无形中扮演了助教的角色,所以我们在学习上除了受到非常敬业、非常关爱我们的老师的教育之外,同学之间的相互学习帮助对彼此的成长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记:您毕业之后做了些什么工作呢?
张: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两年任团总支书记,当时法律专业1982级总共513位同学,黑压压站一片,有的年龄与我相仿,让我当他们的“娃娃头”,对我而言压力很大,很多事情需要现学,绷着脸充大人。好在这批孩子非常单纯可爱,两年团组织的工作,我们亦师亦友,彼此关系不错,直到我离开许多同学很难过,有给我写信的,甚至还有到成都我父母家去找我的。
在做学生工作的这两年中,我发现自己还是非常想从事教学工作的,能登上讲台是我梦寐以求的。
有些老师虽然几十年都没再见到过,但他们的名字我都一直记得。这些老师给我们学生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说老师的言谈举止,如何为人做事的教导,虽然只是三言两语,作为学生听了可能会觉得印象很深,甚至终身受益。
记:在你的求学经历中,还对哪些老师印象深刻呢?
张:读博时,我是赵国良老师的门下。作为赵老师的学生,在读三年,我从他身上深切地感受到作为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之心,他们那一代人所思考的东西,完全是从国家大局的角度出发,其深谋远虑,胸襟开阔,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的高风亮节,成为我做人、做学问的楷模。
赵老师又是一位哲学、逻辑学思维能力特别缜密的学者,他的口才很厉害,号称西南财经大学第一号铁嘴。无论是什么场合,只要赵老师一上台,全场总是欢声雷动。他讲的话不多,但总是一针见血,点到关键。当时报考赵老师门下,我是10位面试考生中唯一的女性。入学后,赵老师对我要求也特严,倾注的心血特多。有时候和他探讨问题,我说了一堆长篇大论,他可以非常简单精要地从中划分出几个要点,就把我的话给概括了。在此,必须提到的是赵老师的贤内助,师母刘继芳老师,刘老师对我的关爱之情我终生难忘!我在事业上的发展,以及能从诸多困难中走出来,都离不开她对我的引导和帮助,真的是一言难尽,难报师恩!
我之所以选择研究经济法,还有赖于戴大奎老师和李昌麒老师。当时刚恢复高考没多久,谁也不知道这门课应该怎么上。加上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多书籍和资料供参考,所以老师们就只能靠手写的讲义给我们讲课。我上课时有个特点,就是做笔记特别快,能把老师的话都记录下来。我对戴老师的每一节经济法课程,都进行了非常系统的记录,而且下课后还要整理一遍。李昌麒老师现在是经济法领域的泰斗级人物,他思维敏锐,观察问题很深刻。这两位老师对我在经济法方面的影响很大。
有些老师虽然几十年都没再见到过,但他们的名字我都一直记得。这些老师给我们学生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说老师的言谈举止,如何为人做事的教导,虽然只是三言两语,作为学生听了可能会觉得印象很深,甚至终身受益。
记:您后来为什么离开了西南财经大学转赴海南大学任教呢?
张:那是一次自我放逐。当时我在西南财经大学承担的教学任务过重,几乎将自己压垮,由于我讲授的税法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选课学生特别多,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我曾经在一篇关于财税法教学改革文章中这样写道:“笔者在西南财经大学讲授财税法(公选)课程时,学生们被要求要三重批条子(指学生本人所在学院批条子、盖章子;任课教师同意并签字;教务处盖章、备案)。靠‘抓阄’、靠自己带小板凳或坐怀听课等五花八门的做法,才得以获得选修机会(指全校公共选修课)。这种换大教室都嫌小的拥挤场面除了令人感动外,令笔者萌生‘急流勇退’念头的则是缺少任课教师之替代,身体能量转换与补偿欠佳,不得已保命为上。”(见《财税法论丛》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首推导读文章。)事实上,当时我除了在学校上课,每一年寒假暑假,都还在社会上一些办学机构讲课,这些机构有很多本身就是学校自己在外办的班,我是作为工作任务去完成。这种没有节假日全负荷的工作状态已经持续了整整10年,就这样我不得不辞职离开西南财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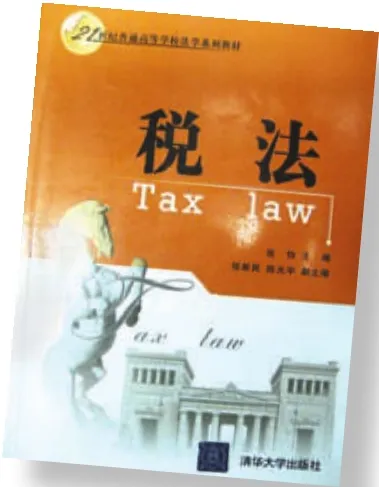

主要著作及论文:
《财税法》、《税法》、《衡平税法研究》、《写给法律人的宏观经济学》,《论非均衡经济制度下税法的公平与效率》、《创建“养护者受益”环保法基本原则》等。
研究社会科学,都应该到社会现实中去发现问题,而不能仅仅关起门来搞研究。对于学术氛围,我觉得是个大环境的问题,还是应该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允许更多的开放性思维。
记:您能谈一下在校生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相关问题吗?
张:我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时候,也参加过一些企业资产重组的方案研究。现在回顾这段时光,觉得作为学生,还是应该要更多地对社会和现实问题密切关注,否则学的东西完全堆积在脑中,只能是个书呆子,对社会起不了多少作用。自己虽然具有法学与经济学专业学习的经历,但是,真正的看家本事——财税法知识的掌握则是在实践中自学的,在财经院校中熏陶和在思考的点滴中积累起来的。我在校外机构讲课时,社会上数以万计的注册会计师、评估师、税务代理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等,他们都曾是我的学生,在听课过程中将实务中遇到的问题不断提出来,这些问题非常现实,也很专业。我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也增长了见识。在此,也建议凡学习财税法者切忌纸上谈兵,一定要深入实际,到事务所、税务机关或企业等单位实习。我认为研究社会科学,都应该到社会现实中去发现问题,而不能仅仅在学校关起门来搞研究。
记:您能谈一下目前的学界氛围和学术状况吗?
张:关于学术打假的问题,西南政法大学在这方面非常重视,主管校领导和学院、学科都在关注这方面的情况。西南政法大学首倡了一种打假软件,要求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论文全都要由打假软件过滤,只有通过的才能送出去盲评。实际上在学校开始设置打假软件之前,我已经安排了自己2005级的硕士生为2004级的硕士生做检索工作,他们在电脑上收集材料,相互对照,如果学生的论文中有太多和其他文章重复的东西,或引用了却没有加注释,就会作出符号令其修改。2005级同学第一次做这种事情,态度非常认真,发现问题后就毫不客气行使监督官的职责,此举对后几届硕士生都起了警示作用。
对于学术氛围,我实在很难评价,因为这其中还有大环境的问题。我觉得国家教育部对于学术研究、学术探讨还是应该适当地放宽一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给学者更多的研究空间,让他们能够思想开放一些,视野拓宽一些。如果仅仅单方面地高喊打假,同时却将学者的思想禁锢在狭小的圈子里,让他们可讨论的问题非常有限,那么他们就没有研究的动力,不去抄袭,又能如何?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辩证地看待问题,尤其像硕士生,他们只有这样的思想层次,他们所看到的学术观点前人都已经说了,能够用到的材料别人都已经用了,要让他们一夜之间成名成家,说出一些惊天动地的话语,实在是勉为其难,所以他们不做勤勉的资料编辑员又能如何呢?当然这样的看法太过消极,但是我的确在为这些孩子们着想,他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不能脱离实际地拔高要求,但是,对于博士生和作为教师的学术科研要求就应该从鼓励创新的角度,给予不同的评价和高要求。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我们的大环境还需要完善,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破除樊篱,解放思想。
“我只是想给学生一个宽松的环境,那里没有禁锢,没有篱笆和高墙,没有制约,让每一个学生都感觉到在老师心目中我是有自己的位置的。”
记:您前面说到学生论文的一些规范问题,联系当下学界造假情况频发,以及青年老师也面临着的学术压力,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张:这种情况我也考虑过,这种压力不仅年轻老师有,我们也有,其中的关键就是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的问题。我们身处这样的环境中,包括一些科研院士也都面临着一些衡量指标。
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涉及到作者的思想水平和创新性,但这些都是非常不确定的。一种学术观点,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在实验室里面通过做实验去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有些情况是不可证明的,或短时间内无法证明。很多社会科学的观点就是证明不了的,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很多社会科学领域有创见的观点很难被认可,往往是立论者在去世很久之后,才盖棺论定。几年前托马斯·谢林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好在他还活着,但也是八九十岁了,身后才功成名就的学者那就更多了。所以,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可以实验的,而社会科学则很难实验。
2011年我的《衡平税法研究》一书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当年仅有6项法学成果入选,这些成果被评价为:“反映了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相关领域的领先水平”。《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评审专家对《衡平税法研究》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该书“是一部颇具创新性的力作,填补了我国税法研究之空白”。但是,谁曾知道《衡平税法研究》是我2009年作为国家项目申报的,未能入围才转而作为中国法学会部级项目再申报,由于我们课题组完成该项目非常认真,结项时受到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专家们的一致好评,受此鼓舞继续研究,才有了这部即将出版的专著(丑小鸭有了成为白天鹅的可能性)。
在我国当前的学术氛围下,要对社会科学成果做出评价,只有“量”才相对客观一点。然而单纯的量的标准来衡量科研所导致的结果却是我们不敢恭维的。这种对量的追求逼迫大家制造泡沫,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就只有这么一条路径可走。所以应该有一个多渠道、开放的研究环境,在学术领域中没有壁垒、没有禁区。身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自然会有成果创造出来,否则,就是在鼓励大家去制造泡沫。
记:您能对现在的学生在人生道路和学术道路方面,提出一些期望或建议吗?
张:我觉得作为老师,对学生还是应该更多地给予鼓励,学生和学生之间肯定有差异,有知识积累和看待问题、思考问题等方面的差异。但是对老师而言,如何让学生能够真正感觉到有自信,能够面对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为人师者,不是要让学生跟随老师,而是要让学生超过老师。
作为学生而言,要避免把老师神圣化。学霸一方是很恶劣的风气,我的学生和我在一起时,往往把我当做亲人,而不是老师。我只是想给学生一个宽松的环境,那里没有禁锢,没有篱笆和高墙,没有制约,让每一个学生都感觉到在老师心目中我是有自己的位置的。
记:最后一个问题,想了解一下您近期所关注或研究的学术问题是什么?
张:继2010年我完成由李昌麒教授领衔的国家级重大招标(A级)项目子项目《改革发展成果分享财税法律制度研究》并免检结项之后,我获准主持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人为本的税收法治观研究》以及入选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的《衡平税法研究》,该成果也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予以立项。几项研究有共同之处,即:关注社会财富分配,财税法治建设,“税收是文明的对价”,是“权利的成本”,是人类社会延续和发展崇高而永恒的主题,这或许就是我终身关注或研究的学术问题。
编辑:卢劲杉 lusiping1@gmail.com
——评《食品法律法规与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