栢老庄·匠人二题
柏原
栢老庄·匠人二题
睡到半夜里打草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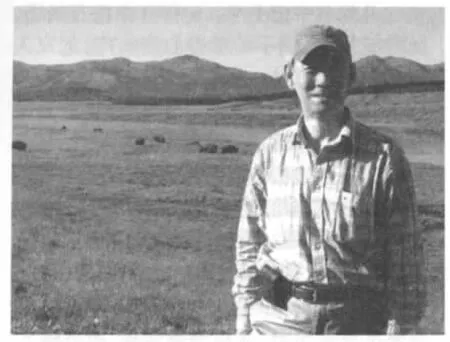
七不隆咚——嚓,八不隆咚——嚓……
一晚,章斯敲着满台的锣鼓家什,一招一式走来了。
章斯?人名吗?栢老庄生产队,男社员几乎清一色姓栢,偏偏里面加一楔子,倒插门女婿,姓章。几百口姓栢的,说话不称姓氏只呼名字,惟一个姓章的,却是只称姓氏而不叫名字。见面叫章斯,别的场合就直接叫章木匠。
噢,原是一木匠。听他满台的锣鼓家什响,手头也不见个家伙什。
大八大八衣大——仓!
章斯嘴巴一径响到了生产队烟房。
烟房什么意思?那时,农村搞的是计划经济,生产队每年种几十亩地烤烟。烤烟烟叶须经漫长而严格的烘烤工序,队里为此建一座专用烘房,社员随口叫它烟房或烤房。章木匠来烟房接班,并不是派他来这里做哪样木活,而是添炭、调温、守夜……一句话,上一个夜班。烟房温度达到要求,上工的人可以躺下歇歇,乃至眯盹一会。但是绝不可擅离职守,烟房温度一但失控,满房悬吊的青翠烟叶,就可能烤成了秦腔的铜锤花脸。
章木匠眯盹一会,真给睡过去了,拉起了浓浓的鼾声。恰此时,烟房门前,村路的远处,出现一条鬼魂般的影子。
夜已深,迷离月色下,村路依稀可辨,梁峁沟壑鸦雀无声。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吠,三四点蛙鸣,音波低垂游弋且莫辨远近,愈显得河川原野的空旷寂寥。那,月色下一条悠忽而来的影子,不让人感到十分可疑么?
不,来者乃生产大队供销点营业员,他的职业有点特殊性。每晚,他都要做一遍购销业务的钱货对账,有时隔壁大队部的几个头头开罢会,凑供销点上来,咂几盅烧酒,摸几把扑克,谝谝谁家小媳妇的风流韵事,谝得高兴就忘了时辰。在他,深更半夜,像一个鬼魂悠忽而来,乃是他的正常生活规律。你瞧,沿路庄头的狗,发现一条鬼魂似的影子,也懒得来几腔汪汪汪的提示,谁不认识谁啊?
营业员名字,有科举登第之寓,我就以“先生”称吧。别理解歪了,现今城里称先生的,可是布满了藏污纳垢的角落,小说写的这位,人家可是念过几年书的,要不咋能当上大队供销点营业员?营业员容易的!先生路过烟房门口,脚步稍一停顿,想跟值夜班的乡党调侃几句,撩一撩熬夜人的精神。探头看看,木匠大师睡得鼾声沉沉,想了想,实在不忍搅了人家一场好梦。迟疑间,突觉心血来潮,灵感火花一闪,往后撤了几步。
木匠有一儿,随公社建筑包工队去外地做工了,媳妇子没带去——废话!走哪都带上老婆,那就不叫贫下中农了。媳妇脸脸可心疼。是吗是吗?说说有多心疼。我心不疼,说了不算。那就这样描绘吧,木匠老两口看媳妇子看得可紧了,尤其章斯,仗恃自己有点专业特长,把门户铆得那个严丝无缝的劲,惹得一村小伙龇牙咧嘴的,背地里不叫他木匠,都叫格老损。
好了,单表先生一位。
当然,还须一个配角,脸脸长得可心疼。
儿媳名字记不准,记得有个梅花的梅。记住这颗字,倒不是觉得心多么疼,老家人祖祖辈辈没见过一朵梅花,女人名字却频频出现红梅、白梅、春梅、冬梅,这颗字看着怪怪的。不过,比起那些从来不认识梅花,却是以画梅而画出名的名人,老家人还是可以理喻的。梅,常去逛逛大队供销点,有买的没买的,就是逛一趟。卖点农家土产,买点洗涤用品,也许先生有意让她沾沾光。问题是,先生苦于无缘去她那串门,格老损把门关得太严了。
天无绝人之路不是?机会总是在无意中撞上。她男人去外地好多日子,年轻媳妇一个,夜夜抱一块枕头睡觉,难道不嫌孤单?此其一。今晚,木匠守在烟房里脱不开身,顾不得自家门户松紧了,而留家守门的那个老婆子,恰恰耳背,那两片耳朵真像聋子的耳朵,此其二。其三,深更半夜,村里的串门一族,早已是飞鸟各投林,谁想这工夫有一位识文断字的先生,串将起来了。
妙哉妙哉,正是这等主意!
仓,采采,衣采采,仓,采采,衣采采……
先生一径行至章木匠门上,伸手轻轻一探,大门竟是虚掩的,可不妙哉妙哉。
下面,就进入秦腔大段乱弹高潮了。可惜,我写不来,现今的名家和新锐,已经把“下三路”写到极致,我这里想当然编上一通,写得走了大样,先生和梅骂说,小说喔都是胡球然(粘)哩么。
两人睡得正香,大门门扇哐嘡一声响,叫人掀开了!猛古冷丁的,章斯章木匠回来了,气咻咻怒冲冲地回来了。梅翘起白亮反光的上身,耳屏息聆听,真是公公的脚步声。离天亮交班早得很呢,他怎么突然跑家来了?全身精光的先生呢,却怀揣一丝侥幸,悄声说,是不是回来取件衣裳拿点吃的?梅说,不像,我听人喔走手不大对劲。先生咬牙小声骂道,格老损!刚刚在烟房那会,他不是睡得死死的吗?梅说,哼哼!他不睡“死”了,你能来我这串门啊?
木匠石锤般的脚步声,一记一记砸得院子通通响,径直向偏窑走过来。偏窑者,儿子儿媳居室,公婆上辈是不轻易进入的,何况此刻,正值深更半夜,格老损究竟想干嘛?先生吓得慌忙蹬裤子,蹬好几脚,硬是摸不着裤裆开口和钮扣,嘴里紧张地咕哝,格……格老损,敢不会闯进来打人么?梅也很紧张,危急关头却比先生来得镇定,尽量安慰说,看不会……不会!黑天半夜的,老公公闯进儿媳窑里,寻着捉野男人,传出去还不把一村人都臊死,那张老脸他往哪搁?倒也是,木匠的脚声一直砸到偏窑窗户下,猛地刹住。
静场。好长好长工夫。铜锤花脸那一声,哇呀呀呀呀的叫场,就是不发。窑里窑外全没一丝呼吸,好像台上台下的人都死了。这会,先生两手仍死死抓着裤腰,怎么着,感觉裤皮带跟自己的不一回事。后来才闹明白,他这是在使劲穿梅的裤子呢,裤腰开口开在侧面,这才叫“胡球然”艺术。
木匠猛地叫一声板,恶声粗气地说,睡觉哩,连大门都不上!上,方言,意为把门板从里面闩住或顶住。梅装作被惊醒的声音,抱歉地说,噢噢——大门忘上了?咋把这件大事给忘了……木匠不依不饶地说,忘了啊?那你操心啥呢?你也不怕谁家喔狗,黑里溜进来寻着吃猪食!梅哗里哗啦的,把衣裤抖落出声音,表示要马上起身弥补过失。木匠公公却冷硬地扔下一句,你们好好睡吧!大门我已经上啦!说罢,甩下一串咚咚咚的脚步声走了。
这才缓过点劲。梅说,哎哎,他哥,我穿的不是我裤子耶!先生吓得懵懵的,说,啊?那我穿的这是谁的裤子?不管谁的先穿着先穿着。梅说,你这就走吗?先生苦笑,不走,在你这坐到天亮吗?你听他说什么来者,你们好好睡吧!你男人不在家,炕上又没第二个人,“你们”是谁?梅咬着牙帮说,人都骂格老损,一点不冤!先生说,先别急着骂,快出去瞧瞧,格老损睡下没有?
梅轻轻拉开一条门缝,窥一眼,霎时愣在那。
木匠公公,压根没进老两口住的那孔主窑,而是在院子里铺排偌大一个阵势,儿媳一时半会看不懂这一阵势的典故。院心杏树横杆上,吊了盏马灯,灯芯子挑得很粗很旺,把一座小院照得明晃晃的。灯光下,摊开了几捆浑秆儿谷草吗麦秸,又拎来满满一桶清水,又搁了一只短腿板凳。此外,地上一溜儿摆着角尺和直尺、木柄撇锥、匠人斧、斫刀……木匠杀一先生,拎一桶清水可以洗涤血手,但是用不着搬出这十八般的兵器。
梅装样儿上一趟茅房。走过院心,不解地问,爸哎——这是准备做啥呀?木匠瓮声瓮气扔过一句,打草圌么,做啥!梅登时张口结舌,原来他是要打草圌啊?天!
留下的,不仅是一个古老语音,并且有圌的编制技艺,老家人习惯说打圌、打草圌。因为老家那地方干旱,古来不生很多竹子,荆条一类自然资源也是越砍越少,编织材料便演变成麦秸和谷草。麦秸谷草的强度、韧性、抗霉变等特点,比别的庄稼秸秆更接近荆条,因此造成我小时的误听“草船”。
打草圌怎的一回事,梅当然懂了。可是男人的打草圌,跟女人的织毛线道理相似,向来是趁闲暇找空隙干的一项慢工活,谁见过女人家睡到三更半夜一骨碌翻起身来织毛衣?再说了,队里不是派你在烟房守夜添火的吗?哪来这份闲工夫,又哪来这般好心情,三更半夜拉开架势打起草圌来了?简直让人哭不得笑不得。梅回到窑里,关上门。先生急不可待地问,哎妹子,你爸嘁哩哩哩唰啦啦啦,鼓捣什么呢?梅没好气地说,人家要打草圌呢!先生愣怔半晌,黑天半夜打的哪家的草圌?梅说,那你问他去吧!先生憋好久,牙缝里挤出一句,格老损噢!
打草圌,可是一项慢工细活,一点急不得的。
家里要添置一只口径有多大、圈帮有多高的粮囤?首先,依体积与周长及高的几何关系,确定它的直径及周长。而后,用两条交叉的柳杆或竹竿,做出一副十字骨架,扎一个木的圆环形圌楦子,圌楦子既是起手编织的依托,又是往后测量用的规矩。而那个几何概念的“圆柱体”,把它由想象的几何图变为草秸实体,正是你要做的事,打草圌。
同时,须用清水一遍遍地喷淋洇制,使谷草、麦秆保持软硬适度,刚而不折,又柔而不软。一切准备就绪,你就可以一节一节地一圈一圈地往上叠加了。叠加,可不是说,你把谷草或麦秆扎成一个一个圆圈,一层一层摞上去,再用柔韧的草腰子穿插编织。不,草圌不是那个打法,草圌是整体性的,犹如压缩了的一只弹簧圈,分解开就是一条螺旋上升线。这条螺旋线在延伸过程中,每隔五六寸、七八寸,就须扎一道腰子,草腰子穿过下边那道圆环的中心线,扎紧后,归入上边这道圆环的本身。节律均匀,循序渐进,却是不露茬口,不显腰子结头,浑然而成一个圆柱体。那么,每一束新加入的谷草或麦秸,都须体现出过渡性和一致性,并且始终维持着圆弧状和均匀度……
有一点想象了?简直有点吟格律诗、谱进行曲的意境了。
村庄男人打草圌,多选择在农闲时节或连阴天气,男人就像一只吐丝作茧的蚕儿,抑或像一只无事结网的蜘蛛,既专心致志,又悠游自如。有的人打草圌,喜欢蹲在圆周内部,有的人却习惯处在圆周外某一切点,一边和串门谝闲的人聊天说笑,一边让草圌在手底下慢悠悠地转动升高。时而捋一束草秆,时而拧一道草腰,要么腾出两只手,卷支烟,喝口茶,吃块馍……现在,你应该想到,这只周秦时代的草圌,章斯他准备打多会去?或者应该这样说,先生,对,先生必须像热锅上的蚂蚁,像钻风箱里的一只老鼠,熬煎到多会去?
后来,村人创造一句典语:章斯睡半夜里打草圌哩么!语义:你所看到的真实画面,其实那才是虚假表象,事情的真实在于,把根本不出现在画面里的某个人给拿住了。
梅,干脆不睡了。梅穿戴整齐了,开始做自己窑里的家务活。小两口住的这孔偏窑兼做厨房,于是儿媳妇揽柴火,掏灶灰,扫脚地,簸秕谷……厨房里的家务,你若故意找事干,一天一夜不睡,也未必把它整清楚了。
丁丁当当的,踢踢趿趿的,梅一会出来了,梅一会回去了,这扇门哗啦开开,那扇门吱扭合上——瞧瞧,多勤快的一个好媳妇,格老损还有什么不满意?木匠公公反被儿媳闹得神经绷紧,忍不住说,你不睡你的觉,急着爬起来干嘛?梅说,老人家农业学大寨,觉都不睡了,做儿女的能睡懒觉吗?木匠公公说,鸡还没叫哩,你扫的这个地,是昨天的地今天的地?梅说,是吗?我以为天大亮了,鸡还没叫吗?烟房怎么这么早就交班啦?公媳这番对话,在外来作家听着,全是没一点点意思的家常琐语,只有置身现场的乡亲乡党,才能体味每一句话的无尽微妙。木匠心想,你爱做尽管做,我只要盯住这扇大门就够了,勿管一只猫一只狗,任你使上什么高家庄的招,反正得从我眼皮子底下过。
院子里,唰啦啦啦,章斯睡到三更半夜打草圌。窑洞里,嘁哩哩哩,梅一骨碌爬起来做家务活。两人挑灯夜战,农业学大寨,一直忙到天亮。若是碰巧来一贴近生活的诗人,欣赏了这幅农家乐图景,马上会写出一首抒情诗。
天亮,梅梳洗一番,肩上一件工具,到生产队上大田,真的农业学大寨去了。
章斯好不疑惑。儿媳一出门,他立即操一把明晃晃的斫刀,气冲冲闯进儿子儿媳住室,憋一股劲去捉人。遗憾的是,窑里空空如也,旮旯拐角搜寻一遍,连个鬼影子都没的。
黄土崖庄及窑洞,我再熟悉不过了。窑洞只有一个门,庄院也只有一道大门,先生不从窑门出来,不从庄院大门出去,还能钻了老鼠窟窿不成?多年后,谝闲传的乡党才把谜底揭开,如此这般如此这般,听得人拍掌叫绝。当然,先生没有钻老鼠窟窿的本事,他只不过爬了爬狗洞而已。
瞧仔细了,院子墙角那块,墙底下有个窟窿眼不是?那窟窿眼儿叫水窗眼。
章斯这种黄土崖庄,俗名靠山庄,庄院依山崖落差而凿,几何俯视图有如“半个月亮爬上来”。弧线那边是高高的斩崖,弦线这边是一溜黄土筑墙,大门开在院墙居中位置。慢着,厕所搁哪了?对,留心一下厕所,弧形斩崖与直线筑墙衔接的一个死角,角角里打了几堵矮墙,圈成一个不规则设施,那就是厕所,方言茅房。再瞧仔细点,茅房矮墙的外侧,院子高墙的内侧,墙根底下凿一小洞,用以排泄院子里的暴雨积水,这就叫水窗眼。眼儿粗细,本来只够一只猫进来,但是泄水年代久了,竟可以钻一只狗出去。水窗眼那块,土壤湿润喜欢长草,所以人们平时不太注意,窟窿眼已经变得有多大。
一个人被逼到死角,只剩束手就擒的份,文化人的形容是,插翅难飞,入地无门,山圪人则有自己的一套俗话。有句俗话说:我看你钻了老鼠窟窿不成!还有一句更粗:我看你能钻沟子吗!这回,先生被逼到了死角,钻老鼠窟窿当然不成,却是将身子往下一个搐搐,钻了水窗眼儿,或说是爬了狗洞洞,实在称得一个发明。
慌乱之际,先生和梅穿错了裤子不是?稍后缓过劲,才顾得上换裤子。换裤时,先生又是灵感一闪,不仅没把裤子换过去,反倒把上衣给换过来,这就不是一般的胡球然艺术了。梅,一直出出进进忙活着不是?她忙个什么劲?你总不至于认为,她真的有那么勤快?忙活半夜,忙的就是一个“出出进进”的形式。对了,要的就是这个形式。形式即内容,哲学家这样说。
其中一趟,她包着红头巾,背着一只大号背篼,扭哩扭哩走出窑门,到茅房墙角那块干点啥,许是解个手,顺便倒倒垃圾。儿媳上厕所,做公公的还能眼不眨盯住了?这才叫:智者千虑,终有一失;或者说,猴子也有个丢盹的工夫;干脆说,格老损到底有个看走眼的时候。上茅房的她,只是她的衣着和走手,即她的形式,里面内容不用我说了。
记住一桩村野轶闻,倒不是事有多大,也不是故事多么的稀奇古怪。山圪,吃罢晚饭浪门子的故事,并不概念化地归入道德范畴,通常都很快地变成村人胡谝冒撩的一道小菜。记住它,只是因了几个文学性“细节”,一桩小小不然的事,细节中竟包含了如此多的创造性含量,真是叫人佩服到家。人,即便是山圪再平凡不过的人,基因中潜藏着如此奇妙的创造天赋!
再者,记住一桩村野轶闻,因一句村庄典语。村庄典语,在外人听来,莫知所云,了无意趣,而由乡亲乡党们的嘴说出,却是这样的妙趣横生,余味隽永。
典语曰:章斯睡半夜里打草圌哩么。
鸡不叫翻了三崾岘
阴阳,故乡方言中神职人员称谓,别的地方多叫风水先生,或叫神汉神婆。不过,几个名称在语言色彩上稍存差异,“风水”偏重于经书知识,“神汉”偏向于鬼魂迷信,“阴阳”介于二者之间。
栢阴阳,无疑是栢老庄一个姓栢的阴阳,按辈分我该叫他家叔。“家”,本族的意思,血缘已经远到不必追溯,按阶级观点则应该称他贫农社员同志,而就“这一个”表述,说来就得啰嗦点了。
栢阴阳如何穿凿阴阳两界,代神与人传递信息,我从不完全信他。他的阴阳职业,在我幼年记忆里仅留下这几个特征:一是他跪堂摇铃诵经的样子,两眼眼皮始终轻轻耷拉着,眼前香案、灶台上搁一本老得发黑的什么书,嘴里呜里呜喇叽里咕噜,伴着极有节奏的铃声,念半晌。想起了,才用指弹蘸舌尖翻那么一页,我没听清哪怕一句台词,但我看出念的长度与书页上字数压根不符。后来,我不愿读佛经原著,心理障碍就出在他那了。二是,他可以用毛笔蘸红墨写字。我晓得,只有学校老师才有权用红笔批作业,除了老师,再就是镇原县县长,县长的红笔见于墙上的枪毙人布告,画一个大勾或大叉,很气派。又一特征,是他的行头,赶赴哪家的祭祀敬神活动时,穿得像个前清老太爷,瓜皮厦帽,长袍短褂,裤脚扎成灯笼状,斑竹烟杆长似竹杖,玛瑙烟咀上钉了精致的铜疤疤,烟荷包和石火链系绳低低地垂过膝盖……一身的古色古香和古墓文物气息。喔,肯定还有一块手帕,比抹布还黑的一方手帕,揣袖筒里哪块,我一辈子也没猜出是哪块。
不过,他的贫农社员特征,比之阴阳先生行头,留给我的印象更鲜明。
我记事清楚的时候,各家的牲畜已归入公社生产队大槽,常见死的牲口拖出饲养场,几个饲养员围在那,血糊流拉地剥皮。每逢这一时机,栢阴阳就会头一个抵达现场,肩上扛一把惟他才有的短柄镢(其专用功能是:刨墓穴时钻穿堂里面施展得开),迈着徐策跑城那样的碎步,颠颠颠颠载舞而来,比天上的臊鸦和外村的游狗信息还灵。当此时,脸盘乐得像朵花,哈喇子珠珠挂在八字胡毛梢上。等我学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才觉悟到,贫农社员面对集体牲畜死亡的这副笑脸,应该赏他几耳刮子才是。剥皮的饲养员碰到大骨头断不开,栢阴阳立即以舍我其谁的口吻叫道:闪开!瞪圆了眼,一镢头砸下去,死牲发出咔嚓断裂声,在场的人溅一身血点并齐声喝彩。完了,必然扛几件血淋淋的大块肢体回去,一连数日,栢阴阳家的气氛像过大年。
另一生动场景,挪到了生产队场屋。
队里几个头头开会,常躲在场屋的大炕上,事先坚决不对广大社员同志宣布。要是有人无意闯入场屋,头儿们很不愉快,说,你忙你的去,我们说事儿呢!可是,有时刚开到节骨眼上,栢阴阳就笑嘻嘻地溜进来了。你想他是什么人?阴阳!鬼魂知道的事他就会知道,你们想瞒过他去?不过,这时候,你再也看不出一星半点的前清老太爷作派,恰是一副舞台典型化了的老贫农形象。腰里绕了两圈毛线绳绳,手松松地杵在袖筒里,肩上搭一条补丁摞补丁的空口袋,啣在嘴角的烟棒棒火早死了,仍然吧哒吧哒地咂着,念经似的。他进来,背过身去,往门槛或粮袋上一圪蹴,缩成很小的一团,表示对于头儿们的会议秘密是绝不听的。队干部说,你忙你的去,我们……他马上答道,我不忙,不忙!我是一闲人,我闲闲的,你们正经开你们的会。队干部当然熟知,这位未经邀请的列席代表,出去了倒不会传什么闲话,全部问题在他那条破口袋,自从走上集体化道路以来,共产党就不曾给他填满过。会草草结束,队长气不忿地说,散球!栢阴阳屁股一拧转过身来,一本正经地说,慢——慢,我的问题,头儿们捎带着研究研究!队长脸都憋红了,向会计或保管甩甩手,说,给装上几升装上几升(指救济粮)!他们要是对他的“问题”研究研究,恐怕就不是“几升”的问题了。
我的用意,不在丑化这位阴阳家叔,他哪么个样看着精彩,我就写他哪么个样。
早年间,栢阴阳并不是中国乡村的破落户类型。听老辈人说,他幼年时家道殷实,他爷爷和我太爷爷,曾经是出生入死的患难之交,在同治朝代民族相残的战乱中,饱经血与火的洗礼,为儿孙后代拼下一份家业。他爷爷一个儿,我太爷爷四个儿,所以我祖上很早就分裂成贫下中农,他家日子则一直过得挺富。但是很遗憾,传到他这一辈,出了个败家子。栢阴阳的青年时期,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不学好”——换作现在的流行语,应该说“酷”是吧?要么这样说吧,不要太潇洒耶!
好,侃一段栢阴阳的潇洒。
栢老庄,地处红水河川道,由川道爬上高而曲的黄土高坡,翻越一道马鞍状崾岘,就登上了北塬。走完一条长塬,再翻越一道崾岘,前面又是一条长塬。走完前面一条塬,再翻越一道崾岘——听我这样说话,是不是像“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的故事叙述手法?不不,我没一句话具有故意重复的意味,每一句都足以让您流一身臭汗!再翻越一道崾岘,脚下陡然出现一泓勺头状的大沟。
往下看,勺头状大沟的半坡台阶上,悬悬地搁了几座窑院,地名叫吴家沟。这儿有一户姓吴的人家,男人死了,留下一儿三女四个娃,不,应该是五个,还有一个遗腹子,当然,还留下他年纪轻轻的媳妇。媳妇子人长得挺俊,听上辈人说,年轻那会俏丽而风骚。我第一次见她,七八岁大点,不知道观察女人的美,见了只管叫“家婶”。在她没变成我的家婶前,栢阴阳常常去她家诵经,抑或是捉鬼,关系很熟。吴家男人一死,此时还在打光棍的栢阴阳,必然要立即填补那个空缺,隔三岔五地到吴家沟串个门,不,应该说“潇洒走一回”。
潇洒?而且还走?对于当今城市人,潇洒有之,走,则是矫情的措辞。我们试看栢阴阳人家是怎样的走法。前面一连说了三座崾岘,外地人不熟悉这里的地形名称,那就从崾岘扯开。
崾岘,方言,黄土高原沟壑地区一种奇特地貌,指两处较高的残塬梁峁之间狭窄的道路连接,多呈平缓的弧形下陷。我说的像不像一个词条?因为连《辞海》也都语焉不详。随意点说,黄土塬面和梁峁岭脊,几十万年来一直处于剥蚀分解过程中,造就了今日沟壑纵横、山峁林立的地貌特点。但是,有些地方早已分崩离析自成一体,有些地方则至今藕断丝连、若即若离;崾岘,正是今日的塬面与塬面、山峁与山峁,或者残塬塬面与梁峁岭脊之间的残存联系。转九十度方向,因为剥蚀裂解的沟壑像树根一样的密织交错,有的沟与沟已经贯通,有的则尚未贯通或未完全贯通,那么,两条沟的沟头逐渐抵近而挤压,中间残存一道高高的弯弯的窄窄的“黄土桥梁”,这就叫崾岘。从人文意义讲呢,崾岘,正是我的祖先们世世代代循此而行的一条交通要冲,亦是大自然在惩罚黄土高原居民的同时,例外留给他们的一个恩赐。
会一次梦中情人,栢阴阳须翻越三座崾岘,穿过两条长塬,爬上一条黄土高坡——至于溜下那个勺头状大沟的台阶,姑且忽略不计。最保守的计算是三十五华里路程,是不是够他潇洒一回了?且慢,我仅仅说了不到一半!栢阴阳风尘仆仆赶到吴家沟,并不意味着款款地躺下了,他还得马不停蹄返回来。也就是说,上面各项数据全都乘以二,实为两扇大坡四条长塬六座崾岘,是不是够他走上一回的?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不理解某些时代背景。一是,栢阴阳做此潇洒之举,必须放在黑夜,夜越黑越好,即从人睡定到鸡不叫这段时间内全部完成。为什么不放白天?害怕家里父母察觉啊,害怕路上撞见乡里熟人啊。二是,这一前提的前提,栢阴阳白天已经劳动了一天两晌,那时他家有七八十亩地,惟靠人力和牲畜做耕耘动力,你可以想见一个小伙子白天的劳动强度。而这一前提之后的“后提”是,栢阴阳赶回家刚刚躺下,鸡偏偏就叫了,父母亲吆三喝四地把他赶起来,接着又是汗流浃背劳动一天两晌……
现在,你可以体会栢阴阳“潇洒走一回”的全部内涵了,这里面,没多少当今文学对性的百般挑逗,更多的是对人本身的赞叹。
他算上辈人,我不能去问肌肤感觉什么,只听说了一个小小细节。
有回,小伙子栢阴阳,深夜走一趟吴家沟,返回后马上被父亲赶着下地。正值三秋大忙,父子二人抢节气种麦。那回好像是在磨子峁峁上,峁上耕地像一根根皮条,一圈儿一圈儿层级缠绕,堆垒而上。父亲吆牛扶犁耕在前,儿抱斗抓粪跟在后(麦种拌在沤化过的土肥中,老家人把播籽的过程叫抓粪)。抓粪小伙,胸前挎一只长方形木斗,一次次跪倒在拌了种的粪土谷堆前,把土肥刨进木斗里,一揽七八十斤重!然后赶上前边匀速行进的牛犁,用一只大碗舀着溜下去,一缕一缕溜在犁垄里。这是一项非常沉重的劳动,隔一两分钟,就向粪谷堆跪拜一次,而遍地堆的粪土谷堆,全得一把一把从他手指缝里溜下去。父亲绕山峁峁的皮条地块犁完大大的一周,又转回到他揽粪土的那个谷堆时,发现他一斗子粪还没揽起!父亲定神一看,他脖颈挂着七八十斤重的木斗,双膝跪地,头歪一边睡着了,还拉鼾呢!父亲气坏了,用驱牛的鞭子抽他几下,才把他弄醒。父亲大骂,狗日的!睡了长长的一夜,你还没睡够?趴着粪谷堆儿你能睡着啊?脖子吊着粪斗你能睡着啊?这他妈出什么鬼了!
那么,再说三座崾岘。
三座崾岘中的两座,我少年时走过,当然我是走在大白天。大白天走着,也觉心咚咚咚跳,耳朵里嘶嘶嘶的响,因为听了太多的关于它们的恐怖传闻。
一座崾岘名叫狼儿崾岘。狼,这一名字并不儿化,如猫儿狗儿等,此地却加以儿化处理,我揣想,是当地人为了减弱口语的恐怖感。凡崾岘,寻常就撞上野狼吗?也不宜做这样的概念判定,那得看崾岘两面大沟深处的生态情况。如果沟谷里人烟稀少而草木丰茂,行人在崾岘里与狼打照面的机遇就多,深更半夜机遇就更多了。因为狼穴必定选择在沟旮旯的深幽处。所谓“狼穴”,实际是黄土地层隐蔽的裂隙,被暴雨积水渗漏侵蚀所形成的地下溶洞,溶洞愈往下去愈见崎岖深邃,只有狼才能探查到底。狼的猎食范围却不以沟垴为界,它从这条沟窜到那条沟,最简捷最隐蔽的路径,即是横跨崾岘土桥。那么,纵向之行人与横穿之野狼,说不准,啥时就在崾岘路上打个猝不及防的照面!时间倒推八九十年,沟壑的野狼可不像如今商标形象,更不同于流行语的浪漫色彩。七匹狼啊?一匹足够啦!与狼同舞啊?深更半夜荒山野岭,七个小伙未必陪得住它一个,除非你手上有枪!
再一座,名叫黑崾岘。黑,听着似乎不像“狼儿”吓人,其实它比狼来了让人心惊。黑崾岘两岸的层级崖坎,遗存许多烂窑古庄,坍塌几百年的窑洞子,全都张着深不见底的嘴巴,瞪着骷髅般一眨不眨的眼窝,白天走过,看去一个个幽深莫测,猜不出它里面究竟藏匿着什么。一个传说,同治之前这两岸是座大村落,战乱中村人被杀得光光,此后变成了鬼魅世界,大天白日亦会瞥见黑窑里游荡的憧憧鬼影。最可怕是女鬼,披头散发,吐出半尺长的血舌,向行人媚笑招手。又一传说,光绪二十七年和民国十八年两次大饥馑,黑窑里钻了些“吃人贼”,把死人尸体拖入黑窑煮着吃,尸体吃光,便捉拿崾岘里的孤单行人。据说,吃过人肉的人,两个眼仁变得血红,看见人的肉体就垂涎三尺,躲暗处死死地盯着路上的行人……我小时走舅家,必经黑崾岘,虽然跟在大人身后,每走一回都要承受一回极度恐怖的心理煎熬,眼光从不敢向两岸的窑洞子偏斜,脊背后面冷汗涔涔。
还有一个叫焦崾岘,被火烧焦的焦,一名石头壕,乃旧时土匪出没无常之地,不细说了。
现在,什么是潇洒走一回,我们体验体验。
六七十年前的一个黑夜。那时,人口及村庄的密度非常稀,从栢老庄走到吴家沟,四十华里荒山野径,一路遇不见大点的村子,偶见三两孤独住户,窗眼里也绝无一丝灯火漏出,意外瞧见前面有一条踽踽独行的人的黑影,那比突然撞上一头狼还让人惊悚!此情,此景,栢阴阳走来了,以强行军的步履走来了,你看他的潇洒!路,呈现为一条飘忽而扭动的蛇,向无尽的黑暗中游动而去;梁峁山咀的浓重投影,歪歪斜斜,缥缥缈缈,像魔怪布下无数个诱人深入的迷阵;沟沟壑壑崖崖坎坎之下一派死寂,保不住哪片树丛草棵骤然作声,后面蹿出一头活物;惟有一抹惨淡的月光,涂抹在蜿蜒的山间小路上,敷染在巨大的重叠的印象派构图的某一面,愈加使人辨不出真实与迷幻、人间与冥界。几十里,听不见人声,听不见狗吠,甚至听不见鸦鹊的滑翔鸣唳;却一直听得见,身后有人尾随,踢踢踏踏沙沙啦啦的脚步,呼哧呼哧嘈杂的喘息,怦怦怦的鼓一样的心跳!尾随的那个人正是你自己。
就这样,栢阴阳翻了一座崾岘——狼儿崾岘,崾岘两边梁峁上的蓬草或庄稼棵稞子,被突发而至的山风掀起一阵异常嚣叫,让人浑身汗毛竖起,同时浑身汗毛也在喧哗。就这样,他又翻了一座崾岘——黑崾岘,崾岘两岸的哪孔烂窑抑或塌崖,不期而遇传来一记噼里啪啦的坠落声,惊得人心脏差一点儿从嗓眼里蹦出……但是,栢阴阳,绝不会掉头而返。栢阴阳依然向第三座崾岘奔去……何其潇洒乃尔!
少年时代,我有时遇见,村里一伙男人圪蹴一堆堆,说那种乡亲乡党们才能听的冷话,如今称作“段子”。小伙子待在一起,总喜欢显摆一番自己的能耐。这个吹说,前晚上他到哪哪哪去了,一口气连着爬了几座馒头山。那个又卖弄说,昨个晚上,自家的几亩几分地拾掇罢,他又帮谁谁谁家赶了几个麦趟子……栢阴阳,总是呆一边笑眯眯地听着,眉梢眼角挂着一副淡淡的表情。好像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不与你们小的们一般见识。要是哪个小伙子牛皮吹大了,他就一下给惹躁了,往地上啐一口,骂道,亏你家先人!把人臊(羞愧)死去!你那也叫本事?我像你这把年纪,五黄六月,赶一天的麦趟子回来,汤喝罢,人都睡定,我才正式上路哩!一坡二塬三崾岘,四十里路我一忽忽就赶到了。赶到了,让你歇呀么……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失口,身子往后一欠,不说了。
小伙们用话激他。故意说,到了也白搭,人家死活不开门喀!栢阴阳被激怒了,说,不开门?她不开门,我就打崖里下了!他说的崖,指我老家黄土庄院的斩削崖面,高度一般在两丈以上,这话有点吹牛。小伙子还激他,说,打崖里下去,狗咬得不成嘛!栢阴阳气不打一处来的样子,骂句脏话,说,关你(指狗)什么事啦?我几下就把衣裳扒了,扒个浑身精光,这一招,倒把它吓坏了,它没见过山里有我这种不长毛的野物唦?我就地打了几个车轮子,吓得它稀屎直冒哩,它哪见过像我这么走路的野物唦?狗叫我吓得连哭带嚎,打崖里上了……
小伙子们继续拿话激他。他不说了,后面的话真的不说了。
进门后,炕头细节种种,栢阴阳从不渲染一句。
柏原,原名王博渊,籍贯甘肃省镇原县。中国作协会员,甘肃省作协顾问。三十多年来致力于短篇小说和跨界散文的创作,曾获全国短篇小说奖。
责任编辑张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