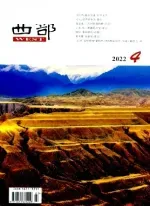海鸥飞翔
——莫斯科的戏剧生活
苏玲
海鸥飞翔
——莫斯科的戏剧生活
苏玲
如果没有去过莫斯科,我们的确难以想象,一个城市,就算它是一个大国的首都,竟然有两百个剧院和演出团体,每天晚上有近百场的各类演出。这一定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各种音乐会、歌剧、舞剧、芭蕾舞剧、话剧、儿童剧,甚至马戏,几乎所有的表演艺术门类,在每年10月至来年3月这个集中的演出月份轮番上场,让人眼花缭乱,不知如何取舍。单就话剧而言,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到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从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到萨杜尔的《骗局》,内外古今,无所不包,更不用说演出海报上年年都会出现从果戈理、契诃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到苏联时期的经典作家布尔加科夫、施瓦尔茨、阿尔布卓夫和万比洛夫等等这些熟悉的名字了。毫不夸张地说,到了莫斯科,就仿佛进入了一个戏剧的海洋,如果你是一个热爱戏剧的人,那这里就是天堂了。可以想见,俄罗斯是一个多么热爱艺术的国度,说它是艺术大国和强国,一点儿也不夸张。
初到莫斯科的人,自然是把到俄罗斯国家大剧院观看芭蕾或歌剧演出作为首选。位于剧院广场一号的国家大剧院以建筑恢宏、具有皇家气派著称。除了开阔的池座,还有围成圆形的三层楼座,正对舞台的中央,是一个宽敞的包厢。过去的沙皇和许多赫赫有名的国内外元首,都曾经在这里就座。剧场以金色廊柱与深红色天鹅绒作为装饰色调,华丽而庄重。圆顶上方巨大的吊灯与四周墙面密集的壁灯交相辉映,盛装的观众彬彬有礼、略显兴奋的表情,都表明着人们把来到这里的日子视为节日。而艺术的盛宴,当然首先是指舞台上世界一流的艺术呈现。在剧院的海报上,芭蕾舞《胡桃夹子》、《堂吉诃德》、《天鹅湖》和威尔第、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哈恰图良、普契尼、格林卡的歌剧,以及莫扎特、肖邦的音乐会,每年都是演出季的保留节目。

然而,真正体现俄罗斯深厚戏剧艺术传统的,却是遍布城市各个角落、规模不等、风格各异的剧院。这些剧院位于城市的四面八方,大多乘坐地铁就可到达。老牌的剧院,比如莫斯科高尔基艺术剧院、莫斯科契诃夫艺术剧院、瓦赫坦戈夫艺术剧院、马雅可夫斯基剧院、现代人剧院等等,几乎占据着交通便利的临街位置,霓虹灯招牌让你远远就能看见它们;而大多数剧场,尤其是近二十年新开张的小剧场或者戏剧工作室,比如青年观众剧院、莫斯科现代派剧院、小舞台剧剧院、幻想剧院,以及新出现的实验剧院等等,要找起来就会让你费些周折了。
说起俄罗斯戏剧的繁荣,应该从十八世纪后半期和十九世纪初开始,那时,几乎每个庄园都有自己的剧团,可以进行芭蕾、话剧的演出,演员由农奴担任。奥斯坦丁诺的谢列美捷夫伯爵剧团,就规模和华丽程度来说,就不亚于当时欧洲最好的剧团。它的剧场能容纳两百五十名观众,舞台布景十分豪华,加上服装和化妆人员,整个剧团达两百人之多。该剧团活跃了十年,直到1756年由戏剧家苏马罗科夫创立的俄罗斯第一个专业剧团在彼得堡出现。当然,这个时期也出现了许多以普通民众为对象的民间滑稽剧和歌舞马戏的表演班子。
真正的俄罗斯民族戏剧出现在十九世纪初,以格里鲍耶多夫的《聪明误》(1824,1831年上演)和普希金的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1866年上演)为标志。而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的上演,则成了俄罗斯戏剧史上的重大事件。十九世纪后半期,俄罗斯民族戏剧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的开端,就是伟大的戏剧家阿·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出现。在小剧院的舞台上,他的《贫非罪》(1854)、《大雷雨》(1859)和《自己人好算账》(1861)等精彩剧目接连上演。1898年,导演和演员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科一起创立了莫斯科艺术剧院。阿·托尔斯泰的《沙皇费多尔》成了剧院的开张大戏,而契诃夫的《海鸥》和《万尼亚舅舅》等剧作也在这里获得了新生。连无产阶级文学的先驱作家高尔基的《在底层》和《太阳之子》,也是在这里获得了首演成功。正是以这个剧院的戏剧实践为基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总结了著名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它不仅影响了之后百年的苏联戏剧发展,而且至今也还是中国戏剧教学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内容之一。这个理论以体验、发掘和表现人物心理活动为创作依据,与契诃夫的心理现实主义戏剧风格相得益彰。从此,莫斯科艺术剧院成了契诃夫戏剧的忠实追随者和实践者,并最终以契诃夫的名字为自己命名,而“海鸥”的形象也开始出现在剧院帷幕的下方,直至今日。1989年,莫斯科艺术剧院被一分为二(即莫斯科契诃夫艺术剧院和莫斯科高尔基艺术剧院),但作为主体的契诃夫艺术剧院无论就选择剧目还是舞台形式,仍然严格保留了传统艺术风格,而契诃夫的剧目也成了两个剧院的保留剧目,且永远是场场爆满。
所以,谈莫斯科,乃至于俄罗斯的戏剧生活,必然是要从契诃夫说起。
说不尽的契诃夫
应该说,在俄罗斯的经典戏剧家中,契诃夫是最能够与现代人心灵相通的作家。在二十世纪的世界舞台上,他也是除莎士比亚之外剧作在全世界被上演次数最多的剧作家。所以,他也被认为是存在于俄罗斯的空间却又超越了俄罗斯时代的作家。
其实,舞台对契诃夫的接受也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契诃夫生于1860年,活跃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文坛。虽然,契诃夫在有生之年就被认为是天才的小说家,但他的戏剧创作意义,连同他对时代和社会问题的态度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不被同代人所理解。1896年10月,他的剧作《海鸥》在彼得堡皇家剧院上演,演出惨遭失败。这对契诃夫来说无疑是个重大的打击,他说:“剧院充斥着敌意,仇恨使空气都被烤热了,而我则按照物理学定律,像一颗炸弹,从彼得堡弹了出去。”这个失败并非没有征兆,小剧院的著名演员连斯基看到剧本后就给契诃夫泼了冷水:“您别再写戏了,这不是您的本行。”何以如此?首先,他违背了传统的奇数分幕法,而用了偶数,突出了戏剧的“日常性”和“生活化”,没有传统戏剧中那种具有转折性的“高潮”;第二,他的人物大多是平常的小知识分子,戏剧情节缺乏冲突;第三,他是第一个在俄罗斯戏剧舞台上用自然景色作为背景的戏剧家。而对音乐和停顿的运用,更是给戏剧带来了一种浓郁的象征意味。这一切,对于熟悉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果戈理戏剧的观众来说的确是难以接受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科创立的莫斯科艺术剧院,让契诃夫登上了世纪之交俄罗斯戏剧的顶峰。而戏剧中那只振翅高飞的海鸥形象,既是戏剧革新家契诃夫对艺术和生活理想的赞美,也标志着新世纪俄罗斯戏剧的到来。
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契诃夫的创作价值又遭到严重低估,当时只有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他的剧作。直至三十年代末,他仍被认为是“天生消极、敏感和意志薄弱”的人。这样的评价,大概是因为契诃夫在自己的生活和创作中始终与世纪之交的悲剧式激情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也没有将俄罗斯的美好未来与任何党派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而正是俄罗斯当时的绝境,成了契诃夫本人及其笔下那些本真美好人物悲剧的原因。而产生于时代夹缝和无处不在的苦闷,摆脱平庸和追求诗意生活的企图,后来一直都是契诃夫戏剧最能打动人心的地方。真正认识到契诃夫创作不同反响的价值,是在他去世半个世纪之后。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契诃夫是擅长采用多种多样的、往往能在不知不觉中起影响作用的写法的,在有些地方他是印象主义者,在另外一些地方他是象征主义者,需要时,他又是现实主义者,有时甚至差不多成为自然主义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这段话,可以说是从导演的角度看到了契诃夫戏剧作品的巨大诠释空间。我们的确可以在不同时代或不同导演的作品中找到佐证。
1975年,列宁共青团剧院首演了契诃夫的《伊万诺夫》。大家都不明白的是,导演马·扎哈罗夫为什么要将伊万诺夫塑造成一个以个人的力量与周围人战斗的人物。要知道,十九世纪时是没有人将契诃夫的伊万诺夫看作俄罗斯的哈姆雷特的。人们没有把他看做是独一无二的人物,更多的是将其看做寻常的、无足轻重的人。契诃夫也说过,他是“没有任何出色之处的”人。1904年,丹钦科在排演该剧时,弗·卡恰洛夫扮演的伊万诺夫就是一个与保守和灰色生活对立的人物。五十年代,鲍·斯米尔诺夫扮演的伊万诺夫也延续了这个传统。到了七十年代,扎哈罗夫终于向前一步,引来了争议。他不仅摒弃了过去对人物的诠释,而且也抛弃了已有的空间布景。他的舞台上出现了两个舞台,一个在前面,另一个大小与之相同,微微抬高,在后。两个平行的舞台空间完全独立,分别代表着伊万诺夫和列别杰夫的宅第。伊万诺夫从前台空间走到后台的空间,但始终没有走出他自己的内心。自然背景也完全被模糊掉了,树影看不见了,鸟鸣也听不见了。一首哀叹贵族生活衰落的忧伤之诗,被一部描绘外省闭塞生活的乏味小说所取代了。从导演手法上看,它是双重和重复的,即空间的重叠,重复的舞台提示,双重的舞台布景,其结局也是重叠的——重叠的自杀。也就是说,伊万诺夫的自杀完成了两次:一次是对那些不理解他的生活理想的人而言,一次对我们这些明白和原谅了他的人(起码导演希望如此)。在扎哈罗夫导演的《伊万诺夫》中,主人公完全摒弃了过去。而到了1976年,莫斯科艺术剧院在奥·叶弗列莫夫指导下排演了《伊万诺夫》,其中的伊万诺夫却完全沉浸在了过去。
同样,契诃夫的另一重要剧作《樱桃园》在不同时代和导演的处理之下也呈现了不同的面貌。1975年,塔甘卡剧院由亚·埃夫罗斯导演了该剧。他一反莫斯科艺术剧院处理该剧时怀旧和抒情的传统,不仅展示了人物的变化,也展现了生活中的混乱、破产,甚至崩溃。他的人物似乎不是在活着,而是挣扎在死前的丑陋抽搐中。同一时期,现代人剧院导演加·沃切克也将《樱桃园》搬上了舞台。从展现主题到手法上的艺术想象,她都采用了反常法。而以《海鸥》和《三姐妹》为蓝本进行多样化艺术探索的例子,在二十世纪的俄罗斯舞台上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海鸥》的著名版本有1980年莫斯科艺术剧院奥·叶弗列莫夫版和1990年现代人剧院版。而另一位当代著名导演托夫斯托诺戈夫在对契诃夫戏剧的现代阐释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在1965年的《三姐妹》中,行为的故意迟缓赋予了戏剧一种宽度,那么,在1982年的《万尼亚舅舅》中,戏剧行动的速度却大大加快。他处理的每一句对白,似乎都是面向公众的忏悔。他的人物也仿佛是在与我们交流自己内心的苦闷与挣扎,而不是他们之间的交流,他们似乎也知道,他们之间是无法相互帮助和相互拯救的。1990年,现代人剧院的《樱桃园》以新的舞台布景和在巴黎定制的服装,而呈现给观众一个新的舞台版本,成了莫斯科戏剧生活的一桩盛事。
似乎可以这么说,契诃夫的经典剧目在不断地培养和造就着一批批优秀的导演和演员。契诃夫的台词在他们的嘴里成了今天的语言,成了契诃夫直接面对我们表达的源于我们内心的苦闷与希望。我们不能将新版本的出现视为人们对传统与前人的漠视,而应该庆幸传统没有被人们当成复写纸和模板。它应该成为支点和跳板,使今人能够以新的方式阐释剧本,在与当今更为复杂的精神生活的碰撞中,复活契诃夫的诗意。
难以呈现的新经典
在俄罗斯当代戏剧史上,剧作家万比洛夫与阿尔布卓夫、罗佐夫一同被无可争议地列为当代经典。而他的命运最为奇特:他出生于1937年,卒于1972年,仅活了三十五岁,仅仅创作四部多幕剧,生前没有一部代表作在舞台上呈现,也没有引起剧坛的任何关注。如今,他的任何上演作品都会成为戏剧界的新闻和焦点。每个演出季,他的名字都会出现在海报上。人们无法理解,他的作品何以在六十年代四处碰壁,而从七十年代直至今日却又备享殊荣。为此,戏剧史上有了“万比洛夫之谜”的说法。
令人更为难解的是,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直至今天,要在舞台上呈现万比洛夫的戏剧作品都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可以说,没有一次排演是公认为成功的,这其中包括1979年由著名导演奥·叶甫列莫夫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导演的版本,甚至也包括1987年由导演维塔里·美尔科夫根据剧本改编的电影《九月的假日》。也就是说,要与万比洛夫的戏剧作品达到完全契合,是摆在导演和演员面前的一道“谜一样”的难题。

万比洛夫的戏剧呈现之难,首先在于它的体裁。与契诃夫一样,作者常把自己的作品称为“喜剧”或“悲喜剧”。但是,几乎没有人会把他的作品当成“纯粹的喜剧”来读或演。人们常把它们称作“严肃的喜剧”或“寓言故事”。像《外省轶事》这样的作品常被人们称为“寓言喜剧”。在《外省轶事》中,他将“严肃的”和“可笑的”、“天使”和“魔鬼”交织,巧妙转换,令人在悲喜中领略作者的深意。在几乎所有的剧本中,作者都以轻松喜剧甚至闹剧开始,然后又达到了最大限度的戏剧紧张,使导演在剧本面前不知所措。
万比洛夫的舞台呈现之难,也在于他笔下的人物。从本质上说,他的人物都是某种程度的“失败者”。由于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而又找不到解决冲突的办法,他们的内心世界常常失衡,精神上备受折磨。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既有的生活原则显得那么软弱无力。《六月的离别》中大学生科列索夫所面临的困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要么舍弃爱情,取得大学文凭,要么舍弃学业和前途,得到塔季扬娜的爱情。
从万比洛夫的作品中,我们还能感受到他对某一类人的偏好。这是一群中年人,他们对现在的生活不满,过早地厌倦了生活,从本性上讲,他们不失善良,而且对周遭的世界有相当敏锐的感受力。怀疑一切,对自我状态的关注,紧张的思考和精神探索,就是这类人物的共同特点。《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里的沙曼诺夫和《打野鸭》里的齐洛夫就属于这种类型。
多幕剧《打野鸭》被认为是万比洛夫最难理解的作品。其中之“难”,也在于对剧中人物齐洛夫的理解。作者对主人公齐洛夫有一个寥寥数语的介绍:他“三十岁左右,身材高大结实;在他的举止风度中无不透出他对自己身体状况的自信。但在他的行为言谈中却有着一种心不在焉和空虚,不过,这点并不是第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他经常挂在嘴上的话就是:“很清楚,生活从根本上完了。”从情节展开的父子亲情、爱情、友情和公德心这些方面看,他的道德水准几乎完全为零。妻子加琳娜一语道破他的“病症”所在——“你别装了……你早就对一切失去了兴趣。一切对你来说都没有差别,世上的一切。你已经没了心肝,这就是原因。心肝全无……”对于齐洛夫这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以及他的出路,批评界曾有很多猜测和争论。作者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齐洛夫是哭还是笑?作者的提示是“他哭过还是笑过——我们从他脸上无从判断”。
自齐洛夫这个形象诞生起,他就引起了戏剧界内外的关注和争议。在七十年代,这个形象远离了戏剧舞台上大多数单薄的、在语言和行动上“积极”的正面主人公形象。人们不能理解这个形象中那些消极因素何以受到作者态度暧昧的展示。这是一个转折时期的同时代人,由于对生活现状的不满,他希望能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使生活充满希望和活力。由于自身的懦弱和社会的纷纭复杂,他难于驾驭自己的行为,更难于按照自己的预想去改变社会。于是,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虚和失重。要么变得麻木冷漠,要么变得玩世不恭,这种自私与冷漠还常常给他人带来巨大的伤害。可以说,生活的主旋律对他来说只有一个,即幻想的彻底崩溃和由此而产生的灾难。应该说,作者万比洛夫对齐洛夫的态度是不明确的。这也是这部戏当时与众不同和引人关注的原因。在后来的讨论中,万比洛夫对齐洛夫的态度已不被人们看重。因为对作者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要告诉人们,生活中有什么问题等待我们思考,生活在困境中的人也值得我们同情。
与契诃夫一样,万比洛夫的戏剧作品也曾经被指责为“荒谬的”、“平淡的”、“太过日常化”和“缺乏戏剧冲突”的。而传统的风格和形式的简洁,使人们难以在文学剧本和舞台艺术的过渡中准确把握并传达出其作品的风格韵致。所以,尤其在六七十年代的戏剧舞台上屡屡发生误读甚至困惑的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从八十年代开始一直没有停止在舞台上呈现万比洛夫剧作的尝试。其中,《外省轶事》、《打野鸭》和《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是被排演次数最多的剧目。无论俄罗斯或者中国艺术家在主题上如何去阐释万比洛夫的戏剧作品,但仅就艺术表现技巧而言,他的剧作就是衡量导演和表演艺术的标杆,这大概也是艺术家们前赴后继知难而上的原因吧!
“语言的剧院”
在莫斯科,每个剧院都在追求各自的鲜明特色。除少数创办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剧院保留自己的传统剧目和艺术风格外,大多数剧院的规模和风格特点都是在苏联时期形成的。塔甘卡剧院就是苏联时期建立并有自己鲜明风格的剧院,它至今拥有国际一流的艺术水准和声望。在俄罗斯,它被人们誉为“语言的剧院”。
塔甘卡剧院位于莫斯科市土城路七十六号,成立于1964年,其前身是莫斯科正剧与戏剧院。它的创立者,是史楚金戏剧学校的教师尤·留比莫夫和他的学生们。他们以毕业作品、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庆祝了剧院的诞生。从1964年至1984年,留比莫夫任剧院总导演。
在苏联停滞时期,塔甘卡剧院曾经一度在国家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被称为“精神上的反对党”。它倡导自由思想,追随梅耶荷德、瓦赫坦戈夫和布莱希特的艺术传统,以文学经典为蓝本,改编排演了大量剧目,以在舞台上寻找文学语言的表现形式为特点,被称为“诗歌的剧院”、“小说的剧院”和“政论作品的剧院”,在先锋戏剧的探索上独树一帜。在这里,留比莫夫导演留下了一系列具有鲜明艺术特征的作品,它们都改编自国内外的经典文学作品,如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1965)、马雅可夫斯基的《请听》(1967)、叶赛宁的《布加乔夫》(1967)、莫里哀的《达尔杜弗》(1968)、莫扎耶夫的《生者》(1968)、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71)、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1971)、阿勃拉莫夫的《木马》(1974)、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1977)、《诗人维索茨基》(1981)、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1989)等。另外,亚·埃夫罗斯也在1975年客串导演了契诃夫的《樱桃园》,成为剧院的代表剧目。
塔甘卡的剧目大都以追求自由的个性和表达为主题,主人公拥有自己的声音和面孔,而盛行于社会的冷漠、自私和小市民习气,是目院抨击和嘲笑的对象。这些剧目以诗意和戏剧性的文学语言见长。《三姐妹》和《诗人维索茨基》具有突出的音乐性和优美的表现力,直抵生活的真实。在戏剧文本的基础上,剧院拓宽了艺术表现的疆域,丰富了表现手段,在抒情和诗意的主题下,探索道德心理冲突,具有鲜明的民主政治倾向。《大师与玛格丽特》保留了小说的主要情节,同时又补充了一条线索,即作者和他的小说也成了主人公。在讲述耶稣受难故事的同时,也展示了大师本身的悲剧性命运。而《鲍里斯·戈都诺夫》则体现着剧院在哲学道德问题探讨上的尝试。在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政权和人民的相互关系、社会的分化和理想的幻灭等等问题上,作品都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塔甘卡剧院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戏剧中加入了大量的文学因素,而好的小说与戏剧性氛围也是相得益彰的。饱满激昂的情感、诗意开放的节奏、富有感染力的对白、游戏的手法和非日常的情感表达,都使戏剧产生了与生活的诗意关系。在制作上,它不追求宏大和繁复,布景十分简洁。据说,这也继承了瓦赫坦戈夫的节俭风格,却与追求象征和倡导简洁的现代主义艺术有着某种相通之处。
1984年,由于与剧院的党务部门和文化部发生矛盾,留比莫夫离开剧院出国,一度失去国籍。埃夫罗斯被任命为总导演,剧院排演了阿列克西耶夫的《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1985)、高尔基的《底层》(1984)、契诃夫的《樱桃园》(1985)。埃夫罗斯去世后,杜边科在1987年至1989年担任总导演。1989年,留比莫夫受演员的联合邀请,担任总导演。他恢复了先前被禁的剧目,并排演了普希金的《小悲剧》(1989)、埃德曼的《自杀者》(1990)、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1993)。
1993年,剧院分为两个部分,即留比莫夫领导的塔甘卡剧院和杜边科领导的塔甘卡演员联盟。1994年,塔甘卡演员联盟上演了契诃夫的《海鸥》。留比莫夫领导的塔甘卡剧院在后来的几年中排演了不少新剧目,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卓夫兄弟》(1997)、索尔仁尼琴的《第一圈》(1998)和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2000)等。
塔甘卡剧院一直是当代俄罗斯剧坛上一面鲜明的旗帜。它以文学经典为基础,以自由开放的原则为艺术宗旨,在提升戏剧的文学性和干预社会生活方面,不断发出掷地有声的呐喊。让戏剧与文学有如此紧密的联姻,让戏剧拥有善于聆听的观众,这要在具有丰厚文学传统的国度才能实现,更需要有一批优秀的演员。由此看来,塔甘卡剧院在当时苏联的出现,应该是一个必然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