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间隔年”
邬颖茹 应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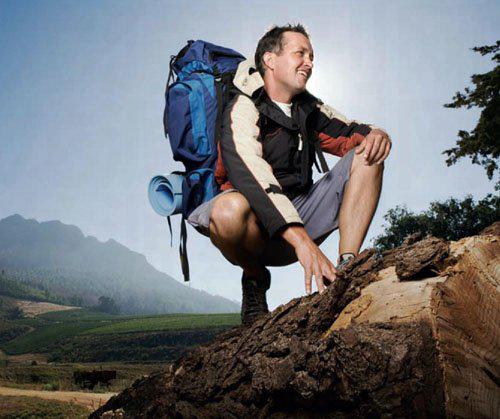
给人生一次“跳出来”的机会
连日来,一则消息在上班族之中引发了强烈震动。7月2日,年仅39岁的著名媒体人、凤凰网前总编辑吴征因心脏病突发离开了人世,白领阶层生命健康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通货膨胀的攀升、生活成本的增加、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得都市职场人背负的生存压力也层层加码。工作中追求更出色的业绩、更快的晋升、更高的薪水,宁愿选择承受持续高压力高强度的工作方式。
猝死、过劳死,这些名词早已不陌生。近年来,28岁的郑州电视台记者刘健、37岁的南宁电视台主持人徐谨都在风华正茂之际因心脏病突发早早地离开了人世。连续出现的几例“职场人过劳猝死”案例,再次为人们敲响警钟。
据2010年《中国城市白领健康白皮书》显示,有76%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白领“过劳”的情况接近六成,包括24小时待命、没有周末、在办公室“安家”等等。另据《2011职场人工作强度与压力调查》显示,到野外亲近大自然是职场人首选解压方式。
其实,在西方,很早就流行着一种名为“间隔年(Gap Year)”的说法,它是指改变你人生的一趟旅程。在年轻的时候,选择一次跨国长途旅行,旅行的同时观看世界,认识自我,明白自己到底需要什么。
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西方世界诞生了这样一批青年人,他们抵抗社会既有的各种制度和观念,用公社式的和流浪的生活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社会主流的不满。他们倡导和平非暴力,反对战争;他们提倡“爱”,寻求直接表达爱的方式的人际关系,主张性开放;他们追求自由,同时也依赖毒品。他们被当时的西方社会称为“颓废的一代”——嬉皮士。
到了80年代。一部分嬉皮士开始回归他们一度反抗唾弃的社会,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过起正常人的生活。从某些方面来说,这可能也是嬉皮文化向主流文化妥协的结果。
只是,不管嬉皮文化是多么地非主流,嬉皮士的流浪式生活,勾起了青年人对外面未知世界了解的渴望,成为了青年环球旅行的导火索。于是,就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的80年代, 当一批批的嬉皮士回归社会的时候,另一批欧洲青年背起背包又开始出行,在全球掀起了背包旅行热。甚至,西方的许多大学教育鼓励学生外出旅行,增长见识,拓展眼界。
“间隔年”就在那个时候诞生的,“间隔年”是西方国家的青年在升学或者毕业之后工作之前,做一次长期的旅行(通常是一年),让学生在步入社会之前体验社会的生活。在“间隔年”期间,学生在旅行的同时,通常也适当做一些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或者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工作。他们相信,这样更加有利于学生找到更好的工作,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工作,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
如今,还有一种“Career break”的说法,指的是已经有工作的人辞职进行间隔旅行,以调整身心或者利用这段时间去学习充电。
体验“间隔年”不是流浪,不是过放荡的生活。无论是学生的“gap”抑或工作一族的“gap”,都是为了从固定不变的生活模式中暂时跳出来,去另外一个环境体验新的生活,经历更多以更好地认识自己,这样才能更好地迎接未来。
就像《为什么要有间隔年》那篇文章所说:“人生的际遇就是这样,其实,只需要给一次‘跳出来的机会,或许就得到可支撑整个人生的幸福。”
不迟到的人生旅行
当了解到这个概念后,广州的的孙纯东计划了一次为期3个月的迷你“间隔年”。不料一些意外,使旅行成了辗转亚洲多个国家的远足,历经13个月。虽然他因此丢掉了工作,却找回了许多更为重要的东西,还遇到了日后的妻子。“间隔年”结束后,他用1年零8个月,将路上的点滴整理成文,出版了《迟到的间隔年》。
尽管整个行程中,孙纯东彻底摆脱“寂寞星球”的“束缚”,但第一次接触到“间隔年”这个概念,去仍是来自这本著名的私人旅游指南读物。“一个伊朗的朋友来中国时,带给我的一本寂寞星球的《间隔年》。看完后,觉得这个概念很酷,可以出来玩,同时又能做义工。虽然不包膳食和住宿,但义工听起来是一件很高尚的事情……”孙纯东说,他最初的间隔年动机“十分虚荣和卑微”。
当时,孙纯东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按他书中的记述:“每天对着电脑上班,时而出去开开小会办办事,工作强度不是很大,有一个很好的上司,领着自己可以接受的薪金。”平日的生活也算过得有滋有味,年度的单位旅游、各种各样的朋友,闲暇时还能继续的兴趣爱好……生活的“无可埋怨”,还是无法拴住孙东纯骨子里的不安分。不过让他感到欣慰,因为他的“出走”,并不是为了逃避,而是寻找,进而更好地面对原来的生活。
他开始为出行做准备,向印度的几家义工中心发去申请信,很快得到印度中南部一个艾滋病组织的回音。于是他计划花两个月的时间在印度做义工,花一个月到西藏旅行。“我把自己的决定告知身边的人。父亲很明确地告诉我,我的间隔年计划因目的性不强,注定会无功而返;我妈妈是洒脱性的中立,说只要我开心便去吧;家里只有姐姐站在我的一边。”身边的朋友听到他间隔年的计划,有的似懂非懂但表示赞成,有的保留意见一笑置之,有的则大骂他神经病。但对他来说,别人的意见已经不重要,“当时,我已经完完全全地沉浸在‘在路上的亢奋中。”让人没想到的是,孙纯东的上司竟然同意,给3个月的假期。
不料到了泰国之后,信用卡的问题让他多逗留了一个多星期。老挝与缅甸陆地无法过境,又让他绕行云南。到达印度时已经过去3个月。为了能完成“间隔年”,他选择辞掉工作,继续旅行,开始了他名副其实“迟到的间隔年”。
原本,孙东纯一直透过网络和大家分享自己的“间隔年”故事。没想到的是,2008年有出版社联系他,他便在自己网络博客的基础上,更加详细地增加了义工生活的部分,突出“间隔年”的主题。
书整理出版的过程,也成了一次回顾。“写到什么地方,心便飘到什么地方。比如写到印度被偷了相机和钱,和当地警察周旋时的那几天,心情总是特别地沉重压抑。”同时他也会想起来那些路上的朋友们。“他们有些现在还一直在旅行,有些回来后又出去,有些和我一样现在过着‘普通的生活。”书中的彻平最近到了欧洲;有过误会的栗林毅,前阵子才邀他去爬富士山;“野人”在新加坡工作了一段时间,最近去了尼泊尔、印度学冥想;庆惠回到东京开始学习包装手艺,最近去了巴厘岛……孙东纯说,由于书以“间隔年”为主题,那些与主题不太相关的故事就被删减了,“起初我以西藏为终点,最后去了尼泊尔,所以那里的经历便省略了。其实也发生了很多事情,丢了护照、遇到没有钱便环游世界的韩国朋友等等。”
回到广州以后,孙东纯开始并不适应“正常生活”,甚至会感到沮丧。“我在书中也写到,这中现象叫‘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间隔年的路上,从一种文化转移到另外一种文化,一次次尝试放下自己的文化习惯、思维逻辑以及价值观念,去适应身处的文化氛围当中,经历着从新鲜亢奋到文化冲击,又从矛盾抵制到文化适应的过程。当我们回到自己原本生活的地方,面对原来的文化环境,也变得需要时间去适应。在外的时间越长,这种不适应的感觉可能也越强。”
对于如何调整这种心态,孙东纯显得颇有心得:“第一,要肯定自己间隔年的正面意义,不要因为这种不适而觉得自己浪费了时间;第二,要知道,一次间隔年并不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旅行家,最重要的是从间隔年得到的‘心的东西而不是知识;第三,社会是现实的,旅行却十分感性,似乎两者水火不容,但我们如果可以尝试用远足的心来生活,这样的生活可能更细腻、丰富,而且容易让人感恩。”
如今,孙纯东已经随他的日本妻子沙弥香到静冈定居。沙弥香是他在间隔年中遇到的女孩,两人在途中产生感情。但由于沙弥香早已签约,将在当地一家国际红十字会属下的医院服务,合约期为4年。想要在一起,孙东纯就必须去日本生活。最终他选择追寻幸福的脚步。
对于旅行,他仍有很多计划。“人的一生,要想有两次间隔年不大可能,而且一个人经历了长途旅行,可能短期旅行就变得不怎么吸引人。间隔年回来后,旅行依然是我的兴趣,但不是生活必需的“调味料”。“现在他最期待的,是计划一次和妻子以及双方父母亲一起的旅行。“我和妻子是在路上认识的,也希望可以让爸爸妈妈分享我们的旅行感觉。”
说到间隔年对自己的影响,孙纯东回答:人活着为了什么,我已经找到了答案。
“间隔年”的旅行无所谓迟到,一只背包+轻松的心态,每个人都该拥有自己的“间隔年”。“间隔年”这个并不新鲜的旅行概念,也为更多的中国青年所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