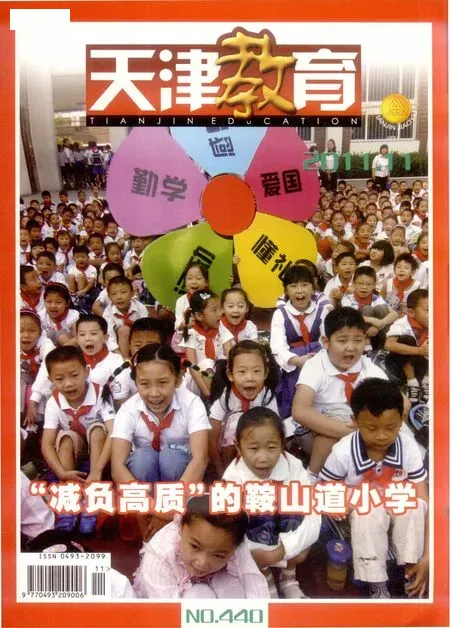教会悟:有思想地生存
■天津市实验中学 安杨华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有一句名言:人是一枝有思想的芦苇。意思是说,人的生命像芦苇一样脆弱,宇宙间任何东西都能置人于死地。可是即使如此,人依然比宇宙间任何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人是能够思想的。如果没有思想,那么人就与其他生物一样,不能有诗意地生存。每个人首先成为一个精神的人,他的人生才会多彩。教育最重要的是促进人的发展,而发展的核心是精神的成长。为学生奠定“精神的底子”、“生命的底色”,引导学生砥砺自我人生修养,这是语文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引导学生通过阅读和鉴赏优秀的文学作品,对促进学生精神成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法国文学家左拉说:“在读者面前的不是一张印着黑字的白纸,而是一个人,一个读者可以听到他的头脑和心灵在字里行间跳跃着的人。”学生只有不断地与品位高雅、品质高尚、具有生命智慧的人对话,从直观、感性、情感层面,逐步进入到理性的和审美的境界,他们的精神品质才会健康成长,心灵世界才会不断丰富,而这些正是学生面对纷繁芜杂的现实世界所必需的。“新课标”关于阅读与鉴赏目标中提出“受到高尚情操与趣味的熏陶,发展个性,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在阅读与鉴赏活动中,不断充实精神生活,完善自我人格,提升人生境界。”这正是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角度,以“立人”为根本目的来提出的阅读鉴赏目标,希望学生在阅读中点亮自己人生航程的心灵之灯。

当前,中学语文阅读教学普遍存在这样两种教学模式是不能实现上述教育理想的:一种是教师只是使学生被动把握作者自身的写作意图和情感态度;另一种是教师只是使学生接受教学参考资料对作品的解读。在前一种阅读教学模式中,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作者说了什么,而不是主动地领悟文本蕴含着什么,学生只会被培养成一群没有精神的、没有思想的“两脚书橱”而已。在后一种阅读教学模式中,学生只能接受统一的、标准化的、他人的解读,而没有个性化、创造性的、自己的解读,学生只不过被培养成是一批标准的“传声筒”罢了。这样两种阅读教学模式同样都是“说明型”教学而非“探究型”、“创造型”教学,学生不过就是知道文本、教参和教师写了什么和说了什么,正如著名哲学家康德所批评的:“他所知道和判断的,只不过是被给予他的那么多。……他正确地领会、保持了,也就是说学会了,却是一个活人的石膏模子。”这种教学思维的陋点是只关注“被”文本或他人“给予”的那么多,对文本被动的“读”运用的是一种“石膏模子”思维。这种“说明型”语文教学无法培养学生独立深入思考的良好的思维品质。因为,这种教学产生的原因在于教师对作者、专家、教参等的迷信,教师不能对文本进行有创意的解读,不过是一位跪着的读者或者人云亦云的听众而已。要知道跪着教书的老师,是无法培养出站着读书的学生的。“说明型”语文教学,注重的是被动的“我知”而不是主动的“我悟”。
阅读教学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没有创造意识的读者,就不能主动地“我悟”。要知道阅读毕竟不同于作者的精神创造,伽达默尔也不得不承认“所有的理解性的阅读始终是一种再创造和解释”。当然,这种创造解读不是主观臆造妄加揣测式的无中见有,而是立足文本,深挖潜藏在文本中可能有的、利于人精神成长的意义。例如解读《老王》一文,许多教师引导学生分析老王和“我”在苦难中所展现的善良,这种教学就是前文所分析的“说明性教学”,学生只是认识两个善良的人而已。而如果注意到文本最后一句话“这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的人的愧怍”,进而追问“‘文革’中作者杨绛一家也经历了种种人生不幸,可她为什么还说自己是‘幸运的人’呢?”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作者叙述老王的苦难很详细,而提到自己的苦难则是一笔带过,如“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而且是运用平淡的语言、平和的语气叙述,表现内心对苦难的淡然与释然。德国思想家狄尔泰说:“我所理解的生命表现不仅是那些意指或意味着某种东西的表达,而且还包括无意表达精神的然而却是这精神的东西为我们所理解的一切东西。”而《老王》中“无意表达”的“精神的东西”则应该是杨绛的幸福观:总有过、总有、总会有比我更不幸的人,不是最不幸的就是幸运的,所以我永远是幸运的、幸福的。这种幸福观在大时代对小人物的挤压中为杨绛支起心灵的庇护所。树立这种幸福观对学生的一生都是有益的。也许有人说作者主观上的创作意图并非要告诉读者这一点,但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幸福观是文本客观上“所能有的”。利科尔指出“理解一段文本不是去发现包含在文本中的呆滞的意义,而是去揭示由该文本所指示的存在的可能性。”这种阅读重在领悟文本“所能有的”、对自身精神成长有益的东西,重在从文本中“我悟”,而不满足于“我知”,这样的阅读才是创造性的阅读。
当然,教师帮助学生认识文本中所蕴含的思想,并不是把自己的体会、参悟直接告诉学生,如果那样的话,那还是让“我知”。所以,教师要教他们掌握产生这些思想的思维,教师要把自己解读文本时的思维过程坦诚地摊在学生面前,与学生做思维上的互动。特别是教学生学会概括文本思想,这个概括过程,就是一个悟的过程。以解读《囚绿记》为例,我们要在一个抽象、概括的过程中,把具体的感性的元素“蒸发”掉,然后“提炼”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来。
《囚绿记》大意是:文本中的“我”很喜欢窗外的绿藤,于是将它从窗的破玻璃洞中牵引入室内,让绿藤装饰“我”的生活。绿藤在室内变得瘦削、枯黄,尽管如此,但每天它的尖端总是朝向门窗外的太阳,尽管“我”把它调转方向,第二天它却依然如故。怎样教会学生参悟这个“囚绿”现象呢?我们要这样实打实地把参悟的思想轨迹展示给学生。让学生明白从“文本”到“思想”是怎样产生的。
抽象的过程就是要先将整个事件的组成元素分解开来,然后将这些具体元素分别扩大、延伸,将其归结到这些具体元素所属的“属概念”上去。比如,我们可以把文中的喜爱“绿藤”的“我”扩大而为喜爱“某种东西”的“人”,这里“绿藤”、“我”这些事件的具体元素是下位的“种概念”,“某种东西”、“人”则是上位的“属概念”。那么“我”为了让绿藤进一步“和我接近,更亲密”,而不顾绿藤的生活习性的将它强引进屋,这一具体事件就可以扩大而为:“人”因自己喜爱“某种东西”而不顾其需求和意愿将其据为己有。这种不顾绿藤的生活习性的所谓“爱”其实已经异化而为“私欲”,而将它强引进屋的行为则可以扩大、延伸为“占有”。而这样做的结果怎样了呢?文本中说“失去了青苍的颜色”,“枝条变成细瘦”。而这种“病”了“弱”了的状态,可以扩大、延伸一种上位的状态“被伤害”。
概括过程就是对这些被分解的元素的上位“属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综合,从而对事件的意义进行提炼,思索这具体事件所昭示的道理。那么把上段分类抽象的思维过程进一步综合整理,我们可得出这样的认识:当一个人的爱异化而为自私的占有时,他给被爱者带来的只能是伤害。这就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了。它是从一个爱绿藤的“我”,为了让绿藤亲近自己把它牵进小屋而使之憔悴这一具体事件中抽象概括出来的思想。
我们还可以从绿藤的角度去分析怎样抽象和概括:“绿藤”可以被扩大为“植物”,再进一步向外延伸抽象成为一个“生命体”。“绿藤”被人牵进小屋,则可以抽象为一个生命体被一种外力“压抑”“扼杀”。“它的尖端总朝着窗外的方向。甚至于一枝细叶,一茎卷须,都朝着原来的方向。”这种一般植物所具有的“向阳性”,可以抽象为“生存本性”。于是,这一思维过程便可概括出一种生命生存的哲理——当一个顽强的生命体被不可抗拒的外力压抑、扼杀时,外力只能控扼它的躯体,但绝不能屈服它按照自己生存本性去生存的本性。
抽象、概括过程就是一个把感性的、具体的事件或事物上升为一个理性的、抽象的道理的思维过程,是一个从文本中生出思想的“悟”的过程。阅读教学就是要培养学生这样的认识能力和概括能力。正如美国艺术理论家阿恩海姆所说:“一种真正的精神文明,其聪明和智慧就应该表现在能不断地从各种具体的事件中发掘出它们的象征意义和不断地从特殊之中感受到一般的能力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赋予日常生活事件和普通事物以尊严和意义。”
阅读教学就要这样——教会学生从文本的具体的个体性的事物或事件中“悟”出其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就是要教会学生学会思想,从而使学生收获一个精神充盈的人生,让学生诗意地生存。这是语文课和语文教师的责任。★
——评《当代中国青年幸福观及其培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