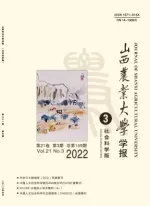论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及对策
白俊琴,王锦慧,原俊平
(1.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山西太谷030801;2.山西省代县中学校,山西代县034200)
土地流转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产物。经过30年的改革和发展,现行的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国民经济发展不适应已初露端倪,它无法解决分散经营的小农生产与现代农业集约化要求的矛盾,无法满足有限耕地资源与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矛盾。加之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建设用地、生态用地的扩张与农业用地之间的矛盾变得日益尖锐。而在农业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耕地弃耕、撂荒的现象大量存在,严重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因此,面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潜能逐渐消散与农地资源短缺的刚性约束和保持农业与不断增长的人口的生产生活水平相适应的双重压力,[1]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基本制度必须进行深化改革,激活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提高农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实行农地的规模经营,加快现代农业的发展步伐,改变农村发展缓慢的局面。
一、农村土地流转的现实基础
(一)大量剩余土地出现
“粮价上涨”!“弃耕抛荒”!这两个本来十分矛盾的词,时下竟然连在了一起。[2]国际国内粮食和农副产品价格不断上涨,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农村弃耕、撂荒土地却大量出现,尤其是在南方一些省市,整座山丘荒芜、闲置和撂荒的土地比比皆是。究其原因,粮价上涨抵不上化肥、农药等农资产品价格的上涨,小规模种田的比较效益低下,土地被视为“鸡肋”而荒废,农业和土地对多数农民已经失去吸引力,青壮年劳动力纷纷涌进城市和工厂,农村呈现全面“空心化”。
(二)国家相关法律政策支持
农村土地流转一直被看作是解决 “三农问题”的钥匙,为此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推动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相关法律制度,为土地流转扫清道路。在立法上,国家颁布 《农村土地承包法》和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从法律上赋予了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提供了法律规范。其后2007年出台的 《物权法》,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 “用益物权”编,给予了其比 《农村土地承包法》更充分有效的物权化保护,有效促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自由流转。在政策上,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3]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中又进一步强调了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重要性,要求在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尊重农民的土地流转主体地位的基础上促进土地承包权流转。这些都为农村土地承包权的合理有序流转,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
尽管有上述的物质和制度保障,我国总体土地流转市场发展仍然相对滞缓,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流转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制度、实施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改革和完善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农业产业化规模经营、农业现代化目标的必然要求。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不彻底
《物权法》出台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物权属性已是不争事实。《物权法》明确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规定为用益物权,给予其物权化保护。[4]但是,从我国目前的立法规定和农村实践来看,都存在未将其彻底物权化的问题。浓厚的债权色彩,成为农村土地流转的障碍和农民权利无法切实保障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债权表现在:第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基于合同产生,合同内容不是由法律明确规定,而是由承包方与发包方通过自由意思加以确定,悖于物权法定原则。第二,承包人对土地没有独立支配权。依据相关法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须经发包人同意,这一规定致承包人对土地承包权无完全支配力。而在法理上,物权的转让应由物权人自行决定,只有债务的转让才需经债权人同意。第三,我国现行法律对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是予以禁止的,严重阻碍了物权人自由流转土地的权利,使农民失去了最有利的融资手段。
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债权属性直接限制了现实中农地流转:一是承包人受制于发包人,不能按照市场方式自由流转,其行使权利经常受到行政部门公权力的干扰。二是流转期限将受到承包期限的限制,依据现行法律,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剩余期限,而农业是一种典型的投入大、生产周期长、见效慢的传统行业,期限限制将直接影响投资者投资现代农业的热情。
(二)土地流转市场机制不健全,流转操作流程不规范
国家鼓励和扶持土地流转的目的,就是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实现现代农业发展。然而,由于统一的土地流转市场仍然没有建立,目前,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流转都发生在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农户 (邻里和亲戚)之间,处于自发阶段,远没有达到农业规模化程度。在实务的流转操作中,流转合同多无书面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益和义务也不够明确,缺乏对违约责任的明确约定,最终难以通过有效的流转实现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5]并且,在流转价格机制上,由于缺乏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又无可参照的历史价格,定价随意性很大,农户在交易中容易受到组织结构或经济地位上居于优势者的侵害。土地有偿流转的特性与市场价格缺失之间的矛盾,阻碍了农地流转的顺利进行。
(三)流转过程中政府干预不当
尽管承包权人作为用益物权人可以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然而现行的法律规定:“当事人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为政府干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留下了一个合理的法律借口。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政府角色分寸拿捏成为尤为重要的问题。总的来说,政府部门主要是做好服务、引导和规范工作,不应成为土地流转的主导者。而现实中政府侵害农民权益的现象却时有发生。出于对GDP和官员个人利益 (如升迁)的追求,有些乡镇村级领导不顾农户意愿,滥用行政权力将土地承包或直接卖给投资商,从中谋取收益,侵占人民利益;有些基层政府将土地流转与政绩挂钩,形成所谓的 “万亩规划”、“千亩大棚”,政府强制在大片土地上种植同一种农作物,以显壮观,树形象工程。这种豪华的运动造成惊人的土地浪费。[6]
(四)农地流转的社会化服务缺位
主要表现在政府管理机构缺失和中介组织缺乏两个方面。一方面,虽然我国在县级有国土局,乡镇有国土站,但它们只是负责国土的规划、耕地的保护、用地的审批,而没有对农地流转交易的监督和管理权限,监督功能的弱化致使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十分混乱,集体土地资产流失及管理失控,权利变动信息不公开,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的利益经常受侵蚀,农地流转纠纷时有发生,阻碍了交易组织的进一步发育。另一方面,农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交易与其他商品相比运作程序相对复杂,涉及到多个主体的经济利益,再加上我国农民本身文化程度普遍较低,获取信息途径少,无法通晓如此复杂的转让程序,这就要求有完善的中介服务机构为之服务 (如资产评估机构、委托代理机构、土地投资机构、土地融资机构和土地保险机构等)。建立健全的中介服务机构能够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理流转。
(五)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不够健全
农地流转的效率低下,与农地资源仍承担着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有关。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未能覆盖所有的农村地区,农户仍流离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土地成为农民生存的主要且最后的保障。因此,当土地流转的费用(租金)低于农户的预期时,他们就有可能放弃土地流转的计划。[7]即使已经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也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一方面进城务工,另一方面保留土地甚至不惜抛荒。结果,在我国这个农地资源十分紧缺的国家,就形成了农村农地的闲置和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存的现象,农民对土地流转的热情度不高。因此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如何充分发挥土地补偿和安置费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农民享有土地收益的主要部分,为农民提供长期的生活保障将成为重中之重。
(六)农地流转后非农化现象严重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市土地已经非常有限,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眼光开始瞄向农村土地,郊区农村的土地更是他们感兴趣的。虽然根据现行制度,农地在流转规程中严格限于农业用途,但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有的是变通办法,如采用 “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态农业示范园”、“现代农业示范园”、“农业科技博览园”、“农业专家大院”等模式,看上去都是农业项目而且很前卫,但实际上主要还是餐饮、娱乐、旅游甚至是房地产项目。[8]尤其是房地产开发商绞尽脑汁拿地,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租代征,打土地政策的擦边球,大量的小产权房由此产生。为追求高额的经济利益,投资商借农地流转之名,随意改变土地用途的现象普遍存在。农地被变更为非农地后,由于重新变更回农地的成本高昂,因此很难逆转。这种农地非农化导致的是耕地的绝对意义上的减少,更加加剧了我国耕地资源危机。
三、农地流转的改进方式
(一)进一步建立健全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体系
为保证农村土地流转的有序性,建议对现行的法律 《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担保法》等进行修改,重新界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涵,明晰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农地承包经营权的产权划分,弱化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强化农地承包经营权,增加承包权人的处分权能,使农户在更加充分的物权化保护下独立自主地进行土地流转;另外,对限制土地流转的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删除 (如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抵押条款),使农户可以多重渠道地进行土地流转。最后,鉴于土地流转将涉及到多层面的法律关系,建议尽快制定 《农村土地流转法》,对农地流转交易做出明确系统化的规定。
(二)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规范土地流转程序
建立健全规范的农地流转市场体系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土地交易场所,为农户进行土地流转提供平台;第二,建立科学的农地价格评估体系,科学地评估土地价格,保护农户出让土地的利益,为土地流转提供依据;第三,建立专门的土地流转管理机构,为土地流转提供政策扶持和监管服务工作;第四,建立完备的市场配套服务设施,发展为土地流转提供服务的各种中介组织。[9]在土地流转程序中,要积极引导土地流转的双方当事人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签订书面协议,要规范和完善农地流转合同的格式和内容,明确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使流转交易有序进行,减少农地流转纠纷发生。
(三)规范政府行为
政府要正确认识在土地流转中的角色定位,明确土地流转主体为农户自己,在职能上不越位,逐步从土地交易中退出,不介入具体的流转活动,不以任何方式强行流转土地,侵犯承包人权利,要成为农户权利的维护者、监管者、仲裁者和公共服务提供者。[10]另一方面,政府在职能上也不能缺位,要做好土地流转的宣传和辅导工作,使农户了解土地流转的好处与意义,提高农户的流转意识和参与度;在具体的流转过程中,不能成为任何一方的代言人,引导土地流转有序进行,鼓励探索多种方式的土地流转,但同时要防止过度流转、无序流转等损害农民利益的问题。最后,要加强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制建设,引导农民依法流转土地,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帮助农户评估土地流转风险,让土地既能流转出去又能退得回来。
(四)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相配合,建立覆盖全部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体制。多渠道、多层次、多方式地兴办养老、医疗、生育、伤残等社会保险,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对于外出打工的农民,国家要制定统一的、非歧视性的劳动就业制度,把农民工纳入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农地流转后的困难农户,应根据物价水平的变动,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浮动的、可调节的最低生活保障金。[11]同时,地方政府应根据自己当地的实际情况,在基本解决农民基本社会保障的地区,加快推动土地流转的步伐;对那些社会保障还没有覆盖的地区,探索 “土地换社保”的具体方法,彻底解除农户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
(五)加强土地流转后的管理
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应加强土地流转后的检查监督和事后管理,保证土地流转合同中权利义务的顺利履行,杜绝受让方打政策法律的擦边球,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各种土地违法经营、利用行为,对违规利用土地行为要出台相关惩治办法;保护我国的耕地资源,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使土地流转真正实现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的经营。
[1]马亮.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J].科技信息,2010(1):20-21.
[2]梁有华.国内外粮价上涨部分农民为何还弃耕抛荒?[N].南方日报,2008-07-02(3).
[3]吴雨才,叶依广.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 [J].农村经济,2005(8):21-23.
[4]丁关良.《物权法》中 “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评析 [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79-83.
[5]黄祖辉,王朋.农村土地流转:现状,问题及对策——兼论土地流转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影响 [J].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8(2):38-47.
[6]齐宜光.农村土地流转:困境及对策分析[J].沈阳大学学报,2009,21(6):119-122.
[7]张玲,姜潓.从社会保障角度透视我国农地流转 [J].中国经贸导刊,2010(16):91.
[8]刘成玉,杨琦.对农村土地流转几个理论问题的认识 [J].农业经济问题,2010(10):48-52.
[9]宋朝晖.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J].农村经济,2009(9):104-106.
[10]王珍,林鸿,何格.农地流转:失范与治理[J].特区经济,2011(2):174-175.
[11]胡斌.浅论我国农地流转制度的问题及对策[J].经营管理者,2011(3):289-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