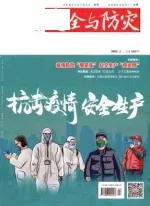我的矿山生活
文/肖功勋
岁月长河般流过,一些记忆是缥缈的,一些记忆又是深刻的。
矿山。我必须重复这两个字,我必须严谨地对待这两个字。因为它在我生命中承受着太多的分量,我所有的发展和转折都在这里发生。
1991年,矿山以博大的胸怀,像迎接归来的游子,迎接我的到来。从那一刻起,我就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拥有了自己的矿灯,自己的换衣箱和工具箱。我开始承担起我必须承担的那份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矿山也就成了我工作、生活的故乡,成为我人生的驿站。
工友们来自全省各地,我们成了亲密的兄弟,住进统一宿舍,在一个食堂吃饭,穿相同颜色的工作服、长统靴。
我们工作在地下300米深处的幽幽矿井。初次下井,心里很有些紧张,最担心有瓦斯爆炸。灾难面前,纤细又脆弱的生命实在不堪一击,平日里听到看到人类与大自然顽强斗争的种种成绩很是感叹,可在300米煤海深处,人与自然之间谈得上对峙么?顶多也只是个相互容忍退让的适应。井口负责安全检身的矿工托着我肩膀检查时眼神充满了阳光,鼓励赞赏兼而有之,我想朝他咧嘴笑笑,终究没能笑出来。
矿井的交通工具——猴车,每隔3米一个座位,由一个简单的平铁片,两个脚蹬,一根柱子组成,跟旅游区的吊索没什么两样,只更简陋些罢了。随着猴车缓缓把人送往矿井深处,灯光昏暗,空气也仿佛变得肃穆而静谧,只有巷道壁上水滴溅落的声音此起彼伏,一种莫名恐惧渐渐弥漫开来。
井下的巷道四通八达,像一座地下迷宫。四周很静,水从壁上滴下的嘀嗒声依然存在。经过的有些地方水深及膝。微弱的矿灯映在水上,无底洞似的,每走一步都那么不踏实。置身这黑色的地下迷宫,我忍不住咬紧牙齿打了一个寒噤。
在深深井巷,被誉为矿工“眼睛”的矿灯显然很重要,但晃来晃去也只能照到面前巴掌大的地方,微光在又长又深的巷道里是那么虚弱、那么单薄。我在这神秘的、神圣的黑色里,就像探险者不经意间闯入一片禁地,无知而好奇。无论面向何方,除了黑,还是黑。衣服是黑的,道路是黑的,人脸是黑的,呼吸是黑的,就连空气也是黑的。
刚下井时,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傻大胆。有一次正在工作面铲煤,一位老矿工突然让我赶快撤退,说顶板马上要塌方。我有点不相信,可没等我撤出几步远,忽听一声巨响,塌下一块足有10多吨大的矸石,盖在了我刚才站着的地方。我被惊出一身冷汗。从这一事件中,我才懂得了要想做一名矿工原来也有很多学问。我开始向老矿工虚心学习,很快掌握了敲帮问顶、凿岩爆破等井下作业技能,逐渐使自己成了一名合格的矿工。
我的工作任务是采煤。不透风的密闭的空间里,机器的鸣响在煤壁间疯狂奔跑,对垒着煤惯常有的沉默不语,瞬间却又被激烈地反弹回来,循环往复地刺激人的耳膜,考验着人的忍受极限。什么叫震耳欲聋?什么是几近窒息?噪音究竟有多少分贝无法感知,但敏感的神经却分明到了极限。不得不提的是,这样的工作环境,矿工的交流基本靠吼或者比划手势来进行。在所能抵达的地心的最深处,在盘根错节曲折回环纵横分布的煤巷,人行的最低处不过一米。我们只得低头弯腰小心翼翼地游走,像一群深海中的鱼,虽然极力躲避可能的伤害,仍然能时时感受到安全帽与头顶硬物交手过招时不间断的撞击。
我们就在巷道中布置的工作面打眼、放炮、架棚、攉煤。我把自己融入煤矿,忘我工作。“五大自然灾害”是我们的天敌,我们必须时刻提高警惕。
工作面的硝烟和着煤味,十分刺鼻。开采的煤层只有0.4米厚,我们只好匍匐着在地上作业,直到现在,我的手腕手肘上仍刺满了永远洗不褪色的煤碴。
工作在这种环境中,我们依然开怀大笑,挥汗如雨,操岩斧、握风钻、推小木车,一起把煤炭从工作面输送到天眼,通过矿车提升到地面。每次出井,黝黑的面庞和汗水浸透的工装在我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的眼睛在黝黑的脸上显得十分明亮而深邃,而当我们微笑时,牙齿无一例外地显得白灿灿的,亮得有些刺目。
那四年,我完全沉浸在劳动的快乐中,没有任何杂念,感受着地层深处挖煤艰、辛、险、苦的同时,也真正体味到了煤矿生活的酸、甜、苦、辣,还经常把盐霜与煤味掺杂浸染的工装欣赏一番,那种心灵的满足和超然,还原了劳动的内涵。
感谢矿山。无论是当时还是今天抑或将来,我很高兴自己曾经有过那段在300米井下工作的日子。如果没有与深深矿井的亲密接触,如果没有那段煤尘搅着汗水的日子,我40多年的时间将会是枯燥的。矿井中的四年时间如煤,开掘着,燃烧着,在我的心中铺垫了一层又一层,让我感到时间与生命一样厚重和沉稳。
矿山往事如潮,苦与乐,得与失,如春潮在心海起伏。我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已不在矿山,但我始终觉得我还是一名矿工,是走在城市的一名矿工。在钢筋与水泥之间呼吸的我,仍散发着一种来自大地深处的“煤味”。我写这些文字,不仅仅是在怀念矿山,而是在感恩——矿山赐予我的那与生俱来的生命本色和做人方式。
——山西焦煤西山煤电斜沟矿矿灯房女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