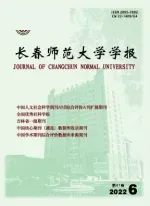略论《文选》中的汉代音乐赋
邸宏香
(长春师范学院《昭明文选》研究所,吉林长春 130032)
萧统将赋置于《文选》之首,可见他对赋极为重视。他将赋分为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等十五类。本文主要探讨《文选》中所收的汉代音乐类三赋,即王褒的《洞箫赋》、马融的《长笛赋》、傅毅的《舞赋》,进而揭示音乐对人的教化作用。
自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也就随之确立下来。由于音乐美妙动人,老少咸宜,可以给人以美的享受和熏陶,它的教化作用历来被统治阶级和儒学家们所重视。萧统将舞蹈也列入音乐类目之下,显然是受到我国传统诗、乐、舞三位一体思想的影响。《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可见诗乐舞都是因情感表达的需要而产生的,且互生互补,达到对情感表达的最高境界。
一、音乐本身之美的感化作用
音乐作为人类的高级精神活动和情感活动,其美感在于通过节奏和韵律的变化来表现大千世界。古人认为“音乐和宇宙自然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代表和体现某种宇宙法则和精神。因此,赋予原初音乐以某种高洁、神秘、陌生特征。”[1]这与自汉武帝以来董仲舒所宣扬的“天人合一”观点相一致。
音乐本身的美,首先在于“器”的美。《洞箫赋》取材时,描写制作箫的竹子生长在“江南之丘墟”,本身“洞条畅而罕节兮,标敷纷以扶疏”,生长过程又“吸至精之滋熙兮,禀苍色之润坚。感阴阳之变化兮,附性命乎皇天。”又有“孤雌寡鹤”、“春禽”、“秋蜩”、“玄猿”之类在它身边围绕,“处幽闭”的特性使它“清净”的特性浑然天成,再加上能工巧匠的装饰,更抬高了洞箫的价值。因而,箫在王褒的笔下变得清新天然,达到了“趣从容其勿述兮,骛合沓以诡谲”的境界。《长笛赋》也对制作长笛的竹子有所介绍,但与箫略有不同。用来制作长笛的竹子生长在“九成之孤岑兮,临万仞之石”的环境之下,生长过程中以“秋潦”、“冬雪”、“回飙”、“重增石,简积”为滋养,而又因“间介无蹊,人迹罕到”,只有“猿”、“鼯鼠”、“寒熊”、“特”、“山鸡”、“雉”之类的生禽与之一起生长。放臣、逐子、弃妻、离友通过长笛在马融的笔下找到了共鸣。通过乐工取材的艰险来突出竹子的难得,“于是乃使鲁班、宋翟,构云梯,蹉纤根,跋篾缕,膺,腹陉阻。逮乎其上,匍匐伐取。”更从侧面烘托了竹子的坚毅。天时地利造就了箫与笛之间的不同——多情与孤傲。
其次,音乐本身的美还在于表演者的素养。《洞箫赋》中,箫的演奏者是一个盲人乐师,由于他“生不睹天地之体势,于白黑之貌形”,所以他在心中的郁结之气也最为自然,箫声所奏出的内容也尽力在模仿山川自然的景色:“浑沌而潺兮,猎若枚折;或漫衍而络绎兮,沛焉竞溢。栗密率,掩以绝灭,晔,跳然复出。”马融《长笛赋》中,演奏者都是专门请来的乐师:“重丘宋灌,名师郭张。工人巧士,肄业修声。”他们名声在外还勤加练习,于是不论游闲公子还是豫暇王孙,都“相与集乎其庭,详观夫曲胤之繁会丛杂”。《舞赋》对舞蹈者更是作了详尽的描写:“于是郑女出进,二八徐侍。姣服极丽,偷致态。貌妙以妖蛊兮,红颜晔其扬华。眉连娟以增绕兮,目流睇而横波。珠翠的砾而照耀兮,华飞而杂纤罗。顾形影,自整装。顺微风,挥若芳。动朱唇,纡清阳。亢音高歌,为乐之方。”对舞女的数量、体态、面貌皆作了详细的介绍,以说明舞蹈带给人们的视觉美感享受不仅仅是源于舞蹈的技巧,更源于舞蹈者个人的素养。
再次,音乐本身的美着重体现在内容上。不论《洞箫赋》还是《长笛赋》,皆是对自然界风光的描写。《洞箫赋》形象地表现了河川的奔腾逶迤,后用各种形象的人和事物来表现其气势,更显恣肆蜿蜒。而《长笛赋》中,各种自然界可喜的事物都囊括在笛音之中,令人如临其境。《舞赋》则更是通过对舞蹈的感受启发人们对于自身的释怀,通过对音乐之美的感受,表现对人精神上的解放。
音乐本身重视美的感受,这一点类似儒家选贤纳士的标准。“在汉代,儒家学者继承了这种思想。乐器赋如此描写,正同儒家传统思想和时代精神相契合,是儒家文化思想折射的结果”[2]。于是,音乐便有了感化功能和教化作用。
二、音乐内在义理的教化作用
首先,音乐具有教化作用。《梁书》中《议东宫礼绝傍亲令》载一事:萧统针对刘孝绰等人主张用张镜《乐宫仪记》的意见,始兴王薨一个月内不能音乐,他提出“张岂不知举乐为大,称悲是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正如元正六佾,事为国章,虽情或未安,而礼不可废。铙吹军乐,比之亦然。”[3]可见,萧统对“乐”的教化功能极为重视。《文选》收录的汉代音乐三赋中,《洞箫赋》和《长笛赋》较能体现音乐的教化作用。
《洞箫赋》主要强调音乐在净化心灵方面的作用。原文在描写洞箫的美妙时,会让人不自觉地“赋歌”,乐声宏亮时,“若慈父之畜子”;而乐声美妙时,“若孝子之事父也。”慷慨时似壮士,优柔温润时又似君子;声音威武时似雷霆,声音平和时又似春风拂面。洞箫的音乐还会感化动物,蟋蟀、尺蠖、蚂蚁、蜥蜴、鸡、鱼都被洞箫的音乐所感化,随着音乐的节奏感情,它们或行或止,或张嘴瞪眼、废寝忘食。在《洞箫赋》中,王褒以慈父、孝子、壮士、君子、武声、仁声等各种形象化的音乐以及鱼虫鸟兽,来证明音乐具有“化风俗”的作用。
《长笛赋》强调音乐的政治性、思想性,将音乐的美感升华至音乐义理的理性认识。传统儒家的美学观认为,真正美好的音乐应是“中和之乐”,也就是和谐统一的境界。笛声可以使屈原、介之推归于“中和”,或返回祖国,或接受封赏,而不是采取过激的行动。即使像南官万、高渠弥这样谋逆行恶的人,听了长笛的乐音也会中止其阴谋,不再作恶。澹台灭明会把自己儿子的尸体从江中收回,皋鱼会抑制他的哭声。蒯聩不会再与儿子为敌,陈不占会为成就大义而增加勇气。不论是“王公”、“隐处”还是“宦夫”、“士子”听到笛声都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各享其乐,至于鲟鱼、驷马、玄鹤也会因听到笛声而涌出水面,仰首倾听,闻笛起舞。就连绵驹、伯牙、瓠胡、罄襄之类的人也会为笛声而称赞。笛声所奏的“中和之乐”在马融笔下更是成为可以“通灵感物,写神喻意,致诚效志,率作兴事”的教化工具。至此,音乐已经缩小其愉悦身心的功效,而成为一个用来宣传礼法制度的工具,“溉盥污,澡雪垢滓矣”。万事万物只有通过笛声才可以达到“中和”的境界。
其次,音乐最基本的功能是愉悦身心、陶冶性情,通过节奏的变换以及音符的配合使人放松。不同的音乐可以带给人不同的感受。随着佛教的传入及道教的兴盛,儒家的正统地位开始受到挑战。虽然雅乐还占有统治地位,但是被孔子看作“淫声”的郑卫之声也相应地发展壮大起来。音乐独立的审美价值也逐渐被重视。《舞赋》之中傅毅的歌词写道:“摅予意以弘观兮,绎精灵之所束。弛紧急之弦张兮,慢末事之曲。舒恢炱之广度兮,阔细体之苛缛。”可见,音乐和舞蹈的魅力在于可以使人心情舒畅,独舞时观众可以跟着心旷神怡的舞曲击打节拍,群舞时观众们又因不断变换的队列音乐而入迷赞叹。到最后舞蹈结束,“黎收而拜,曲度究毕。迁延微笑,退复次列。”观赏者莫不称快,足见音乐使人们和舞者融为一体。
三、音乐美的发展
《文选·序》中提到“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的编排标准,这三篇音乐赋严格遵循汇聚、类分和时代相次原则,在表现音乐的教化作用和娱乐功能方面,由侧重音乐内容到侧重音乐形式,再到音乐内容与形式两者并重。
王褒生在西汉宣帝时期,“宣帝中兴”的局面使他更强调对音乐内容的重视,尤其是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洞箫赋》中直接提到音乐可以“感阴阳之和”、“化风俗之论”。这种教化主要是对心灵的感化。王褒更强调音乐通过内容来表现感化作用。他认为箫声可以使“贪饕”、“狠戾”、“刚毅强暴”、“逸豫”的人发生改变,是由于洞箫吹奏的是类似于参差的曲子。徐华在《两汉乐赋中所见音乐理念的新突破》中认为,“道德”乃自然之道,以合于自然的音声来消解种种人的私欲,从而达到归于人道之正的目的。”将道德的说理寓于音乐的内容之中,比作“慈父”、“孝子”、“壮士”、“君子”之类,虽然比较生硬,但是已经开始从只有雅正的正声才可以感化人们心灵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开始肯定新声的作用。“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伟之。故闻其悲声,则莫不怆然累欷,撇涕泪;其奏欢娱,则莫不惮漫衍凯,阿那者已。”他认为音乐的感化之美是通过音乐的内容表现出来的。他甚至在文章的末尾提到,箫声之所以会有这种感化的作用,是因为“赖蒙圣恩,从容中道”,这也从另一方面证实音乐的感化作用在于音乐的内容。
傅毅的《舞赋》先细致描写了二八郑女的舞蹈,紧接着描写了群舞,将审美的主题放到对舞蹈形式的欣赏之上,通过舞蹈的形式美,使得听惯了雅正音乐的君子可以“严颜和而怡怿兮,幽情形而外扬。”主张通过单纯对音乐形式和内容的感受来获得身心的审美以及心灵的净化,相比《洞箫赋》只将音乐重心放在音乐的内容上进步很多。
《长笛赋》站在音乐本体的角度,运用“论记其义,协比其象”的方式,发掘音乐形式与内容的规律或精神因素,以此来满足不同层次欣赏者的审美要求。在对音乐外在表现方面,细致描写演奏人在吹奏笛子时的场景:“杂弄间奏,易听骇耳,有所摇演。安翔骀荡,从容阐缓。惆怅怨怼,窳赧。聿皇求索,乍近乍远。临危自放,若颓复返……反商下征,每各异善。”将笛声描写得出神入化,既正面描写笛声的变化,又通过乐师手指变换描述笛声,说明笛声每一个音符都十分美妙。赋中提到,善于欣赏笛声的人是通过笛声“知礼制之不可逾越”、“知长戚之不能闲居”,说明音乐音符的美可以使人感受到礼教的教化,承接下文说明笛声和义理的关系,内容的气概似老庄孔孟,笛声的节奏又似商鞅韩非,乐曲的曲调又亦雅亦俗,不论是人还是自然界的万物都会受到笛声的感化。赋作举介子推、伯牙等例说明笛子吹奏的音乐蕴含的义理可以达到“人盈所欲”的境界,笛声不论是在音乐的形式还是在内容上都可以有“溉盥污秽”的作用。
虽然这三篇赋所选题材的表达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通过对表演工具或演员的描写,说明音乐本身具有美的感化作用,通过对赋中所描写音乐的总体分析,考察音乐和自然的关系,感受音乐可以受到自然的熏陶,而这与传统“天人合一”的观念是相通的。通过音乐内容揭示内在义理,说明音乐具有教化作用,不仅体现在“中和”,还体现在对传统儒家学说的突破上,提出郑卫之声也可以对人的心灵起到净化陶冶作用。《文选》音乐三赋的安排体现出汉代音乐观中美的变化,以及音乐的内容、形式的美感对人的感化作用。
[1]刘志伟.从音乐意象看阮籍文学创作与音乐的关系[J].西北师大学报,1992(6).
[2]郑明璋.论汉代音乐文化视野下的汉赋创作[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文学研究版,2007(3).
[3]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访南音洞箫制作师李志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