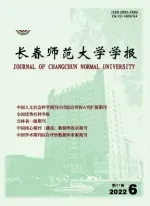辽代奚人的生活探析
李月新,梁 磊
(1.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赤峰 024000;2.长春师范学院历史学院,吉林长春 130032)
奚人早在元魏时就活动于松漠地区,并与中原地区形成较为密切的联系。唐末五代之际,伴随君主专制意识的确立,奚人也被纳入到契丹人的势力范围,并在辽朝统治下得到较大的发展。奚人在维系自身习俗文化传承的同时,也兼收周边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尤其在生产经营模式与生活习俗方面都呈现出多元的色彩。
一、奚人活动的大致范围
奚或奚人,在隋朝以前的中原史籍中被称之为库莫奚[1],其族源自鲜卑部落系统之东部鲜卑宇文部,与契丹族原本属于“异种同类”的关系,即族属与文化传统相同而分别属于不同的部落。宇文部被东部鲜卑慕容部的首领慕容元真所击破,其遗落者窜匿松漠之间。[2]古代的松漠,以西拉木沦河上游的松林地带和老哈河两岸的科尔沁沙漠闻名,地理范围大致包括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及河北东北部地区。受大兴安岭山体影响,以多浅山丘陵和河岸台地为其地貌特征,呈现出草原、松林、河流、湖泊星罗棋布的自然面貌。与东部鲜卑分离之后的奚人,便与契丹人共同生活在这一地区。《魏书·太祖纪》载“登国三年 (388),太祖亲自出讨,至弱洛水南,大破之,获其四部落,马牛羊豕十余万。”弱洛水即今天的西拉木沦河。魏太祖北征,在破奚之后渡河,可知当时的奚人活动的主要区域应该是西拉木沦河上游南岸。就其地望而言,奚人一直活动于松漠地区的西部,东接契丹。
独立发展之后的奚人,一直活跃于松漠之间,并将其势力向西南发展。到了隋唐时期,奚人所居之地“在京师东北四千余里。东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北至国”。[3]又《新唐书·奚传》中称“其地东北接契丹”,“依土护真而居”。土护真水即今天的老哈河,老哈河自西南流向东北,所以奚人应该活动于老哈河的上游地区,契丹人活动于老哈河的下游。
伴随着契丹的壮大,为了躲避契丹的扩张,奚人的势力一直向西南发展。“当唐之末,(奚)居阴凉川,在营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数百里……后徙居琵琶川,在幽州东北数百里”。[4]阴凉川即老哈河上游的支流阴河流域,可知到唐末之时,奚人仍以老哈河上游流域为中心活动。后来迁徙到了琵琶川,即辽宁喀左境内。到了契丹阿保机统治时期,契丹势力强盛,室韦、奚、等族皆服属于契丹,“奚人常为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诸怨叛,以别部西徙妫州 (河北怀来)”。[4]从此之后,居于原地的称为东奚,西徙之后的称之为西奚。
阿保机建国之时,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将奚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唐天复元年 (901),痕德堇可汗继立,任命阿保机为本部夷离堇,专任征讨、扩张事宜,接连击破室韦、于厥及奚族部落,俘获甚众。903年,阿保机以德祖 (即阿保机之父撒拉的,德祖乃其谥号)曾经俘获奚族七千户,迁徙至饶乐水附近的清河,并重新组编为奚迭剌部,下辖十三个县 (即石烈,契丹语称县为石烈)。“明年 (906) ……袭山北奚,破之……十一月,遣偏师讨奚、诸部及东北女直之未附者,悉破降之”。《辽史》载到太祖五年时,“上亲征西部奚。奚阻险,叛服不常,数招谕弗听。是役所向辄下,遂分兵讨东部奚,亦平之。于是尽有奚、之地。”
北宋时期的宋绶出使契丹,沿途记述到,“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统和二十四年 (1006),五帐院进故奚王牙帐地[5],圣宗即于此建中京。这说明进入契丹时代的奚人,其居住地域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活动范围有所扩张。奚人大致生活在辽中京管辖范围,即今天的内蒙古赤峰地区、辽宁朝阳西部及河北承德一带。
二、奚人的经营模式
公元3世纪左右,迁居到古松漠地区的鲜卑部落,保留了其原本牧放兼狩猎的经营模式。奚人同契丹人一样曾经长期地生活于鲜卑族群之中,因此被上了较为深刻的鲜卑烙印。4世纪从鲜卑部落分离之后的奚人,“每随逐水草,以畜牧为业,迁徙无常”[3],并且善射猎,继续了其鲜卑时代的牧放兼狩猎的经营模式。北魏登国三年 (388)之时,大破库莫奚,获其四部杂畜十余万,杂畜即指马、牛、羊、豕等。由此可知当时奚人的牧放经营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到了 (北魏)高宗、显祖时期,从库莫奚每年向北魏贡献的名马文皮等物品可知,此时的库莫奚逐渐恢复了元气,经营模式兼及狩猎。《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中称奚人过着“逐水草畜牧”的生活,并且“马逾前蹄坚善走,其登山逐兽,下上如飞”,这说明牧放兼及狩猎的经营模式于奚人社会之中一而贯之,并且一直延伸到契丹辽时期,北宋使臣看到的仍是奚人过着畜牧羊、牛、马、橐驼等牲畜,并“逐水草射猎”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奚人的牧放业中以牧养青羊、黄豕为特色。[6]据宋人韩元吉描述,宋人为了报复契丹人每次向宋朝索要食料的行为,在出使过程中往往会为难契丹接伴官员。因为“燕北第产羊,俗不畜猪”,所以宋朝出使辽朝的使臣便会要求吃“猪肉及胃脏之属”。为了满足宋朝使臣的要求,契丹接伴官员疲于奔命,往往要到距离较远的奚人居住区去寻找。[7]因为奚人有牧养黄豕 (黄毛猪)的习俗,所以猪肉及内脏这样的食物才能够在奚人的居住地区找得到。
随着奚人与中原政权接触日深,贡市贸易也成为奚人经营模式中的组成部分。库莫奚曾多次向北魏要求“入塞,与民交易”,而且在太和二十一 (497)年以前就“与安营二州边民参居,交易往来”[2]。其后其与中原政权的贡市关系从未断绝,尤其与唐的互市贸易最为发达,双方除了频繁的朝贡与赐予之外,还在幽、营等州地开榷场贸易。通过榷场贸易,奚人用马匹交换中原地区的农副产品、纺织品和日用品。20世纪70年代在喀喇沁旗发现了一批极具域外风格的唐代金银器,其中一件银盘底部外侧錾刻铭文一行:“朝议大夫使持节宣州诸军事守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采石军等使彭城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臣刘赞进”[8]。这批铭刻有汉字的金银器,很明显不是当地生产的产品,应该是在唐末之时,通过商贸往来流入奚族及契丹故地的。进入契丹辽时期之后,奚人成为辽朝的臣民,与南方的宋再无直接的朝贡往来,但是奚人经营的商业贸易却继续保存了下来。曾出使契丹的宋使余靖在其《武溪集·契丹官仪》中,曾经记载辽朝在中京地区设置度支使,专门管理商业贸易事宜,可见中京地区的商品贸易经济也是比较繁荣的,这其中就不乏奚人的参与。苏颂也在奚地看到了“朱板刻旗村肆食,青毡同贵人车”的景象,并解释说,出奚山路,入中京界,道旁店舍颇多,人物亦众[9]。
古代的松漠有很多地区都比较适宜农业生产,同时奚人受到农耕文化的影响较深,所以奚人约当唐之时就经营着粗放型的农业生产。当时的奚人“稼多,已获,窖山下”。[1]五代初期的“去诸之族,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秋熟则来获,窖之山下,人莫知其处”[4],去诸族人每年借边民的荒地耕种,这里的边民应该是居住在奚人南部的汉人,可见此时的奚人仍沿袭着其农业耕种的传统经营模式。进入契丹时代之后,大量的农耕民族 (如汉、渤海)迁居到中京地区与奚人杂居。受其影响,奚人的农耕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奚)亦务耕种,但无桑柘,所种皆从垄上,盖虞吹沙所壅”[6]。曾出使辽朝的北宋人宋绶在《契丹风俗》中就记载奚人“善耕种”。同样出使辽朝的北宋使臣苏颂记述了其路过中京地境时的见闻:“农夫耕凿遍奚疆,部落连山复枕冈。种粟一收饶地力,开门东向杂夷方。”并在诗后加上注释:当地“耕种甚广,牛羊遍谷。问之皆汉人佃奚土,甚苦输役之重。”可见辽中期以后,奚人的农业经营日渐繁盛,出现了“田畴高下如棋布,牛马纵横似谷量”[9]的画面。如此广大面积的农田,皆为奚人所有,当地的汉人则依靠租佃奚人的土地生活,这说明租佃关系在当时已经产生,并成为奚人农业经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奚人所居之地盛产长松,“奚人业伐山,陆种斫车,契丹之车,皆资于奚”[10]。奚车早在唐时就有盛名,《新唐书》中记载,大中元年,张仲武讨伐北部诸山奚时,一次就缴获奚车五百乘。进入辽朝之后,奚车成为契丹最常用的工具。地处辽南京通往中京驿道上的打造部落馆,有番户百余,即是奚人工匠的主要聚居地区。关于奚车的形制,宋人沈括在《熙宁使虏图抄》中对奚车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其辎车之制如中国”,特点是:“后广前杀而无般,材俭易败,不能任重而利山行。长毂广轮,轮之牙,其厚不能四寸,而轸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车,驾之以驼,上施巾荒,惟富者加毡文绣之饰。”这种奚车的形象在辽墓壁画中较为常见,如内蒙古翁牛特旗乌丹镇解放营子辽墓壁画中所绘的车,长辕、高轮,车上前后有彩色车棚,棚顶有黄色垂幔,并垂有流苏。车棚有四根细木立于车辕之上,后棚较小,棚顶有朱红彩绘,用白骆驼驾辕。[11]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号辽石棺墓中也绘有三辆长辕、高轮的毛毡车。[12]奚车有车轮高大的特点,这样的大车轮比较适宜在草地上行走,是游牧民族较为实用的出行工具,所以在北方草原地区十分流行。
三、奚人的生活习俗
由于受到自然环境及周边民族的影响,奚人逐步形成了牧放、狩猎兼及农业的经营模式,正是基于此,其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也反映在了奚人的生活之中。
奚人同契丹同源,在生活习俗等方面颇为相近。同契丹人一样,奚人也是髡发,沈括在《熙宁使虏图抄》称“其人剪发,妥其两毛”,苏颂在《和晨发柳河馆憩长源邮舍》中描述自己在辽朝中京境内看到的汉人“皆削顶垂发以从其俗”。从其俗,应是指进入契丹统治范围的汉人改变了原来的传统,顺从了生活在当地的契丹人和奚人的风俗习惯。契丹人髡发的样式很多,但是沈括和苏颂所见的都是减去头顶部分的头发,留下两鬓的头发,很有可能奚人的髡发也是以此种样式居多。
奚人每逐水草,以畜牧为业,其饮食结构当是以肉食为主。农业成为奚人的经营方式之后,粮食中诸如、黍出现在奚人的饮食之中。奚人对粮食进行简单的处理后,以“断木为臼”的方式去壳,用瓦鼎等炊具煮成稠粥,“杂寒水而食”[1]。五代时期的去诸所帅之奚众仍是采取“爨以平底瓦鼎,煮为粥,以寒水解之而饮”的饮食方式。[4]可见将稠粥用寒水浸泡然后食用的方式很有可能是奚人独有的饮食习惯。进入辽朝之后,奚人的饮食进一步丰富,除了肉奶制品、糜粥、之外,汉人的传统饮食也逐渐被奚人所接受。苏颂在《奚山道中》描述奚境之内“村店炊黍卖饧,有如南土”。
因其牧放生业,奚人居毡庐,环车为营。毡帐这种居住方式在游牧民族中十分普遍,而“环车为营”说明奚车不仅是交通工具,同时也有军事上的防御功能。而且奚人部落皆散居山谷,无城郭。进入辽朝之后,一部分奚人仍然保持着传统的牧放生活模式,如宋人刘敞在其奉使辽朝途中所作的《铁浆馆》一诗中就描述了奚人以车帐为生、昼夜移徙的生活模式。但也有一部分奚人受到汉人、渤海人等影响,农耕经营扩大,开始定居。王曾记述到“自过古北口,即番境。居人草庵板屋”[6],这里的番境,即是奚人活动的地域,这一地区多松林树木,奚人就地取材,建造房屋。沈括在《熙宁使虏图抄》中记载更为详细:“其民皆屋居,无瓦者墁上,或苫以桦木之皮”。但是,奚人仍然山居谷汲,保持了其原来散居山谷的习俗,“封域虽长编户少,隔山才见两三家”[9]。并且就如同苏颂在《和宿牛山馆》一诗中所说的“部落不成城”一样,奚人没有营建城郭,只是在板屋之前编荆为篱。但是契丹统治者为了在宋朝使辽的使臣面前充门面,“尽驱山中奚民就道而居”[13],其后果就是扩张了汉人与奚人杂居的范围,使得奚人受汉文化影响日深。
奚人曾有一段附属突厥的经历,所以颇同突厥,有死者则采用“以苇薄裹尸,悬之树上”[14]的树葬方式。这种葬俗与契丹颇为相似,并在北方的游牧民族之中颇为流行。《新唐书·契丹传》中称契丹“风俗与突厥大抵略同。死不墓,以马车载尸入山,置于树巅”。契丹人三年之后收其骨焚之,没有记载奚人如何处理,但是应该与契丹略同。但是随着奚人经营模式的转变,农业生产在奚人生活之中日重,奚人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多。唐朝之后,特别是进入辽朝之后,一部分奚人也开始实行土葬,如耶律德光曾发西奚酋扫剌之墓,粉其骨而之。目前尚未有关于奚人墓葬的考古报告,但是部分学者根据某些特征对赤峰地区及承德地区的一些辽代墓葬曾作出过是奚人遗迹的推断[15],但是更为准确的界定奚人墓葬的标准目前仍未可知。
四、结语
中国古代的松漠地区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带,生活于此的奚人在其发展过程中既与鲜卑、突厥、契丹等游牧民族渊源颇深,同时也与中原农耕民族过从甚密。结合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奚人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牧放、狩猎兼及农业的多样化经营模式。同时,在保持自身习俗文化传承的同时,也兼收并蓄地吸收了周边民族的文化影响,融合到自身。因此,辽朝的奚人既有车帐而居、牛马纵横、四时畋猎的一面,也有三世同堂、开垦梯田、善于耕种的一面。正是因为奚人经营模式及生活习俗的多样性特点,所以在辽代的中京地区形成了一副“居人处处营耕牧,尽室穹车往复还”[6]的生活画面。
[1]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奚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6273.
[2]魏收.魏书·卷一百·库莫奚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22-2223.
[4]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4:909.
[5]脱脱.辽史·卷三十九·地理志三[M].北京:中华书局,2003:481.
[6]王曾.王沂公行程录[M]//赵永春.奉使辽金行程录.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28-29.
[7]韩元吉.桐阴白话[M]//说郛·卷二十.北京:北京市图书出版社,1986.
[8]喀喇沁旗文化馆.辽宁昭盟喀喇沁旗发现唐代鎏金银器[J].考古,1977(5):330-331.
[9]苏颂.奚山路.牛山道中.过新馆罕见居人.和仲巽奚山部落[M]//赵永春.奉使辽金行程录.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73,79.
[10]沈括.熙宁使虏图抄[M]//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中疏证稿,北京:中华书局,2004:130.
[11]项春松.解放营子辽墓壁画发掘报告[J].松辽学刊,1987(4):107.
[12]项春松.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二号辽墓[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3):81.
[13]陆振.乘轺录[M]//赵永春.奉使辽金行程录.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17.
[15]项春松.赤峰市郊区发现的辽墓[J].北方文物,1991(3):33-39.
[16]田淑华.辽金时期奚族在承德地区活动史迹探考[J].北方文物,1997(4):8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