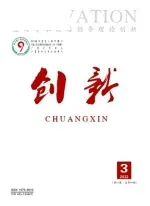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政治发展述评
吴 磊 于春洋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政治发展述评
吴 磊 于春洋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政治发展体现在政治社会化、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以及民众政治心理等四个方面。研究这一时期农村政治发展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丰富了人民公社史的跨学科研究,另一方面有助于重新审视人民公社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民公社;农村政治发展;作用;意义
从1958年第一个人民公社成立到1984年宣告解体,中国农村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度过了26年。人民公社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重要的阶段,时至今日,在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组织体制和农民生活的细枝末节中我们仍然能看到公社的影子。
从1950年代人民公社成立伊始,学界对人民公社制度及公社化运动的研究就从未停止过。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学术界整体研究角度有了新的转变,人民公社史也有了突破,开始注重多学科交叉、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研究,一度呈现欣欣繁荣的景象。
对于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政治发展的探讨则主要集中于政治社会化、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以及民众政治心理等四个方面。
一、政治社会化
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1]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和含义:一方面,它强调了政治生活领域的个人通过教育或者其他媒介获得一定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从而逐渐成为一个政治人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政治系统通过教育社会成员遵循系统的规则,履行其应承担的角色,使得社会成员接受某种特定的政治态度、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观。
由于国家政权体制以及基层政权组织的特点,人民公社时期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具体包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政治符号、大众传媒、家庭的政治社会化、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
第一,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民公社时期的政治教育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为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对广大农村基层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主要有会议、传播媒体、工作队(团)等形式,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体制上,大力推行共产主义制度”;“政治上,强化阶级斗争,树立对领袖的崇拜意识”;“思想上,加强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以及“心理上,抓住农民‘均平’‘求富’的心理,吸引农民走公社化道路”①详见陈彬《人民公社时期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研究》。。
第二,政治符号。政治符号的表达也是农村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人民公社时期的政治符号往往以标语口号等形式来表达特定的政治含义。“象征性符号是可塑的,尽管它被完全扭曲,但它还能保持内在能量,即动员、激励以及强力的力量。”[2]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标语口号具有来源特定性、标语制作材料多样性、动员效果鼓动性的特征。[3]标语和口号一般都具有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以及极富影响力的特点,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及地方各级政权通过标语口号这种政治符号的表达形式,向农村社员宣传党的政策方针、重大会议精神以及最高领导层领袖人物(如毛泽东)的思想。
第三,大众传媒。大众传媒作为一种重要媒介,从来就不是独立存在的。它通过反映、阐明、报道各种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实现其社会价值,同时也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种关系的束缚和控制。人民公社时期最为常见的大众传媒方式是报纸杂志、有线广播、样板戏等。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新闻媒体所传播的党的思想教育信息具有很强的政治导向性。报纸杂志如《人民日报》、《红旗》、《新闻半月刊》等成为人民公社宣传的阵地,激励着广大社员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挥劳动积极性,投入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而最普遍的场景就是田间地头有线广播的大喇叭播放着一些诸如“最高指示”、“会议精神”等这样的节目。一项统计资料显示: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有广播站5000个,农村的广播网基本建立起来了。[4]农村社员在这些大众传媒的影响下,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促使了政治的农村社会化进程。
第四,家庭。在“成分论”、“阶级论”、“血统论”的舆论大背景下,家庭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体制与社会关系互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政治社会化不同于以往普遍意义上通过儿童的政治潜意识来完成,而是借助于现实的内部政治氛围来影响其所有成员特别是成年人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政治评价、政治态度等个体政治文化的诸方面。在人民公社时期,特别是“文革”时期,“家庭的血亲关系”就是以一种新的政治化形式而存在并成为了分配社会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基本依据。这就是曾经流行多年并决定了许多人命运的“成分论”。
最后,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这是人民公社时期政治社会化最常用和最具影响力的途径。从人民公社建立伊始,中国的农村便开始进行了一系列规模不等、打击对象不同的“阶级革命”。在农村实现政治、经济和文化整合的过程中,党和政府通过阶级斗争以及发动政治革命来实现国家对于基层政权的渗透和控制,并将对普通民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
农村政治社会化在当时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有学者甚至将其看做是“农村社会整合的软性要件”,[5]这种软性相对于法律、纪律、行政命令等硬性要件,政治文化以一种无形的力量整合着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政治文化的传播,广大的农村社员从公社成立之前的“经济人”逐渐向“政治人”发生着转变。此外,在政治文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传播过程中,广大农村群众表现出了对主流政治文化极高热情的支持和认同,他们也逐渐开始拥有政治意识、政治态度和政治认知,从而开始卷入到政治革命的浪潮之中,构成了政治社会化中上层政治与下层社会互动有机结合的全部过程。
二、农村基层政权
基层政权问题是研究乡村政治必须涉及的重要问题。农村基层政权是联系国家与普通民众的重要纽带,它一方面保证了国家政策自上而下的贯彻和执行,另一方面还传达着下层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人民公社时期的基层政权具有特殊性,它是“一大二公”的集权体制,一直实行“政社合一”的制度,即把基层政权机构(乡人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机构(社管理委员会)合为一体,统一管理全乡、全社的各种事务。这属于典型的“社政式”管理模式。[6]人民公社不仅具备了一级政权的性质,而且置生产、流通、交换、消费于公社的监管之下,而且还履行着政治管理、社会管理、文化管理以及军事管理的职能。人民公社体制也成为国家对基层进行微观管理的重要制度基础。
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此时期基层政权治理模式的探讨上。徐勇认为人民公社时期的治理模式为“理治”,这个“理”是指社会理想和革命领袖的政治口号。①详见徐勇的《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和包先康、李卫华的《国家政权建构于乡村治理理念的变迁》。国家通过政治教育、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等途径将社会理想和政治口号自上而下传播到基层社会,并通过基层政权即公社(也包括各级党组织)来控制基层社会的方方面面。一个具体表现是人民公社时期所实行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张静和纪程将农村基层政权与国家政权建设相联系,并认为人民公社的体制变迁深刻地反映了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正如吉登斯所言:“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其目标是要造就一个有明确边界、社会控制严密、国家行政力量对社会进行全面渗透的社会,它的形成基础是国家对社区的全面监控。”[7]但是不可否认,人民公社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或可称之为民族国家构建)存在着两方面的致命弊端:一方面,由于后发国家急于迅速实现现代化的愿望和压力,中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的集权特征由于其人为的、“计划”的痕迹而更为明显。[8]而另一方面,由于基层政权利益与农民的社会利益没有新的结构支撑,社会利益由于公社体制的限制(如取消自留地、限制发展副业)进一步受到约束,这种分离结构的延续造成了基层政权多种问题的出现,如“公社不以农民利益为上,而以上级要求或自身利益为准绳、基层政权对社会利益的恣意行为等等”。[9]于建嵘则将公社基层政权组织形式定义为“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国家通过对土地所有制等经济制度的改造和意识形态的动员,建立了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国家行政权力冲击甚至取代了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地方政府及乡村干部通过代理方式实现了对乡村社会权力的垄断。[10]
人民公社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最终于1984年宣告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本土地制度的现代乡镇管理模式,社政式的管理模式从此在中国乡村销声匿迹。但是,正如不能否认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一样,人民公社时期乡村基层政权建设同样在中国乡村政治变迁中具有着深刻的影响意义。它不仅有机地整合了乡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资源,而且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村基层政权体制建设提供了良好的过渡平台。
三、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
国家与社会关系也是研究人民公社时期乡村政治的一条重要路径。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土地制度从耕者有其田、土地入股到集体化;农民从个体农业经营者到变成公社社员;农村基层政权从乡政并立到政社合一;社会发展战略从新民主主义转向过渡时期,所有这些,都是在国家工业化话语下进行的。[11]国家已经通过公社这种新型的政治体制将社会纳入到自己的轨道中去,而社会也在不断适应中与国家发生着互动。公社体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点是社区政权化、社会国家化,即形成了所谓的“国家社会”。[12]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对农村实行了公社集体化,将农村经济成分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框架之中,从而扼杀了市民社会的前提——市场经济。第二,社会高度政治化。国家通过政治教育、政治宣传、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等形式,广泛地在社会进行政治动员,从而造成了社会的高度政治化。第三,农民成为“公社人”、“组织人”。广大的乡村社会的农民被纳入了公社体制之中,国家与社会保持了高度的一体化,农民在组织内逐渐丧失了独立的地位。有学者提出了“资源—体制”框架来分析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即一方面经济资源的需求成为了国家介入乡村社会的主要动机,另一方面乡村社会的经济资源状况决定了乡村社会机制选择及其运转的主要因素。[13]
在“强国家、弱社会”体制下,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在国家与乡村这场博弈中,乡村社会逐渐丧失了自主性与活力。通常是上层自上而下的政策甚至是非理性、不切合实际的政策也会畅通无碍地被贯彻和执行。
国家对乡村社会的过渡干预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人民公社制度的彻底瓦解。在公社模式下,国家集体主义抹杀了农民在农业中的主体性地位,在民主政治层面忽视了群众政党民主参与意愿的表达,在经济层面过度干预从而造成了农业经济形式单一和农业产出效益比不高的局面。当国家与社会的博弈一旦出现不均衡,社会利益的需求超越了国家意志之时,国家权力随之在控制薄弱的地方逐渐退出,政治体制变革也就不远了。
四、民众政治心理研究
政治心理通常是指人们对政治过程和政治生活的一种不系统的、不定型的、感性的反映,表现为一定的政治动机、政治态度、政治情绪、政治信念等。对于世代居住于乡村社会的广大农民而言,人民公社制度的嵌入无疑是在外部对传统村落的冲击的互动模式下产生和建立起来的。公社化如一场前所未有和极具变化的浪潮冲击着农村社会和农民的生产生活,并对普通民众的心理产生着重大的影响。而随之变化的民众政治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民公社体制施加着某种无形的影响效应,并促使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调整和变革。
人民公社时期的民众政治心理糅合了传统与现代,感性与理性,并随着国家上层政策方针的变化而逐渐调适。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传统的平均乌托邦思想与共产主义理想的结合。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等大同的平均主义思想,公社化运动所宣扬的“一大二公”、“人民公社是天堂”等口号与普通民众心中的大同理想是不谋而合的。其次是对于领袖权威的极端崇拜。人民公社时期,民众建立起了对于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的极端崇拜,“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14]51这种方式正是舆论的宣传与动员。第三是群众团队归属心态。勒庞曾指出:“从社会心理学看,每个个体均有社会集群倾向即团体归属感。尤其在社会动荡时期更为迫切,有的为了寻求力量支持,寻求社会承认,有的人则是寻求心理上的安全感,在某种程度上缓解或摆脱恐惧、孤独、被歧视甚至被迫害,具有更强烈的集群心理。人多势众的原则似乎成了惟一的历史原则。心理的需求转化成组织行为,个人只有结合成组织,希望在组织中以求得保护和发展。”[14]9人民公社时期由于划分阶级成分,乡村传统的等级和秩序被打乱并重新洗牌,以往高高在上的地主和富农反而成了阶下囚,而贫农得以翻身并且享受更多的政治资源和更高社会地位。因此,在阶级队伍上,群众对于团队的归属具体表现在对于无产阶级的靠拢。最后是“巨大的社会遵从和行为依附”心态。集权的公社体制超越了原本传统的自然村落,农民在公社之下失去了以往小农经济的自主权,心态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强大的政治氛围和巨大的政治压力中,农村普通民众具有着巨大的社会遵从和行为依附心理。在“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公社制度之下,广大民众在知觉、判断、信仰及行为上自觉不自觉地跟随别人的思想行动反应。由于意识形态领域高度集权的特征,个体无形中产生巨大的政治压力,只能从本能出发,被动地随社会潮流而动。[15]
五、结 语
以往对于人民公社的研究大多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叙述和评价,近些年来由于跨学科研究的兴起,一些学者开始应用制度分析理论、产权理论探讨人民公社制度建立、发展及其瓦解的原因,人民公社史研究的思路和领域也有了较大的突破,但是缺乏对于这一时期农村政治发展的探讨和研究。人民公社史作为中国现当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是如果单纯从历史学或者经济学角度去叙述人民公社的发展过程,往往会忽视公社的制度背景、制度变迁以及制度意义。人民公社时期乡村政治发展研究其实乃是运用“政治—社会”互动的研究路径去看待制度与社会变迁、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16]运用政治学的方法和路径进行人民公社史的研究,旨在总结中国在当代跌宕起伏的政治发展进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为进一步探讨中国特色的民主化道路提供历史借鉴。
[1][美]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9.
[2]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杭州: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0.
[3]韩承鹏.标语口号的特征分析[J].上海党史与党建,2009,(7).
[4]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M].人民出版社,1959.
[5]匡和平.政治社会化:农村社会整合的“软性”要件[J].宁夏社会科学,2007,(6).
[6]欧阳兵.从社政式治理到社团式治理:乡村公民社会成长的 60 年[J].岭南学刊,2009,(5).
[7][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北京:三联书店,1998:146-147.
[8]纪程.“国家政权建设”与中国乡村政治变迁[J].深圳大学学报,2006,(1).
[9]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3-40.
[10]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18.
[11]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2]谢志岿.论人民公社体制的组织意义[J].学术界,1999,(6).
[13]彭勃,金柱演.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发展沿革——“资源—体制”框架的可行性分析[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999,(1).
[14][法]勒庞.乌合之众[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51.
[15]叶青.“文革”时期群众组织产生与社会心理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4).
[16]徐永志.中国近现代政治社会史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D6;K27
A
1673-8616(2011)05-0032-04
2011-05-22
中央民族大学“211”三期创新人才培养项目《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政治社会化研究》(0212110309100424)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吴磊,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1);于春洋,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呼伦贝尔学院马列部副教授(北京,100081)。
潘丽清 实习编辑:潘复添]
——舒城舒茶人民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