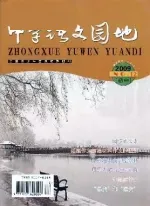选取美学视角,鉴赏形式之美——以中国古代诗歌鉴赏为例
沈玉荣
王国维说:“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形式美是指色、形、声等在整齐一律、平衡对称、对比调和与多样统一中所呈现出来的,足以引起美感的一种美的形态。形式美的人文内涵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孕育形式美的社会内涵,它包含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当时的文化特征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另一方面是创造形式美的个体个性的内涵,它包含创作者个人的家庭背景,人生经历,情感色彩和个人的创作特色。
这里以中国古代诗歌为例,从色、形、声三个方面对形式美的人文内涵略做分析。
一、色:实物色彩感情色彩
“色”即色彩。提到色,我们可能会想到绘画,因为绘画的色彩是人们显而易见的。例如红色代表热烈兴奋,黄色代表温暖明朗,蓝色代表抑郁宁静,绿色代表生意盎然欣欣向荣,而黑色则代表严肃恐怖,白色带有纯洁凉爽。但是,诗歌中的“色”却与此不同。它可分为实物色彩与感情色彩。实物色彩是指诗中描写事物颜色的字词,而感情色彩则是诗人在一首诗歌中所蕴涵或透露出来的感情趋向。如果说实物色彩是单一的、独立的,那么感情色彩则是融合的、复杂的。感情色彩是以实物色彩为基础但又高于实物色彩的那一层色彩。我们可以从色彩来欣赏绘画的形式美,但却无法从一首诗中几个有关色彩的字词中真正领会出诗的韵味。只有充分了解诗歌形式美的人文内涵,从实物色彩上升到感情色彩,才能算真正体会了形式美。
李贺的《雁行太守行》可谓“色彩缤纷”。“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中有“黑云”“金鳞”“夜紫”“红旗”“黄金台”。如果只从实物色彩上来看的话,这些色彩之间存在着矛盾,我们也无法看出这首诗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是黑暗还是光明,是希望还是绝望。如果我们了解这首诗创作的社会背景和作者生平、经历和创作特色,就不难看出这首诗所要表达的感情。
李贺生活在中唐与晚唐的过渡时期,在文学史上他被划入中唐诗人的范畴。李贺是没落的宗室后裔,他的诗歌才能很早就获得盛名。李贺一生少年有才,但却因不得志而最终早逝。他诗歌的中心内容是诉说怀才不遇的悲愤。李贺的诗歌中带上了他所独有的幽冷与凄婉的色彩。李贺诗歌的另一个特色是他的语言极力避免平淡而追求峭奇。为了求奇,他便在事物的色彩和情态上着力。 李贺写绿,有“寒绿”、“颓绿”、“丝绿”、“凝绿”、“静绿”,写红有“笑红”、“冷红”、“愁红”、“老红”。陆游说:“贺词如百家锦衲,五色眩曜,光夺眼目,使人不敢熟视。”而《雁门太守行》全用大红大绿去表现紧张悲壮的战斗场面,以绚丽写悲壮,在强烈的矛盾对比中营造紧张的气氛,最终抒发作者怀才不遇却一心报国的豪迈之情。可谓构思新奇,形象饱满,感情充沛。
二、形:特殊形式机敏幽默
诗歌中的“形”,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形”,它既不是线条,也不是形体,而是诗歌形式的句式。中国古代诗歌常以“言”来划分。所谓“言”,就是指每一句诗的字数,一字为一言。我国古代诗歌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其中杂言诗与以四言,五言,七言为代表的正体诗相对。而诗歌中最致力于“形”的莫过于杂体诗。由于杂体诗在抒情言志功能上与正体诗的差别,在特定场合,它常常以特殊形式和机敏幽默的风格而出奇制胜,在社会生活中起到正常体格诗作所无法相比的作用。相传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在长安得官后乐不思蜀,五年之后意欲抛弃他的结发妻子卓文君,于是寄了一封只写了从“一”到“万”几个数字的信给卓文君。卓文君看了之后,便明白了丈夫“无意”(一说“无忆”)的暗示,于是也提笔给她的丈夫写了一首奇妙的数字诗:“一别之后,二地相悬,只说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字无可传,百思想,千系念,万般无奈把郎怨。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十倚栏……”这首诗从“一”说到“万”,又从“万”写到“一”,以形式的回环往复充分表达自己缠绵徘徊的感情。司马相如看了这首诗后,被妻子幽怨曲折的自述打动,不禁内疚万分,终于与妻子和好如初。可见杂体诗正是把深刻的人文内涵蕴藏在特殊的形式中,使诗本身起到抒情言志的作用,使简单的形式美得到深化与升华。
三、声:韵律和谐节奏鲜明
“声”是指音韵、节奏。而诗歌的文体特征中就有韵律和谐与节奏鲜明这两点。可以说与其他形式相比,诗歌在音韵和节奏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押韵是诗歌最主要的文体特征之一
押韵对于诗歌意义主要表现在:通过把音韵相同的读音配置于诗中一定的位置,形成有规律的反复,为诗歌创造一种同声相应,回环往复的韵律之美,同时通过韵脚的串联,关上粘下,把跳跃性的各诗行中不相关的意象构成一个整体,加强诗歌结构和形象的完整性,增强诗歌的抒情强度,使诗歌便于吟诵,记忆和流传。
诗歌要求押韵从《诗经》就开始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穷其起源,恐怕是为了配合音乐的缘故。因为诗歌最初是配乐演唱的,边塞之外,庙堂之中,宴席之上,“不学诗,无以言”。吟唱起来,押韵的诗句比不押韵的诗句更加流畅,和谐,与音乐的配合自然更加丝丝入扣。到了后来,当诗歌脱离了音乐,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之后,押韵仍然是诗歌形式中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诗人认为诗歌本身就不能缺乏音乐的美感。
当然,不同的韵部,由于声音的乐感不同,可以表现出不同的感情色彩。下面仅以卢纶的《塞下曲》与孟浩然的《春晓》做一个比较。 《塞下曲》中的“高”,“逃”,“刀”压“四豪”的韵,而《春晓》中的“晓”,“鸟”,“少”,压的是上声十七筱的韵。这两首诗读起来,音调自然是不同的。前一首声调高昂,给人一种意气慷慨的感觉,后者音调曲婉,与“春愁”的惆怅相得益彰。
(二)节奏是诗歌音乐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诗歌中通常表现为声音长短,高低,快慢多种形态的富有规律性的变化。诗的节奏与诗人内心的情感变化存在着相对应的关系。郭沫若在《论节奏》一文中指出:“抒情是情绪的直写。情绪的进行自有它的一种波状的形式,或者先抑后扬,或者先扬后抑,或者抑扬相间,这发现出来便成了诗的节奏。”可见,诗的本质是抒情的,而人的情感的变化本身也具有节奏性,诗的节奏必须反映诗人内在地方的情感节奏。
作为诗的表现形式,节奏主要是通过音节的组合与停顿有规划地配置而形成的。汉字是单音字,一字一音,古代诗歌通常以两个字组合为一个节奏单位,习惯上又称一顿。四言诗每句两个节奏,分两顿,五言诗每句三个节奏,分三顿,七言诗每句分四个节奏,分四顿。顿的划分既要注意音节的整齐,又要兼顾意义的完整。举两个最普通的例子: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操《短歌行》)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王之涣《登鹳雀楼》)当然,就某一首诗而言,节奏的高低,缓急,轻重,既与诗歌叙写的情感内容密切相关,也取决于诗人的艺术个性。一般说来,抒发豪迈情怀的诗歌节奏急促有力,表现欢乐激动情绪的诗歌节奏明快轻松,描写艰难情景的诗歌节奏低沉迂缓,反映细腻心理变化的诗歌节奏轻柔舒缓。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看,性格浪漫外向的诗人写诗,语言通常明快激越,性情抑郁的诗人则喜欢用精细的笔墨表现青烟薄雾般的淡淡哀愁,讲究情韵的起伏悠长。
在创作中,优秀的诗人还常常能够因物赋形,随情易声,在节奏的安排上有时故意当快而慢,或当慢为快,使诗歌的节奏起伏跌宕,从而反映诗人情感的起落。其中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就是最好的例证:“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以过万重山。”全诗气势豪爽,船快意也快,给人一种空灵飞动之感,尤其是第三句,用两岸猿声衬托船行之快,节奏却由快转慢,缓冲语势,使人读到此处不由得放慢语速,拖长声调,去体会诗人的“此情此景此境”。
色、形、声,构成了形式美的人文内涵,三者都是相辅相成的。不仅诗歌,其他文体形式美的人文内涵大抵也包含这三个方面。形式绝非无言,绝非仅仅是承载内容的空架。人文内涵赋予了形式美经久不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