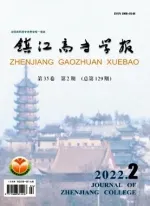试析“官分文武”之制中的怪现象
田 原,何 星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0 引言
《尉缭子·原官篇》中说:“官分文武,王之二术。”文武是一对复杂的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它体现在两者力量的此消彼长上,也体现在它们长时间的混溶之中。隋唐时科举制度产生,到宋朝“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确立,之后历朝无一不标榜文治,文官士大夫成为统治的中坚力量。而相较于“文人治国”的政治传统,武人的地位变化也十分值得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有黄宽重的《中国历史上武人地位的转变:以宋代为例》、穆静《五代军人的地位与处境及其影响》、陈峰《北宋武将群体素质的整体考察》等。但以往的研究大多从文武关系的对立角度出发,阐述“重文轻武”的传统及其影响。而笔者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官制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困境:在“官分文武”的制度设计下,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多疑及现实的无奈,使得文武关系长期处在一种失衡的状态下。文官武官虽然看似处在对立的关系中,实际上却不能完全实现两者的职权分离。尤其“文人治国”下的“文武混溶”现象,无疑是统治者对“官分文武”制度的一种自我破坏,这着实值得深思。
1 “官分文武”的制度设计
黄宽重认为,上古时代,贵族阶层都是标榜文武合一的,文武在社会上并无高低之分。而到了战国时代,“士”阶层中开始分化,一部分形成以读书为专业,取尊荣为目标的“文士”,称为“儒”;另一部分形成以慷慨赴死之精神相标榜的“武士”,也就是“侠”[1]388-389。顾颉刚在其《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中也提到了相同的观点[2]85-91。即战国时代,社会阶层中开始有了文武的分化。不过那时的文人能武,武人重文,文武关系是融洽的,相互地位也是平等的。笔者认为,真正影响文武关系的因素在于日后不断建立和完善的政治制度,所以,制度层面上的文武关系更值得我们关注。
据《文献通考·职官考十二·将军总叙》记载:“三代之制,天子六军。其将皆命卿。故《夏书》曰:‘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盖古之天子,寄军政于六卿,居则以田,警则以战,所谓入使治之,出使长之之义。其职在国则以比长、闾胥、族师、党正、州长、乡大夫为称,在军则以卒伍、司马、将军为号,所以异军、国之名。”三代的王是一国的最高政治和军事统帅,辅佐国王的王室贵族平时掌管民事,战时则为将带兵,并无专门的文、武官制之分。一直到秦建立前,都是如此。《通典·职官一·历代官制总序》中记载:“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不师古。始罢侯置守。太尉主五兵,丞相总百揆,又置御史大夫。”自秦时起,便形成了文臣、武将、监司三大职官系统,大致划定了中国传统社会政府体制的基本框架。不过此时,严格意义上的文官武官之分尚未出现。据说,“武官”一词最早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课之。”但由于尚处官僚政治的初期阶段,贵族政治遗留,真正的文、武官制之分是到东汉时期才明确确立的[3]。其后,随着职官制度的完善,文武官制的区分也愈加规范化、明确化。对于文武关系,黄宽重认为,中国古代是从文武合一走向了文武分途,文武关系趋于对立[1]388-391。这一现象伴随着唐朝科举考试制度的实行,文人阶层的兴起;经历了五代十国的军人干政,文人在政治上附庸于武将;再到宋朝的重文轻武、贬抑武将政策,文武地位明显转变,从而达到顶峰。宋朝对于军功阶层的抛弃,着重培养文官政治,要求官僚队伍各就各位的政策,使得文武分途成为宋代乃至日后朝代的定势。
笔者认为,对于社会管理,官分文武是必然的要求,治民和治军明显是两种不同的管理体系和需要,即使是在三代时期,贵族阶层集行政和军政于一身,平时为官,战时为将,这种职分的区分也是实际存在的。所谓“文武分途”,主要也应当是职分划分意义上的对立。为何到后来,不仅文武官制相区分,形成了文官和武官阶层,而且两者的相互地位和关系呈现出一种对立的形态呢?究其实质,这是王权出于其统治需要的一种选择。李世民曾说过:“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4]6030也就是说,无论重文还是用武,其都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宋朝自一开始就走上了文治的道路,也不过是统治者吸取五代十国军人干政的教训,忌惮武将罢了。文武分途并不是世人的刻意选择,也不是所谓学科或知识层面的专业化,它是一种政治制度的设计,其本意是让文武官相互监督和制约,可以看作是古代分权的一种手段。只不过由于文武本身的差异,统治者更加警惕掌握兵权的武将,所以在实施过程中向文官倾斜了。这也就是后世所谓的“重文轻武”之传统。赵匡胤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5]293可见,统治者不怕文臣贪污,但惧武将夺权。他们特意将文臣武将放在对立面,造成文武分途之局面,实际上也是帝王的一种统治权术。
2 怪现象之“文武分途”与“文武混溶”的矛盾
如前文所述,自宋代起,统治者尤其重视文官武官的各司其职。宋太祖对武将群体予以抑制,逐渐剥离了武官的民事职权,意图实现文武关系的平衡,稳定统治秩序。然而,政治制度中刻意制造出的文武分途似乎又被统治者自己打破了,这不得不说是文武关系中的一个矛盾点,那就是“文人治军”。其典型也是在宋朝,即任命文人担任主管全国最高军事行政机关的枢密院和兵部的长官,并充任部队的长官。有学者列出的统计表显示,在枢密院存在的167年里,枢密院正职共73人,其中文职出身55人,武职出身18人。副职共129人,其中文职出身108人,武职出身21人,文职出身的比例相当高,而从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年)到北宋灭亡为止,文官几乎将武官排挤殆尽,独掌西府长达71年[6]。同时,战时还由文臣任统帅,领兵作战,谓之“儒将”。文官向武官职分的入侵,明显不符合文武分途之说,倒像是“文武混溶”。到明清时期亦是如此,如赵炳然曰:“总督之职,即古帅臣,文武兼该亲督战阵。”[7]2651又如吴应箕说“将”:“‘将’何易言哉!今武臣之有‘总’有‘副’者,将也;文臣之为‘抚’为‘督’,即身为大帅而将将者也。武以材勇跳荡于疆场,文以方略发踪于帷幄,如是曰‘将’也。”[8]233说的就是明朝直接负责军事责任的文臣,谓之“文帅”、“文将”。清朝亦是如此,织田万也说:“盖清国之于文武官,其区分不甚分明。每遇有战乱,文职督兵致力无异乎武职……”[9]410所以,实际情况中的文武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权力机构中的文武在事权功能层面也原不曾有明确的分割。”[10]
文武分途的制度规划下为何又会出现这样一种“不甚分明”的情况呢?原因很多,但有一点必然是武官应有的权力和职分被缩减了,因而不得不由文官补上。统治者让文官分武官的权,是害怕武将专权,军人干政,帝位不稳。然而笔者疑惑的是,既然官分文武的本意是为了相互制约,那么过分的重文轻武是否会削弱分权的效果。更令人困惑的是,如果文臣一旦有了武将的权力,成为了“文帅”、“儒将”,那他的性质与武官又有何异?统治者那么警惕武官,如何就这么放心那些文人呢?现实中,“文武分途”的表面下,有着“文武混溶”的实质,不仅不利于军政的良性运行,更是违背了创制文武对立关系的统治者的本意。宋初开重文之风的宋太祖、宋太宗对于文人的态度也不是绝对信任的,有学者认为,他们心中“文”“武”分野并非惟一的措意范畴,“作兴士风”,端正“君臣之道”才是帝王所更加关注的[11]。正如赵匡胤所言:“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12]62他不是说要把武臣培养成“儒将”,成为文人,“知为治之道”即可,“道”就是儒家的仁德政治和君臣伦常,说到底,是忠君教育。制度设计者的初衷在于文武制衡,而最后的走向却令人扼腕。
与“文武分途”和“文武混溶”这对矛盾相对应的,还有长期以来存在的文人“尚武”和武人“右文”之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对现实制度不合理的最好说明。文武关系越不平衡的时代,这种现象越盛。例如宋明两代的文士尤好谈兵,士人对兵事的兴趣很高,宋人辛弃疾、陆游就是很有名的例子,而明代名臣于谦、王阳明、张居正等则均著有兵书。武人“好文”的例子也有很多,宋朝还有很多武官纷纷谋求由武资转换文资,做文官,要不就希望成为“儒将”。“武夫”成为带有蔑视和侮辱含义的称呼。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甚至有废除文武分科,求全才治天下的呼求。但这种寄希望与文武全才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想法是过于理想化和不现实的,正如王夫之所说:“若以古今之通势而言之,则三代以后,文与武固不可合矣,犹田之不可复井,刑之不可复肉矣。”[10]可见“文武分途”与“文武混溶”的矛盾不仅困扰着今人,也是古人一直想解决的难题。
3 结语
总的来看,古代的文武关系是十分复杂又矛盾的。“文武分途”与“文武混溶”这一对矛盾产生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对于文武关系的重新认识,更是对于所谓“文人治国”的反思。传统政治中,我们将治理国家的重任交给了士大夫阶层,这样的选择应该怎样去正确和全面地评价,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钱穆先生称赞古代的文武分职,军人不干政制度是中国旧制中的一项优良传统[13]29,但如果我们全面地研究“文人治国”的内容和文武关系的面貌,也许就能找到美好的制度设计为何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原因了。
[1]黄宽重.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
[2]顾颉刚.史林杂识[M].北京:中华书局,1963.
[3]张金龙.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官、武官与禁卫武官释义[J].江海学刊,2001(3):126-127.
[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6]陈峰.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方针[J].历史研究,2001(2):30-32.
[7]陈子龙.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吴应箕.楼山堂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9]织田万.清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10]赵园.谈兵(下):关于明清之际一种文化现象的分析[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2(2):5-14.
[11]邓小南.谈宋初之“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J].史学月刊,2005(7):51.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3]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