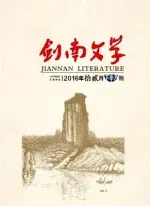历史•神魔•现实——浅论《封神演义》中“武王伐纣”的现实意义
李爱红
山东经济学院 山东济南 250014
神魔化历史是历史艺术化的独特方式之一:用神魔的外衣来装扮历史,放任艺术想象在历史的画卷上随意泼墨,但核心的历史框架依旧清晰可现——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可谓是一部另类的历史演义,历史人物的主角地位被神魔人物取代;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由神魔人物主宰;改朝换代之际,封侯与封神同行。但既然演绎了历史便同时关照了现实。因为历史题材的文学虽然以往昔历史为表现对象,但它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精神与当代思想精神应是息息相通的。正所谓“过去未来皆现在”。所以《封神演义》的神魔描写不是终极目的,尽管我们常常驻足、沉迷于“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神魔斗争,而将“武王伐纣”的史实搁置起来。但我们万不可忘却历史与现实这对孪生姐妹的存在。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美学家克罗齐曾经说过:历史“假如它有什么意义而不是一个空洞回声的话,那么它也是现代的”,“因为事情是明明白白的,只有一种对现在生活的兴趣才能推动人去查考过去的事实。因为这个缘故,这种过去的事实并不是满足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为了满足一种现在的兴趣”。为此,他认为现实感是一切历史“固有的特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关系是“统一性的关系”。
“善恶书于史册,毁誉流于千载”,中国自古以来的信史传统和“史贵于文”的价值观念,对中国文学的最大影响当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兴起,出于慕史、重史的文化心理,文人们纷纷操觚演史,大量名为《……志传通俗演义》、《……史演义》、《……志传》的历史演义小说问世。生活在农业生产社会,受封建制度钳制的民众对英雄创业、豪杰争锋、贤相安邦、权臣误国等改朝换代、朝政兴废之事尤为瞩目。尽管这类家国大事与他们熟悉的日常生活相隔甚远,但渗透在历史演义中的“历史感”深深吸引着他们。所谓“历史感”,通常指历史实录的逼真性、客观性以及独特性。但“历史感”不是独立存在的,它离不开“现实感”的参预催化。过于浅薄的历史感,未免会陷入矫情、幻灭之中。但如果没有具有社会功利性的现实感作为依托,历史感就会因单调的讲述和陌生、晦涩的人事与话语而显得过于厚重。那么历史感也就失去了历史本该给予我们的无可辩驳的思想哲理和认识审美功能。历史感与现实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使普通大众读者,在历史中可以看到他们熟悉的镜像,甚至捕捉到自己生活的影子。
《封神演义》作者为何选择这样一段历史来关照现实?首先是史实本身的原因。“武王伐纣”是讨伐暴君,遵循了历史前进的规律,而成为历代君王的警示牌;但又因其是以下伐上,违背了封建伦理的大道,而成为敏感话题。这一段带有双重性的历史,一直以来是被作为反面教材,强调其警示性,所以尽管有悖君臣之礼,反暴政的合理性却给予其在夹缝中生存的理由。甚至某些帝王或真诚或虚伪地以此自省,作为自己仁慈爱民的明证。明嘉靖皇帝就曾面对毅然等待死亡的海瑞说过:“此人可方比干,然朕非纣耳”。可见纣王始终是盘旋在历代统治者头上的阴影。所以作者选择了这段历史作为演绎对象,凭其合理性可以堂而皇之地“指东骂西”,宣泄心中的不满,大快读者之心;其敏感性,则给人以启示,生发出无限的想像——关于当朝帝王,关于自己的宗庙社稷,关于自己的未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题材的文学是和现实“对话”的文学,作家选择哪段历史,如何对历史事实增删取舍,主要取决于“对话”的需要,取决于主体的自觉创作活动的驱动。面对生生不息、不舍昼夜的历史逝川,作家的艺术思维必有褒贬臧否的选择取舍。因为并非一切历史都能适应与现实“对话”的需要,都能够“肆其胸臆”。当已然的历史变成了作家心目中的“历史”,它标志着作家已经投注了“现实感”,用现代意识同历史进行“对话”而达到了古今统一。黑格尔对此更是做了很好的阐释,他说:“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正当的要求,即对于一种历史,不论它的题材是什么,都应毫无偏见地陈述事实,不要把它作为工具去达到任何特殊的利益或目的,但是像这样一种空泛的要求对我们并没有多大帮助。
《封神演义》中“武王伐纣”的历史事实掩埋在神魔斗争的光影中,但剥离了神魔的外衣,历史感依然会扑面而来,作者投注的现实感也清晰可现。被夸大化的纣王的恶与文王的仁,是作者极力彰显的一个对立面,肯定仁政、痛贬暴政,抨击弊政奸恶,颂扬圣君贤相的思想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反观现实,小说恰如当朝的一面镜子。鲁迅曾说:“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足见出明朝统治者的残暴。明朝自朱元璋始,廷杖、剥皮、凌迟、抽肠等各种酷刑也不曾停歇,其暴虐程度绝不逊于造炮烙、蠆盆、酒池肉林的纣王。成化以后,最高统治集团渐趋堕落,王朝生活奢靡、腐化,武宗、世宗、神宗等,都是不务政事,恣肆胡为,酒色财气俱全的昏君,政治失控,思想文化统治趋于崩溃。然而,面对这样让人痛心疾首的政局,即使在“肆其胸臆,以为自得”的文网疏弛时期,文人学士的言路也没有畅通无阻,直言君之过尤其要慎之又慎。恰恰得益于“武王伐纣”这段历史的特殊性和小说的神魔外衣,作者做到了真正的“肆其胸臆”。商容在九间殿悲泣而奏的一段话,可谓恳切的忠良之言,足见出作者对当朝者的忠肯以及曾经心存的那一丝希望:“臣昔居相位,未报国恩。近闻陛下荒淫酒色,道德全无,听馋逐正,紊乱纪纲,颠倒五常,污蔑彝伦,君道有亏,惑乱已伏。臣不避万刃之诛,具疏投天,恳乞陛下容纳。真拨云见日,普天之下瞻仰圣德于无疆矣。”谆谆话语,肺腑之言。等到闻太师条陈十策时,已是在危急关头的“救时急着”,但至少希望还在,忠心不灭。“子牙暴纣王十罪”是国势倾颓后天愁民怨的暴发,愤恨可以发泄,但失望至极的悲哀、落寞成为沉重的十字架永远压在心头。《封神演义》的作者是不幸的,因为他生逢末世;他又是幸运的,因为《封神演义》给了他言说的机会。同样幸运的是同时代的小说读者。小说抨击弊政、歌颂仁德是带有相当程度的人民性的,这不仅反映了作者开明的政治观念,进步的历史观,同时也是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普通民众的一种精神宽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不再是虚无缥缈的理论,因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足以削去倒行逆施的失道之君的冠冕。尧舜之治是中国古代民众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对于这样的社会,早在二、三千年前,人们就梦寐以求了,但直到整个封建社会结束也没有实现。自然,善良的人们决不会放弃美好的理想,他们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圣明君主的身上,这对于灾难深重的华夏民众来说,无疑是一种理想之光,它至少可以作为一种标准或参照,以此来对黑暗的现实统治进行有的放矢的批判。《封神演义》中风景雍和,民丰物阜,行人让路,老幼不欺,市井谦和的西土社会实际上就是尧舜之治的现实缩影,读者在小说中体会到了他们期待已久的生活,也找到了踏入理想社会的革命路径。
毋庸置疑,《封神演义》托古讽今,曲折地反映了明代的社会现实。借古讽今历来是历史题材文学的题中之义。顾名思义,借古讽今是借历史来讽喻现世,其中必然有强烈的功利性与目的性。借古讽今的基本美学特征是讽喻,因而历史本身的含义随着文学历史世界中内容重心偏离了历史的具体存在,而逐渐暗淡下去,愈来愈清晰的是它的喻义所在,即作者赋予它的特殊的现实价值。“先欲制今而后借鉴于古”往往是历史题材文学作者的创作出发点,为了曲折地吐露对现实世事不便说明或不欲明说的看法,必须合理地选择一段历史将其看成某一现实生活或情感形式的对应物。在这里,作者首先关注的是作品对现实具体事件或“讽”或“谏”的隐喻效能;而对用以讽谏的历史本身的真实性,则通常颇为随意,大多情况下无非妄作“假借”或“假托”之用。“有时甚至为了特指的需要,不惜夸张乃至全然改变历史真相。……使被讽喻对象哭笑不得而又无可奈何,而读者方面则心领神会,直接从中受到联想和启发。”正如夏衍所说:“讽喻史剧的性质上就需要能使读者(观众)不费思索地从历史里面抽出教训来的‘联想’。”果戈里也说“借过去来鞭挞现实,这样的话,会获得三倍的力量”。《封神演义》的隐喻最先来自“武王伐纣”这段历史与明朝的隐秘关系。小说中大肆宣扬的是孟子的民本思想,《孟子》中的言论被反复提及、引用,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曾罢祀孟子,删节《孟子》,而且其中删节的言论都是由“武王伐纣”的历史引发出来的,所以历史本身对于现世就有着特定的喻义。此外,《封神演义》中纣王集诸恶于一身,文王成为仁政的化身,虽然远远偏离了史册记载,但讽谏的效能却大大增强了:公道自在人心,称扬王道、仁政,反对暴君、暴政的思想倾向自然地渗透到读者心中,尤其是感同身受的劳苦民众读者,共鸣之感尤为强烈。再者,小说中描写了几类惊人之举:臣叛君、子杀父、妻休夫,这些在当时有悖彝伦的伤风败俗之举,不是作者的主观臆想,而是现实激发的想象。明朝的“靖难”、“夺门”、“议礼”三件大事,都是封建宗法制所严令禁止下强横发生的篡逆、背叛行为,随着统治阶层对宗法制的冲击,下层民众的信仰也开始动摇,儒家伦理道德的矛盾性和虚伪性被越来越多的人嘲弄。《封神演义》中这些惊人之举隐喻的正是当时伦理道德缺失后,是非黑白的颠倒,以及时人的茫然和困惑。
确切而言,《封神演义》是一部历史题材的神魔小说,由题目即可知道小说重心在于“封神”,神魔描写是重点。但神魔外衣没有阻滞小说现实意义的发掘。一方面,借神演史的历史艺术化方式有着“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武王伐纣”是关涉革命与叛逆的敏感历史话题,高明的作者找到了神魔这个挡箭牌,为自己撑起了保护伞,因此可以卸却所有约束与顾忌,大胆地直击现实要害。另一方面,神魔小说的浪漫主义本身有着现实主义的基础。高尔基曾经说:“神话乃是一种虚构。所谓虚构,就是说从既定的现实的总体中抽出它基本的意义而且用形象体现出来,这样我们就有了现实主义。但是,如果从既定的现实中所抽出的意义再加上依据假想的逻辑加以想象——所愿望的和可能的东西,那么,我们就有了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就是神话的基础。”《封神演义》不是神话小说,但神魔形象与神话里的形象有相同的本质和生成机制,都可以视作一种概念的化身和思想的象征,对现实的概括、抽象和幻化。举例来说,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背叛正义和弃暗投明的现象,神仙中就有申公豹的卑劣活动,也有长耳定光仙的正义行为,这两个具体形象就概括了现实中某一类人的思想品质。再如申公豹外形描写,也是对现实生活的幻化。作者赋予他以一个面朝脊背的形象,这种超现实的外在标志,正是他助纣为虐、倒行逆施的象征。
诚然,历史多彩地塑造了我们,而又是我们人自身构成了历史。历史是我们生活的航舵,规范着我们的行为,规定着我们的话语,而又是我们以自己的话语宣布着历史的规定,用自己的行为延续着这种规范。历史是我们在时空舞台上表演的一幕幕故事,而又是我们记录、讲述着历史,把它变成我们的叙事。现实之于历史不是简单的影射或比拟,相似的历史进程给人同样的感慨,历史的重现或者时代化的演绎、摹写,可以帮助人们理解眼前的人和事。“重蹈覆辙”的悲剧常常发生,但有了像《封神演义》作者这样有敏锐体察力的先知先觉者,及时提醒、惊醒世人,悲剧也许就可以避免,至少是让人有备而战。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完整历程来看,现实是历史的发展,不可能不留下历史的痕迹;历史是现实的由来,也必然能从中找到现实某些事物的渊源,它们两者必然相互涵盖着某种超时空的,带有恒定性、普遍性的本质意蕴,相似禀赋。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真正深层的原因,似乎还应该到历史文学内在机制中去寻找。我们应该谨记爱•霍•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所说的:“我们既不是爱过去,也不是从过去中解放自己,而是掌握过去,理解过去,把它当作理解现在的一把钥匙,由此才能构成发展、丰富着的对话”。
[1][意]克罗齐,“历史和编年史”,转引自《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4-335页.
[2][魏]李康,《运命论》,[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296页.
[3][德]黑格尔著,贺麟等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页.
[4]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5] [明]黄佐,《翰林记》卷十一“禁异说”,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7页.
[6]《封神演义》第九回“商容九间殿死节”.
[7]《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版,第2680页.
[8][9]郭沫若,《从典型说起》,《郭沫若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年版,第543 页.
[10]夏衍,“历史与讽喻”,《文学界》,1936年(创刊号).
[11]高尔基,《苏联的文学》,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页.
[12][英]卡尔著,吴柱存译,《历史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