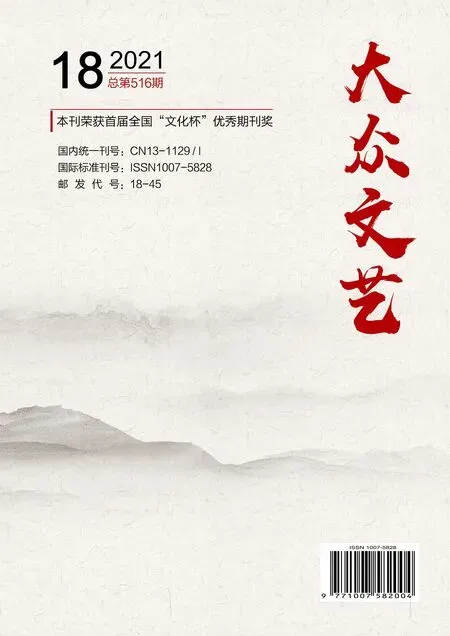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教学内容创新研究(之二)
吴海进 (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 贵州贵阳 550025)
在本项目第一阶段的研究中,详细论述了区域性文学风格(又称地域性文学风格)作品的创作主体身份、地域性风格的评价尺度和地域性文化根性等内容,可以说,现有的文学概论教材均未能作此深入的论述。那么如何将这个深化了的基本问题深入浅出地在教学过程中反映出来呢?该采用哪些方式方法来丰富课程环节,带动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呢?成功的教学活动,一方面在于教授知识的创新性,另一方面在于教授方式方法的艺术性。
人的所有社会行为都是对象化了的行为,教学活动也不例外,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对教授对象的知识结构、兴趣爱好、文学阅读经验等方面做细致的了解,进行有针对性的课堂内容准备。我校处在多民族聚集的省份,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中几乎少数民族生员占到60%(通常按行政班50人计算),苗、瑶、侗、彝、水、傣、回、藏、布依、仡佬等族学生在同一班级中,毫不夸张地讲,类似于联合国开大会,在上课过程中他们的眼神和表情是丰富到难以捕捉的地步。加之文学概论本身就是的理论很强的课程,按照传统的大学教学模式—“填鸭式”来整齐划一的满堂灌,毫无疑问,教学效果很差。
地域性及地域性文学风格体现得最明显的莫过于各民族传统文学作品和民族作家文学作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不是所有民族作家的文学作品都具有地域性风格,如扎西达娃上世纪的很多作品就没有这个特征,他的作品体现的是先锋实验的意味,对藏民族文化的传达是很少的。但是,类似于汪曾祺这样的非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则具有根植于其生活的土壤的浓烈的地域性色彩。在流派文学风格中,这种整体的风格差异更加明显。
因此,在处理地域性文学风格的教学中,首先要具备比较眼光和比较视野,在教学中采用对比模式来处理课堂内容。就单个作家而言,可以找出具有地域性风格和不具有地域性风格的作品做比较,可以从作家不同生活环境(居住地、社会变化、人生境遇等)中创作的作品进行比较,如近年在文学界影响较大的藏族作家次仁罗布2006年发表于《西藏文学》第4期的短篇小说《杀手》就是一篇力道不错、但不具有地域性的作品,它是一部西化非常严重的非理性主义小说文本,然而从2009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放生羊》以来,开始专注于贴近藏民族的心灵世界,其作品中所彰显的藏族文化根性可谓是力透纸背,今年发表于《民族文学》第1期的中篇小说《神授》就是明证;就不同作家而言,尤其是民族文学作家,可以比较其体现民族性、地域性差异的作品。如同属京派作家,沈从文和老舍两位现代文学大师,各自的地域性风格及其所追求的文化根性是差异非常大的,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和老舍的北平胡同世界显然体现出两位作家不同的情感倾向,前者是从都市来寻找精神的栖息地,后者则专注于都市中小人物的命运并以此来反映时代的变迁和历史事件对个人的冲击;就作家的身份而言,可以从民族作家与非民族作家来做比较,这类比较不是看写什么,主要看怎么写,使用怎样的语言,在话语特色上有怎样的差异,因为语言的差异其实就是思维方式的差异;当然也可以从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上作比较,如同属史诗,《荷马史诗》是作家文学,而我国的《格萨尔王》《阿诗玛》等就是民间文学,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语言、故事的叙事等作比较,以此来反映中西方关于史诗的概念、史诗风格的差异性。如此等等,在课堂上充分使用比较眼光和比较视野,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均可纳入,活跃课堂,启发学生的思考。
第二,在深化区域性文学风格的认识上,使用跨文化的研究视角,将跨文化的思维向度补充进课堂教学中。在西方,言必称希腊,以为这是西方文化的源头,如果不了解西方古代史,则容易对基本的问题产生误解,在近几个世纪的考古发掘中,“希腊源头”之说也越来越显得理屈词穷。在人类早期文明中,文化的交流已经开始,那么要追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就得从早期开始,而不是站在21世纪的瞭望台上去寻找。张忠利、宗文举合著的《中西文化概论》[1]一书中从地理状况、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三个大的方面详细地论述了中西方文化的成因和起源,其中将地理状貌作为一个基本切入点,在生产力低下的早期社会,人所有的行为和社会活动基本是遵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模式,不像我们现在的多元立体性商业化模式。同样,要了解我国南北方文化差异的问题,也不能仅仅从现象上入手,而应该从基本的地方性知识入手,如地方性的气候、土壤、时节变化、植被覆盖、人口迁移和饮用水源等实际性问题来揭开一些作品中的相关问题。如当代作家张承志的作品《黑骏马》《北方的河》以及他笔下的西海固,这些作品中关于人所处的艰苦环境以及人的坚强意志的凸现,均是“文化持有者内部眼界”的深描和深刻阐释,在难以想象的生活绝地中保留着一批精神上无比强大的人。张承志正是基于当地信仰的产生、当地信仰者的精神世界和精神传统来敬畏和颂扬的,因此,他的文本不仅是文学作品,更是一部部形象化的了心灵史。以《黑骏马》为例,很多学生在看完这个作品之后,发问较多的是:为什么白音宝力格要离开草原?为什么索米娅还要生下其其格这个孩子?如果要给出答案的话,这些学生会拿出一副道德的手铐,将白音宝力格锁在负心汉的道德审判柱上。这种简单认识导致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没有把握地方性历史知识和地方性人文传统。社会变迁过程中,旧的观念意识按照现实的原则在运行,而新的观念则是以脱离本源地在滑行,这是白音宝力格与索米娅二者身份不同之所在。索米娅是草原的守望者,而白音宝力格是草原的养育者和逃离者。因此,这个故事的悲剧性也就彰显得异常的美丽而无奈。在贵州,苗族及其文化可以说和汉族及中原文化一样悠久漫长,虽然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是其语言则一直保存在苗族人的日常生活中。在汉化程度不算太深的苗族地区,依然流传着本民族的古歌、仪式和说唱样式,这些都是与苗族的信仰、习俗、历史以及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地方性知识与地域性文化特色异常鲜明。诸如此类的地域文化与作品的世界进行恰当的联系、分析,就能使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更加具体、明了。
第三,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弄清楚一个基本问题,即作家个人的创作风格与地域性文学风格的关系。王元骧在《文学原理》中谈到了民族风格、时代风格、流派风格与个人风格的关系,他说:“在它们之间,个人的风格总是基础。因为文学创作都是通过作家个人来进行和完成的,而作家的创作个性既然都是在个性心理特征的基础上,通过长期创作实践所形成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统一体,所以不论它多么独特,总是以主观的形式反映着作家所属民族、时代和社会集团的物质生活和文化心理……表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他进一步指出:“文学作品的个人风格、民族风格、时代风格和流派风格又毕竟不是同一层次上的概念。就生成的原因来说,个人风格主要由作家个人才能的特点所决定,民族风格主要由作家所属民族的文化意识和文学传统所决定……并不是每一个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家,都有同样鲜明的民族风格、时代风格和流派风格,它们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不平衡的。”[2]王元骧的学术观点非常明确地廓清了一个基本问题,即作家个人风格只是其他风格的基础,并非唯一评价要素和尺度,这与笔者前期批评诸多文学概论教材中论述区域性文学风格存在的问题时提出的质疑有相似之处。试想,如果分析、评价一部作品,只是简单地将其比附于作家个人创作风格,那么我们何必读这个作家的其他作品呢?如果简单比附于作家个人创作风格,在理解具体作品的时候就会形成偏狭之见。我们总不能因为读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就简单地将爱、美、自由以及“三美”主张套用着去评价他的其他所有作品,未免有贴膏药之嫌。这就要求在解释和阐述作家及其作品的时候,需要发现作品的差异性和可能性意义空间,仔细阅读同一作家的多个文本及其多种有效理解意义,找出其关联性,我们会发现:作家的文化特质往往在不同文本之间形成互文性,打破传统的文本是封闭性系统的观念。尽管王元骧没有在教材中具体谈论区域性文学风格的相关问题,但是他的这种学术眼光和对问题的深入探究,给区域性文学风格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思考路径。
作家的个人风格因个体差异如气质、禀赋、敏感、生理等不同而不同,这个具有现实条件的限制性和局限性。从意识层面讲,作家个体风格的不同显现于文本中具体的话语以及话语背后所表征的思维差异,这是属于人的意识认知范畴的问题;而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中体现的地域性风格,则不是简单的意识层面的问题,而应从个体无意识这个层面来考虑,因为文化的存在与演变是不以当人个体的意志为转移,它会通过改变、迁移、涵化以及分割等方式借助外力和社会关系等内化为某一族群的心理记忆,它是集体无意识中原型的样子。然而作家毕竟是单个个体,那么,在书写区域性文学风格作品的时候,族群性心理记忆有可能在“浅睡眠”中溜进作家的笔下世界,这些是与作家的气质、禀赋、敏感、生理等形成的个人风格要素是无关的。地域性文学风格展现的合理理由不是在文字上做描摹,而是文化根性及其文学特色的心理隐射。
总之,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的教学内容上的创新可以直接带动教学方式方法的变化,比较眼光和比较视野是突出地域性文学风格的衡量尺度,跨文化研究的视界则是分析文本内部因素与外部生成的重要依据。同时,在教学中,需要弄明白作家的个人风格与文学中地域性风格的区别与联系。三个立足点都对解决区域性文学风格有着关键性作用。
[1]张忠利、宗文举.中西文化概论[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30.
[2]王元骧.文学原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16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