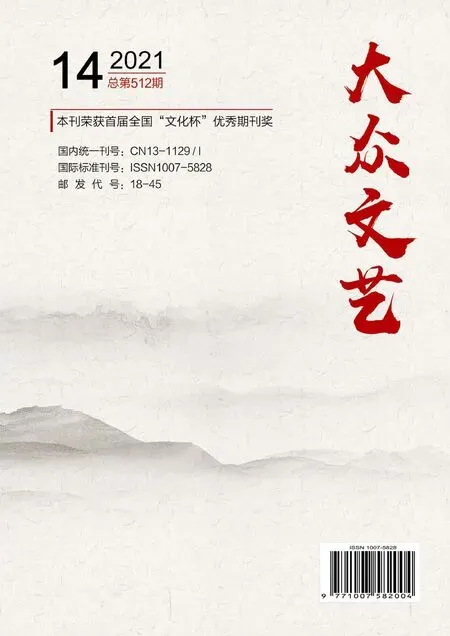蜘蛛网后的天地——由唐传奇与易卜生戏剧女性命运的分析探当代女大学生的生存前景
周婷婷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陕西汉中 723000)
一
文学就像一个蜘蛛网,总是四角附着在人生上的。缀网劳蛛的是那些用一颗热心冷眼审视着社会百态的勇者。古今中外莫不如此。透过他们剖心沥血编织的千千网,会发现粘附于其上的虫豸——人类的弊病、社会的痼疾、女性的悲剧。易卜生戏剧和唐传奇中涉及妇女问题的创作即是如此。
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在其戏剧创作的鼎盛时期(1869——1883),其最杰出的成就是创作现实主义的社会问题剧。这一时期他完成了六个剧本,其中直接涉及到妇女问题的有两个——《玩偶之家》和《群鬼》。易卜生曾强调,人们欲了解他,必须先了解挪威。19世纪70、80年代的挪威,经济发展迅速,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条件限制而形成的停滞生活逐渐活跃起来,挪威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发展中的弊病以及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也日益显露。
而唐传奇兴盛的中唐时代,中国处于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这样一个男权社会,妇女是毫无地位可言的,至于挣扎于社会最低层的侍婢、媵妾、妓女,她们更是戴着旧而粗劣的阶级镣铐。这在唐传奇里俯拾即是:《霍小玉传》《柳毅传》《李娃传》《莺莺传》等等。
蒋防的《霍小玉传》写娼女霍小玉与才士李益的爱情悲剧。每读此篇,我们往往执着于霍小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韧刚烈,而忽视了两个人物—霍小玉之母和李益之妻。霍小玉之母净持本是霍王宠婢,霍王刚死即被“诸弟兄以其出自贱庶,不甚收录,因分与资财,遣居于外。”[1]可想而知,那寥寥资产怎够没有经济来源的母女维持生计?如此只能让其女自堕娼家,这对一位母亲来说是怎样的无奈之举。无独有偶,易卜生继《玩偶之家》后关于妇女问题的又一部剧作《群鬼》中也有相似的情节:安格斯川为了金钱,竟然无耻地诱骗他的继女吕嘉纳去卖淫。更可悲的是,吕嘉纳在知道自己是私生女而且无望去她所向往的巴黎时,甚至做好了在无路可走之际,主动去“阿尔文公寓”卖淫的打算。这又验证了鲁迅那句话“不是堕落,就是回来。”[2]
读《霍小玉传》会很自然的同情小玉被李益无情抛弃的不幸遭遇,但谁又会看到李益后娶之妻卢氏的凄惨婚姻呢?在唐朝,卢姓乃豪门望族,卢氏更是李益的表妹,嫁给李益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必然结果。先不论李益与霍小玉之间的纠葛,单看霍小玉死后,李益由于良心不安而承受着小玉诅咒后,他“自此心怀疑恶,猜忌万端,夫妻之间,无聊生矣……尔后往往暴加捶楚,备诸毒虐,竟讼于公庭而遣之。”[1]卢氏又何其无辜!女性没有婚姻自主权,只能是家族利益的牺牲品,婚姻并不是男女感情的事,而是家庭贪婪的工具。《群鬼》的主人公更是如此。阿尔文太太因为一分家产被迫嫁给风流成性、嗜酒如命的阿尔文,婚后即暴露了他拈花惹草、荒淫无度的肮脏面目,甚至于“索性把丑事闹到自己家里来了。”[3]阿尔文太太表面风光的十九年婚姻生活就是这样的一片苦海
对于这种只剩下痛苦与煎熬的婚姻,卢氏与阿尔文太太的反应可谓同中有异。物质上,离开原本所依傍的男人和家庭,她们自己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生活上,卢氏恐怕只能回到那个专制大家庭——再次被待价而沽,阿尔文太太更是无所依从;精神上,卢氏谨奉三从四德,阿尔文太太在曼德牧师的引导下信奉着那个不断给她带来苦难的上帝。卢氏最终还不明白丈夫为什么对她拳脚相加乃至被遣;阿尔文太太婚后一年曾向曼德牧师求救,她也曾反抗过,在上帝的引导下她又回到了恶魔的怀抱。稍感宽慰的是,她除了忍受惨痛的婚姻生活外,还有事可做,“添置了产业,做了些改革工作”,[3]甚至筹办孤儿院。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为了自己的孩子不能不忍受”,“要不是有事可做,那日子也没法过。”[3]这也是卢氏不可能也做不了的事。
从女性的家庭观、婚姻观而言,卢氏与阿尔文太太的悲剧表现及其原因具有相似性。表面看来是遇人不淑、上帝安排,其实质是维持悲剧不断上演的法律制度在作祟,还有稀奇百怪、陈旧腐朽的思想观念在世人甚至更多的是在女性自己心里作怪。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以卢氏为代表的自幼即被灌输三从四德观念的古女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吸取教训,规避悲剧的重演。而阿尔文太太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发出“我再也不能忍受,我要争取自由”的呐喊。[3]
二
同样出自易卜生笔下,较《群鬼》更早两年问世的《玩偶之家》,那个为全世界所熟知的女性—娜拉,真正迈出了争取自由的第一步。那“砰的一响” —关大门的声音也震醒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渴望自由、追求自主幸福的无数女性。
中国有句古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忠于职守,从不寻花问柳,对妻子温存体贴”[4]的海尔茂危急关头的言行无疑充分应证了这一点。海尔茂自始至终都把娜拉当做一只宠物,诸如“小鸟儿”“小松鼠”之类;一个“爱花钱”“爱吃甜”的孩子;一个没有思想没有经济能力,完全依附他,只供消遣取乐的人形玩偶而已。小到个人兴趣爱好,大到家庭经济,他对娜拉的言行控制,真可谓是目力所及无所不至。娜拉为过圣诞节买回了许多物品,海尔茂的反应是“你又买东西了?什么!那一大堆东西都是刚买的?我的乱花钱的孩子又糟蹋钱了?”[3] 他对娜拉一面“小鸟儿”“小松鼠”的亲昵叫着,一面像责备爱花钱的几岁孩童那样说教。可见,在这个所谓的幸福美满的家庭里,娜拉是没有任何经济支配权的,因为在海尔茂心里,娜拉实际上并没有为这个家挣过一欧尔。与其说他是妻子,还不如说她是这个家庭的第四个孩子,会唱歌、乱花钱的孩子。
这种家庭经济收入一元化状况,是导致娜拉伪造签名借债的直接原因。作为家庭唯一支柱的丈夫倒下,而身为附庸闲物的妻子没有任何经济能力去救治丈夫。这也造成家庭中一方压过另一方,面对危机不能共同担当的状况。一幕悲剧由此上演,家庭的悲剧却是作为女性娜拉们的喜剧,虽然这个喜剧来的不那么令人愉快。
显然,李朝威《柳毅传》里龙君小女的婚姻境况就理想多了。
《柳毅传》主要描写儒生柳毅英勇解救远嫁异地被逼牧羊的洞庭龙女,并与之几经周折,终奉欢好的爱情喜剧。
我想柳毅与洞庭龙女之所以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除了李朝威或者说中国大众的理想情节;柳毅的豪侠刚烈、重情重义;还有某些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说洞庭龙女不再是龙君小女,也没有财势熏天的洞庭龙君做父亲;没有勇猛暴烈、视其如己女的钱塘龙君为叔父,而是和娜拉一样,除了丈夫别无所依,即便柳毅再怎么豪侠重情,一介书生又如何插足他人婚姻?如何解救龙女于水火之中呢?她还有着娜拉无可比拟的优势。为了答谢他的救命之恩,“龙君因出碧玉箱,贮以照夜玑。皆起进毅。毅辞谢而受。”[1]又说:“宴罢辞别,满宫凄然,赠遗珍宝,怪不可述……毅因适广陵宝肆,鬻其所得,百未发一,财以盈兆。”[1]二人婚后,“前列丝竹,后罗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间。”[1]。而娜拉,面对丈夫积劳成疾,不去南方疗养就有生命危险的境况,自己却只能想出伪造签名背夫举债之计,何其艰难。
伍尔夫曾在她的女性文学论著《一件自己的屋子》里向世人发出惊世骇俗的疑问——“为什么男人喝酒,女人喝水?为什么这一性那么富足那一性那么贫乏?”[5]这种贫乏是女子的不幸,更是社会的悲剧。它到了易卜生那里,便酿成了家庭的崩溃。
当柯洛克斯泰以伪造签名事件威胁娜拉之时,娜拉为了保护海尔茂的声誉和地位,已经做好了投水自杀的准备。然而,这个可怜的女人要面对比死亡更让她难以接受的事情——丈夫的转变。危机发生前,甜腻地称她“好宝贝”“亲宝贝”“小宝贝”的那个丈夫,在仅仅看到那封来自柯洛克斯泰的信,甚至还没看完,就显露出他穷凶极恶的丑陋面目。刚刚还声称“我常常盼望着有桩危险事情威胁着你,好让我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3]现在只剩下对娜拉的谩骂和指责:“没想到是个伪君子,是个撒谎的人——比这还坏——是个犯罪的人……你把我一生幸福都葬送了。我的前途也让你断送了……我这场大祸都是一个下贱女人惹出来的!”[3]他甚至不介意娜拉去死,只是觉得她的死对自己没有一点好处,甚至会让他惹祸上身。但是当事情有了转机,确认自己没事了,他又换成另一副嘴脸,再次声称:“你放心一切事情都有我……我可以保护你,像保护一只从鹰爪子底下救出的小鸽子一样。”[3]海尔茂始终都没有变,娜拉却已经看清她所谓的丈夫只是将她当做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哄她开心也可贬之于尘的男人;她所谓幸福、有无限美好蓝图的家庭只是一个空洞的“玩偶之家”。娜拉此时才算真正的成长起来,在那八年的婚姻生活里,她除了伪造签名那一“壮举”,其言行就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试想如果没有这次风波,那么她还将如千千万万个妇女一样,沉浸在幸福的泡沫里。
娜拉又是不凡的,她能挑战悖于情理的法律,无视虚伪的社会道德去救病得快要死的丈夫,就一定有胆识走出这个框限了她八年的“玩偶之家”她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我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3]娜拉以她毅然决然的出走彰显了女性觉醒的力量,而更多的女性却还不具备自我救赎的条件和力量,她们只能以另一种悲剧的形式倾诉自己的不甘与不幸。
蒋防笔下,霍小玉即是如此。
霍小玉本是霍王小女,因父逝而母身份卑贱被驱逐,最终沦为娼家。这般境遇,如此身份,于世情,她和李娃一样本是通透彻观,看尽世态炎凉的。所以她才会“极欢之际,不觉悲至”,对李益有那样一番表白:“妾本娼家,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思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1]。李益的反应与海尔茂的转变有“异曲同工”之处,李益信誓旦旦地说“粉身碎骨,誓不相舍”,又主动提出“请以素缣,著之盟约”,可谓山盟海誓、言之凿凿。岂知家中太夫人已为他定下婚约,李益当然是“逡巡不敢辞让” ,而霍小玉还在苦苦探寻他的音讯。当怯于再次会面的李益被一豪士强行带到她面前时,小玉“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继而“斜视生良久”,发出千百年来被抛弃、受侮辱的中国女性对男子,也是对男权社会的斥责和诅咒:“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6]
霍小玉最终“长恸号哭数声而绝”。不同于19世纪挪威正在觉醒的女性代表娜拉以决然出走来表达对家庭社会的愤怒并追求自我新生,封建社会受欺凌女性代表的霍小玉,不可能意识到造成她爱情悲剧人生惨剧的社会原因,更没有能力与整个黑暗残酷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观念相抗衡。她坚贞美好的爱情寄托是绝不容于那个社会的,而她似乎也除此别无所愿,所以她只有死路一条,只不过她的死博得了世人的同情和怜悯而已。更多的人把她当做小说中美丽悲凄的女主角来品评,很少有人把她当做一个活生生的人看,意识到比她更悲惨的女性实在是不胜枚举。即使推及至今,谁又敢说这样受侮辱、被欺凌的女子不存在呢?
娜拉还可以“回到从前的老家去”,找点事情做,而霍小玉除了自怨自艾,继续从事妓女的行当,别无选择。这也是娜拉出走,而霍小玉走向死路的一个因素。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社会历史环境的不同及对自我认识的迥异。19世纪的挪威,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女性也可以做些编织、绣花以外的事情以维持生计。《玩偶之家》中的林丹太太就是典型的例子,她通过娜拉的引荐,可以在银行谋求一职,而且之前林丹太太还“开了个小铺子,办了个小学校”。这于霍小玉所处的中唐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再者,通过伪造签名借债危机,娜拉已然看清这个“玩偶之家”的真面目,而且她已经“从梦里醒过来”,坚信自己是跟海尔茂一样的一个人;小玉难以避免的有一种下层女子,特别是最为世人所不耻的娼家女的卑贱感,她从一开始就是以一种依附的姿态与李益生活在一起。当遭遇背叛时,她无力抗争,只能以死相咒。她认为她的不幸是李益甚至更多的是李益之妻造成的,所以才会有“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 [6]的诅咒。
三
易卜生戏剧的特色之一就是在剧中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并让其主人公们就此进行激烈的争论。我们通常认为易卜生在剧中提出问题,但并不指明解决问题的途径。易卜生也说过:“我的工作是提出问题,我对这些问题没有答案。”[3]《玩偶之家》似乎完全符合这一特点,易卜生告诉我们娜拉终于出走,但没有告诉我们出走后的娜拉如何生存,是堕落,是回来,还是另一条未知的路。
但是,我们忽略了林丹太太这个角色。剧中林丹太太是作为娜拉故友的形象出现的,丈夫死后,一无所有,还要照养重病的母亲和两个弟弟。在亲人需要她维持生计的三年间,她开过小铺子,办过小学校,就像她所说:“反正有什么做什么,想尽方法凑合过日子。”[3]而娜拉为了还巨额债务,不但生活上竭尽节省,而且“弄到了好些抄写的工作”,“每天晚上躲在屋子里一直抄到后半夜,”[3]我想象不出这样的娜拉有什么堕落的理由。鲁迅所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应该是指民国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中国式娜拉们的抉择和可能的悲剧下场。最终,林丹太太与旧情人柯洛克斯泰在海尔茂家里偶遇并走到一起。林丹太太这样对柯洛克斯泰说:“我一定得工作,不然活着没意思。我现在回想我一生从来没闲过。工作是我一生唯一最大的快乐。现在我一个人过日子,空空洞洞,孤孤单单,一点乐趣都没有。一个人为自己工作没有乐趣。尼尔,给我一个人,给我一件事,让我的工作有个目的。”[3]林丹太太的工作目的论不仅揭示出女性更道出绝大部分人的观念,具有普遍性意义。
易卜生通过林丹太太艰辛的生活以及她之后的选择,为即将或已经出走的娜拉们展现了一条发人深思的道路。
《群鬼》中的安格斯川是个卑劣、唯利是图的家伙,但是他有句话值得我们这些涉世未深的女大学生谨记——“外头迷魂阵太多,不容易抵挡。”[3]步入大学,意味着一脚已经踏入纷繁扰攘的社会,我们或早或晚都要面对各种选择,是就业还是考研、出国亦或嫁人。就婚姻而言,在当今这个普遍开放、相对民主的社会,诸如卢氏、龙君小女式的包办婚姻已不多见,但娜拉的出走,霍小玉的悲剧,给我们当代女大学生的启示是深刻的。难道娜拉和海尔茂的婚姻就不是自主的吗?难道霍小玉和李益就不是自由恋爱吗?她们何以一个离家出走,一个以死相抗?如果说娜拉的出走是觉醒的开始,霍小玉的死便是无奈之举了。
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字——穷。正如伍尔夫所言:“女人历来是穷的,不仅是三百年来,而是有史以来就穷。”[5]鲁迅也说﹕“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吧,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为钱而卖掉。”[2]
在霍小玉、李娃的时代,女人没有正当职业可以维持生计,至于原因,不必赘言。幸运的是,我们当代女大学生可以和男生竞争上岗,我们有更为广阔的就业空间;不幸的是,在当代这个所谓民主开放,讲究公平竞争的社会,很多用人单位更愿意招收男性。这是个很可笑的链条——女大学生工作后要结婚、生育、哺乳、养育幼儿,男性及社会舆论也要求女性将精力更多的倾注于家庭;用人单位却因为女性经期、孕期、产褥期、哺乳期等“四期”增加成本而拒绝女性!
社会竞争是残酷的,更何况是不平等的竞争。当代女大学生面临的是比男子更为严峻的就业压力和生存境遇。社会的变革、观念的颠覆不在一朝一夕,而就业、生存却是迫在眉睫的事。
身处在这个“迷魂阵太多”、公平太少的社会,我们该何去何从?
生活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伍尔夫曾预言:“我想再过一百年女人不再是被保护的人了,她们自然会很合理地参加一度拒绝她们做的种种活动和苦工……等做女人这件事不是一个被保护的职业以后,什么事都会发生出来。”[5]
社会现实也要求女大学生克服传统观念和心理障碍,女性不同于男性,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脆弱的理由。像卢氏、阿尔文太太那样痛苦悲哀的活着,经历娜拉玩偶似的婚姻生活,恐怕都是我们所深恶痛绝的。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事情就是凭借自己的力量骄傲、自主地活着,就业无疑是其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经济保障。那么怎样就业或者说如何更具竞争力?
首先,我们要全面地认识自己,要有身为女性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我们不必像霍小玉那样妄自菲薄,更不可像娜拉一样无知地充当他人的玩物。男女价值体现领域也许不同,但其价值大小本应是相当的。中国自古以来就讲究阴阳调和,况且世界这么大,市场经济又千变万化,如果只有一性,如何应对?而且,女性的直观感觉、语言表达能力、形象思维能力;女性的耐力、韧性较男性都有明显优势。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积极主动地去适应社会。
其次,参加社会实践,锻炼实际工作能力。大学生被“锁在”校园或图书馆里是很可怕的,大学也不该沦为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不应被课堂、图书馆所局限,不仅要充实理论知识,更应放眼社会,利用实践活动最大限度地丰富自己。不仅动脑,更需动手,以期更有效、更快速地融入社会,满足用人单位对我们实际工作经验及能力的要求。
我们具有较娜拉、吕嘉纳、霍小玉她们远不具备的社会条件去争取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也有能力规避她们的悲剧。
她们的不幸一定程度上是由经济能力的欠缺造成的。而现在,据世界银行估计,“全球女性2014年的赚钱能力将达到18万亿美元,是中国与印度两大新兴国家GDP的两倍多”[7]。将来,我们可能会经历一段漫长而又劳碌、黯淡的生涯,但我们完全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努力在这个充斥着种种压力与竞争的社会,越走越好。
[1] (宋)李纺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4年,第2010—2359页.
[2]鲁迅.鲁迅散文杂文. [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329页,第330页.
[3](挪威) 易卜生. 易卜生文集(第五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29—250页.
[4]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上).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87页.
[5]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件自己的屋子. [M].王还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150页.
[6]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24页.
[7]袁岳:苏菲的选择.[J].中国企业家,第357期,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