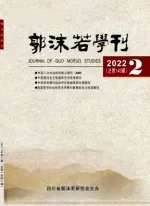片断回忆
郭汉英
要了解郭老,单从学术角度来看就不简单,同时又必然要涉及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我是搞物理的,学识和能力都很有限,对于社会科学和政治更是外行,只能追述我所接触、印象较深的几件事。当然,大凡追忆都难免受到心理、观点和水平的限制,何况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对于有关问题有不同看法,是不可避免的。在我们这个时期尤其如此。
父亲对子女是身教多于言教,即使言教,也往往是点到为止。他鼓励我们独立思考、注重方法。这种点到为止,反而印象深刻。
一
周恩来一直是父亲最为敬重的一位领导。1946年,父亲在内战爆发前所作的《南京印象·梅园新村之行》中对周恩来有传神的描写:
轩昂的眉宇,炯炯的眼光,清朗的谈吐,依然是那样的有神。对于任何的艰难困苦都不会避易的精神,放射着令人镇定、也令人乐观的毅力。我在心坎里,深深地为人民,祝祷他的健康。
早在1927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安庆惨案,父亲随即奋笔疾书了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4月12日,蒋介石公开背叛大革命,父亲很快受到“通缉”。不久,父亲赶往南昌参加周恩来、朱德领导的八一起义。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南下途中,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初,周恩来等决定父亲赴苏,却因病错失机会。随后又决定先潜往日本。然而,他在日本受到严密监视,无法脱身。1937年抗战爆发,一直与地下党有联系的父亲冒险回国投身抗战,成为长江局领导下的秘密党员。母亲于立群也是由周恩来、邓颖超等正式引上革命之路的。1938年5月在武汉,邓颖超作为介绍人之一,书面通知母亲,她被吸收为党员,而另一位介绍人正是父亲,这位就工作生活在她身边的秘密党员。
1941年11月,在祝贺郭沫若五十诞辰时,周恩来曾高度评价郭沫若,说他有三个特点,即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战斗生活,称郭沫若为“革命文化的班头”。
在重庆期间,周恩来经常来家里与父亲以及文化界的朋友聚会。正是由于与周恩来、邓颖超如此密切的关系,从小我们就称他们为“好爸爸”“好妈妈”,我们也就被称为“好儿子”“好女儿”。不过,我从小傻头傻脑,从当年的照片上还看得出来;老舍先生一见我就叫“大傻子”。庶英伶俐乖巧、记性又好。世英最淘气、好打抱不平,好爸爸叫他“小土匪”。
正是这个“小土匪”,长大之后反叛精神也强。高中时期还是中学全校大会的旗手。考进北大哲学系时正好赶上三年困难时期。他那个使父亲无言以对的“三面红旗”之下为何有人饿死的问题也反映了他的个性。后来,世英和几个中学同学组织的读书小组,被打成“反动小组”。那无非是一些青年学生基于独立思考的议论,至于“反动行为”,毕竟查无实据。在总理亲自过问下,世英被保留学籍,下放到河南黄泛区农场“劳动锻炼”。我和弟妹们都不理解,当年可以信奉无政府主义,可以“粪土当年万户侯”;今天却容不得同样是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的独立思考!?
父母亲嘱咐我到农场去看望世英。世英和农场的工人相处得很好,外号“狮子”的全国劳模和其他农工很喜欢他。接触了农业生产实际的他,了解到不少真实情况。1965年夏天,经总理同意,世英结束劳动锻炼,继续学业。世英打定主意不再搞哲学,而要学农业技术,从北大转到农大。然而,“文革”开始后,农大“东方红公社”的头头恰恰被“中央文革”控制,成了反对总理的急先锋。没有多久,世英就被“揭发”出来,作为反对总理的“重磅炸弹”。1968年,“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群众专政”等提法盛行,世英的处境非常危险。记得在和他讨论“群众专政”与无政府主义没有什么区别之后不久,他就被“隔离批斗”。几天之后,世英受迫害致死。总理办公室马上派人前往调查,仍无法查明真相。
1967年春,在海军服役的民英不解刘少奇同志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头号走资派”,马上要转为正式党员的他,在苦闷中离开人世。一年后,世英又诡异死去。连续的打击给年逾古稀的父亲和体弱多病的母亲带来极大痛苦。父亲无言地抄写民英、世英的日记,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
1970年2月,在外交工作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下,父亲以特使身份出访尼泊尔。总理亲自来家里送行,特意提到世英。他说,迫害世英,不仅针对你们,也是针对我的。
二
文革期间,江青想利用郭老在戏剧艺术上的声望,要他担任样板戏的顾问。父亲一直不赞成大树八个样板戏的作法,在庭院中散步的时候,曾经不无幽默地说:现在不是“百花齐放”,而是“八花齐放”。他清楚江青的用意,拒绝了这番“好意”。后来赶上珍宝岛事件,江青又借口保护郭老的安全,请郭老搬进钓鱼台居住。理由是钓鱼台国宾馆防空设施好,再者可以随时听取郭老对样板戏的意见,并且把这两条理由通报给了有关的中央领导。父亲再次以年老耳背为由婉拒住进钓鱼台。自然,样板戏顾问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这件往事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可过来人都会知道,这在当时需要何等的胆识和勇气。
“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闹剧开始不久,社会上就广为传播“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为共产党,崇拜孔二先。”“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的“最高指示”。
1974年1月,在各部委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之前,总理来看望父亲,转交了主席的诗,又语气沉重地说:我是温和派,在一些人眼里,温和派就是右派。当时,总理要我留在家里,帮助父亲准备材料,以备万一。
不久社会上又传出领导讲话,说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其实,早在1973年,江青等就秘密组织写作班子,准备公开批判《十批判书》,并把暗箭射向周总理。
那时候,江青、张春桥先后到家里来过。当时我在家里,为重听的父亲传话。江青、张春桥指责郭老抗战期间写下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要父亲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承认《十批判书》批判秦始皇、肯定吕不韦是错误的。江青一伙的居心叵测,使郭老反感、愤怒到极点。他当面驳斥张春桥:“我当时是针对蒋介石的”。张春桥无言以对。
郭老当然清楚江青和张春桥的来头,他深信历史自有公论。其实,父亲早就料到会有这样一天。“文革”伊始,他就公开表示要烧掉自己的著作,辞去科学院院长。这是他对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一种警示:他做好准备,愿涅槃得以再生。只是他没有料到,过了八年,不同的学术观点竟被提到如此的政治高度,其用心显然并不在他个人,而是针对“那个宰相”。
在“批孔”那段时间里,由于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前途深切的忧虑和来自社会各方的巨大压力,父亲明显衰老下来。就在江青到家里纠缠了两个多小时的当天晚上,他的体温骤然升高,肺炎发作,病情一下子就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
已经身患重病但仍坚持工作的总理十分关心父亲的身体,亲自嘱咐在父亲的书房和客厅铺上地毯,夜里要有人值班。
当时为了帮助父亲准备材料,学物理的我不得不“恶补”了一番。柳宗元的《封建论》当然也在恶补之列。恶补之后,我大吃一惊。柳宗元作为杰出的思想家很不简单,他论述了从古代“封建制”到秦代开始的“郡县制”的转变,“非圣人之意也,势也。”然而,这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封建论》中的“势”仅仅停留在政体的优劣上,没有涉及社会经济基础的转变必然引起的上层建筑变更的大势所趋。当然,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一直存在不同观点,现在更是这样。但这毕竟是与政治问题有所区别的学术问题。“百代都行秦政法”,“莫从子厚返文王”,其潜台词恰恰是把人民共和国等同于一个朝代,而领导人不就成了帝王?难怪父亲冷静地说,历史自有公论。
当时的中国政坛,哪里有“能纳人善言”,“实行民主合议制”的影子?与几百年前失败于骄傲的农民起义领袖作比较,不是值得深思吗?
不久,总理病重,父亲非常牵挂。1976年1月8日,总理病逝的噩耗传来,父亲无力行走。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一句古诗:“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母亲以隶书写了两封信给邓妈妈。一封以父母亲的名义率全家表示沉痛的悼念:
惊悉敬爱的周总理逝世,泪落如雨。总理一生伟绩,永悬日月,我们愿化悲痛为力量,以总理为楷模,努力工作奋斗到底。敬请节哀,为党的事业而保重。
另一封以她个人向邓妈妈表达深切问候。当时父亲已无法站立,但坚持让我搀扶着去向总理遗体送别,向邓妈妈吊慰。“以总理为楷模,努力工作奋斗到底”——这是绝不妥协的决心。
1月11日,北京百万人在寒冬中哀送灵车,父亲次日写下《纪念周总理》的挽诗:
革命前驱辅弼才,巨星隐翳五洲哀。
奔腾泪浪滔滔涌,吊唁人涛滚滚来。
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
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
同年清明,天安门人潮涌动,全国民众自发悼念敬爱的总理、声讨“四人帮”。我每次去北京医院探望父亲,他都要我绕路天安门。我很快发现父亲的诗句出现在大幅挽联上,也见到过不少便衣,有的在陪父母亲出游时我还认识。其中一位好意暗示会出事,劝告我别再来了。当我如实向父亲讲述所见所闻的时候,父亲的眼神流露出忧虑。他要我去告诉同在医院住院、已经是国务院工作组成员的王震同志。王老同样忧心忡忡。不久,自发悼念活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群众受到强力驱赶。
很快,油印的挽联挽诗集锦出现了。父亲要我找一本。那本千方百计找来的集锦长时间一直放在父亲的书房里。
三
父亲早年学医,翻译过英国科普作家威尔士的巨著《生命之科学》。虽然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古代史的研究上,但身为科学院院长,他一直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关心我国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的境遇。
郭老十分欣赏战国时代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50年代他就提出:“凡是自由讨论的风气旺盛的时代,学术的发展是蓬蓬勃勃的;反之便看不到学术的进步。”(《三点建议》,1954年12月9日《人民日报》)他期待着这样一个时代。
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一直是个问题。公私合营之后,民族资产阶级“消失”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仍然要按照“世界观”,把知识阶层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60年代初的广州会议,好不容易“脱帽加冕”,成了“人民知识分子”。其实,阶级属性并没有真正解决。尽管父亲已经在1958年由周总理和聂荣臻同志介绍“重新”入党,而“文革”伊始,我在单位里仍然被红卫兵划为另类。
“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颁布后,劲夫同志靠边站,科研工作大多都处于停滞状态。科学院的运动由总理过问,总理联络员刘西尧主持日常工作,比起高校和其他一些机关来,中科院的情况还算好。
1969年,刘西尧同志主持座谈会,要讨论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问题,我参加了。原来两年前,一位湖南的中学教师写了一篇彻底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文章,受到“中央文革”和陈伯达的支持,随后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那次会议是征求意见,打算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公开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父亲对此十分重视。早在日本留学时期,父亲就接触过相对论,听过爱因斯坦的演讲。他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是哲学意义上的相对主义。如果由《红旗》杂志发表这种文章,和‘无产阶级文化派’有什么两样?这样做会在世界上引起哗然,阻碍我们自己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我理解父亲的心情。在当时的情况下,公开反对批判相对论难以奏效,而默认这种愚蠢的批判泛滥下去,后果将更为严重。父亲说,好爸爸也知道这件事情,而且很关心。我告诉父亲,我已经和几位朋友设法打进那个“批判组”去,用孙悟空的办法,在内部斗。父亲笑了,提议不妨设法搞个内部刊物,允许不同的意见发表,这样做或许更稳妥。这也是好爸爸的意思。
父亲认为,科学的批判,密切联系实际的批判是会推动科学发展的,但是我们至今还缺乏这种批判精神。用哲学观点来判断科学的是非,是荒唐的;自上而下地来支持这类愚蠢的批判,就更加荒唐。他嘱咐说,你们参加这场辩论,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历史一再证明,一切无知的批判科学的人,是一定会受到科学嘲弄的。显然,好爸爸和父亲的意思非常明确。
后来成为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的闫沐霖教授,当时刚刚进“批判组”,又是负责人之一。我们一起议论多次,设法扭转以哲学批判代替科学研究的状况。不久,在西尧同志的支持下,原来的“批判组”被一些搞自然科学的朋友打了进去。那场企图公开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闹剧被制止了,变成内部讨论。母亲为内部刊物题写了刊名。
在刊物的第一辑中收录了许多不同观点的文章,不仅有“批判组”的,还有北大、原子能所的。此外,引人注目的还有上海理科大批判组以“李科”为笔名的文章和北航的文章。上海的文章表明,对相对论的批判并不仅仅有陈伯达的插手。北航的文章同样有背景,那位湖南教师当时就被调入北航,那里的负责人不是学物理的,而他的背景人所共知。
1970年,著名数学家和数学物理学家陆启铿先生刚到“批判组”,当时只有四十出头,他提出不应该只有一个狭义相对论,而可能有三个狭义相对论。1974年,陆先生带领邹振隆和我在刚刚复刊不久的《物理学报》上,就此公开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这时,批判组已划归物理所,成为十三室。周培源、彭桓武和胡宁等著名物理学家对发表此文表示支持,也有人立即反对。振隆和我多次向周老、胡公等请教。当时华罗庚也在北京医院住院,父亲要我向华老请教。1970年,我在上海遇见华老时就向他请教过,此后华老一直非常重视。论文发表后,华老指出论文在方法上不够简单。不久,华老写下手稿,要他的助手和我们一起组织以他的名著《从单位圆谈起》和相对论为主的读书班。
父亲几次询问情况,提醒说,随着科学实践的深入,任何理论都会有所发展;基础科学研究一定要有批判精神,不要囿于现有的理论;要多向行家请教,要多听不同意见,特别是反对的意见。然而,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持续不止,十三室的研究工作不得不全面停止,读书班也半途搁浅。当时,西尧同志调离科学院到国务院工作,在科学院主持工作的新领导的指示下,物理所突然派工作组到十三室进行“整顿”,试图把十三室定性为“裴多菲俱乐部”。依据的“关键材料”,不少来自上海理科大批判组。据称,我们有三条主要“罪状”:一是有人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二是打着批判相对论的旗帜,行反对批判相对论之实;三是业务上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段经历同样印证了我们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较之“无产阶级文化派”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议论,也印证了父亲从文革伊始的担忧。
父亲得知此事后,要我去找郁文同志。郁文同志建议我直接去找那位曾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院领导。那位领导刚刚恢复工作,在了解了包括华老、周老等老科学家对相对论研究一贯给以支持的全面情况后,态度有了转变。
现在谈起这些往事,感到可笑。可是,人们却不知道作为院长的父亲,那时在顶着压力,按照他的良知和周总理的意愿,打着“太极推手”。
父亲直到晚年病重期间,对科技发展的大政方针、对科学家和领导干部境遇等问题的关注一直在他心中念念不忘。1972年,原子能所一部的18位科学家联名建议成立高能物理所。父亲了解后,立即表态支持。“批林批孔”中,华老身边仅有的两位年轻助手被军宣队通知立即回校。父亲闻讯,迅速向上反映,最后经过邓颖超办公室,问题才得以解决。1975年初,父亲得知劲夫同志仍然在科学院印刷厂“监督劳动”,马上向有关同志提出自己的意见,劲夫同志得以在春节时与家人团聚。这类事情,只要力所能及,他都会尽力推动。
现在父母亲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我也过了古稀之年。回忆往事,我每每生出这样的感觉:时代造就了郭老,郭老也反映了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