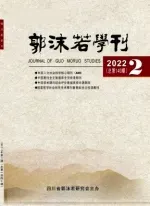“革命文学”论争中的“启蒙”意识及其嬗变
刘婉明
(南京大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7)
“革命文学”论争中的“启蒙”意识及其嬗变
刘婉明
(南京大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7)
1928年“革命文学”从五四启蒙传统中继承者至少有三: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追求,知识分子在这一追求中的“启蒙者”地位,以及相信文学会对社会改革产生作用。“小说与群治”的关系被放在唯物辩证法的体系中重新阐说,旨在贯彻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无产阶级文学”在这场运动中被赋予了“启蒙”的使命。
革命文学;启蒙;现代性
引言
1928年“革命文学”的兴起,虽然始自高调批判五四一代的“既成作家”,然而“革命文学”的提倡者们从五四启蒙传统中继承者至少有三: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追求,知识分子在这一追求中的“启蒙者”地位,以及相信文学会对社会改革产生作用。“革命文学”的诉求其实延续了“欲新一国之民必新一国之小说”的主题。所不同者,这一次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小说与群治”的关系被放在唯物辩证法的体系中重新阐说,旨在贯彻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无产阶级文学”在这场运动中被赋予了“启蒙”的使命。
一、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的引进
1928年,革命的失败迫使人们重新思考所面临的人生、社会与历史问题,随之而起的“革命文学”运动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思想的译介热潮。此时的马克思主义,被当作一种最“现代”的思维方式和实现民族国家现代化的积极方案而接受,并且,它积极的未来取向显然适应了疗治大革命失败所带来的普遍失望情绪的需要,为个体如何重新参与时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解答。“革命文学”运动的一个共识是,必须对“现在”的“本质”拥有清楚而深刻的认识,即惟有掌握了“现社会的构成,现世界的趋向,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形势”[1]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才有可能参与历史,把握“将来”——实现民族复兴的事业,而能够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的,只有马克思主义。阿里夫·德里克(ArifDirlik)曾有论道,在1927年以后的十年间,“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塑造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中国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观念。”①彭康在他介绍唯物史观的文章中写道:
一切都不能存立在空间和时间以外,为着这空间性和时间性,一切都须被卷入在历史这个圈子里,随着变化,发展,消灭。
人一出生,就是社会的动物,他要营社会的生活,即须融入社会——历史这个旋涡里随着辗转,尽他愿与不愿。不断地随滚在这大流里,人可以经验一切都在流转,找不到什么东西是在那里停住;展开在他面前的只有森罗万象的变动,静止不是他能知道的世界。
一定要在这变的世界里生活,这是人底必然的规定;努力去把握变的世界和动的历史底本质以确定应付的态度,因而继续且改善他底生活,这也是人底必然的手段。[2]
彭康以及其他 “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都相信,惟有掌握了历史演进的规律,才能看清他们的时代——“现代”的本质与将来,参与其中,才能继续在历史进程中的“人”的——而不是“动物样的”——生活。
“革命文学”运动从“文化批判”开始,其提倡者和他们的五四前辈一样,认为国家民族亟需一次在“科学的真理”指导下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朱镜我的《社会与个人底关系——自由与平等底意义》就从法国大革命说起,深信马克思主义将完成法国革命的未竟之业,实现“自由与平等”的启蒙追求。这些刚刚从日本帝国大学里接受完马克思主义洗礼的人们,毫不怀疑这种学说将指引出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出路,带来“自由的王国,平等的故乡,没有暴力,没有支配,没有服从,自由和平等的完全的统一。”[3]而这也正是他们发起这场“革命文学”运动的动因。
成仿吾写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上的《祝词》就总揽这场运动对它自己的这种看法:将民族的命运置于“世界史”的进程中,用唯物史观的语言勾勒民族复兴的前景,相信这场运动所带来的“革命的理论”标志着一场“伟大的启蒙”的开始。
一睡千余年的我们,睁眼醒来,凡事落在他人很远很远的后面。
百余年的世界史上,我们“中华帝国”只是被榨取与被笑骂的对象;一叶一叶的历史上堆着的,尽是我们全民族说不出的耻辱与痛苦。
㉕Jeffrey A.Parness,“Old - fashioned Pregnancy,Newly - fashioned Paternity”,Syracuse Law Review,57(53),2003,p.69.
……“文化批判”当在这一方面负起它的历史的任务。它将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的批判,它将描出近代帝国主义的行乐图,它将解答我们“干什么”的问题,指导我们从那里干起。
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科学,文艺及其余个个的分野皆将从“文化批判”明了自己的意义,获得自己的方略。“文化批判”将贡献全部的革命的理论,将给与革命的全战线以朗朗的光火。
这是一种伟大的启蒙。[4]
同期的《编辑初记》中也写道:“本来这样的刊物在中国还是一种创试。我们这几个埋头窗下,不知世事的同人所以敢于不畏艰险,冒昧地开始这种启蒙运动的原因,一是因为时代已经需要这样的干粮,二是因为我们预期全国觉悟的青年必将起来,在精神与物质两方面,长为我们的后盾。”[5]冯宪章发表于《思想》第2期的《真理探求者——为“思想”致一般青年》则以诗歌形式表达这种“启蒙”意愿:“科学的真理才是病态的社会底唯一救世主:/它不忌讳地把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矛盾暴露,/更指示出一条新社会的坦途/……/廿世纪的青年朋友——/在这阴霾的云雾低压重重,淫雨霖霖的霉天期中,/《思想》负着探求科学的真理底任务前进;/这是文化上伟大的启蒙运动的企图。”[6]
旨在开展马克思主义启蒙事业的意图反映到文学上,首先便是用这种语言重新叙述文学史,“革命文学”家们对五四一代的高调批判也可视为这一意图驱使下的行为。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将唯物史观运用于文学领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语言展开 “革命文学底历史的追述”,重新理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历史谱系:
中国十年前的文化运动,实为当时资本与封建之争,反映于社会意识者。杂志“新青年”就是这个斗争的勇敢的先锋队。……
中国一般无产大众的激增,与乎中间阶级的贫困化,遂驯致智识阶级的自然生长的革命要求。这是革命文学发生的社会根据。
一九二六年,郭沫若氏的“革命文学”,正是这种自然生长的革命意识的表现。……一九二八年的今天,社会的客观条件,完全变了。
……中国的文学革命,经了有产者与小有产者的两个时期,而且因为失了他们的社会根据,已经没落下去了。然而一个历史运动,绝对不能中断。那么,新兴的革命文学,在历史运动的必然性是什么?
革命文学,不要谁的主张,更不是谁的独断,由历史的内在的发展——连络,它应当而且必然地是无产阶级文学。[7]
在李初梨的这份历史谱系中,五四时期对“新文学”与“新国民”关系的探寻在“革命文学”运动中被赋予了明确的指归: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有着内在必然性的连续的历史运动,“革命文学”的必然性就是迈向现代的历史进步运动的必然性,也就是缔造新民族的必然途径。如果文学确实能够影响社会人生,如果未来必然将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时代,而“革命文学”又是反映了最现代的最进步的“无产阶级意识”的文学,那么,有什么理由不加以大力提倡?无怪“革命文学”的提倡者们坚信他们定将战胜茅盾们的 “幻灭”与 “动摇”。正如彭康所言,只有唯物史观是“唯一真正的历史哲学,要它才可以解释历史,改造社会,推进人生。”[2]郭沫若号召文艺青年“当一个留声机器”的口号也并不应该仅被视为政治宣传的副产品(更何况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否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政党文化政策还有待讨论),郭发出这一呼吁是因为他相信“那种声音”是属于未来的。
二、“启蒙者”的身份意识及其对“革命文学”观念的影响
“革命文学”的提倡者们以“普罗列塔利亚特的前锋”自许,站在“革命的智识阶级”的精英立场上,相信自己正在从事的是一场“伟大的启蒙”。这一启蒙的对象首先是国内的智识青年,尔后才延及普罗大众。冯乃超八十年代回忆时就说,他们当年回国的初衷是进行革命理论的指导,宣传的对象是“知识阶级”:“1927年蒋介石叛变了革命,我们认为,这暴露了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期的弱点,主要是缺乏理论指导。因此觉得,很有赶紧向中国的读者——知识阶级,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和展开宣传工作的必要。”[8]《文化批判》创刊号《编辑初记》中写道:“我们志愿把各种纯正的思想与学说陆续介绍过来,加以通俗化。但我们豫先假定了我们的读者诸君中的大部分是一些想要知道一点新的东西而且愿意自己去思索的青年。……新的思想自有它的思考法与表现法,初入门的人最初或者有点看不惯,但是觉悟的读者当能耐烦去接近而理会新的思考法与表现法。”[5]第2期《编辑杂记》中又写道:“我们的一般读书界没有想到我们会这样提出这些问题,也从来没有见过我们这样的论述方法——或者因为这种种原故,本刊在短时期之内许不容易完全使一般读者满意。……我们将要使读者把捏着辩证法的唯物论,应用于种种活生生的问题,在历史的必然性上观察,而理会自己应有的努力。 ”[9]
这些创造社新锐们俨然以启蒙者身份,经营面向无产阶级的启蒙事业,而他们用以明确自身身份的标识就是“无产阶级意识”。这种意识并不直接就是当下普罗大众脑中所思所想——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大众的思想很可能已浸入了太多的资产阶级和封建意识形态,而是先觉的启蒙者——“革命的智识阶级”所拥有的超越性的历史洞察。他们所服膺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思想,在它的首倡者法捷耶夫那里,也正需要站在“高度的哲学的水平”上,运用“普罗列搭利亚特的前卫的世界观”方能把握。[10]
这种对自己做为时代“启蒙者”身份的确信直接影响了“革命文学”家们对“无产阶级文学”的看法。《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李初梨首先指出,文坛上那些“写穷的文学”、无产者自身写出的文学(如果其意识还未从有产者意识解放出来)、“写‘革命’‘炸弹’的文学”、写无产阶级理想或苦闷的文学,以及“描写革命情绪的文学”,均不能称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继而为他理想中的“无产阶级文学”张本正义:“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使命,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态度,而是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7]
同样,太阳社出身的钱杏邨在有关他理想的“无产阶级艺术”的早期叙述中,最看重的也是“无产阶级的意识与情绪”[11](P361)、“无产阶级前卫的眼光”、“无产阶级的现在的唯一的客观的观点”,至于题材则可以无限制,读者也未必限于无产阶级,“总之,问题是在观点,不在题材。 ”[12](P507)
在《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一文中,李初梨坦然接过鲁迅对他们“无产阶级文学使者”的讽刺,“我们可以大胆地承认鲁迅先生那一个反语,‘车夫的本阶级意识形态不行,早被别阶级弄歪曲了。另外有人掌握着,但不一定是工人。’”并指郁达夫所谓“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学,必须由无产阶级自己来创造”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他引述列宁的论断为证:“伊里奇说过:‘许多人以为只要劳动者,无须顾虑他们的前锋,把他们自己的运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纯粹的劳动运动自身,就可以消化一种独立的意识。但是,这才是一个深刻的误谬。’”李初梨进而强调,无产阶级文学应该是“无产阶级前锋底一种意识的行动”,且现阶段惟有“革命的智识阶级”能担此任,所以,无产阶级的文学批评,当然应该“以他的意识为问题,不能以他的出身阶级为标准。”“无产阶级的出身者,不一定会产生出无产阶级文学。”“一个文艺家,应该同时是一个革命家,——普罗列塔利亚特的前锋(Vorhut)。Goonon——Baudon,可以说是大地深处的雷鸣,也可以说是前锋的怒吼,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前锋。我以为一个前锋的任务,是要把大众自然生长的要素,结合于他的目的意识;绝不是单单地只去听大众的自然生长的声音。”[13]
“革命文学”运动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实现民族的复兴与现代化,与此同时,个体也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成为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的一员,而获得历史性的存在:“个人是社会地——即阶级地——生活着的个人”[3]如果未来必然走向无产阶级的时代,这就意味着,惟有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人才能成为参与历史,与之并进。因而“无产阶级意识”是早期“革命文学”提倡者最看重的身份标识,他们相信获得这种“意识”需要超越性的历史洞察,而不是当下受资本主义与封建意识形态蒙蔽的普罗大众能够“自然生长”出的,所以,最可能创作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应当是“革命的智识分子”:
在无产阶级没有阶级的自觉以前,要它创作反映这无产阶级底意识形态底文学这是不可能的事。也许他们有所创作,在他们没有阶级的自觉以前,这种创作必然地要反映有产者底意识形态,都不是无产阶级底文学。反之把以前的文学作篇总结算,同时在无产阶级底意识形态上创作无产阶级底文学底人,都大半是革命的智识分子。[4](P635)
“革命文学”延续了五四时代相信文学应当暴露社会黑暗,文学家应当通过写作充当时代先觉者,从而对社会变革发生影响的观念,但是,这种观念在“革命文学”中被推向了极端,“文艺家”被要求必须同时是“革命家”,或者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不能满足于仅仅只做“文学家”,而希望以“普罗列塔利亚特前锋”的身份直接参与革命行动,文学写作也被视作革命行动的一部分,呈现出政治与美学的双重激进面目。郭沫若对 “革命文学”的理解明显沿续了“文学革命”时期的浪漫余绪,文学和革命之所以是一致的,乃是因为“文学是革命的前驱,而革命的时期中会有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出现。”文学之所以能为革命前驱,则缘于文学家们神经质(melancholic)气质(Tempcrament),“因为他的感受性敏锐,所以一个社会临到快变革的时候,在别种气质的人尚未十分感受到压迫阶级的凌虐,而他已感受到十二分,经他一呼唤出来,那别种气质的人也就不能不继起响应了。”[15](P6-7)在这里,文学家以其敏锐的感受性成为引领时代的革命先锋。
将“革命的智识分子”视为“革命文学”乃至整个革命事业的领导者——“普罗列塔利亚特的前锋”,这样一种身份认定也就赋予了这些左翼知识分子“革命的启蒙者”身份,即用自己所掌握的“无产阶级意识”祛除普罗大众所受封建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蒙。在这些“革命文学”家们看来,革命程序的启动需要两个必要条件:首先是率先掌握了先进意识形态的“革命的智识阶级”自上而下对无产阶级的意识注入,然后才是接受了革命思想“启蒙”的无产阶级的实际革命行动。这本是列宁布尔什维克党理论的观念,到了中国的 “革命文学”家们那里却做出了“文学家”必须同时是“革命家”的阐说。以“文学家”而身兼“革命家”,与职业革命家间的距离显然不是单凭浪漫蒂克的革命激情就可弥平,无怪这些“革命文学家”们一旦加入政党组织就屡屡遭遇“‘我们’是谁”的逼问。
结语
“革命文学”的提倡者们无不满怀普罗米修斯式的启蒙使命感,马克思主义思想使他们相信自己所代表的正是昭示历史理性前行的必然方向。后来的历史证明,当年的“革命文学”家们的大多数很快就放弃了“文艺家”的身份转变成职业“革命家”,他们也许可被称为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所描述的由法国革命催生的雅各宾式知识分子的中国版本,②而且,对历史理性所许诺的乌托邦的追求,在民族国家危机的影响下显得更加迫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中,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产生的“革命文学”,与五四文学一样,伴随着浓厚的知识精英色彩,试图结合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的努力背后总能找到“启蒙”的现实目的。
(责任编辑:廖久明)
注释:
①参见阿里夫·德里克(ArifDirlik)《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程凯《1920年代末文学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与唯物史观文学论的兴起》,《文史哲》,2007年,第3期。
②参见[美]刘易斯·科塞(LewisCoser),《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MenofIdeas)中对“知识分子和权力机构”的论述,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1]成仿吾.祝词[J].文化批判,1928,(1).
[2]彭康.唯物史观的构成过程[J].文化批判,1928,(5).
[3]朱镜我.社会与个人底关系——自由与平等底意义[J].思想,1928,(1).
[4]成仿吾.祝词[J].文化批判,1928,(1).
[5]编辑初记[J].文化批判,1928,(1).
[6]宪章·孤凤.真理探求者——为“思想”致一般青年[J].思想,1928,(2).
[7]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J].文化批判,1928,(2).
[8]冯乃超口述,蒋锡金笔录.革命文学论争·鲁迅·左翼作家联盟[J].新文学史料,1986,(3).
[9]编辑杂记[J].文化批判,1928,(2).
[10]A.法捷耶夫(А.Fadeyev).创作方法论,(何丹仁译)[J].北斗,1931,1(3).
[11]钱杏邨.从东京到武汉[A].阿英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12]钱杏邨.关于中国文艺的断片[A].阿英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13]李初梨.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J].思想,1928,(2).
[14]钱杏邨(署名克兴).评驳甘人的《拉杂一篇》——革命文学底根本问题底考察[A].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5]郭沫若.革命与文学[J].创造月刊,1926,1(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A
1003-7225(2011)01-0031-04
2011-02-18
刘婉明,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