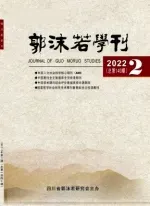郭沫若的杀子意识与小说现代性
吴耀宗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 香港)
郭沫若的杀子意识与小说现代性
吴耀宗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 香港)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郭沫若并非首创杀子书写的作家,然而在1920年代创作的数篇小说中部署父母谋杀亲生子嗣的情节,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其一方面取源于西方的杀子书写传统,将爱的罪罚的寓意移植过来,制造双重的震撼,另一方面又铺设复杂多层的小说心理结构,以承托对于子的负累的叙述。如此开拓性的艺术经营,为中国小说建构了前所未见的现代性,是为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新里程碑。
郭沫若;杀子意识;中国小说;小说心理结构;爱的罪罚;子的负累
一、杀子:由背叛开始
郭沫若(1892-1978)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者之一。尤其是写于1926年以前的早期小说,可谓处处新颖,频频创拓,惟其建树长期被鲁迅(1881-1936)的光芒所掩盖,学界至今还未能给予全面的发掘与肯定,殊为可惜。如郭沫若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著作《牧羊哀话》,乃是最早以异域金刚山为叙事场景,以朝鲜民族为主人公的中国现代小说。论者归纳此作之特点时,或指其“在飘逸的意境中展开一个动人的故事…燃烧着爱国热情的火焰”[1](P91),恒为坚决反日的国族寓言,或称之“富有异国情调的童话牧歌兴味的情绪趋向”,“成功地表现了浪漫主义的悠远性和哀伤的情绪美”,[2](P117-118)固然各有肯綮的发现,但却不曾留意到杀子意识在文本中与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牧羊哀话》在1919年2、3月间完稿,在11月的第7期《新中国》上刊发。小说叙述朝鲜李朝子爵闵崇华的在野事迹。闵崇华因对朝廷失望而辞官,隐居于金刚山下,忘情于大自然,不问世务。无奈继室李夫人不安于室,为求归返京城享受荣华富贵,竟而勾结府中司事尹石虎谋杀亲夫。尹石虎之子尹子英既为人正直,又与闵家小姐青梅竹马,阴差阳错之下拾获谋反的密函,毅然欲晓父亲以忠诚大义,结果命丧刺客刀下,成了闵崇华的替死鬼。郭沫若通过尹石虎在接到儿子的耗闻后大呼“杀错”的情节安排,叙述奸臣误戕子嗣的惨祸,确立了个人日后小说反复表述的一个重要命题——背叛遭致灭子断根的恶果。(QJ.9:3-14)
诚然,杀子叙述并非郭沫若首创。在其写就《牧羊哀话》的一年前,亦即1918年5月,鲁迅已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以狂人怀疑与控诉妹妹为家族长辈所食的意识流语言揭露封建礼教杀子的罪行。不过,像郭沫若那样直接且反复书写杀子的并不多见,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谓别树一帜。事实上,《牧羊哀话》只是启端,郭沫若在其后小说中叙述杀子意识时有更精彩更深层的表现,反映当时现代人复杂的心理与个性,对中国小说现代性的建构做出重要的贡献,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讨论。
二、双重性叙述:从爱的罪罚到子的负累
《牧羊哀话》中的尹子英虽然年少,毕竟已懂事,能做出全福远祸的选择,不像郭沫若之后小说中的受害者均为幼童初婴,完全没有自卫能力,更显得无辜。
1922年4月1日,身在上海的郭沫若就以留日所在地九州为叙事场景,创作了“精神出轨”的婚外恋小说《残春》。《残春》的主人公仍旧是爱牟,开篇写居于大阪的四川同乡白羊君前来博多湾,央请他齐赴门司探访跳海不遂的昔日同窗贺君。爱牟依依不舍地道别妻子晓芙和两个年幼的儿子,来到了门司的医院。首日未见贺君,却在白羊君的介绍下认识了照料贺君的S姑娘,并对这“中等身材,纤巧的面庞”,“眼睛很灵活,晕着粉红的两颊”的日本护士留下深刻的印象。探病结束后,爱牟到白羊君的寓所一宿,临睡前和他谈起S姑娘的身世,得悉她经常申诉“肺尖不好,怕会得痨症而死”的烦恼。于是在睡意惺忪之际,竟梦见自己和S姑娘孤男寡女同登门司市北的笔立山山顶,“在山后向着濑户内海的一座茶亭内坐下”,这时 “山上一个人也没有”,S姑娘竟“缓缓地袒出她的上半身来”,要求学医的爱牟给她诊察。就在爱牟准备“诊打她的肺尖”的时候,白羊君突然气喘吁吁地跑来,通知他晓芙在家中手刃二子的厄闻。接着,进入读者眼帘的乃是一段案发现场鲜血淋漓的暴力叙述:“我[爱牟]听了魂不附体地一溜烟便跑回我博多湾上的住家。我才跑到门首,一地都是幽静的月光,我看见门下倒睡着我的大儿,身上没有衣裳,全胸部都是鲜血。我浑身战栗着把他抱了起来。我又回头看见门前井边,倒睡着我第二的一个小儿,身上也是没有衣裳,全胸部也都是血液,只有四肢还微微有些蠕动,我又战栗着把他抱了起来。我抱着两个死儿,在月光之下,四出窜走。”[3](P27-32)值得庆幸的是,这恐怖骇人的景象原来只是一场噩梦,爱牟家中的小孩其实完好无缺,并没有被母亲杀害。尽管如此,以爱的罪罚作为主题却是明显可见的。
郭沫若曾经夫子自道,指出《残春》这篇小说的着力点不在于叙述事实,而是在于描写心理,表现为潜意识的一种流动;而论者也引述此见,认为“小说写梦,写潜意识,写一种被压抑的青春期生理欲念”[4](P70)。是言不虚,说明郭沫若确实运用了西方心理小说技巧,为中国小说发掘现代性的特点,但笔者又以为论者多忽略另一重要的环节,即作者使用重复格来描写两个小孩惨遭母亲杀害后的景况,其实在当时也是超前创新的小说叙述模式。郭沫若刻意经营,把“倒睡着…身上没有衣裳,全胸部都是鲜血”这句子结构近乎雷同地重复一次,引领主人公与读者先目睹长子之浴血惨死,紧接着把镜头一转,使复见次子同样浴血惨死的景象。换言之,晓芙惨无人道手起刀落,杀害二子的手法一致,死状不殊,这等于把爱牟的生命延续给灭绝了两次,给予不忠丈夫的是双重的惩罚,给予观/读者的是双重的震撼。
约莫两年后,当小说《漂流三部曲》三章中的最后一章《十字架》在3月18日脱稿时,我们再次看到郭沫若在文本中制造杀子的双重效果。这回要犯下杀子罪行却是作为父亲的爱牟。小说写爱牟阅读晓芙从日本的来信,知悉她和孩子们在福冈生活十分困苦,而弃医从文的自己又无力改善他们的生活,愈是想着爱妻为他所做的牺牲,愈是自艾自怨,感叹要放弃做艺术家。抑郁之极,竟而呐喊道:“我不久便要跑到你那里去,实在不能活的时候,我们把三个儿子杀死,然后紧紧抱着跳进博多湾里去吧”。仅仅在脑海中产生杀子的想法,或不容当真,但是小说在收篇处让爱牟给妻子写信表明心迹,信中言之凿凿说要回日本和他们相依为命,倘若无法忍受生活的压迫时就走上这全家殉死的末路,可见杀子意识是何其鲜明强烈。倘若说为人父者竟而提出杀害无辜小孩的想法给读者带来了首度的震撼,则小说随而将这杀子的意愿文本化,让爱牟“反反复复讴吟”成一首悲愤喷薄的新诗,给读者带来二度的震撼:“去哟!去哟!/死向海外去哟!/火山也不论!/铁道也不论!/我们把可怜的儿子先杀死!/紧紧地拥抱着一跳,/把弥天的悲痛同消。”[5](P271-273)尽管杀子只落于言筌,尚未付诸行动,但从隐喻的层面来看,爱牟其实已经在申诉子的负累的时候重复谋害了自己的小孩。
再看于同年10月17日写就,①属于郭沫若小说爆发期的作品《曼陀罗华》。②有别于前述二作的托诸睡梦或想愿,此篇着实写孩子命丧父母之手。叙述者“我”在福冈医大的同学哈君被妻子逼着同赴日本本岛极北的A市旅行。二人带着新生的次男诺儿同行,但爱慕虚荣贪图享乐的哈夫人却以此为负累,在火车上拒绝喂奶与照料,结果婴儿患上肠内壁溃烂的疾病,回返福冈不久就一命呜呼了。从某种程度上讲,哈夫人刻意忽略孩子,任由其患病不治,等于亲手结束了小孩的性命。这一回,郭沫若以“二曝童尸”的方式来讲述这人间的惨祸。首先,他让叙述者“我”携带听诊器跟随哈君回家,发现“孩子睡在前房里,脸色是惨白的,嘴唇是淡紫的,嘴角上浮着些泡沫,鼻孔里流出些血浆,微闭的眼睛已经蒙上了一层白雾。…生命已经不在这孩子身上了。脉搏没有了,心脏停止了,只有腹部还有些暖意”。作者以近乎工笔描绘的手法来曝露尸骸,但似乎意犹未尽,随即又写“我”陪同哈君领着死婴到大学医院去诊断报销,把叙述场景转至解剖室,叙述两个当值的医学士对尸体进行检查的工作。这时,郭沫若再度向读者展示被无良母亲剥夺了的可怜小生命:“小小的尸首睡在解剖室中的大理石的解剖台上。死后已经两天,脸上带着惨戚的土色,蒙着白雾的眼儿仍然微微开着,鼻孔里塞着两团棉花。身体各部已经现着紫色的尸斑,手脚的惨白如象羊脂玉一样了。 ”[6](P366-368)如此二曝童尸,过程详尽,在视觉和精神上都给予读者的双重冲击,其实和《残春》中的写法一样直接、残酷,一样令人发指。
虽说文本是想像的产物,但字里行间流露出如斯浓厚的杀子意识,不可能凭空捏造,匮缺现实的因由。事实上,郭沫若早年一直在贫穷线上挣扎。不同于徐志摩等欧美留学生,其在四川乐山的老家并不富裕。1914年初东渡瀛州,须在神田日本语学校苦读五个月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后,方获中国政府发给官费,是为此后维持留学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1915年中旬预科毕业,被分到冈山的第六高等学校就读。1918年夏毕业,升入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科。1923年3月获得医学学士学位,留学生涯乃告结束。郭沫若未至日本之前虽奉父母之命于1912年娶张琼华为妻,但因不满意婚姻而将她交由家人照顾,无后顾之忧,因此尽管念医科费用高,参考书昂贵,仍然可以应付个人的生活。然而在日本有了家室后,就常常陷入经济拮据的困境了。1916年8月,因友人故到东京,与22岁的护士佐藤富子(安娜,1894-1994)相识并堕入爱河,12月在冈山开始同居的生活。二人结合,并未获得双方家庭的认可。郭家二老严厉反对这自由的婚姻,一度与儿子断绝书信往来,不予经济支援。而出身士族的牧师佐藤右卫门更是无法接受女儿与中国人同居,毅然给予富子“破门”的处分,断绝父女关系。随着长子和生(1917年生)、次子博生(1920年生)、三子佛生(1923年生)的陆续出世,郭沫若每月所得三十三元官费乃不敷使用,一家数口常常因为拖欠房租而被逼迁,时时得典卖参考书,才免于断炊。这也是郭沫若的经济与心理负担要比其他留日学生如郁达夫、成仿吾等来得沉重的缘故。其后郭沫若虽然取得医学士学位,但因为耳疾而弃医,生活并无改善;1923年携带家眷在沪鬻文为生,又一直没有固定的收入,贫困潦倒,丧失知识分子的尊严,对妻子亦颇多怨尤;为求生存,被迫将妻小送返东瀛。长期陷于这样的困境中,郭沫若内心之压抑扭曲与巨大痛苦可想而知。诉诸文字想像,在情绪强烈的书写中时而流衍成恐怖的杀子意识,使读者为之惊悚觳觫。
三、怨恨、愧疚、歆羡:作为基底的小说心理结构
从前文所讨论的双重性叙述,可见郭沫若的杀子书写乃是心思别裁,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艺术建构。笔者以为,这艺术建构之所以不流于浮夸的伎俩,不堕入猎奇之范畴,是因为郭沫若在早期小说中设置了复杂多层的心理结构,使残杀子嗣的念头具备必要、可信的生活理据与现实逻辑。
这心理结构主要由三个层面交混而成。首先,是对于家累的怨恨。阅读郭沫若的小说,会发现主人公多兼具丈夫与父亲的身份,终日长嗟短叹,怨恨家庭所带来的沉重压力。如《鼠灾》,由耗子咬坏冬服一事触发方平甫对于家累的连串抱怨,愤诉妻子无视其福利,儿子爱扯坏其书籍,像他这样一个日本医学部的穷留学生既要读书,又得养家,“一个月四十块钱的官费简直不够做个什么”。[7](P17)又如《未央》,写爱牟无力解决家小之温饱,其三岁大的长子因为长期挨饿以至营养不良,在外又受日本小孩的欺负,所以夜里总要哭闹几回,须由父亲伴侧不停唱歌才能入睡。有时,襁褓中的次子也加入啼哭的阵营。“天天如是,晚晚如是”,爱牟开始头昏、眼花、耳鸣,濒临崩溃的地步:“他的‘神’,已经四分五裂,不在他的皮囊里面了。他自己觉得他好像是楼下腌着的一只猪腿,又好像前几天在海边看见的一匹死了的河豚,但是总还有写不同的地方。他觉得他心脏的鼓动,好像在地震的一般,震得四壁都在作响。他的脑里,好像藏着一团黑铅。他的两耳中,又好象有笑着的火焰。他的腰椎,不知道是第几个腰椎,总隐隐有些儿微痛。…儿子们的呼吸声,睡在邻室的他女人的呼吸声,都听见了。他自己就好像沉没在个无明无夜的漆黑的深渊里一样”。[8](P36-40)如此痛苦的精神折磨使爱牟在《行路难》的上篇里如同火山般爆发了。爱牟为节省开支及方便创作小说,决定举家搬离博多湾,迁往佐贺的熊川温泉附近。偏偏去退房时自觉受了日本人的气,回到家里孩子们又向他讨“饽馅”吃,他终于忍不住咆哮:“饽馅!饽馅!就是你们这些小东西要吃什么饽馅了!你们使我在上海受死了气,又来日本受气!我没有你们,不是东倒西歪随处都可以过活的吗?我便饿死冻死也不会跑到日本来!啊啊!你们这些脚镣手铐!你们这些脚镣手铐哟!你们足足把我锁死了!你们这些肉弹子,肉弹子哟!你们一个一个打破我青春时代的好梦,你们都是吃人的小魔王,卖人肉的小屠户,你们赤裸裸地把我暴露在血惨惨的现实里,你们割我的肉去卖钱,吸我的血去卖钱,都是为着你们要吃饽馅。饽馅,饽馅!啊,我简直是你们的肉馒头呀!”[9](P295)通过语言暴力,爱牟再无保留地将长期郁积心中对于小孩的怨恨给宣泄了出来。
倘若小说止于书写人物一味地怨恨家累,则未免留流于片面浅薄。郭沫若在表达杀子意识时,不忘现代人细腻复杂的精神状态,因此又反复叙述作为一家之主的主人公因为无法维持妻小的温饱而心生愧疚之感,是为心理结构的第二个层面。试看《漂流三部曲》的第一章《歧路》,主人公爱牟送别妻小回日本后,忆想种种往事,感叹自己“逡巡苟且”的十年生涯,一事无成。曾经“做过些诗文”,又自比但丁的他如今“从灿烂的土星坠落下无明无夜的深渊里”,因为“他女人对于他的希望,成了他莫大的重担。他自己对于他女人的心期,又成了精卫的微石了。他的脑筋沉重不堪,心里炽灼得不堪,假如电车里没有人,他很想抱着头痛哭起来”。在第二章《炼狱中》,爱牟由于写不出长篇小说来卖钱,索性与友人到无锡去游玩,偏偏在游玩的途中又感到无限懊丧。来到惠山的假山石亭上时,见风景怡人,认为本应“坐在这台上负暄…赏月…读书…作文…和爱人暧语…和幼子嬉戏”,可是现在的他只能深深懊悔:“我的妻儿们都是被我牺牲了!”愧疚至深,无从排遣,以至身在上海或无锡,都一样感觉堕入炼狱,痛苦万分。再看第三章《十字架》,妻子晓芙自日本福冈来函,一再提到为了孩子的缘故而搬家花费,爱牟则在心里愧疚地回应:“我们在这世间上究竟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我们绞尽一些心血,到底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替大小资本家们做养料,为的是养儿育女来使他们重蹈我们的运命的旧辙!”[5](P249-270)许多时候,这种愧疚感又会在思考小孩面对的环境问题上浮露出来。如《圣者》和《月蚀》,同样写爱牟写带了孩子回上海生活,却发现上海“看不见一株青草,听不见一句鸟声…中国人的精神只是丑恶的名利欲的结晶,谁也还顾不到儿童的娱乐,儿童的精神教育上来”,住在民厚里就像住在监狱一样,“寓所中没有一株草木,竟连一抷自然的土面也找不出来。游戏的地方没有,空气又不好,可怜我两个大一点的儿子瘦削得真的不堪回想,他们初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见了都说是活泼肥胖;如今呢,不仅身体瘦削得不堪,就是性情也变得乖僻的了。”小孩实不适合在上海这城市成长,可是“如今是被我误了,我因为要占有他们,所以才从自然的怀中夺取出来,使他们和我同受着都市生活的痛苦”。归根究底,还是自己造的孽,因此爱牟在心里呐喊:“我是罪过!我是十分罪过!”[10](P41-61)
在怨恨和愧疚之外,又经常表达对于稚子童心的歆羡,构成郭沫若早期小说心理结构的第三个层面。例如《圣者》,写爱牟到闸北会见朋友之后,在回家途中被“街市上送年的腊鼓声和爆竹声,叠叠地把自己的童心呼醒”,于是“在一家小店里买了两角钱的花炮,想拿回家去逗引孩子们的欢心”。果然,这花炮一点燃,孩子们都欣喜万分。郭沫若着力描绘他们天真的“拍掌欢笑声,也像这火花一样顿时焕发了起来。放天旋子的时候,儿童们的心机也如天旋子一般,才在地上迅烈地旋回,又迅烈地旋到天上。放蛇箭的时候,儿童的心机更如一颗彗星,不知一直飞到哪处的星球去了。”后来孩子虽然被烟花炸伤了眼睛,但翌日即若无其事地游戏,使爱牟 “感谢得想流眼泪”,“对着他的孩子,就好像瞻仰着许多舍身成仁的圣者”。[11](P56-63)在《漂流三部曲》的《十字架》中,则通过爱牟妻子之口,叙述从上海回返日本后生活十分穷困,感叹“还是只有孩子们好,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没有不安的心事。 ”[5](P268)又如《行路难》下篇,爱牟一家五口乘火车去佐贺市北的熊川温泉,和一对衣着华奢的中年夫妇乘客同一车厢。爱牟自觉形秽,尴尬苦闷,突然又发现自己太软弱,还不如他的几个孩子“自从上了车便跪在车座上贪看车外的景色”,他们欢呼、歌唱、争论,“他们的意识中没有什么漂流,没有什么贫富,没有什么彼此。他们小小的精神在随着新鲜的世界盘旋,他们是消灭在大自然的温暖的怀抱里。他们是和自然一样地盲目的,无意识的。他们就是自然自身,他们旁若无人”。从新屋旅社迁至熊川村边的临水楼房时,爱牟因为书斋窗口对着楼下房主人的尿缸而生气,三个孩子却因为有柿子吃而十分开心。爱牟发现“孩子们是最宽容的,他们就搬到这里,也觉得什么都有趣味。他们没有经济的打算,也没有故作的刁难。他们是泛美主义者。在他们心中的印象一切都是新鲜的,一切都是有趣的。他们的世界是包藏在黄金色里的世界。他们的世界是光,是光,是光,是色彩,色彩,色彩”。[9](P319-335)稍做比较,乃见为人父母者在沉耽于报复爱的背叛或剔除生的负荷时(如《残春》等),手中利刃成了狂饮稚子之血的凶器,但在歆羡童心之际(如《行路难》等),刀却是用来替小孩剥柿子,表现家庭温馨、亲情洋溢的工具。郭沫若反复强调和歌颂稚子的天真无邪、烂漫活泼,既突显他们沦为父母与现实世界的牺牲品的无辜无助,亦对照出成人内心深处的阴鸷黑暗。
以上三个主要层面交混运作,既互相矛盾又彼此照映,组合成郭沫若的小说心理结构,为其杀子意识提供了厚实基础与丰富底蕴,赋予这种残暴叙述前所未见的深度与厚度。
四、异源殊途:对中国小说现代性的追求
本文在开端已指出,郭沫若书写杀子要稍晚于鲁迅。必须进一步说明的是,郭沫若通过杀子叙述来建构中国小说的现代性,与鲁迅所代表的一脉是泾渭不同的。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如此建构中国礼教制度源远流长的“食统”(吃人传统),首开中国现代小说书写杀子的先河:“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究竟中国人在易牙之前如何吃人,我们不得而知,但春秋时代齐国的厨师易牙为献媚求宠而烹杀亲生子以飨桓公一事,却是见诸《管子》之“小称”篇,[12](P608)可资参考。尽管鲁迅为了表现狂人“语颇错杂无伦次”的精神状态而刻意写出“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这样时代错乱的字句,③其杀子叙述之源出于中国传统文化却仍是明确无疑的。
郭沫若则不同。其杀子叙述具有的爱的罪罚的强烈意味,此乃鲁迅小说中所匮缺,说明其来有自,并不属于包含易牙烹子传说在内的中国书写传统。试看《残春》,爱牟从爱妻手刃二子的梦魇中惊醒过来后浑身冒汗,心中暗呼:“啊!这简直是Medea的悲剧了!”翌日再到医院探访贺君,又见到了S姑娘,一方面因为她头上簪着自己买来的红蔷薇而“感受着一种胜利的愉快”,另一方面却觉得“Medea的悲剧却始终在…心中来往”,以至“不敢久于勾留”,匆匆辞别二人赶回博多湾家去查看究竟。所谓“Medea”,一般译作“美狄亚”,乃是希腊神话中国王爱的斯的幼女。美狄亚谙巫术,对来到国境内的英雄伊阿宋(Jason)一见钟情,不能自拔,既背叛父亲助伊阿宋取得金羊毛,又残杀自己那十岁大的弟弟亚比西托士(Absyrtus)以阻延追兵前来缉拿,更施巧计解决伊阿宋的宿敌珀利阿斯,使其顺利登上国王的宝座。然而伊阿宋后来还是移情别恋,抛弃美狄亚母子,另娶柯林斯国王克瑞翁(Creon)的女儿为妻。美狄亚为此深受打击,结果不但毒死了克瑞翁父女,更手刃自己的两个孩子。郑振铎在其编著的《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中指出,美狄亚残杀稚子乃是“对于以欺诈报答她的热爱的男人的复仇的顶点。因为,自此以后没有人敢再招伊阿宋为女婿,他的一生便不再有孩子。他活得很久,但生活却很艰苦;没有温柔的女孩来看顾他,没有儿子的壮臂来保护他…他成了一个孤独,无人注意的老头子。 ”[13](P65-100)爱之既深,恨之亦切,杀子旨在使爱的背叛者堕入无尽孤苦的深渊。
在希腊神话中,杀子叙述屡见不鲜。例如与美狄亚同列于第一部“底萨莱的传说”的阿塔马斯(Athamas)故事亦颇相似。阿塔马斯为了拉拢强邻联盟,抛弃妻子涅斐勒(Nephele),另娶底比斯国王的女儿伊诺(Ino)。伊诺企图铲除丈夫和前妻生下的儿子菲里克苏士(Phrixus)、女儿赫勒(Helle),但奸计只得逞一半——赫勒溺毙,差一点被献作宙斯祭礼的菲里克苏士死里逃生;反而是自己所出的两个男孩无一幸免,双双命丧于亲生父母之手——阿塔马斯在打猎时突然发疯将长子射杀,而伊诺则抱着次子投海自尽。[13](P36-42)又如第六部 “雅典系的传说” 中关于特洛士(Tereus)的记载。特洛士娶了雅典公主柏绿克妮(Procne)为妻,但又垂涎于妻姨斐绿美拉(Philomela)的美色,不仅强奸了后者,还割其舌头,使无从指控自己的罪行。柏绿克妮知悉此事后,毅然携子伊堤斯拉(Itys)进入森林,与妹妹合力杀之,并将尸体放入铜釜中烹煮,供特洛士宴食。[13](P418-426)郑振铎在转述这两个传说时阐明:“为了她 (指伊诺)是赫勒溺死的原因,她便也溺死了她自己的孩子”,而“他(指阿塔马斯)对于涅斐勒的负心终于得到了恶报”。[13](P36-42)
由上述神话传说,可知杀子在西方文学传统中被视为对背叛爱情者的至高惩罚。笔者以为,这种指喻关系不见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因为在中国文献中,杀子既不涉及爱情,亦不发挥惩罚负心人的隐喻功能,许多时候纯粹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而做的抉择举措,如易牙烹子献君即是。因此,尽管郭沫若在1922年11月7日写成的《神话的世界》一文中,认为“人类的感受性与表象性相同…所以各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多有相似之处,④但当他需要书写美狄亚式的惩罚性杀子行为时,就无法再仰赖中国传说,而必须求诸一己在日本留学时所累积的西方文学学养了。这种取源于希腊神话传说、移植爱的罪罚的做法,赋予中国小说中的杀子叙述一种崭新的寓意和表现力度,建构了中国小说现代性。
再者,郭沫若小说借杀子来表现子的负累,此亦不见于鲁迅及其继承者的沉痛寓言中。20世纪初,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通过说话错乱无序的狂人,从历史的“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听“大哥说爹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母亲也没有说不行”,发现“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的杀子罪行。[14](P447-454)在1919年4月写下的另一个短篇《药》中,则叙述夏三爷冷酷不念亲情,到官府告发侄子夏瑜参与革命,以致后者被处死;华老栓不使患痨病的小栓就医,而以血馒头作药引,终至儿子丧命,這些都是封建传统杀子的具体表现。[15](P463-472)到了30年代,巴金继承鲁迅批判中国旧礼教文化的精神,撰写了长篇小说《家》。巴金设置了高大公馆这样一个被黑暗所统治、“狭的笼”般陈旧闭塞的空间,来叙述象征着不合理封建制度的祖父及父辈为了维持旧秩序与尊严,如何向子孙如高觉新等人伸出专制与迫害的魔爪,摧残、扼杀青春之子的生命。[16]其后,张爱玲在40年代完成的中篇《金锁记》里,塑造了一个与鲁迅的狂人本质相似,但又有所发展的疯子曹七巧。曹七巧受到中国传统父权社会婚姻买卖的迫害,走上爱、欲无望的绝路,和狂人一样是被“杀”(吃)之“子”。待其分家自立门户,性别错置地身代父职之后,竟也摇身一变为“杀子”之“父”,在三十年里 “戴着黄金的枷”,“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17](P183)极其变态地从精神与肉体上摧毁子女长白和长安的幸福。
从鲁迅到张爱玲,中国现代小说家在表现杀子命题时,多聚焦于讽刺与控诉封建“父”文化如何残暴地以强抑弱,如何扼杀青春萌发的“子”文化。郭沫若在建构小说的现代性时,则另辟蹊径,不把笔锋指向鲁迅一脉所针对的封建父权,而是选择叙述子的负累,来反映二十世纪初现代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压迫,逼使这些贫弱无助、苦闷不堪的“子”登涉疯狂的杀子之路。从另一个角度观之,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还期盼曙光,够呼吁“救救孩子”,郭沫若创作小说,却要冷血地终止孩子的性命,中断现代知识分子生命的延续,这是否意味着现代社会的逼害未必亚于中国五千年吃人的封建礼教,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五、重读郭沫若小说:由杀子意识开始
郭沫若膝下共十一人,⑤子嗣颇多。其小说亦多以主人公的家庭生活为叙述主体,频频刻画父母与稚子的亲密互动。职是之故,不管是将之比作身边小说,或称为中国式的私小说,学界过去只注意到郭沫若笔端充满亲子之间的喜怒哀乐,却忽略其时时流露出恐怖骇人的杀子意识。学者武继平尝言:“郭沫若是个浪漫诗人,但同时他也以现实中阴暗的私生活为题材写小说。而他这种小说所具有的主题格调沉闷阴暗的性格正好跟他的诗歌的豪放明朗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反衬。”[18](P154)郭沫若早期小说反复书写杀子的冷血场面,恰恰印证了这阴暗的主题格调的说法。
让我们再看 《残春》。爱牟眼见两个孩子惨遭妻子杀害,忍不住厉声责问。这时,晓芙回答道:“你这等于零的人!你这零小数点以下的人!你把我们母子丢了,你把我们的两个儿子杀了,你还在假惺惺地作出慈悲的样子吗?”说着就把手中鲜血淋淋的刀子向丈夫投去,爱牟当场毙命。[3](P32)如此在恶梦中与稚子一同横死刀下的结局,或许不仅仅是对于养家无方又背叛情爱的主人公的当头棒喝,暗示现代知识分子的绝无出路,同时亦提醒我们必须重新解读和认识郭沫若的小说。就这一层面而言,研究其杀子意识只是个开端。
(责任编辑:廖久明)
注释:
①《曼陀罗华》,郭沫若原注只说“10月17日(作)”,发表于1926年。《郭沫若全集》以1925年10月为创作时间,李标晶主编的《简明郭沫若词典》和武继平的《郭沫若留日十年》皆列为1924年10月之作,但没有交代原由。参照以郭沫若在1924年6月作(自注),刊载于同年8月20日《洪水》的散文〈盲肠炎与资本主义〉(《郭沫若全集》卷18改题为〈盲肠炎〉),与〈曼陀罗华〉中小孩之死于肠病的安排似有呼应,笔者赞同《简明郭沫若词典》和《郭沫若留日十年》的做法,将之定为1924年10月,亦即早期的小说。
②郭沫若在1924年8月至10月短短的两个月内共作九篇小说,占个人小说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笔者称之为郭沫若的“小说爆发期”。见吴耀宗:《郭沫若小说爆发期的拟欧造境》,《东岳论丛》,2009年,第12期,页68-72。
③桀、纣和易牙生于夏、商、春秋不同时代,鲁迅把三人错配在一起,显然是为了表现狂人错乱的精神状态。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卷,第452。
④如举例指出中国“有人神化生宇宙之说,而印度也有;又天狗食日月之说,而斯干底那维亚半岛也有。有人是粘土造成之说,而希腊也有”。郭沫若:《神话的世界》,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286页。
⑤郭沫若先与佐藤富子生四男一女:和夫、博生、佛生、志鸿、淑禹;再与于立群生四男二女:汉英、庶英、世英、民英、平英、建英。其子嗣共十一人。
[1]刘纳.谈郭沫若的小说创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4).
[2]朱寿桐.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3]郭沫若.残春[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4]李标晶主编.简明郭沫若词典[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3.
[5]郭沫若.漂流三部曲[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6]郭沫若.曼陀罗华[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9卷.
[7]郭沫若.鼠灾[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9卷.
[8]郭沫若.未央[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9卷.
[9]郭沫若.行路难[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9卷.
[10]郭沫若.圣者[A].月蚀[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9卷.
[11]郭沫若.圣者[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9卷.
[12]管子.小称[A].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册)[C].北京:中华书局,2004.
[13]郑振铎编著.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2006.
[14]鲁迅全集第2卷[M].
[15]鲁迅.药[A].鲁迅全集第2卷[M].
[16]巴金.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7]张爱玲.金锁记[A].张爱玲.回顾展I——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一[C].香港:皇冠,1991.
[18]武继平.郭沫若留日十年[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
I206
A
1003-7225(2011)01-0059-05
2011-02-21
吴耀宗(1965-),男,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