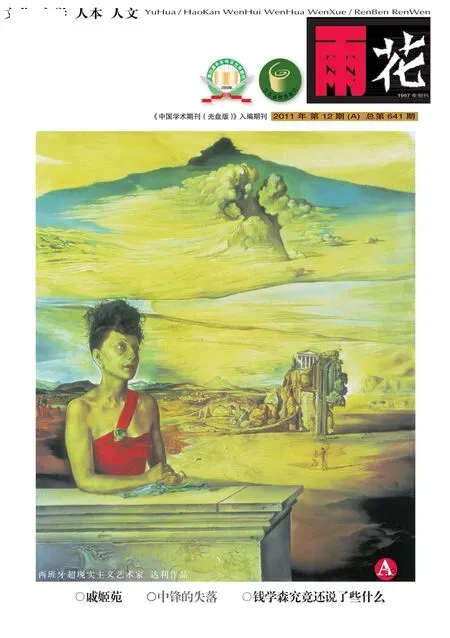往与生
● 陈元武
也就是这样的狠人,手指上还沾着狗血和油脂,却掐着香烟屁股吸得滋滋有味,那烟一拨一拨地吐出来,缓慢地吐成连贯的一串,看得我心底直冒凉气。

屠杀者
他个子细瘦,脸上油光洋溢,这是屠夫的经典脸色,还有他的头发,他的手上,总是油腻腻的,带着些微血红。
他屠猪、牛和狗,更多的是狗。他不喜欢狗,认为狗下贱,会吃路边的人屎,狗还会咬人,狗就该杀了吃肉。他过去是货郎,去陌生的村庄,就碰到个把恶狗,撵着他不肯放松,他抡扁担砸也砸不走,那狗直盯着他的后背唁唁地叫,呲牙咧嘴。狗就该全杀光了,这村庄才会消停。村庄里有太多的狗,有的狗诚实,咬人前会做一些威胁性的攻击动作,有的狗阴损,省去了这些麻烦的程序,趴在门缝里瞅人,看到不认识的人也不叫,只是冷冷地看,然后突然从门后蹿出来,扑到你身上就是一口。但这样的狗怕恶人,比如像他,他天天杀狗,身上带着味道,狗闻见了就赶紧跑开,紧张得浑身发抖,俯下脑袋,唁唁地叫,声音已经明显缺乏底气。
村庄里的狗早被他杀光了,他盯上了流浪狗。集镇上有的是流浪狗,只是身体肮脏,毛皮污秽,形容猥琐。他套狗的办法多着呢,一只麻袋驮在摩托车后边,里面有一个套圈,活套,看到狗就甩过去,套上狗脑袋就走,走不出一里地,狗就断气了,再塞进口袋里,驮回家。他家在村庄的另一头,一棵大树底下,一座上岁数的瓦房和一地血污的脏院子。树上钉着无数的狗皮,各种颜色的,狗到了那里,腿都软了,尿裆甩尾,后腿直不起来,汪汪地流泪,声音带着哭腔,朝他可怜巴巴地哀求。他抽着一只烟,冷冷地看着那些狗,盘算着怎样干净利落地下手。狗命长,勒断气了,放在地上,只要鼻子触到地气,不一会儿就缓了过来,还是活的。因此,他勒狗的时候,顺便就把狗皮脱了下来,一把剖皮刀一拉,狗的肚子就开了,里头是一层雪白的肉,狗挣扎,但不管用。他的动作麻利得让我惊讶,两分钟不到,狗就净了身。皮扔在一边,淌着血的肉身还在扭动。剥了皮的狗扔在一旁,接着剥下一条狗,一样的程序重复着。白花的狗堆在一起挣扎,它们还没有断气,看着自己的皮淌着血扔在不远处,直到死,它们眼睛里都满是冤屈的神色。
这人太狠了些。也就是这样的狠人,手指上还沾着狗血和油脂,却掐着香烟屁股吸得滋滋有味,那烟一拨一拨地吐出来,缓慢地吐成连贯的一串,看得我心底直冒凉气。
这算什么,我杀牛时,你肯定不敢看下去的。他脸上轻松地说着杀牛的经历——那牛见到我就流泪,我也不为难它,毕竟牛是好畜牲。我抡大锤砸它脑门,三五下就砸晕了,牛倒了,我才放血,这样牛不痛苦。也有的牛岁数短,年轻有力气,不容易断气,像年轻的公牛,砸脑袋也砸不死,血淋淋的还会朝我哭,我那时心就软了,下手就会啰嗦些,这反倒增添了它的痛苦。牛也不容易啊,我砸到手酸,它倒下了,尿了一地,屎也拉出半截。牛舌头吐出来,那就算是冤死的牛。它们死不瞑目,我也会难过,难过好几天。这杀牛不能手软心慈,否则它遭老罪了,于心不忍啊。我说你也会有心软的时候?他点点头,所以,我轻易不杀牛,杀牛有罪过的。那年我杀了一头牛,肚里还有孕,罪过,剖开肚子才知道的。那年我就倒霉了,骑车撞到沟里去,摔断了一条腿和一条胳膊,差点连命也搭上。
我说那你杀狗就不手软,他盯着我看,好像我的问题很白痴一样。是啊,那狗是贱物,杀它我心软什么。不过,有一回,杀一条流浪狗,我也心软了,那两条狗是夫妻俩,都让我逮来了。我碰到它们时,它们正躲在一只大垃圾箱底下,好像刚下了窝崽。我没注意是几只,就套了回来,头天就杀了那只黑的,那白的是条母狗,肚子底下拖着奶呢,我杀它时,它拼命挣扎,似乎在向我作揖求饶,我下手时迟疑了一下,它吭哧就给了我一口,咬到骨头上了,我怎么斫它踢它就是不肯松开嘴,直到它咽了气,我才掰开它的嘴。赶紧去医院打了狗针,回来,弄它的皮,怎么弄也弄不下来。那狗只好扔了。回头我老是做噩梦,那条白色的母狗在梦里一直追着我咬。我惊出一身冷汗,醒来,床上湿透了一边。回头我再去找那狗尸体,想好好埋了,做个道场忏悔忏悔。他的眼睛里已经泛红了,抹着泪。
那你以后别杀狗了啊。他说,早就不杀了。开个小饭馆就好。村庄里的狗叫声又渐渐密集了起来,白昼里也见到狗追着撵着,调情浪笑,做那事情。村庄里需要狗,村庄里的壮年人越来越少了,都到外边去不回来了。田地荒芜,草长得茂盛,山上的野狐和野猪就常常来村庄寻事。狗能撵它们,村庄里就多一些消停的日子。这狗少了,村庄也不安宁。
他拍了拍墙角靠着的一只药弩,以后就靠它上山打猎去,野猪太多了,成群结队祸害村庄。他信心满满地,脸上似乎又泛起一阵隐隐的杀机。我问,上回让狗咬得疼么?咋不疼,撕心裂肺地疼。那你还喜欢杀狗杀牛杀野猪?他答不上来,反正我抡刀的时候就来精神了,砍肉的时候就心生欢喜,蛮有成就感的。我无语。
他似乎就是书上所说的那种天生恶人吧,喜欢宰杀牲畜,内心里的魔是很可怕的,有的人怕杀生,是心里天生的慈悲。而他恰恰相反。这种人也怕疼痛,也怕死亡,怕自己身体上的伤口流血淋漓。肉体是平等的,此身痛即彼身痛,《夷坚志》里说了许多这样的事情,某人杀狗,见狗身上有花绣,颇为眼熟,后来一想,竟是他父亲生前身体上的特征,他于是恸绝于地,从此不再杀生。我想告诉他这些故事,但一想,他会听得进去么?但愿他能够在某一天自然觉悟。
佛说,放下屠刀,立地可成佛也。
幸存者
这是我所听到的最为令人悚然的故事。
60多年后,他幸存了下来,身体健康,每餐能够吃得下两碗大米饭,一个山药和若干鸡蛋。有时候,他还喝酒,一餐喝下将近半斤酒。他家的房子是永安寻常可见的旧式瓦屋,三间半,有辟舍和厢厅,和院子形成一个回字。院子里种着一棵不知岁月的柚子树。院门外是一口荷塘,初夏的时候,荷叶田田,挤挤挨挨,让每一阵经过的风都放大了声音。
这里和村庄的核心有着一些距离,村庄的核心就是祠堂和大庙,祠堂外竖着一对石旗杆,爬满了岁月的苍苔。平时经过祠堂的时候,门口几条卧着的狗就跑了出来,悄无声地跟踪着我走过去几十米,然后折返,依旧卧在太阳底下。
我去他家的时候,柚子花正在开着,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柚子花香味。他挑着一担水桶要上山,我有点替他担心,这么大的年纪还上山挑水?他已经习惯了劳动的日子,子孙们不让他干活,他便不适应,就会生病,或者生闷气,生闷气就不想吃东西。于是我一路跟着,听他用本地话说那段往事:那时候,日本人还没有投降,国民党省政府也搬到永安来了。日本人的飞机隔三岔五地就飞来轰炸,飞机飞得很低,像一只暗绿色的铁老鹰一样在头顶盘旋,然后俯冲,声音像鬼叫一样难听,炸弹就扔下来,轰轰,在吉山就炸过一次,死了好多人。刘大姆的男人就是那年给炸死的,他正坐在家门口扎竹筐,一颗炸弹落下来,人给炸成好几段,头颅飞到了十米外的菜地里,刘大姆正在菜地里摘菜,一声巨大的动静就将她男人的头给炸了过来,她当时就吓晕死过去。他说的那个刘大姆是村里的老人之一,现在估计也去世了,小脚老太,坐在板凳上目光呆滞地看每一个人,嘴角带着神秘的微笑。
山坡上开着各种无名的花,黄的或者白的,细小,碎琐而美好。草修长地挡住我们的去路,趟着草走很费劲,也很无奈。但他挑着水桶走得很稳健并且轻松,日本人扔过炸弹后不久,又再来了一回,这一回是单架飞机,在村庄上空盘旋了许久,扔下几枚臭弹,没炸响,村庄里的人好奇围观,原来是白色的陶瓷大罐,哗地摔碎,冒起一阵白烟,然后看到蟑螂和老鼠到处惊恐地奔跑,还有臭虫什么的,很小,见人就咬,估计是饿了许久。人们好奇过后就散去,各自回家。过几天,村庄里就有人生病,病来得很凶急,两天就挺在床上了。然后是不停地死人,症状都差不多,眼睛流血,上吐下泻,最后全身抽搐而气绝。那便液腥臭难闻,嘴角流出来的血也是黑污的,揩也揩不干净。村庄里一下子就死几十人,活着的人害怕了,不敢回家看,也不敢去别的村庄,就跑到山上露宿。国民党政府的医务人员来过村庄一次,取样化验并进行了焚尸消毒。全村都喷一种药水,味道很难闻,火化工全身穿得不见眼睛和鼻孔,抬起死人就在村庄附近空地摞起,浇上汽油焚烧,那烟黑黢黢地冒起来,在山上的人看着不敢下来,跪在那里哭,哭得昏天黑地的。然后是死寂般的日子,听保长说那就是鼠瘟,日本人故意传染给我们的。
许多年过去,也没人敢回家住,就集体搬迁到另一个村庄,就碰到了现在的老伴,就有了现在的家。我说您原先的呢,他说不敢回去,估计都死光了吧。后来,政府分田地土改,那个村庄也渐渐被人记了起来,有胆大的人就回去了。说是鸡和猪等家畜都成了野生的,狗吃过死人也都死绝了,房子倒了一大半,剩下的也不能住人,残破严重。政府统一拾掇了房子,荒芜的田地也重新开辟起来,村庄重新升起灰白的炊烟。他胆子大,也回来了。分了一块好大的地,但村里的水井都封填上,水就从河里挑回来。河水一直流着,干净。村里的大榕树让雷劈去一半,那是天厄。
我脖子上也长了一个疽,一直烂,直到见骨头,天天流着臭脓。后来是一个郎中给了我一副药,是烧蜈蚣和蛇蜕和其它的草药,糊了三个月,才长肉不流脓水,好了留下这个杯口大的凹。现在脖子也使不上力气,挑担子时头就一边偏着,他们叫我歪头阿五。那时候,在村子里住的人也是担心那些细菌会不会重新祸害人?政府里的人来解释过说不会了,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细菌可没那么长寿命。但我的脖子疽就让我害怕,那时候老感觉自己要死了,晚上就不敢吹灭了灯睡觉,房间里也要点个松明子或者豆油灯,有点光亮才敢睡觉。房间对大河那边,一开窗,就能够看得到哗哗的河水或者满天的星光。我说晚上也能看得到河水?他说是的,他的眼睛晚上也能看得清东西。比如某一天夜里,他就看到一只黑鸮飞进刘大姆的家里,他喊了起来,人家以为看到贼了呢,都披着衣服冲出来。一只黑鸮,那就是要死人的灾物,那东西一来,家里准不太平。后来才知道,刘大姆的孙子拉肚子,拉得虚脱了,黑鸮是闻到腥臭味才来的。果然,她孙子就没抢救上来。刘大姆哭瞎了眼睛就是那一年的事情。
这柚子树好,听说可以避瘟疫,庙里的神像都是柚子木刻出来的。我种了棵柚子树,院子前挖了一口塘,这花香能够让日子舒坦起来,人活得利落,就不会着病。莲荷柚子(连和佑子),村里人没文化,就图个吉利。我那门上的门神老爷也是我自己绘的,咋样?我说很像很逼真,那种年画手法,不是轻易能绘得出来的。
我想继续打听鼠疫的事情,他的脸沉了下来,沉默,然后是抽噎,声音越来越响,他摆了摆手,不想说哩,不想说哩,伤心的事情,伤心一辈子的事情!亲人父母都不知道埋在何处,那把火都烧成灰了,让风一吹,漫天飞舞的,哪里还有踪影?
沉默,我沉默,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