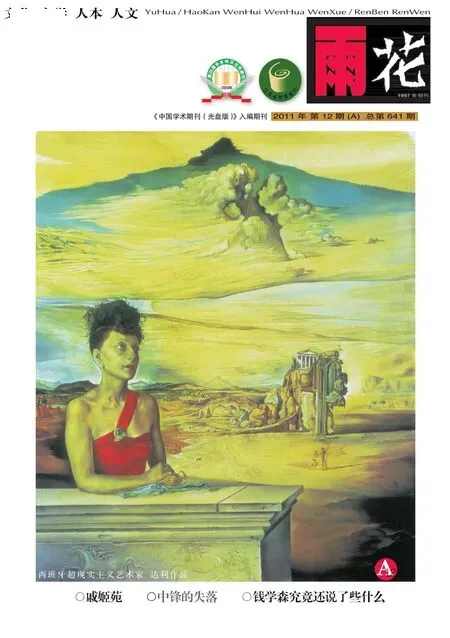以“人”的名义质询
● 李晓灵

2010年,一系列关于“小姐”的事件牵动了媒体敏感的神经。7月5日,东莞警方为了显示扫黄决心和力度,将一名缚住双手、赤裸着双脚的“小姐”像拉动物一般用绳子牵着指认现场,并在镇电视台播放;9月,杭州市拱墅区祥符派出所又向预设为“小姐”的“发廊女”的家属寄发了贴有照片的所谓“挽救信”。而在此前,河南郑州公安局在扫黄过程中,也曾赫然公布了一些“卖淫女”的裸体照,一系列对有卖淫嫌疑的“小姐”的公开侮辱性执法行为伴随着媒体的聚焦和散播,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对此,赞扬者有之,说非此等严厉执法不足以彻底铲除黄祸,但更多的是对其执法理念的质疑和批驳,这些批驳大多站在“法”的高度,从维护公民隐私权和批驳中国传统法家式“羞耻刑”的角度进行评论。勿容置疑,单个执法者的粗暴行径确实应该受到文明法的质询,但仅仅从法的视角去评论事件本身,多少有点避重就轻、隔靴搔痒之嫌。
法是现代社会带有强力性质的暴力制约,是一个社会的最后屏障。换言之,法是一个社会最后的底线,法若崩溃,社会的毁灭将不可避免。在极富激情的柏拉图看来,人类社会的理想王国正是因为置身于品行高贵,不谋私利,几近于神的“哲学王”的昊昊光辉之下,才显得至善至美,光芒万丈。只有当他非常失望地意识到人性的阴暗和孱弱后,才极为矛盾地在《法律篇》中提出了“法律之治”的预设,不难想象,苦心孤诣,誓为人类构想理想乐园的柏拉图此时的心情是何等无奈和悲凉。柏拉图“法律之治”是对“哲学王”的补充限定,并非是“哲学王”的彻底毁弃,而是一种人类社会构建的理想设想:“哲学王”是最高理想,“法律之治”是最后防线,两者并行不悖,但高下之分昭然,而且二者不可逾越,亦不可互为遮蔽。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并不是人类最理想的至高准绳。
可是,为何什么事都要拿最后一道防线来衡量?一切皆从法眼之下,人类文明必将沦为暴力张牙舞爪的祭台,人类社会亦将演化为罗马斗兽场式的暴力而又血腥的世界,而“人”则将最终退化为失却“人性”的兽类。从这个角度说,对人类孜孜以求的“伊甸园”而言,真正意义上“人”的社会,确乎应该有更为高尚、更为人性的标准。
也许,对于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当下中国而言,狼奔豸突于经济的高铁之上,文明的迷失、文化的虚置、道义的废弛使得我们在更高的文化疆域有心无力,乏善可陈。于是乎,“法”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退而求其次、无可奈何的选择,并因此固化成最后的守护,而“人”则成为有意无意的牺牲品。由此,我们的每一个进步由此都弥漫着焦虑的雾霭,纠结成了我们普遍的心态。
那么,何不超越“法”的层面,以“人”的名义来思考呢?
《圣经》中有一个故事。耶稣正在教训众百姓,有一个行淫时被抓获的妇人被文士和法利赛人带到耶稣跟前。文士和法利赛人说,“夫子,这妇人是正在行淫之时被捉拿的。摩西的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耶稣没有回答,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说完仍旧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人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妇人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此次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在西方基督教文化看来,人类的始祖因为偷吃了“伊甸园”的禁果犯了罪,被逐出,由此导致了人类天然的罪性。只有神是完美无缺的,而人是不完全的,人人都有罪,所以摩西制定了“十诫”来约束人类,以免陷入撒旦的圈套,堕入罪的深渊。这样,就承认了犯罪是人的本原性特质,绝非神类的“人”对罪不可剔除,亦不可避免。正是因为如此,耶稣才毅然背负人类的罪,作为活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替“人”赎了罪。尽管如此,“人”的整体被赎,依然难以改变个体人的犯罪。那么人犯了罪该怎么办呢?耶稣首先警告人,罪的工价乃是死,告诫人不要犯罪,犯了罪就要悔改,因为“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悔改可以消除人的罪责,“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这是人的自我救赎之路。而社会对犯罪的人该怎么办呢?“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要宽恕,要用爱去感化他们,如同耶稣对有罪妇人所作的评判一样,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同时,“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救赎”,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审判者借此秉以仁慈宽恕之心,并进行充分的自我反省,首先被救赎,终而实现人类的整体救赎,审判者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救赎是他们进行审判和救赎的前提。其根本的逻辑是,没有哪一个人会先验地占据道义和法律的高地,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都有可能犯罪,所以博爱、宽恕是用以救人自救,乃至人类整体救赎的至善良方。
根本上讲,西方基督教文化在承认“人”的原罪本性之下,倡导宽恕、仁慈、爱,以神的感召,进行精神救赎,将灵命的自我悔过和外在的宽仁引导相结合,将审判者的先在自省和他者解救,与犯罪者的自我悔罪与社会救赎同时进行,从而在博爱的大旗下实现社会的整体进步,人道主义是其精髓所在。
在此精神的烛照之下,对有罪之弱者的同情与怜爱,成为体现人性光辉的最高祭台。对女性,尤其是受伤害的女性,譬如沦落风尘的女性,更是如此,它成了西方文明的一个良善标记。
小仲马在他的《茶花女》中非常动情地宣示了这一信条。他对误落风尘、看似有罪的女子进行了极富人性的抚慰。“可怜的女人哪!如果说爱她们是一种过错,那么至少应该同情她们。你们同情看不到阳光的瞎子,同情听不到大自然音响的聋子,同情不能用声音表达自己思想的哑巴;但是,在一种虚假的所谓廉耻的借口之下,你们却不愿意同情这心灵上的瞎子、灵魂上的聋子和良心上的哑巴。这些残疾逼得那个不幸的受苦的女人发疯,使她无可奈何地看不到善良,听不到上帝的声音,也讲不出爱情、信仰的纯洁的语言”①。
接着,小仲马又列举了一些心灵高尚的人对这些受伤的灵魂的救治,雨果刻画了马里翁·德·洛尔姆,缪塞创作了贝尔纳雷脱,大仲马塑造了费尔南特。有时候一个伟人挺身而出,用他们的爱情甚至以他们的姓氏来为她们恢复名誉,是异常高尚的事,所以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家和诗人都把仁慈的怜悯心奉献给那些可怜的娼家女子。
小仲马又说:“基督教关于浪子回头的美妙的寓言,目的就是劝告我们对人要仁慈,要宽容。耶稣对那些深受情欲之害的灵魂充满了爱,他喜欢在包扎他的伤口的时候,从伤口本身取出治伤口的香膏敷在伤口上。……崇高的宽恕行为应该唤起一种崇高的信仰。”②他对玛格丽特的哀怨绝唱是最好写照。
可以说,以小仲马为代表的西方艺术家真正践行了西方文化的这一人性宣言。宽恕、慈爱、人性地救赎这些苦难的女性的灵魂是西方文明从理论到践行、始终不渝的法则。
但是,当代文明语境下,我们何以前仆后继地出现对这些女子毁及人性尊严的严厉惩罚呢?
不可否认,中国儒家也讲宽恕,也讲仁慈,甚至推及到了动物,所以有“君子远庖厨”,不忍其觳觫的感叹。但是,另一方面,与儒家宽恕仁爱相抗衡的却是法家“人性恶”的滔滔恶浪。在“人性恶”的基调之下,法家坚信,自私自利是人性本质,也是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趋利避害是人之根本,即使骨肉手足之间也莫不“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以至于“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于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在法家眼里,人性就是欺骗、争夺、压迫,甚至是血淋淋的暴力虐杀,仁义慈爱毫无价值可言,甚至是好用者必亡的“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悌”、曰“诚信”、曰“贞廉”)。以此种法家思想治国,则无论尊卑贵贱,皆刻薄寡恩,唯利是图,德义丧尽,如班固所言“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令人胆战心惊,不寒而栗,吴起杀妻求将,陈平盗嫂受金,无所不用其极。“人”前所未有地露出了狰狞残暴的一面,由天使而一变为永难救赎的撒旦,向着绝望的罪恶之国一路狂奔。
而历数中国数千年历史,“外儒内法”一直是历代统治者的不二秘籍。谙熟法家奥秘的统治者对越律犯乱者往往严刑酷法,刀劈斧凿,株连九族,残暴之极。就是现代中国也是迷信严法厉刑,动辄公捕公判、游街示众,以此震慑犯罪,“文革”更是到了极致。究其实质,这些做法都显示了统治者一以贯之的信条:非以挑战人性底线的方式难以达到钳制天下、长治久安的目的。其显而易见的潜台词是,只有彻底毁及民众做人的尊严,才能杀一儆百,除恶瘤于一旦。统治者深信,百姓高压之下,为了保全自身,必会胆战心寒,全心顺服,如此则天下太平无虞矣。岂不知,“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人最后的领地被毁,鱼死网破,以死相搏,也会是一种选择。更为甚者,暴力迷信的肆意膨胀,使得个人的自我救赎和整个社会的救赎都全然落空,社会因此沦入恶的轮回之中,终遭灭顶之灾。拨乱反正以后,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淡化和扭转,公判公捕逐渐淡出视线,注射死刑也以较为人道的方式成为死刑的选择。但是,文化心态上,践踏尊严,非厉法无以治乱,非暴力无以治罪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当矛盾被激化,体制性恶果往往会转嫁到个体身上,弱者无奈的选择,就成了以恶制恶、文化群氓暴民式的发泄对象和牺牲品。对“小姐”们毫不顾忌其人性底线的做法恐怕与此相关。
同时,在万恶淫为首的传统文化理念之下,古代动辄对所谓的“淫妇”们刀割斧劈,甚至千刀万剐、以“凌迟”处之。延及现代,对“性”上越律犯规的女性,亦是罪加一等。女性似乎是现代文明“性幻想”的符号,也想当然地成为性罪恶的“祸根”和主要攻伐对象,“小姐”尤甚。“小姐”是改革开放的“副产品”,是所谓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清新的空气一起进来的“蚊子”中的一个,是社会丑恶现象的标志性符号之一,既伤风化,又有损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损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再深一点,她们亵渎了人类最为宝贵的“生殖权”,所以,非重罚不足以治乱,岂需奢谈人格尊严?
岂不知“小姐”亦是父母所生,哪个天生就是娼妓和“小姐”?几个女子愿意做人人践踏的“小姐”?实际上,每一个“小姐”都有一笔心酸账,都有一部令人不忍卒读的屈辱史,而每一个“小姐”后面亦有一个千疮百孔的家庭。如若这些不能消除,同时,那些庞大的男性消费群体不能消除,单靠羞辱几个艰难地生存在社会底层的弱女子,究竟能起到多大的效果?而且,和久治不愈的贪污腐化、社会不公等问题相比,究竟哪一个更加具有危害性?
执法者如此严惩“小姐”,实际上,在占据社会公权优势的同时,想当然地预设了自己道德和人格的潜在优势,就像阿Q自豪地宣称“上辈子我比你阔多了”一样,面对弱势的“小姐”,其心态往往是“好龌龊啊!”然而,真是这样吗?未必。正如耶稣所说,他们只看见别人眼里的刺,而看不见自己眼里的梁木。一个眼里有梁木的人对一个眼里有刺的人说“看,你眼里有刺!我来替你拔掉!”岂不滑稽?
尽管后来为了表示对“小姐”们的宽仁,社会开始变换口径,将她们改称为“失足女”,依然耐人寻味。所谓“失足女”,言下之意,定然是自己一不小心,方才误入歧途,然而,人们不禁要问,她们究竟是无意间“失足”,还是无奈间“被失足”?如果是“失足”,又是为什么“失足”?谁应该为其负责?
细细思之,多数“小姐”如若“失足”,确是无可奈何的“被失足”,社会没有提供给她们足够的空间和尊重,使得她们绝望地滑向黑暗的深渊,社会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且,“失足女”的定义暗含着一个微妙的深意:既然是自己不意“失足”,如若有错,错在其身,关社会与他人何事?由此,社会和管理者在巧妙的文字游戏中,借仁慈之名将自己脱了个干干净净,可谓煞费苦心。
孟子说过,羞恶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如果羞恶之心不被保全,人将难保为人,人性之善必被毁灭,而人性之恶则会如脱缰之野马,为所欲为。
注释:
①②(法)小仲马著、王振松译:《茶花女》,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