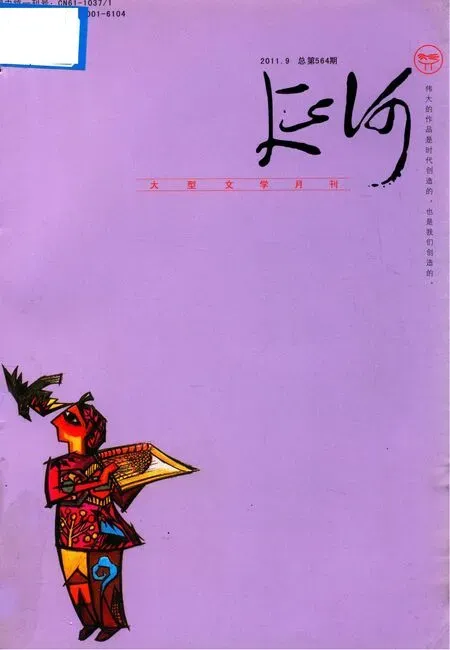希尼诗选
[爱尔兰]西默斯·希尼贾勤 译
自我的诗泉
小时候,无人能阻止我去看水井,
还有带着吊桶和辘轳的老水泵。
我爱那幽深的坠落、困陷的天空,
水藻、菌菇和湿苔藓的气味。
一口井在砖厂,盖着朽烂的木板。
我体会当桶拴在绳子的一端
骤然落下时激起的丰沛传响
那么深,你看不到井中倒影。
一口浅井在干涸的石渠下
却丰产得好像一个鱼塘。
当你把长长的根拽出柔软的泥层,
一张苍白的脸在井底荡开。
还有的井有回声,用鲜亮的乐音
回应你的叫喊。还有口井令人害怕
从那儿的蕨草和高高的指顶花间
窜出一只老鼠扑踏过我的倒影。
而今,去窥探根须,用手指搅弄泥土,
像大眼睛的纳西瑟斯,凝视某个泉源
都有损成年人的尊严。我写诗
只为凝神自照,只为使黑暗发出回声。
铁匠铺
我只认得一道进入黑暗之门。
外面,旧轴和铁箍正在锈蚀;
里面,锻砧短促的铿锵声,
不可预料的扇形火花
或新蹄铁在水中变硬时的咝咝声。
锻砧定然是在中央某处,
一端如独角兽尖,一端方形,
坐定在那里:一个祭坛,
他在形态和音乐中消耗自己。
有时候,围着革裙,鼻子里满是茸毛,
他倚在门框上探出身来,想起双蹄
在风驰电掣的来往车辆中叩击;
然后咕哝着进屋,轻重兼顾
要打出真铁,要锻出吼声。
半岛
当你再也无话可说,那就驾车
在半岛上兜它一天。
如同在飞机跑道,天空如此高远,
岛上并无界标,你不会抵达
只是经过,尽管总是绕着初见的陆地在转。
黄昏时分,地平线饮尽了大海和山岳,
犁过的田野吞下了刷白的山墙
而你再次回到黑暗中。回想起
上釉的海滩以及原木的倒影,
把浪花撞碎的岩石,
踩高跷的细脚鸟,
安然驶入浓雾的岛屿
而后开车回家,仍然无话可说
此时你将设法解开所有风景的
密码:事事物物如此明快的呈形,
水与土就在万物的尽头。
安娜荷黎什
我的“清水之地”,
世界开端处的小山
那里涌出的泉水,注入
闪光的草地
注入故乡小路上
黑色的鹅卵石。
“安娜荷黎什”,你这辅音
柔美的坡度,元音的草地,
记忆中的灯盏
摇摆着穿过
冬夜的庄院。
推车带桶
那些小山上淳古的居人
隐于齐腰的雾中
在井边、在粪堆上
敲碎薄冰。
一首新歌
我遇到一个从德瑞加夫来的女孩
这地名,一种失传的兴奋香水
让我想起河湾流转之地,
有蓝色的渔犬从暮霭中跃起
踏脚石一如没入
浅滩的黑色臼齿,旋涡多变的
亮面,莫尤拉河
在赤杨树下何其欢乐。
德瑞加夫,你正是:
夕阳中的水,逝去的音乐——
是平静远古的祭酒
由偶然降临的处女灌溉。
而现在,这河的舌头却要
从深深获取的生息之地
上升并泛滥,在元音的拥抱中
以子音来命名领地。
卡斯勒道森,请加入我们的军队
还有阿普尔兰德,每一道殖民者设下的围栏——
如同褪色的草地要被纯绿占领——

波兰插图画家Pawel Kuczyński作品
如同元音,正是爱尔兰的古诗与礼器。
雨的礼物
1
暴雨倾盆,停也不停
好几天了。
安静的哺乳动物
踩在泥中的脚沾满稻草,
他开始用皮肤
感觉天气。
灵活的雨的鼻子
舔着踏脚石
拔起根来。
他调测深浅
遍涉人生之水。
调测深浅。
2
有人费力地趟过淹没的田野
打破洪水的界面:
有朵泥水之花
开上他的倒影
仿佛切口一般
带血穿越盆地。
他的手在探寻
铁铲尚未挖掘的
水下的红薯垅,一个沉于海底的亚特兰蒂斯
他依靠其生活。因此
被困在他耕作的地方
天空和大地
正在他探索着丰产土地的双手中流转如故。
3
雨在聚集
滩头传来
整夜不息的轰鸣水声。
世界熟悉的响动传入童年的耳中
他们听到自然反复的
倾吐,一段急流
淌着口水经过山墙,
莫尤拉河在它的砂砾大床之上
不停地说出:
破晓时分所有雨水管里流出的水
都以自己的姿态溢出下面的桶
再从每个桶中漾出
一如女人披散的长发。
我竖起耳朵
却听不到——
共荣之血在召唤
使我要求
上古洪荒之水以前的知识。
异代逝者柔和的声音
正在岸边低语
我想提问
(也为了我的孩子们)
关于败腐的庄稼,河泥给
烧坚的陶土河床上釉。
4
茶色之水通过喉音
诅咒自己:莫尤拉
是它自己的伴奏和配乐,
发尽潜力
将所在之地铺成河床,
管簧之乐,一位暮年的歌者
把她雾霭的低吟吹入
元音和历史。
一条涨水之河,
交尾的呼唤声
升起,给我快乐,使我成为富有的戴维斯,
把共同的大地深藏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