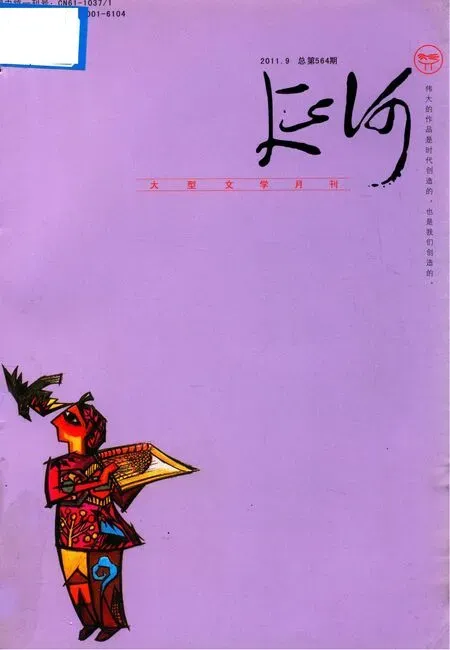打场子
庞爱莲
一
呸,狗日的!
呸,婊子养的!
随着骂声,一把竹子笤帚很夸张地扫着地上的尘土,尘土也仿佛领会了老孙的意思,一窝蜂地扑向方开文的冰棍箱子,也扑向坐在马扎上的方开文。
拿笤帚扫地的人是老孙。老孙大概有六十多岁,一张猪肝脸,嘴上朝前呲着三颗黄黄的大门牙,他一边借扫地为名,用笤帚搅起地上的尘土,一边嘴里喷着唾沫星子,恶狠狠地骂着人。
方开文知道老孙是在骂她,心想:我惹不起你还躲不起你么?我不还口,让你骂!
她没想到老孙越骂越来劲,脏话像臭水一样从老孙的嘴里涌出来。方开文实在无奈,就说:老孙,你扫慢一点嘛,你看这黄尘把人眯的。
老孙听出了方开文话语中的胆怯和恳求,更加来劲了。哎呀!你是哪个庙上的尼姑,你还想管老子?老子在这巷子口一个人卖冰棍多少年了,你到那个拐角旮旯去闻一闻,老子在这儿尿出去的尿都比你从小到大喝的水多哩。
老孙,你卖冰棍,我也卖冰棍,我又没惹你,你怎么骂人哩?
哎呀!你还没惹老子?老子就扫这巷子口屁股大的一点地你都不让扫,你还没惹老子?老子不光骂,还想打人哩!以为老子是松包?
老孙骂着就用脚去踢方开文坐的马扎,那马扎一活动,方开文趔趄在地上,接着老孙又飞起一脚踢了冰棍箱子,不等方开文站起身来扑救,那箱子“啷”一声倒地甩开,冰棍扬了一地。
方开文扑到冰棍箱子前往起拾冰棍,眼泪扑簌簌地滚下来,边哭边唠叨,老孙你欺负人!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你做这样的缺德事!
老孙这时背对着身后的巷子,面朝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坐在他的冰棍箱子跟前,仿佛没事人一样,脸上隐隐地露出一丝得意的神情。过来一个行人向这边看时,他就赶紧对着那人喊:冰棍,一毛的,两毛的。
方开文哭哭啼啼地拾掇起冰棍箱子,经老孙这么一折腾,她心情坏到了极点,自然不能卖冰棍了,就用自行车后架驮了箱子合上马扎走了。老孙看着方开文离去的背影,嘴角一歪,脸上露出了一股得胜却又胜得不光明正大的阴阴的笑。
二
方开文回到家就病倒了。
她几天不思茶饭,肚子上却隆起一个硬硬的疙瘩。这疙瘩里装着老孙多日以来的谩骂,装着所谓市场规律的弱肉强食,装着“改革开放形势一片大好”光圈下的世态炎凉,还装着对丈夫携了买断工龄的所有钱南下深圳经商一去三年杳无音信的怨怼。这些恶浊之气搅和在方开文的肚子里,就像一些不断繁殖的毒蛇穿梭往来,大有要了方开文的命的气势。
女儿玫玫才四岁,摸着那疙瘩问妈妈:你这肚子里是怀了小娃娃么?我小姑肚子里就有小娃娃了。她摸摸玫玫的头:不是,是气。玫玫就偏着小脑袋问:妈妈,你怀气干什么,气也能生出来么?
方开文无奈地冲女儿笑笑,眼泪流出来了。孩子还小,自己和丈夫一起说下岗就从电影公司下岗了,往后拿什么来养活她?
下岗这三年多来,方开文尝试了好几种小生意。先是到市场摊子上卖羊杂碎,一月不过,那生意就渐趋红火了,一天下来,怎么也能收入个一二十块钱。正当她做得起劲的时候,不知谁乘她上厕所的机会,给她的杂碎锅里下了泻药,凡是那天吃过她羊杂碎的人都抱着肚子来寻她算账,说她那杂碎这次没洗干净,说不定连肠子里的屎尿一起都做到锅里,让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吃了,才这样拉肚子的。弄得她草草收拾了杂碎摊子,躲起来,不敢再去那儿。风声过去之后,她又在一个巷子口卖馄饨热包子。方开文心眼实诚,包的馄饨和包子都皮薄馅大,价码也合理,每天从早晨一直到上午十一点,她的摊子上都不断地有人来光顾。早晨人多的时候,闲着没事的老头老太太为了喝她的馄饨吃她的包子等半个小时也心甘情愿。方开文自是喜上眉梢,赔着笑脸忙得风车一样转个不停。收摊子回家后,从围裙的兜兜里大把抓出钱,很快意地数着。可是好景不长,仿佛是一夜之间,就没人来她的摊子前吃饭了。她不知原因,见了老主顾还大声喊,人家理也不理地走了,还边走边说饭是做得好啊,可惜得了乙肝病,谁还敢吃?听到这句话,方开文脑子里刹那间一片空白,张着的嘴还没来得及收拢,举着包子的手也愣在半空,这才惊奇地知道,有人给自己造了谣。
以方开文二十九岁的年龄,她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想凭苦力、凭本事在社会上谋生,怎么就这么难?
方开文躺在床上,既睡不着也醒不来,浑身软得像面条,肚子里的疙瘩却越来越硬。回忆着自从下岗自谋生路以来经历过的一件一件的事,这些事就像一剂比一剂重的染料,把她的心一层一层地往灰染。
三
这时姨夫来了。
方开文的姨夫在农贸市场入口处设摊修理手表。他原先是县百货公司五金钟表柜台的营业员。由于喜好钟表行当,自学精通了钟表原理,自然也就会修理手表了。他比方开文早三年离开百货公司,如今早已占据了“三尺”谋生的摊位,靠修表挣来的钱养活一家五六口,供三个孩子上学。
方开文从小就没了母亲,人常说“姨姨怀里闻娘香”,她小时候大多数时光都是在姨姨家度过的,方开文从小生就得顺眉顺眼,甜言软语的会说话,再加上姨姨跟她本是连着骨肉血缘的,所以,不仅在姨姨怀里闻到了娘香,还在姨夫身边感到了父爱,姨夫看她也像亲生的女儿一样。
姨夫进门就说:开文,睡着干什么?起来!起来给姨夫熬绿豆米汤去,姨夫大半辈子了,就好这一口。方开文听姨夫跟她要吃喝,也就尽着力气从炕上爬起,身子虽说有些软绵绵的,头也晕晕乎乎的一时确定不了方向,可那灰气却也仿佛被姨夫的话荡去了一些。姨夫喝着绿豆米汤说,开文,你也来它两碗。哎呀,人家当官的有钱的人都喝什么五粮液、茅台,那是喝排场哩;我喝这绿豆米汤是调养身子做活过光景哩。喝上两碗绿豆米汤,出去跳弹那么几下子,浑身从里到外都是顺溜的,娃娃,不信,你尽管试试。姨夫又舀了一碗绿豆米汤,先不急着喝,用筷子搅着说: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不能让气憋死,更不能自己把自己憋死!他老孙,老孙是个——姨夫想说老孙是个裤裆里的球,又觉得当着方开文这么骂不合适,就稍微停了一下说:老孙是个屁,我放出来的屁!他敢踢踏你,你就不敢踢踏他?他敢骂你,你就不敢骂他?娃娃,在社会上混事,可不比咱们以前在单位里,在单位里有制度捆扎着,有领导调停着,还有工资压着。在社会上有什么?什么都没有。社会上的人都是属狗的,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了,他就往后退了,要不,怎么也得让一让了,说不定还会给你摇摇尾巴溜达你哩。不要哭,眼泪只有你的娘老子亲人见了才会觉得惜惶,让欺负你的人见了,他就觉得你是松包,会往死地整你;不要怕,欺负你的人是一堆干柴点着的火,你一怕,就成了风,你这风就会把那火煽得更旺。像咱们这些从单位里走出来工人,光有志气力气不行,还缺一项至关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匪气。用匪气去对付那些有匪气的人,就像老孙那号的。要在这街面上立住脚,首先就要打场子。娃娃:打——场——子!你懂不?
姨夫的一席话,让方开文如醍醐灌顶,从此,“打场子”这一概念在方开文的意识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姨夫走后,方开文一遍遍地回味着姨夫关于打场子的话,她对姨夫的社会经验是深信不疑的,可是,她还是有许多朦胧模糊的疑问解不开。

波兰插图画家Pawel Kuczyński作品
方开文从小到大一直是一个听话、乖巧、温顺的人。小时候上学,老师教育不要迟到,迟到了不是好学生。她总是老早背着书包到学校里去,即使门不开,在教室门口等着,被风吹、被毒太阳晒,也从没觉得自己来得太早有什么不应该。老师说,同学之间要相互团结,不能打架斗殴。即使有个别同学骂她是“没娘娃娃”,或者动手打了她,她也绝不肯还手的,顶多也就是躲到墙脚哭一哭了事。她心中建立了一个信念,打骂人的学生不是好学生。老师还说:要好好学习,将来才能有出息。她就认认真真地学习,只是由于自己生性反应迟钝,比如说这样的数学题:有两个同样的杯子,一个装满牛奶,一个装满开水,把牛奶喝去四分之三杯,再把水喝剩五分之一杯,然后把剩下的牛奶和水归并到一个杯子里,问杯子是满还是不满?问混合起来的水奶是奶多还是水多?方开文就弄不懂,只好回家请教姨夫。
姨夫自然算不得好家长,在这方面连一般的家长都算不上,本来稍微动一下脑筋就能弄懂的问题,他总是不按老师的思路走。他说:你们老师也真是吃饱了撑的,那牛奶和水,不都是喝的东西吗?你先一口气把牛奶喝完,要是觉得渴,就把那杯水也喝了,要是不渴了,就不喝水了,要么就少喝一点,奶贵水不值钱,知道这点就行了。方开文在姨夫那里得到的是生活经验,而不是数学分析思路,自然数学就不开窍,考试成绩不高。像方开文这样的学生,数学学得不好,你就是再努力,再遵守纪律,在老师眼里也算不得好学生。参加考试什么的也不会榜上有名。还好方开文是非农业户口,毕业时可以以城镇青年的名义招工,才有了电影公司的工作。
在学校里,老师一再教导,不要打人,不要滋事生非,要懂文明、讲礼貌,那为什么社会上总是那些打人、骂人的人吃得开呢?
方开文想来想去,对这档子事越想越糊涂,她就索性不想了,她现在觉得想那些事都是扯淡,你说就是想清楚了又如何?有人给你安排工作么?有人给你发工资么?眼下还是在这县城的一隅找个能容下自己和冰棍箱子的地方,赚几个钱养活自己和娃娃要紧。
她又一次在街上转悠着看,街道不太长,巷子口却不少,而每一个巷子口又都有两三个卖冰棍的,唯独这政府大院和文化馆之间的巷子口只有老孙一个人卖。遇上幼儿园放学和中学小学放学,老孙一个人忙都忙不过来,生意自然是不错了。方开文心中决定,还是要到政府大院和文化馆之间的这个巷子口卖。
老孙满以为方开文不会再来了,这天看到她又来了,心里想这女子怎么她妈的就不长个记性?我老孙要是能容人的话,还能一个人在这个红火的巷子口卖冰棍长达五年?
呸,狗日的!
呸,婊子养的!
这回老孙懒得用笤帚扫了,光吐着唾沫骂。
方开文的心就呯呯跳起来,手也有一些抖了,她想起姨夫那关于“打场子”的教导,心里才慢慢地平静了,人也镇定了一些。人一镇定,就能生出一些胆量来。
呸,狗——日——的!
呸,婊——子——养的!
方开文仿佛是学老孙骂人,却又学得那么没底气,声音飘飘的、颤颤的。
老孙扑过来,指着方开文的鼻子问:你骂谁?!
方开文说你刚才要是骂我,我现在骂的就是你。
老孙说我骂你。
方开文也说我骂你。
老孙说你嫩娃娃想跟老子打架哩?
方开文说龟老汉——想跟老娘——打架哩?
老孙想过去掀方开文的冰棍箱子,方开文就眼疾手快地抱住老孙的腿,老孙扬手打方开文,方开文就咬老孙的腿。
两人打成一圪塔时,不知一下子从哪里冒出了许许多多的闲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看。不多时,公安就来了。
经过正面教育反面教育,方开文终于和老孙一起相安无事地在这巷子口卖冰棍了。在这些看似平淡的日子里,方开文不知道自己今后炼摊的道路还会充满曲折。
四
北方的冬天说来就来,霜降节气还没到,狂风已开始卷着杨树叶子哗啦啦地满街飞了。冬天一来就没人吃冰棍了,先是老孙不卖了,改卖烤红薯,接着方开文也不卖了,改卖棉花。
老孙卖烤红薯还可以在巷子口卖,方开文卖棉花就要到农贸市场上工商指定的地方去卖。这又意味着要打场子,好在方开文有了头一回跟老孙打架的经验,也没费多大的周折就打下了场子。
尽管打下了场子,可方开文还是跟一个卖棉花的姐妹结结实实地打了一架。
和她一溜一起卖棉花的还有两个半老男人和一个来自米香县的小个子女人。本来那三家卖棉花的比方开文来的早,到方开文加入时,他们心里是老大的不高兴,几家都试着找了几回茬,发现方开文也不是好惹的,又加上天一凉,生意分外地好做,乡下人秋后卖了红小豆、卖了玉米,人人手里都有了闲钱,嫁女儿娶媳妇的人家都要来买棉花。大家都顾着忙生意了,彼此相安无事。临近年关时,生意一日比一日的好。这一天,米香小女人的娘家大侄子弄了一大包炮仗,又一时半会找不下摊点,就被米香小女人拉扯到自己跟前了。起先,方开文和另外两个男人都不想让米香小女人的大侄挨着他们卖,尽管互相之间不抢生意,可那炮仗和棉花同样都是见不得火的东西,要是万一……
米香小女人见大侄可怜,又是头一回见世面,一心想要大侄挨着她做。再说既然能南下几百里来到这儿谋生,可见也是有那么三下两下的,方开文他们谁都不想因为生气而影响了自己的生意。年关生意是那么好,棉花卖得飞快,大把大把地往兜里揣钱,一天下来怎么说也能嫌一、二百块钱,一个国家干部一月才能挣八九十块钱,想想看,就跟抢人似的。方开文晚上回到家里都懒得数钱了。
事故终天发生了。是一个集日,晌午人正一涌一涌地多的时候,有一个卖碗碟的人带着一个五岁多一点刚会擦火柴的小男孩,出于恶作剧,小孩划着火柴点了一支小炮,悄悄地塞进炮仗堆跑了。瞬间,那炮仗摊子嘣嘣、叭叭大炮小炮烟花一齐炸响、一齐释放,哪来得及扑救?炸起来的纸屑飞起来的齐花直往米香小女人的棉花堆里钻,还没等人们怎么反应过来,炮仗、棉花就一扫而光了。那两个男人离得远一些,挪开了自己的棉花没受太大的损失,方开文紧挪慢挪,还是把那些优质棉花、优质网套都烧掉了,只剩下十来床黑心棉网套。
米香小女人姑侄俩烧得只剩下灰不溜秋的人了,第一次做生意的娘家侄蹲在地上哭鼻子,姑姑也一时不知所措。方开文看看自己最值钱的东西都不翼而飞了,再看看米香小女人,一下子来气了,扑上去把那小女人压在身子底下就是一顿猛打。她先是骑住用手扇耳刮子,再用脚踢,踢肋骨、踢腰、踢屁股,等到娘家大侄反应过来,拉扯他姑姑时,米香小女人早被打得躺到地上爬不起来了。
米香小女人住了一个星期院,身上还是觉得不好。原来,人家结婚好几年了,老是怀不上孩子,这回总算有了身孕,眼看就快四个月了。本来婆婆和男人都不让她再去做生意了,可她觉得腊月这一向生意分外好,误了就等于是直接把钱扔了。再说,她认为现在身子还轻,支应得来,等过了年,就在家里好好调养着,等着生孩子。可是这一挨打,就觉得气短,觉得浑身哪儿都疼。她想,幸好方开文打自己时没踢肚子,那狗东西也是觉得女人的肚子无比贵气么?现在孩子还在。
就在米香小女人住院期间,她的婆家娘家都来人了。尤其她的婆家上头也是有人的,人家不受,告下了方开文。方开文的姨夫从中周旋,看能不能私了,人家说不私了,必须法办。米香人想出出这口恶气。
正当腊月二十七这天,方开文被判拘留十五天。
监所的门打开,狱警把方开文一把推进去,哐啷一声锁响,她被关进黑屋子里,还没等她的眼睛适应过来,就感到有两个人扑到她身边,抡起拳头就打。方开文身上挨了两拳头正纳闷自己刚进来脚还没站稳哩,怎么能得罪了人?这时又听见其中的一个指挥另一个:脱,把她的裤子脱下来,看看那儿长毛不!方开文心中呼地升腾起一股怒气来,她觉得男人对女人实施性侵犯有时还能说得过去,同样是女人,同样是受难人,也要这样骚情人,一时间怒气化作力量,飞起一脚照着那个指挥的女人口鼻踢过去,顿时鼻血哗哗直流。那女人流着鼻血还想招架,她就一把抓住那女人的领口,一字一顿地说:你大大要是脱下老娘的裤子弄出个你来,还算是马下骡子——世上常有的事,你也要动老娘的裤子,你算哪个庙上的一根葱?说着又左右开弓煽了那女人两巴掌。方开文想再收拾另一个,那个见势就嗵一下跪下说:老大,别打了。我们让你当老大!我们让你当老大!从现在起你就是我们的老大。
方开文停下手来,这才慢慢看清楚两个女人:一个大概四十岁多一点,一个才不过是十七、八岁的样子。
方开文就在监所里当了半个月的老大。
“老大”对方开文来说,不是一个虚名,是有待遇有实惠的。比如说晚上睡觉老大不睡其他人就不能先睡,而老大睡了其他人就必须要睡。那尿桶也是要放到距离老大最远的地方;早晚的洗脸洗脚水、刷牙水都是由别人给倒好,老大才用的,用完之后,自有别人再给倒掉;再比如说,家里人或朋友来探监,带来吃的东西也必须要有老大的一份,放风时也一定是由老大先走出房门……
方开文自小到这么大那享受过这等待遇?
在里面关着尽管憋闷,尽管每顿饭都吃不饱(按现今的政策,理论和原则上是可以吃饱的,可监所的大师傅为了给自己创收,喂了两头猪,饭匀给猪吃了一些),可三个女人相处在一起了,就要拉话,一拉话时间就过得快一些了。往往一个话题说着说着就到了晌午,吃过饭,再接着拉一个话题,拉着拉着又到了晚上。从拉话中方开文得知那两个女人身世都不好,也都是些恓惶人哩。那两个人还告诉她:在她们刚进来的时候,里面是关着几个人的,她们都是过了“号规”的,所以,在方开文进来时,她们也理所当然地给方开文过了“号规”。进来后,方开文才知道,原来里面跟外面是差不多的,都要有一个权威、一个“掌柜的”管着;不一样的是,这年月在外面只要有钱,不管那钱是怎么来的,都能让人活得看起来体面。而在这里却凭得是力气、是内心的残火。你只要敢打别人又能打得过,你就能当老大。她想,今天的老大自然有自己这几年来“打场子”的历练。
好像也没怎么熬煎,半个月就到了。方开文“全毛全翅”地回家了。她走了这些天,玫玫是由老姨带着的。玫玫见她回来了,一下子扑到她怀里哭起来。她一边用手抚摸着玫玫的头安慰玫玫,一边对她说:憨女子,妈妈这不是回来了吗,你还哭啥?
玫玫说:老姨跟老姨夫拉悄悄话,让我听到了。他们说你被关到黑房子里吃不饱恓惶着哩。
方开文心想:哼,恓惶?我这一回算是尝到了当皇上娘娘的味道哩!嘴上却对玫玫说:妈妈在那儿遇见了一个同学,那个同学照顾妈,没把妈关进黑房子里,只让妈给他们打扫一下卫生,还给妈吃他们干部灶上的饭。玫玫这才破涕为笑,用绵绵的小手搂住妈妈的脖子,生怕她再去了哪儿。方开文这时似乎也觉得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就搂住玫玫像犯了错误的学生跟老师保证一般,妈以后尽量不随便跟别人打架了,妈要挣钱跟你一起好好地过光景。
一开春,方开文把烧剩下的那几床黑心棉的网套以更便宜的价钱处理给几个外地来的打工人之后,就不再想天暖时卖冷饮冰淇淋天凉时卖棉花了,这样来回里捣腾,每捣腾一回,都意味着要打一回场子,打场子总归不是好事,不是自己吃亏就是别人吃亏,而所谓的占了光也总是在一段时期内不得安生。她在市场上转悠了好多次,也算是做了一个初步的考察吧。大买卖做不来,需要大本钱大眼光,这,她没有。再说也怕担风险,丈夫如今不知是发达了还是沦落了,是死了还是活着,是又娶了别的女人不要她了还是一个人混成了寻吃的没脸面回来见她了,不管怎么样如今都是她一个人顶门过日子。她是挣起赔不起呵,还是做小本生意的好。
五
交通发达了,外地的水果顺着国道就运到县城里来了,县城的人又爱图个新鲜稀罕,水果的生意一直不错;现在科技也发展了,几乎一年四季都有水果卖,一点都不受时令限制,而且在这个县城里只要占下一个好摊位,就多少年都不用挪窝了。方开文决定卖水果。
农贸市场的进出口处长20多米,两侧面对面排了两溜卖水果的,全城也数这儿生意好做。干部职工们上下班买了菜也总要再捎带着买一些水果回去;幼儿园的娃娃们放学,哪一个娃娃都是由一个大人往回接的,娃娃们看见了要吃不用赖着不走大人就给买了,城里人总是有钱的,现在的娃娃又金贵;逢集日,乡里人进城,卖了东西再买一些东西回去,也往往要给在家里等着的娃娃买一些水果回去;还有到医院去看望病人的……这是县城卖水果的黄金地段。
方开文跟工商提出申请了,工商不同意,他们说:那儿只能有那么多的摊位,你没看再多一个都放不下了吗?方开文跟工商缠,你们行行好,再通融通融吧。工商说除非那儿有谁不卖了,空下一个位位了,你就可以占这个位位。
也是天遂人愿。一个在市场进出口处卖水果的后生晚上收了摊骑着自行车去看对象,在国道的转弯处不小心遇上了往炼油厂送油的大罐车,大罐车忽地一下挂上靠路边的自行车,后生当场死亡。
于是,方开文就填充了空下的摊位。
刚坐到水果摊子上时,由于是工商亲自安排的,其他卖水果的人倒没像以前老孙那样明着耍流氓,只是一个个都对她铁青着脸,用形象语言告诉她:我们十分不欢迎你,见不得你。方开文发现这些卖水果的都是四五个人一伙,不是你把他叫姑夫,就是他把你叫姨姨。而且有几个人听口音是人们所说号称最难缠的那个地界的人,靠前头那个男人看起来老实巴交,却是工商局副局长的小舅子。面对这样的阵势,方开文一开始不敢有明显的“抢生意”的意识,还主动地去巴结一下那些男男女女们。中午她去市场里的摊子上订饭,就主动问问同行们,要不要给他们也捎着,有时从家里带来了饭,也要给同行们碗里夹一筷子,让他们尝尝。自然不敢明着撒泼打场子了,可她还是在暗中跟每一个人较着劲。
这一天是个集日,乡下的一个男人推着自行车,车前把上挂了一嘟噜高粱刷子从这儿路过,方开文正背对着往摊子上摆水果,那人的自行车挂上了她的后衣襟,“嘶”地一声,扯开一道口子。
那人看见挂了,憨憨地笑了一下:哎呀,我没操心。刚想走,方开文一把拽住自行车:没操心就完了?你得赔我衣服。我这衣服是一百二十块钱买的,穿了一向是有点旧了,你就赔我五十块钱吧。
那人说:我刚来,准备卖刷子哩,身上就没带钱。
谁也不会大呐二喊地说他有钱。
我确实没钱。不信,你搜!那人一副可怜相。
方开文说让我个婆姨人家摸你的身子?你也不尿泡尿照一照,看自己长得俊不?少废话!有钱就给我放下,没钱就先把自行车扣下,打闹下钱了再来推。
方开文心里是清楚的,一件旧衣服挂了个口子其实没什么,她现在是想撴住个把把给其他卖水果的人看哩。
中午,卖刷子的人没打闹下钱央了一个在城里上班的两姨妹妹来要自行车。那两姨妹妹给方开文祷告了许许多多的好话,方开文才说看在你是城里上班人,说不定以后有什么事要用到你的份上,给十五块钱,把车子推走。见那两姨妹妹还有难色,方开文就说十五块钱还多么?!我要去裁缝店补衣裳,要误生意,补了的衣裳又难看……
人走了,方开文右手举着刚到手的十五块钱,在左手上啪啪地拍着:哼!谁怕谁哩,别以为老娘是好惹的,别想自己沾了光让老娘受了害!
说罢,用眼睛的余光扫卖水果的同行们。
方开文总是在卖水果时不动声色、用心用意地打着场子。这样也就相安无事地卖了十五六年水果。
不知不觉,玫玫已经谈恋爱结婚了。方开文望着长大了的玫玫,觉得自己也老了。可是无论方开文还是玫玫,都不知道这之后还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大事。
六
玫玫出嫁那天,方开文给玫玫传授的不是夫妻之道,也不是生活中的一张一弛,而是坚持按照“打场子”原则教诲的。
结婚以后,祝强对玫玫不是那么言听计从了,也没有过去那么殷勤了,玫玫为这些当然要跟他计较了。俩人相跟着上街,玫玫说,祝强我要吃冰糖葫芦,吃那种一个桔瓣一块猕猴桃一颗山楂的,你给我过去买去。看着马路对面的冰糖葫芦摊,祝强说你自己买去,想吃什么的挑什么的。
玫玫受到冷落气呼呼地一个人过去挑,她买了三串举着来到祝强跟前,祝强问你一个人能吃得了三串?!
吃不了不会扔么?反正又没人管我!
玫玫说着歪头啃一串,把另外两串扔到当街上用脚踩。祝强忍住心中的怒火没在街上发作,回到家里就有了一场小别扭。玫玫觉得自己一点错都没有,反正是这个谈恋爱时爱自己爱得很厉害的男孩变了。唉,男人都不是好东西。想着想着委屈地哭了,哭着哭着就给妈妈打电话。
哭着打电话的玫玫现在是一只傻傻的小鸡。这只小鸡在方开文的物质满足和匪气呵护中长大了,其内心依然瑟缩在母鸡的翅膀底下。
方开文刚刚收了水果摊,听到玫玫的哭腔就过来了。这时祝强已下好了面条,喊声:妈,您来了,正好一起吃饭吧。
方开文说:吃个屁!你还能吃得下去?
祝强赔着笑脸,妈,我没觉得有什么大事呀,怎么就吃不下去了?
方开文听到玫玫的哭腔本来就是揣着气来的,现在看到祝强的不在意火气腾地一下就上来了,她刚想一把抓住祝强的领口扇他耳刮子(很多次打场子时面对要跟她挑衅的人她都是这么做的。)可一想,祝强不是别人,就硬压了压火气,用手指着祝强的鼻子:姓祝的,你小子什么东西,这刚结婚才几天,你就欺侮玫玫了,你当玫玫没爸就没人管成了你的出气筒了?
祝强说:妈,您别生那么大的气,我没欺侮她。
那你怎么不哭?你羞先人哩,还当老师哩!
方开文替玫玫出够了气,走了。
祝强气呼呼地没理玫玫,后半夜终于把玫玫揽进自己的被窝。小两口打架了还不记仇呢,何况并没发生什么事。祝强这样想着。
玫玫过生日那天,祝强下午最后一节特意跟别的老师调了课,带玫玫去吃肯德基。玫玫最喜欢吃肯德基了,看着玫玫吃炸鸡腿的可人样,祝强就轻轻地在玫玫的额头上吻了一下。
吃着吃着玫玫想起了一件事,要跟祝强商量。
玫玫说自己单位里的年轻人都住着楼房,人家一开口就说卧室呀、卫生间呀,唯独咱们还住在你们家的烂窑洞里,人家说话,咱跟人家连茬都搭不上。
祝强说:玫玫,你可不能说咱家的窑洞烂啊,结婚时,我妈专门花了三万多给咱们收拾了窑洞,这当初也是按照你的意愿做的。
玫玫说我这不也是形容吗?我是想咱们也租一套宽敞一些的,时新一些的楼房出去住。
祝强没料到玫玫有了这样的想法,他为了不在生日时惹玫玫生气,就说行,容我再考虑考虑,跟妈商量一下。
祝强妈一听说玫玫要出去住,心里“咯噔”一下,为了给祝强结婚,她总共花费了近十万元,其中有两三万还是拉的饥荒。光是祝强住的那两孔套窑,里里外外装修她就花费了三万八。如今,他们却要出去住?一开始,她坚决反对,告诉祝强这不可能,你们出去租房不要花费很多钱么,再说租住房屋又不能按自己的意愿收拾……
祝强走后,妈又想,现在这些孩子是娇惯大了的,一家就那么一个两个的,不依了他们怕是也不行的。趁祝强跟玫玫还没睡下,妈就说:玫玫,妈不是不同意你们出去住,只是你现在怀着孕,生孩子时还是住在家里好。一来家中的窑里有热炕,最适合女人坐月子;二来我伺候你月子也方便,咱们门挨门的,不用走多远;再说等你生了孩子我们都在一起好拉扯。等孩子大一大,你们再……
婆婆刚说到这里,玫玫就火了。她这个外貌漂亮的小女子一天光知道玩了,什么心思都没操过,她哪知道过日子不易、坐月子热炕好、养孩子操劳啊?再加上方开文整日地在水果摊子上,给了她足够的钱让她去花销,玫玫是从性惯了的。她面对着婆婆的一片苦心却大睁着两眼吼起来:什么?等孩子大了,那还不到猴年马月了?那我也老了,还能上得去楼吗?不行,非出去住不可!
祝强说:玫玫,你怎么能跟妈这样说话?
玫玫“哇”地一声哭了。边哭边诉:我给你们怀着孩子哩,你们还这样对我!没卸磨你们就想杀驴了,我怀个孩子容易吗?我受了多少罪……哭诉着拨通了方开文的电话,妈——你来接我,我在他们家一会儿都呆不下去了。
方开文风风火火地来了,是带着一股子匪气来的。她踹开门,上来就扇了祝强两巴掌。你狗日的一次一次地欺负玫玫,你觉得我们娘们家好惹吗?
祝强妈为了不把事闹大,在她那边的窑里坐着硬是没有出门,可她心里说不上来地难受,眼泪像两条线在脸上扯着。这两条线很结实,似乎不是水做的,很长时间了都没断。
方开文听了玫玫的述说,不就是出去住吗?家里呆不下去了,还不让出去住?不怕,妈明天给你打问去,咱就出去住楼房。
方开文走后,家里很安静。安静得祝强和妈妈都听见了自己的呼吸声。
祝强又跟玫玫和好了。他是爱玫玫的。况且妈妈离休在家没事可做,就等着抱孙子哩。他也想维持这个家的安宁。他责备玫玫,你就不能跟妈好好地说话么,妈也是跟咱商量,也是为咱好。事后玫玫也承认自己是鲁莽的。
从这之后每到下雨天祝强都到玫玫单位去给玫玫送伞并把她接回来。要是玫玫不喜欢吃妈妈做的饭,祝强就自己下厨尝试着为玫玫做吃的,要不,干脆把玫玫领出去吃。
又是一个下雨天,祝强这天下午有教研组活动,他给玫玫打电话,让玫玫自己打车回来。
祝强和他的教研组正准备活动时,校长来了。校长来通知他们,上面过两天要来检查一项工作,有新的东西要准备。为了更充分地做好准备迎接检查,教研活动就先停止了。
祝强回到家正忙着在电脑上查资料,妈妈到坡下的邻居那儿串门没带伞,刚才看见祝强回去了的,就在坡下喊,让祝强给她把伞送下来。祝强离开电脑,举着伞到坡下挽了妈妈的胳膊把她接上来,这时玫玫打车也刚来到他们身后。
玫玫一下车就来气了。指着祝强骂:吹牛!明明是不要老婆赶回来侍候你妈的,还说有教研组活动,你妈好,你就把她当老婆一起过吧。
玫玫总是这样出其不意地给祝强耍流氓,气得祝强一口气出不上来。他这一次是真的动手打了玫玫。
方开文自从上次离开玫玫家眼皮子就有些跳。人常说“眼皮跳,祸事到”,可她不信这些说法,这些年在社会上炼摊炼的她只相信匪气和钱这两样东西。一样能让她立足,一样能让她生存。她觉得眼皮跳是让祝强那小狗日的给气的。这些天她一边卖水果,一边给玫玫打问楼房。她也想让玫玫搬出去住,她觉得玫玫乖,在人家家里住着就要受气的,又不像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时玫玫正好又打来电话了。她想,这才过了多长时间,这些狗日的又欺负玫玫了。她急急火火地去往玫玫家。这时眼皮又“嘣嘣”地跳了几下,这种感觉就像是导火索,倐地一下点燃了架在她心上的干柴。
听玫玫愤愤地说了原因,方开文这次想给他们上硬的,她觉得这些人是捱砖不捱瓦的货。
她先到祝强妈窑里:亲家,你活得可滋润哩,你会享受嘛!年纪轻轻地就让儿子侍候着。我娃给你们怀着孙子哩,倒在你们家挨打受气,回到旧社会了?祝强妈说:亲家,强强也只是给我送了一把伞……
你就不捡那没理的说?祝强他打了我娃你瞎眼了?你不让我娃出去住,是想让我娃两口子在跟前伺候你,听你调拨哩!你还没到那份儿上。呸!你个瞎了眼窝的货!
祝强妈先前一直在单位上,自己生平没打过场子,也没见过人打场子。因此几乎没跟什么人吵过架,这回却被玫玫妈唾在脸上骂,气得像一只兔子被丢进狼窝里,又被狼以极下作的手段戏弄着。既不屑于争辩,又绝不是对手。
骂完祝强妈,她就过来用手拽了祝强,要祝强当着她的面给玫玫下跪并发誓:从今往后再也不动玫玫一指头。
祝强不。
方开文说你小子要是下跪发了誓,今天这事就当没发生,要是不,这事就没完!
祝强还是不。
她说你乖乖跪下发誓,要不你可不要后悔,老娘我是谁?我是世面上混过来的人,我喝的糖水比你娃娃喝的白开水都多,你要是还强硬,吃亏的就是你,你可想清楚了!
祝强说不用想,我不!
方开文这次领走了玫玫。
一个星期后,方开文给玫玫租下了一套两室两厅一百平米的房子。房子是新房子,主人装修过之后没住多长时间就去西安了,据说要三五年之后才能回来。距离玫玫上班的地方也不远,玫玫看了很满意,高兴地抱住方开文的肩膀撒娇。妈,这世界上数你对我好。
方开文说:憨女子,那你以为哩?!
只是房租贵了一些,每月得三百五十元,再加上水电费,怎么说也得四五百,玫玫对这些花费有点发愁。方开文就指着她的鼻尖嗔怪:死女子,看你憨的,这钱你出?还轮不到你哩!我得让祝强妈那个老东西给你出。咋?她娶得起儿媳妇这么快就养不起了?!
方开文很快就叫了一辆货运车领着玫玫去搬家,玫玫说,妈,这怕不好吧,怎么也得再跟我婆婆和祝强打个招呼吧。
招呼个屁!
不是有妈在,你娃娃早就被他们家的人欺负死了,我看他们谁敢拦着挡着,我就打折他们的狗腿!
搬家这天,家里只有祝强的妈在,可她始终都没出来看一下,她知道,出来了就要跟方开文发生冲突,她想,这样也好,就让他们年轻人先搬出去住一段时间再说。
祝强晚上从学校回到家里,一开门才傻眼了:窑门空洞洞的,只虚掩着,里面的电脑、电视、冰箱……里面所有的东西——也就是妈妈为他们结婚新置办的东西都搬走了,只剩下几片碎纸屑,只留下一堆乱七八糟的脚印。祝强回过身子就要去找他们算账,刚想往门外扑,妈堵到了门口。妈说:儿子,你跟玫玫这是过日子,过日子就讲究个平平和和,互敬互谅。她们搬东西时我知道,可我没挡。搬走了也好,过两天,你打问一下地方,也去住,不就一切都解决了嘛,生什么气哩?你们年龄都还小,刚开始过光景,有了矛盾谁也不要记恨谁,慢慢地就顺溜了。
祝强终于在一个晚上八点钟左右打听到了“自己的家”,他敲门进去,方开文跟玫玫在一起说着话。玫玫看到祝强来了,眼睛里顿时露出几分欣喜。祝强看到玫玫的表情,心想,还是妈说得对,闹矛盾有什么好哩?这不,已经过去了。
没想到,方开文又开口了。祝强,你小子来了?来了就好,赶紧给玫玫跪下赔情道歉,发誓以后再不动我的玫玫一指头。
玫玫说:妈——你看你!
方开文说你还替他说话,要不是有我护着,你早让这小子打死了。
祝强心里刚刚驱开了乌云,又仿佛呼地一下被更沉更重的石头压住了。心里扎扎地疼着。他看着方开文说:我不!
他转身就要走时,方开文从后衣领上一把拽住了他。她说:你小子听着,你要是不跪,你看看玫玫肚子里你的娃娃,我就要给你处置掉!
祝强没转身,可是他站住了,他没想到方开文会说出这样的狠话、损话。
他这时才想起了当初跟玫玫谈恋爱时许多跟妈一起的长辈们都告诉他,玫玫的妈不好惹,要当心。那时他听着听着就烦了,他不知道这些大人们咋这样,他跟玫玫好,是要跟玫玫过日子,跟她妈有什么关系呢?当初,妈妈也反对,可是自己觉得玫玫长得漂亮,又活泼可爱,他是一心要娶玫玫的。要是让他跪下去向一个自己喜爱的女子求婚,那是完全可以的。如今却要他忍受屈辱,是玫玫有错在先的,但自己那天情急之下动手打了玫玫也是不应该的,道歉可以。对于自己的过错他当然可以在以后慢慢化解。没想到玫玫妈居然这样不依不饶地逼迫自己。唉,怎么结婚过日子如此之难呢?
祝强站了足有一刻钟,他拉开门,默默地走了。
回到家,祝强跟妈说了,他征求妈的意见:要不,我就妥协?!
妈说:强强,知道过光景的难了吧?当时因为我,你们两人都不冷静。可责任不在你一个人身上,玫玫这娃娃缺乏最起码的教养,这是我先前就看出来的。你要是一味地连他不对的地方都纵容,那以后还活个什么人哩。你岳母威胁你,那多半是吓唬你哩,你不想想看,她要是稍微有一点人味、人性的话,玫玫肚子里的娃娃不光是你的娃娃,是我的孙子,也是她的外孙哩,她当外婆的能不心疼么?
稍稍过了一段时间后,方开文打电话给祝强的父母,给祝强的叔叔,给祝强的舅舅。要他们在下午三点钟到一个指定的地点来商量事。接到电话后,祝强的“社会关系”们都有些发愣,到那儿去商量什么事呢?只有祝强的父母清楚方开文的意图,可他们怎么也想不清楚方开文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方开文跟这些人约会的地点是医院妇产科门外。这些人一个个都准时来到妇产科门外时,方开文领着玫玫已经坐在那儿的塑料椅子上等候了。玫玫这时的身孕少说也得有七个月了,即使坐在那里也是显山露水的。方开文知道祝强的叔叔是县委组织部的副部长,舅舅是县信访局的局长,祝强的爸是一所中学的事高级教师,不管他们是什么,正在忙着什么事,就都在自己的一声召唤下到这儿来了,心里还是有几分得意的。
带着这种得意的表情,她更是对自己的必胜充满了自信。她当着这些人的面把她先前对祝强的要求重复了一遍,并且再一次郑重申明:如果祝强不给玫玫跪下发誓,她就要让玫玫除掉肚里的孩子。
“社会关系们”一听是这事,一个个脸上的表情都严肃起来。他们一再劝说方开文年轻人刚开始过日子还都不懂事,祝强给玫玫赔情道歉是可以的,可也没必要搞得那么死板。大家彼此都在一个屋檐下,还是不要伤了和气的好。
方开文说:你们说得倒轻巧,祝强不照我说的做,哪一天要是把我的玫玫打死了,我一个孤老婆子依靠谁来过光景呵?
祝强的爸妈、叔叔和舅舅一个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尤其是叔叔和舅舅他们在领导岗位上混了这些年,还真没遇到过这么棘手的问题哩。他们只能再三好言相劝方开文,要她不要意气用事,多为今后的方方面面考虑。
方开文看着他们一个个地走了,气就不打一处来:哼,摆什么臭官架子!别看老娘是个卖水果炼地摊的,今天就要给你们一点颜色看看,谁怕谁哩!当即,她领着玫玫走进妇产科。
在方开文的强烈要求下,给玫玫引产的手术开始了。
玫玫没生产过,对引产这件事,颇有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她从小到大听妈妈的惯了,压根就没考虑合适不合适,她还以为引产跟挂瓶吊针一样简单哩。
方开文问护士扎了针以后娃娃什么时候能下来,护士说要等宫缩,宫缩来了才能视具体情况而定。她又问是不是马上就宫缩了,护士说最早也要等到明天下午或者晚上。她就在医院里陪了玫玫一晚上。
方开文本来第二天是不准备出摊卖水果了,忽然又想起头一天上午镇政府的王镇长说他到西安看人去,要十箱子梨枣,当时方开文没货,说好了第二天上午十点半来取的。她又看看玫玫什么反应都没有,能吃能喝,还咯咯地笑呢,就叫来姨姨陪着玫玫,自己再到水果摊上去,只卖一个上午,只是为了把王镇长要的那十箱子梨枣给王镇长。
方开文由于在医院里耽搁,出摊时已经快到十一点了,王镇长来了等了二十来分钟还不见方开文,就在昌旗的水果摊上看梨枣,眼看着就要点钱成交了,这时方开文风风火火地来了,她一见是王镇长,赶忙扯了他的袖子:哎呀,王镇长,真是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我为了给你准备好货,一大早就忙活了,饭都没顾上吃,这不还是来晚了,现在才赶过来。十箱子梨枣我已经给你准备的好好的了,你可不能不要呀。
王镇长刚要解释什么,方开文说哎呀你还站着干什么?你看看这些枣,水亮水亮的,价钱嘛也好说。
王镇长经不住方开文的拉扯,只好让司机搬了那十箱子梨枣放进车里走人。
昌旗本是一个老实人,他平时是不太跟这些婆姨女子们计较的。他常说,无非就是个生意嘛,少卖两个多卖两个有啥。可是今天不同往日,一来他昨晚上耐不住哥们三缺一的邀请,出去耍麻将,到天麻麻亮才回来,一夜输了八百多块钱。他卖水果一个月还不知能不能赚下这些钱哩,一大清早就被老婆骂了个狗血喷头,连饭都没吃上。自己也觉得心疼得不得了。二来他刚刚到手的生意就被方开文抢跑了,十箱梨枣,本来对于半斤八两地零售来说,就是一笔大生意了。这一下子,他就能赚几十块钱,可忽然之间一分都没有了。
昌旗越想越生气,他就拿起西瓜刀往自己的架子车车帮上啪啪地砍,一边砍一边嘴里还骂着:狗日的!狗日的!
方开文拍拍装进腰包里的钱,知道昌旗是给自己撒气,她只要不理睬,一会儿也就过去了。可这时候的她哪里还能受得下一点点气?她一扑跑到昌旗的水果摊子跟前,哟——,昌旗,你这是骂谁哩?你不是骂我吧。
方开文这么一挑衅,昌旗憋得连气都出不上来了。他生来胆小,一般不跟别人吵嚷。这会儿连面前方开文的脸都没看,只看见自己手腕上的那根青筋呯呯地跳。刹那间他觉得自己的那根青筋特别地讨厌,好像正在为方开文帮腔似的——帮着别人把自己软弱的一面充分地展示出来。他想不敢迁怒别人还不敢迁怒自己吗?昌旗就拿起西瓜刀来照自己手腕上的青筋割了一刀子——狗日的,我让你跳!
方开文一看昌旗用刀子割了他自己的手腕子,就张开两只胳膊把头向后仰着,哈哈哈哈大笑起来,哎呀,昌旗,我还以为你有本事要拿刀剁我的脑呀,你就那么一点球胆量,还想跟老娘我闹腾?
昌旗听着方开文那极度刺耳的话,看着自己手上正在往出流的血,那血刹那间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苗,红红地照耀着他。让他觉得无比高大威猛起来,心一横,他妈的不就是个流血么?谁的血不是血,举起西瓜刀就向方开文稍稍后仰还没来得及完全直立起来的胸腔上刺去。
从昌旗作决定到完成动作前后不过是几十秒的时间。
方开文还想说什么来着,一句话没说出,嘴里就含糊不清了,接着两只胳膊扎煞着扑腾了几下倒到地上不动了。
人们先开始并没在意。寻常方开文跟别人挑衅也是见惯了的,看到居然是她倒在地上,心想肯定是跟昌旗耍赖了。有一个人还开昌旗的玩笑:哎呀——昌旗,这下你可惹下乱子了,“老娘”不赖你三天的大匠工钱才怪了。
一个来买水果的人,一回头看到这个倒在地上不动的婆姨腔子上插着一把刀,吓得瞪大了眼睛,手里还举着猕猴桃惊奇地呐喊:这,这不是杀人了嘛!
大家这才纷纷到跟前去看,一时间,人们一下子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过来看热闹,一边看一边议论着什么,人又多又吵,还有从不远处正往这边赶的人,这时110也拉着警报开过来了,警察们大声喊着:让开,让开……
七
刚刚过了中午,玫玫的宫缩开始了。她正在老姨的陪同下半躺在病床上削苹果。苹果皮削得很薄很细呈长长的螺旋状,还没到削到苹果蒂就觉得肚子里被什么搅了一下,腰也开始乏困,沉沉地往下坠着。玫玫看一眼老姨,老姨人上年纪了,正坐在床沿上打盹。老姨——,老姨!玫玫喊第一声时老姨没反应,喊第二声老姨才睁开眼睛看她。玫玫说:老姨,我肚子疼了。怎么办?我妈咋还不来?
老姨说:好玫玫哩,女人生娃娃都是这样疼。你这才刚开始,什么时候疼够了,娃娃出来了,就不疼了。这疼,谁都不能顶替,连皇上娘娘都是这么个疼法。说过后,她又觉得自己说漏了嘴,心想玫玫这是生娃娃吗?这明明是日蹋自己跟她婆婆家哩。
玫玫听了老姨的话,有了一些心理准备。好在过了一会也就不疼了,她就吃起苹果来。吃着苹果想起应该给妈妈打个电话的,可是怎么打妈妈都不接电话。这时肚子又开始疼了。
玫玫起先在老姨的说教中还能忍受,快到下午四点时就怎么都忍受不了了。她一会儿觉得腹中像有几把尖锐的刀子在搅,一会儿又觉得有一种巨大的力量要把她的上身和下身从腰处分界。她被折磨得满头大汗筋疲力尽,不是哭喊着妈妈,就是喊着祝强。她时时张着两只手乱舞,想抓住什么,可是跟前只有一个值班护士和年迈的老姨。她觉得孤独极了,喊妈妈不应,喊祝强吧,她之所以提前忍受这样的苦痛,不正是跟祝强进行着你强我也强的争斗么?护士铁青着脸,老姨在用她枯瘦的手抹眼泪,嘴唇不停地嚅动着只有她自己能听见的三个音,造孽哩。
下午五点钟,祝强正在学校的阶梯教室里观摩北京特级教师的示范课,手机在裤兜里不停地震动,他摁下手机的红色关机键,表明自己现在正忙。可不到一分钟又震动了,再看看号码是自己高中时的一位女同学,好像是在医院里工作,平时不太联系,只是同学聚会时相互在手机上留下了号码。他以为同学找他闲聊,就急速调到短信息中的常用短语上,翻出“我有事,过会再聊。”发过去了;心还没静下来,手机再度震动起来,他生气地猫腰跑出教室,接通后,对方急急地:喂、喂——是祝强吗?你怎么搞的?你们不是年前才结的婚吗?你爱人在医院里做人流,痛苦极了,你为什么不在场?你不知道吗?
面对同学发来的短信,祝强这才知道方开文真的这么做了,他感到一阵晕眩,两腿也开始发软,他正想往医院冲,又觉得不对,自己这是去干什么?她们把亲生的骨肉往死弄,自己还要去帮忙、安慰吗?他不能去听课了,一口气跑回家,在窗外看到妈妈正坐在沙发上安然地织着毛衣。那毛衣是水红色开司米线的,小小巧巧的,快要完工了,是给他未出世的孩子织的。祝强看着织毛衣的妈妈,看着那小衣裳,眼泪瞬间哗哗地流,他一步跨进门里,妈,她们不要那孩子了,正在医院里做人流哩。
妈的手抖动了一下,放下那小毛衣,一动不动地坐着,许久才说了一句话:随她们去吧。
祝强说:妈,我想跟玫玫离婚。
妈说:这是你自己的事,往后还是你自己掂量吧。
祝强默默地来到自己居住的空荡荡的窑里,坐下来把自己跟玫玫相识到现在的经历细细地捋了一遍。当初好多人都反对他跟玫玫结婚,而他却铁了心。现在再细想想,玫玫好在什么地方呢?漂亮、幼小,显得楚楚动人。真的幼小么?其实玫玫的年龄跟自己是差不多的。他今年二十六岁,而玫玫也二十三岁了,他之所以一直觉得玫玫幼小是因为玫玫简单。她对一切都是从不考虑的,仿佛一个刚刚上幼儿园的小姑娘,蹦着跳着,开心了,咯咯地笑;不开心了,哇哇地哭闹。祝强当时是极欣赏玫玫的这种简单的。
窗外有熟悉的脚步声,祝强侧过身,看到窗玻璃外妈妈到厨房去做饭了。看着妈妈的身影进了厨房,他的视线又停留在门框上方不知几时结下的一张蛛网上。夕阳下,蛛网一圈一圈地,经线纬线是那么和谐而讲究地搭配着。祝强忽然觉得生活也是一张网哩,是一张用肉眼看不见摸不着的情感的经线和纬线织成的网。目前属于他的这张网就出现了问题,不是这根经线断了,就是那根纬线断了,或许那些经纬本来就不属于同一种材料,是不能在一起搭配的。
夜里十点钟了,祝强想去医院看看玫玫。
推开病房的门,日光灯下,玫玫仰面躺着,祝强却觉得是那么陌生,原来红活、圆实、饱满的一个人现在变得瘪瘪的,脸白得像一张纸,头发一绺一绺的,像在水里洗过又没揩干,把枕巾和枕头都洇湿了。老姨坐在玫玫身边打着盹。
看见祝强来了,老姨睁开眼睛显得十分不好意思,玫玫却裂开嘴冲祝强笑了一下。祝强坐在玫玫身边握住她的一只手,却什么话都没有,他和玫玫的老姨都处在尴尬与难堪之中。几分钟后,祝强用手理了理玫玫披散到脸上的头发对她说:玫玫,都是我不好,害你受了这么大的苦,今后我们——“解脱”了吧。祝强本来是想说“离婚”二字的,可是看着疲惫到极点的玫玫,终于将那“离婚”二字用“解脱”代替了。
说罢,祝强轻轻地带上门离开了。随着脚步声远去,玫玫闭上眼睛似乎要睡去,在似睡非睡之间,周围的空气好像一下子变成了水,托举着她,身子轻飘飘的,一忽儿飘到这儿,一忽儿飘到那儿……
祝强打车回家。
路上出租车司机随随便便地说:哎,咱这城里真是邪性了,北头前天出车祸死的那个男人还没埋,今天城南又杀人了。
祝强本来心情很坏,根本不想跟司机聊什么天,只是懒懒地应了一句:噢,是吗?
你不知道?司机原来以为祝强是知道的,这个县城本来就小,哪有一点事,全城立刻就传播开了,更何况是杀了人这样的大事。
得知祝强还不知道这件事,在很大的程度上引起了司机传播这件事的兴趣,他说:是个卖水果的女人被一个卖水果的男人杀了。人们都说杀的活该,那女人平常太霸道了。
祝强没怎么搭理出租车司机,心里却一紧一紧地想,该不是自己的岳母……该不是方开文吧。
八
这之后,方开文卖水果的那个摊位空了很长时间。人们说:那个摊位太邪性,谁占了那个摊位谁就没有好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