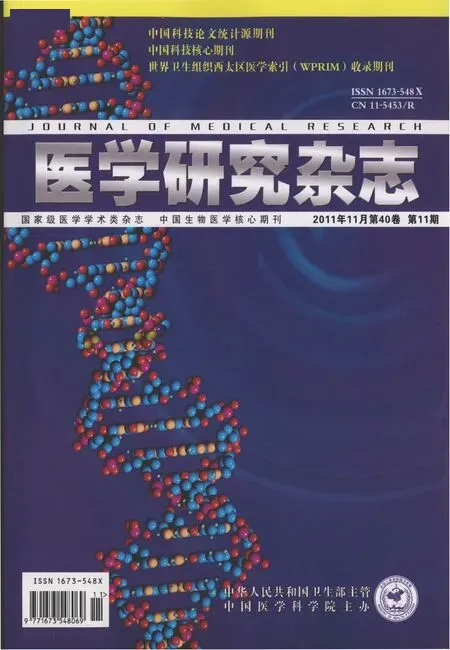内皮祖细胞研究进展
郑 睿 姚建民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发病率正逐年提高,其已经转变为目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三大主要疾病之一。目前的主要治疗方法有内科药物治疗、经皮冠脉支架置入术(PCI)、激光心肌再血管化、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尽管近期发现的新生鼠心肌细胞可以完全再生[1]的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认为的心肌细胞是一种终末分化细胞、缺乏再生能力的观点,但是对于成人来说,上述旧观点依然成立,一旦发生不可逆的大量缺血性坏死,势必导致相应区域的心肌细胞被纤维结缔组织所替代,从而导致心功能的降低。冠状动脉血供的重建是治疗心肌梗死最有效和最根本的方式,但是,面对患者中病变较重、远端血管完全闭塞、血管纤细的情况,上述治疗方式所能提供的血运重建效果明显不足。因此,为了缩小心肌梗死发生后的梗死面积,更加有效地重建缺血心肌的血供,近年来逐渐开展的细胞移植技术为我们展现出了一片治疗方式的新天地。因此,关于探索更进一步改善心肌梗死患者预后的治疗方式已经成为目前极为迫切的问题。
一、内皮祖细胞的基础研究现状
以往,血管生成(vasculargenesis)是指中胚层源性的前体细胞原位分化为成血管细胞(angioblast),继而分化为内皮细胞形成原始毛细血管网;而血管新生(angiogenesis)被定义为,机体或组织受胚胎发育过程或出生后血流增加的需要而从已存的血管以一种出芽的方式发生的毛细血管分支。在内皮祖细胞(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EPC)被发现以前,血管生成普遍被认为只存在于早起胚胎的发生过程中。但自从1997年Asahara[2]报道了一组异源性的骨髓源性CD34+细胞可以分化为内皮细胞(endothelial cell,EC)后,出生后血管生成的存在便被证实以及广泛的接受了。之前,细胞因子的应用已经被证实能够增强组织的新生血管(neoangiogenesis)的生成[3],但是,考虑到存在于循环血中的EPC数量非常稀少,而这一问题可能已经限制了细胞因子应用,因此,一系列基于EPC的血管生成功能的动物或临床实验已经展开,目前在再生医学领域已经初步证实了其潜在的治疗效果[4]。
在 Asahara的发现后不久,Shi[5]报道了一种与前者发现的EPC具有相似功能的细胞群,他们有着相似的抗原决定簇,但是两者的形态及增殖却有着明显的不同。这前后的两种细胞日后被分别称为早期EPC(early EPC)和晚期 EPC(late EPC)[6]。相继的报道,虽然冠以内皮集落形成细胞(endothelial colonyforming cell,CFU-EC)和内皮细胞集落形成单位(endothelial cell colony-forming unit,ECFC)的称呼,但实质上也更进一步的支持了有关于EPC的这一分类[7]。
由于造血干细胞(hematopoietic stem cell,HSC)和EPC同时表达某些细胞表面抗原(表1),许多研究人员尝试着去寻找HSC和EPC之间的可能联系。目前比较明确的是,依赖于不同的细胞培养条件,成血管细胞(hemangioblast)有向造血系或者内皮系分化的双向分化能力[8],因此,上述两种细胞有着共同的前体细胞——成血管细胞。但研究人员并不局限于此种结果,他们开展了更深一步的探索。但是后续研究结果众说纷纭,基于CFU-HILL分析,有人指出其为造血源性,或更有之归为单核细胞源性[7,9,10];也有人指出 EPC 并非源于 HSC[7,11,12]。当然,针对Rehman等的研究,他们得出了相当有说服力的关于EPC的单核细胞起源的抗原表形分析结果,但是我们认为其中关于细胞的连续4天的培养可能没有考虑到移除早期能够贴壁的成熟内皮细胞及单核细胞,才导致了其关于EPC起源的如此确定的结果,或者说对其来源的一种误解[13]。但是,CD11b+/VRGFR1+细胞确实参与到了肿瘤的新生血管中及其周围[14],因此,我们依然对此质疑。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上述明显不同的结果显然证实了EPC不同亚单位的存在,即我们可以理解为不同的分离方法造成的有相似功能的不同亚单位造成了上述截然不同的关于EPC起源的结果。更有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对于早期EPC应该有着更进一步的分类,认为早期EPC依然属异源细胞群,其中包括CD34+/CD45+(CD133+)造血干/祖细胞及 CD45+/CD14+单核细胞[7,12]。所以,为内皮祖细胞冠以单一的称呼EPC可能导致了不同研究的有争议的结果,其中血管生成所募集的各个组分的混合显然不利于研究的可重复性,往往导致了我们的错误结论。

表1 分离常用的特异性标志
Lyden[14]的研究结果显示,把载有VEGF的基质胶种植到1天突变小鼠体内(实验前接受了野生型小鼠骨髓移植处理),发现其恢复了其体内具有功能的血管的形成,可见β-半乳糖苷酶阳性的VEGFR2+内皮祖细胞及β-半乳糖苷酶阳性的VEGFR1+/CD11b+髓系细胞。这两类细胞的生成也从一个侧面支持了我们上面的模型。
尽管有着上述的不确定因素,但是根据Lin[11]的结论,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即EPC来源于骨髓。这样,结合上文的依据及对EPC的两个亚集的分类[6],我们做如下假设:早期EPC来源于造血系,主要起分泌细胞因子辅助晚期EPC的功能,而晚期EPC来源于生血管细胞(angioblast)系,主要起血管生成的作用(图1)。这一假设与 Yoder[15]提出的工作模型相比具有一致性,并且更符合我们目前所公认出生后的血管生成过程。同时,在其工作模型中亦涉及到了由不同功能细胞构成的EPC,他将其分为造血细胞及高(或低)增殖潜力的内皮集落形成细胞(high/low proliferation potential endothelial colony forming cells,HPP- or LPP-ECFC)。

图1 EPC的衍化途径
许多研究者指出,骨髓源性的内皮祖细胞对于成人新生脉管系统的相对贡献目前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似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采用的实验系统,具有很大的不定性,范围大概从较小的贡献到50%左右的贡献,甚至于起绝对主要的作用[14,16~19]。因此,尽管像Yoder所说,他们提出的模型更符合传统观点的血管新生,而不是新认识到的关于出生后的血管生长的血管生成,但是我们认为很可能是实验对象的基因背景、原发或移植肿瘤、新生血管过程中的不同时相等问题导致了EPC对于成人新生脉管系统的贡献比例不同[17,19]。因此,我们及Yoder提出的模型可能同时存在于体内,根据不同的内环境或条件分别起主要或次要的作用。
二、表面标志
由于缺少区别与其他细胞群的特异性的表面标志及功能性分析(例如成熟内皮细胞及造血细胞),有关EPC的纯化及特性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尽管EPC用于再生医学或肿瘤学治疗中的靶细胞的潜能一再被众多文献所证明,但是其中具有争议性的临床实验结果亦不断出现[20~24],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以下一些未明确的问题所造成的,即EPC的分离、鉴定、特性等等。为了解决这些质疑以往骨髓移植观点的争议性结果,首当其冲的就是如何准确地分离出大家所公认的内皮祖细胞。
目前,从外周血分离EPC共存在3种不同的方法。前两种基于培养细胞的差速贴壁原理,在3种方法中得到了最为广泛的应用。在具体步骤中,第一步的单个核细胞(mononuclear cell,MNC)的分离与以往相同,即取离心后的棕黄色细胞层。但是接下来的步骤对于前两种方法(称为方法A、方法B)来说便截然不同了。对于方法A,MNC种植于纤连蛋白包被的组织培养皿,培养48h后,收集非贴壁细胞重新种植于新的纤连蛋白包被的组织培养皿中,培养3天,在大约4~7天,早期EPC集落出现,呈现出中间为圆形,周围包被有纺锤形的细胞形态。
对于方法B,单个核细胞被种植于Ⅰ型胶原包被的或纤连蛋白包被的组织培养皿中,培养过程中,每天弃掉非贴壁细胞。对于外周血,在大约2~3周时(脐带血及骨髓样本时间相对较短),晚期EPC集落出现,呈现出铺路石样圆形细胞。
从对方法A、B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其显然是两种不同的细胞群,但是两种不同的细胞都具有吞噬乙酰低密度脂蛋白和结合植物凝集素(如Ulex europaeus agglutinin-1,UEA-1)的能力,并且这一特性被认为是EPC的特性之一。但是,我们要想到,纤连蛋白包被的组织培养皿已被用于分离单核细胞几十年之久,在A、B方法中,我们如何能排除其中生长的单核细胞对于EPC的污染呢?因此,单用差速贴壁法来分离培养EPC就显得仍欠成熟,有着复杂的不确定因素。但是,其较低的成本花费方面的优势依然显示了其用于临床的巨大潜力。
第3种方法基于荧光激活细胞分选技术的使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流式细胞分选仪(FACS)的使用。首先,某些特殊抗原被选择为EPC的标志,并且使用免疫荧光标记的单克隆抗体与上述抗原结合。根据其前向散射(forward scatter,FS)、侧向散射(side scatter,SS)及特异性标记的荧光,EPC被计数或分离出来。在研究者意识到EPC的亚集之前,仅仅2~3个抗原的结合通常被用来分离内皮祖细胞(表1),但是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EPC与造血干、祖细胞(HSC/HPC)的相似的抗原表形,要想将EPC与其分离开来单靠上述方法是不够的,因此,越来越多的争议接踵而至,并且表现出较以往更加的混乱和难以分析。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EPC的亚集被阐述的更加清晰,抗原的使用也越来越趋于标准化,例如CD34、CD45、CD14、CD133、VEGFR -2 用于 FACS 上的EPC分离纯化,而其他的抗原或特性则被用于分离细胞的鉴定。
其中,对于早期EPC,其特性有:①4~7天培养后产生;②不典型的融合的单层梭形细胞;③表达内皮细胞和造血细胞标志(比如,不仅仅表达 Flt-1、eNOS、vWF、CD31,而且表达 CD45、CD14、CD11b);④结合UEA-1凝集素且吞噬acLDL;⑤维持造血分化潜能和功能;⑥低增殖能力;⑦体内外不产生血管样管道;⑧体内外应用可改善新生血管的生成;⑨源于CD45+造血细胞系;对于晚期EPC,其特性有:①2~3周培养后产生;②典型的融合的铺路石样细胞;③表达 CD31、CD34、CD105、CD146、VE-Cadherin、eNOS、vWF、VEGFR-2,不表达造血细胞标志 CD133、CD14、CD11b或者CD45;④结合UEA-1凝集素且吞噬acLDL;⑤无明显的造血潜能;⑥高增殖能力;⑦体内外能产生血管样管道;⑧体内外应用可改善新生血管的生成;⑨源于骨髓(或angioblast)、可能也有血管壁[6]。
尽管至此基于抗原的分离方法的发展很鼓舞人心,但是有实验结果指出,CD34+/AC133+/KDR+细胞并未得到EPC,因为作者证明这仅仅得到了原始的造血祖细胞并且其无法在体内形成血管[12,25]。所以,寻找更加特异的表面标志依然存在着进一步探索必要性,当然,这也同时指出了我们基于单一分离方式的不足。
除了上述我们涉及到的问题以外,有很大必要性指出,某些细胞表面标志在体外培养或器官发育的过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随着成长而不断改变[6,21]。也就是说,没有唯一的表形存在,只有对于细胞的发育、分化阶段进行严格界定,才能保证我们结果的可重复性。因此,在这里,我们使用多重标准,步骤为:首先,细胞的差速贴壁培养法,之后使用FACS进行基于表形的分离和鉴定,同时辅以形态和功能特征来准确确定EPC。
三、单独移植EPC还是与其他辅助成分共同移植,其效果仍存争议
许多基于移植没有精细分离的骨髓细胞群的临床实验已经有所报道[4],但是目前对于注射这种含有大量不必要细胞群的成分是否可能在长期效果中表现出毒性仍然在研究之中。据我们所知,骨髓细胞含有EPC、造血细胞及其他多种不相关的多能干细胞,而这些细胞能够分化为多种细胞,存在于缺血组织的这些多向分化的细胞及其复杂的相互作用增加了患者日后潜在并发症的可能性,比如心肌细胞成形术后晚期发生的致死性心房纤颤(late-onset lifethreatening arrhythmias)已有报道[26]。另外,在此领域,许多相矛盾的结果依然存在,比如对于动脉粥样硬化损伤,Sata等发现移植的骨髓细胞减少了实验鼠的粥样斑块负荷,尽管其参与了斑块的构成[27];而Silvestre等却指出BMC移植后鼠粥样斑块明显增大,但其却极少参与斑块的形成[28]。因此,BMC移植的应用应该在长期的审慎的临床评估下进行。
随着科技的发展,蛋白质组学的概念已深入人心,关于EPC细胞培养上清液的质谱分析表明,EPC可分泌多种促血管生成的因子,并且可以发现EPC细胞中现已证明的众多重要标志,但是,作者对于EPC的定义并不完善,以及对于其分泌成分的作用方式也并没有阐明,所以对于外周血中EPC这一更具代表性的细胞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似乎我们可以通过蛋白质分泌谱的不同从而根本上区别目前困扰我们的早期EPC及晚期EPC的区分问题,并极有可能通过对比研究找到更具有区别意义的标志性表面标志。据报道,早期和晚期EPC的联合移植较单个成分的移植表现出了一种相互协同的作用,增强了其血管生成能力[29]。因此,这些研究表明,针对EPC治疗的有限的有效性,应用细胞或细胞因子的联合移植可能是增强EPC移植效果的一个很好补充,部分研究人员已经开始认识到了区别对待两种EPC的必要性。适时,我们应该放宽视野,将EPC的移植与其他有效的成分的移植结合起来,更进一步拓宽其实用价值。
另外,有文章指出,通过转基因诱导一种嵌合蛋白,即基因阱(VEGF trap),实验所募集到的骨髓源性的细胞(RBCC)仅起到一个旁分泌的效果,而没有表现出晚期EPC的功能[30]。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缺血或损伤是体内新生血管的主要启动因素,但本实验目的器官并没有受到缺血或损伤的影响,而利用了基因阱造成的EPC的募集。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推测这只造成了早期EPC的募集而对晚期EPC没有影响?据我们所知,他们均可被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EGF)所动员。更进一步说,在Grunewald等的报告中是否存在两种EPC亚集的动员的一种分离现象呢?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晚期EPC的募集似乎就与组织缺血或损伤的程度有关了。同时,这一现象用于我们对早期和晚期EPC的研究可能有重要作用。
总之,面对冠心病患者中病变较重、远端血管完全闭塞、血管纤细的情况,传统治疗方式所能提供的血运重建效果明显不足。因此,为了缩小心肌梗死发生后的梗死面积,更加有效的重建缺血心肌的血供,近年来逐渐开展的细胞移植技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因此,关于探索更进一步改善心肌梗死患者预后的治疗方式已经成为目前极为迫切的问题。
1 Porrello ER.Transient regenerative potential of the neonatal mouse heart[J].Science,2011,331(6020):1078 -1080
2 Asahara T.Isolation of putative progenitor endothelial cells for angiogenesis[J].Science,1997,275(5302):964-967
3 Carmeliet P.VEGF gene therapy:stimulating angiogenesis or angioma-genesis? [J].Nat Med,2000,6(10):1102 -1103
4 Rafii S,Lyden D.Therapeutic stem and progenitor cell transplantation for organ vascularization and regeneration[J].Nat Med,2003,9(6):702-712
5 Shi Q.Evidence for circulating bone marrow-derived endothelial cells[J].Blood,1998,92(2):362 -367
6 Hur J.Characterization of two types of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and their different contributions to neovasculogenesis[J].Arterioscler Thromb Vasc Biol,2004,24(2):288 -293
7 Yoder M C.Redefining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via clonal analysis and hematopoietic stem/progenitor cell principals[J].Blood,2007,109(5):1801-1809
8 Pelosi E.Identification of the hemangioblast in postnatal life[J].Blood,2002,100(9):3203 -3208
9 Bailey A S.Transplanted adult hematopoietic stems cells differentiate into functional endothelial cells[J].Blood,2004,103(1):13-19
10 Ciarrocchi A.Id1 restrains p21 expression to control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 formation[J].PLoS One,2007,2(12):e1338
11 Lin Y.Origins of circulating endothelial cells and endothelial outgrowth from blood[J].J Clin Invest,2000,105(1):71 -77
12 Timmermans F.Endothelial outgrowth cells are not derived from CD133+cells or CD45+hematopoietic precursors[J].Arterioscler Thromb Vasc Biol,2007,27(7):1572 -1579
13 Rehman J.Peripheral blood"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are derived from monocyte/macrophages and secrete angiogenic growth factors[J].Circulation,2003,107(8):1164 -1169
14 Lyden D.Impaired recruitment of bone-marrow-derived endothelial and hematopoietic precursor cells blocks tumor angiogenesis and growth[J].Nat Med,2001,7(11):1194 -1201
15 Yoder MC.Defining human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J].J Thromb Haemost,2009,7 Suppl 1:49 -52
16 Ziegelhoeffer T.Bone marrow-derived cells do not incorporate into the adult growing vasculature[J].Circ Res,2004.94(2):230 -238
17 Peters B A.Contribution of bone marrow-derived endothelial cells to human tumor vasculature[J].Nat Med,2005,11(3):261-262
18 Garcia-Barros M.Tumor response to radiotherapy regulated by endothelial cell apoptosis[J].Science,2003,300(5622):1155 -1159
19 Nolan DJ.Bone marrow -derived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are a major determinant of nascent tumor neovascularization[J].Genes Dev,2007,21(12):1546 -1558
20 Ratajczak MZ.Phenotypic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ization of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J].Curr Opin Hematol,2008,15(4):293-300
21 Matsuoka S,et al.CD34 expression on long-term repopulating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changes during developmental stages[J].Blood,2001,97(2):419 -425
22 Clauss M.The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Flt-1 mediates biological activities.Implications for a functional role of placenta growth factor in monocyte activation and chemotaxis[J].J Biol Chem,1996,271(30):17629-17634
23 Muller A M.et al.Expression of the endothelial markers PECAM -1,vWf,and CD34 in vivo and in vitro[J].Exp Mol Pathol,2002,72(3):221-229
24 Purhonen S.Bone marrow-derived circulating endothelial precursors do not contribute to vascular endothelium and are not needed for tumor growth[J].Proc Natl Acad Sci U S A,2008,105(18):6620 -6625
25 Case J,et al.Human CD34+AC133+VEGFR-2+cells are not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but distinct,primitive hematopoietic progenitors[J].Exp Hematol,2007,35(7):1109-1118
26 Makkar RR,Lill M,Chen PS.Stem cell therapy for myocardial repair:is it arrhythmogenic? [J].J Am Coll Cardiol,2003,42(12):2070-2072
27 Rauscher FM.Aging,progenitor cell exhaustion,and atherosclerosis[J].Circulation,2003,108(4):457 -463
28 Silvestre,J.S.,et al.Transplantation of bone marrow-derived mononuclear cells in ischemic apolipoprotein E-knockout mice accelerates atherosclerosis withoutaltering plaque composition.Circulation,2003.108(23):2839-42
29 Yoon,C.H.,et al.Synergistic neovascularization by mixed transplantation of early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and late outgrowth endothelial cells:the role of angiogenic cytokines and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Circulation,2005.112(11):1618 -27
30 Grunewald,M.,et al.VEGF-induced adult neovascularization:recruitment,retention,and role of accessory cells.Cell,2006.124(1):17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