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洛丽塔
胡亮
关于《洛丽塔》(Lolita),我们已经不便过多地谈论:道德家就站在我们身后,顺手就可以剥我们的皮。连小说家自己,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化名为小约翰·雷博士,所作的序言,也不得不指认这部小说“无疑会成为精神病学界的一本经典之作”,并进而提请读者注意小说中所有的角色,这些角色提醒我们“危险的倾向”和“具有强大影响的邪恶”。很显然,我们的小说家,哪怕隐身于一个化名,也仍然对那些潜在的道德家心存畏惧。这一点特别好玩:小说家只能通过小说人物实现自己的自由和幻想,当他终于完成全书,就会亲手扼死这种梦游,退后一步,举手投降,一下子变得索然无趣。然而,作为一个讲真话的读者,特别是讲真话的成年男性读者,我们得承认,这一堂思想品德课是无效的,我们甚至得承认,这危险,这邪恶,盛来了全部诗意。“洛丽塔是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同时也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得由上颚向下移动三次,到第三次再轻轻贴在牙齿上:洛—丽—塔。”这就是故事的开篇。我们看到,从开篇,来自巴黎的亨伯特·亨伯特先生——小说的主人公——轻易地取代了来自圣彼得堡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先生。如果继续下去,亨伯特和“性感少女”的日日夜夜将会不断流向我们,就像“一滴难得的蜂蜜倒确实落进了橡果的壳斗”——当然,偶尔,我们脑子里也会浮现出纳博科夫那伪装的苛颜。
但是,这篇小文所要关注的,恰好不是洛丽塔,不是“古老的欧洲如何诱奸年轻的美国”,或者说“年轻的美国如何诱奸古老的欧洲”,而是围绕洛丽塔展开的,附着在故事之上的魔术般的文体学奇迹。你以为是亨伯特在贫嘴吗?不,是纳博科夫在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叙述模式。两者都是诗人:洛丽塔就是那个漩涡。层出不穷的杜撰、隐喻、双关、谐音、戏拟、互文、拆字和造词修辞格,如此贴切地配合了情节的推进而又一点都不捎带文字游戏的匠气:单就这一点而言,《洛丽塔》即便比之于伟大的《石头记》——啊,贾雨村,甄士隐,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也有过之而无不及。纳博科夫的俏皮话满纸游弋,目不暇接,且让我信手拈来一段:“我不是任意糟践一个孩子的性精神变态的罪犯。强奸犯是查利·霍姆斯。我是治疗专家——两者的差别就在于微妙的间隔。”强奸犯,rapist;治疗专家,therapist:“这个强奸犯”就是“治疗专家”。当你通读全书,就会不止一次地遭遇对这个词和其他词的奇妙拆造,以及能够内在地暗示和深化故事情节的人名、地名、食物名和旅馆名。这一点,我也不准备再作解说。我所要细细探究的,乃是穿插在此书中的零碎的诗学——我只能暂时称之为“洛丽塔诗学”——辨析这些诗学到底是亨伯特的观点,还是纳博科夫的观点,换言之,辨析这些诗学是小说人物自我表达的结果,还是小说家自我表达的结果。
1
诗人亨伯特对古罗马和古波斯充满了向往:这是我的猜测,或者说发现。因为,这是两个享乐主义时代,或者是纵欲时代,也完全可能是性感少女时代。亨伯特在这两个时代找到了古代诗人典范。我们已经得知,亨伯特不止一次这样呼唤洛丽塔,“最特别的就是她,这个洛丽塔,我的洛丽塔,使得作者古老的欲望具有个人的特色,于是,在所有一切之上,只有——洛丽塔”,这是模仿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对其情人蕾丝比亚的呼唤,“生活吧,我的蕾丝比亚,爱吧”。我们有理由相信,除了卡图卢斯,亨伯特还对普洛佩提乌斯以及贺拉斯歌颂十六位妇女的诗歌,充满了一种吾道不孤的亲近感。至于古波斯诗人,那是经过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创造性地翻译出来的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他的《鲁拜集》。我们看到,这一次,亨伯特几乎喝醉了,杜松子酒和洛丽塔在他的脑子里跳来跳去,然后,小说里忽然就出现了一个让人特别惊诧的词组:“血红色的斑马啊。”血红色,incarnadine,正是菲茨杰拉德在译诗中使用的爱词。如果这个细节不够确定的话,那么,亨伯特还会在后文中表达得更加清楚,“睡眠像一朵玫瑰,正如波斯人所说的那样,”——这已经是第二次暗引《鲁拜集》了,对此我们不可不察。
不久,我们还会注意到亨伯特对但丁和彼得拉克的赞美,因为但丁在佛罗伦萨的一次私人宴会上爱上比阿特丽斯时,她只有九岁,穿着一袭深红色的连衣裙;而彼得拉克爱上劳丽恩时,她也只有十二岁,在风、花粉和尘土中奔向一片美丽的平原。亨伯特对他们的赞美,让我们心存疑惑,这是对诗人的赞美,还是对性感少女情结的赞美呢?或者说,正是性感少女情结造就了诗人?对亨伯特而言,这或许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关乎此,我们还有另外的证明材料。早在巴黎教书时,亨伯特就十分崇拜美国诗人爱伦·坡,他常常亲热地直称后者之名,“哈里·埃德加”。埃德加二十七岁时与他不足十四岁的表妹弗吉尼亚·克莱姆结婚,并在佛罗里达州的彼得斯堡度过蜜月。亨伯特毫不迟疑地将他推为“诗人中的诗人”,后来,我们的亨伯特甚至自称“埃德加·亨·亨伯特”。可是亨伯特的学生们却不这么想,他们将poet讹为popo,将神圣的埃德加称为“波波先生”。这让我们啼笑皆非,因为popo,在法国民间乃是“屁股”之意。
后来,我们的亨伯特为了生计,在编写一部法国文学手册的时候,终于犹豫了。七星诗社最杰出最大胆的几位诗人,皮埃尔·德·龙沙,特别是雷米·贝洛,关于女阴的描写,“覆满纤细的苔藓般绒毛的小丘,中央有一小条鲜红的窄缝”,让他犯了难:引用还是不引用呢?结果不得而知,我估计,亨伯特最终将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必定会用他那冥顽不化的性感少女美学挑战刻板的出版商美学和家庭妇女美学。在后文中,我们将会发现,亨伯特引用了曾经在龙沙《情诗集》中多次出现的,那献给一个银行家之女,也有可能是献给太后的伴娘或一个村姑的名句,“受到爱情的影响而神思昏昏”,来抒写他对洛丽塔的迷恋和沉醉。可以清晰地看出,这是正面的,而非“嘻哈”的引用。由此可见,亨伯特对龙沙们的偏爱也是不容怀疑的。
前面谈到爱伦·坡,现在学术界似乎已经有了公论:他与波德莱尔都是源头性的诗人,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法国,虽未携手,实则联袂,共同开创了现代主义诗歌之先河。波德莱尔似乎并没有性感少女情结,但是亨伯特肯定对这个“道德观上的第一位超现实主义者”十分着迷,他这样忆起洛丽塔,充满了嫉妒和担忧:“而在她的一旁总蹲着一个棕色头发的少年,洛丽塔赤褐色的美和她腹部水银似的娇嫩的褶皱肯定会惹得他在未来好多个月里经常出现的梦境中扭动身子。”这些描绘就直接受到波德莱尔《黎明》一诗的启示。让我们首先取读陈敬容先生的译文《朦胧的黎明》:“这正是那种时辰:邪恶的梦好像群蜂/把熟睡在枕上的黑发少年刺痛。”这个译文坚实,洗练,但是对颜色的判断和对动词的选择似乎不够精确;我手边还有胡小跃先生的译文《晨曦》,且让我也在此引来:“这时,蜂拥而至的令人恐怖的梦幻/害得棕发少年在枕上辗转不眠。”——这就对了。波德莱尔为亨伯特提供了趁手的人物和场景,但又增加了他那种情敌环伺的恐惧感,所以紧接着,他就发出了意味深长的叹息:“波德莱尔啊!”这叹息,包含了对波德莱尔的颂扬,以及情敌环伺的恐惧感对这种颂扬的干扰,甚至,还包含了一种慌不择路的诉说与求告。这且按下不表。我们知道,波德莱尔乃是法国象征主义的鼻祖,法国象征主义,乃至更大范围的象征主义,后来还出了很多天才人物。在这些人物中,亨伯特似乎对法国诗人魏尔仑颇有好感,他在故事的叙述中,曾两次暗引后者的诗歌:第一次是《一去不返》,第二次是《月光》。但是,亨伯特对另外两个象征主义诗人,法国的兰波以及比利时的梅特林克的态度则十分暧昧。他搞了一个恶作剧,在叙述中提及两部作品,《青舟》和《醉鸟》,事实上就是将兰波的《醉舟》和梅特林克的《青鸟》进行拆装组合的结果。这至少说明,后面还会得到印证,亨伯特试图并且已经调侃了他们。

2
总体来看,亨伯特对诗人还是很友善的;但是,他对学者、画家和小说家的态度则十分倨傲。只有一次,而且是唯独的一次,他称乔伊斯为“卓越的都柏林人”,并仿效了《尤利西斯》中斯蒂芬·德达勒斯的祈祷:“上帝、太阳、莎士比亚”。另有一次,他完成了一篇学术论文,《济慈致本杰明·贝利的信中的普鲁斯特式主题》,这篇论文虽然让六七位学者一致发笑,但是仍然牵涉到那经久不衰的伟大母题:时间和回忆。我们可以认为,亨伯特用这种方式,几乎向普鲁斯特含蓄地表达了有限的赞美。除此之外,让我们来领教他的毒舌。
亨伯特的妻子瓦莱丽亚已经有了外遇,那是一个保皇党人,身材矮小的白俄前上校,他陪同瓦莱丽亚前来取走衣物,并向亨伯特正式告别。“我想,”他在向亨伯特请教了瓦莱丽亚的日常饮食、经期、衣服、读过或该读的书之后说,“她大概会喜欢《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吧。”气炸了肺的亨伯特到底没有忘记,借助于这个恶棍的口,或许还有这个荡妇的胃口,表达了对罗曼·罗兰的厌恶。
另外一个故事是,洛丽塔的同学,与她合演莎士比亚的喜剧《驯悍记》,叫做莫纳的少女,她常常把巴尔扎克说成鲍尔扎克:“给我讲讲鲍尔扎克吧,伯父。他真的那么出色吗?”可是,亨伯特什么都没说,他甚至懒得纠正这个被讹掉的名字,——对他而言,莫纳显然比莫纳的问题更加吸引人。
关于陀思妥也夫斯基,亨伯特曾这样忆起某个瞬间,“我觉得脸上露出了一丝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狞笑”,这里的自嘲显然不怀好意,——他对陀氏的这个态度让我十分意外。
而约翰·高尔斯华绥,亨伯特则直接断言,这是“一个豪无生命力的平庸作家”。他之所以与洛丽塔一起前往南方某州的木兰花园,并不是因为高氏“称道它是世上最美丽的花园”,而是因为那里的“儿童”。
画家呢?当亨伯特初次走进黑兹家,就在门厅里看见了《阿尔的女人》。这是在美国十分普及的复制品,为中产阶级妇女群起跟风雅爱。但是亨伯特显然不喜欢凡·高。所以,这幅画挂在黑兹太太的门厅,而不是她女儿洛丽塔的房间。洛丽塔的房间,除了华而不实的杂志、撕下来的彩色广告、广告上画出来的箭头和“纯洁的床”之外,不会有艺术品。由此可以看出,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亨伯特宁愿做什么?对啦,不是黑兹的丈夫,而是洛丽塔的养父。
当然,最让亨伯特牙痒痒的,不是上述人物,而是弗洛伊德。我们知道,弗洛伊德生在捷克,长在奥地利,最后却死在英国,他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研究对象注重现实人物与文学人物的结合,研究方式注重心理学与病理学的结合。据我统计,亨伯特至少七次无情地讥笑了这个响当当的奥地利医生。第一次,他说得比较含蓄,但又充满揶揄:“那是一个背井离乡的名人,以有本事让病人相信他们目睹了自己的观念而著称于世。”第二次,精神分析已经成为亨伯特的恐吓伎俩,他对洛丽塔说:“如果我们俩的事给人家发觉了,他们就会用精神分析法治疗你。”洛丽塔不知精神分析为何物,却也不免怵然而惕。第三次,亨伯特一本正经,他如此布道:“我们必须记住,手枪是弗洛依德学说中原始父亲中枢神经系统的前肢的象征。”第四次,亨伯特这样对他的敌人奎尔蒂——后文还将重点谈及此人——进行了推论和假定:“他不用自来水笔,任何一个精神分析学家都会告诉你,这意味着病人是一个受到压抑的水中精灵。”按照精神分析学说,水中精灵常常因为异性小便而激起强烈的性欲。第五次,亨伯特自称:“一向是那个维也纳巫医的忠实的小追随者”。第六次,亨伯特不再反讽,不再戏拟,而是直陈观点:“二十世纪中期有关孩子和父母之间关系的那些观念,已经深受精神分析领域喧嚷的充满学究气的冗长废话和标准化符号的污染。第七次,亨伯特表达了对恋母情结学说的怀疑和否定:“当时我只是个婴儿,回想起来,不论精神治疗大夫在我后来‘抑郁消沉的时期’怎么蛮横地对我加以盘问,我还是找不到可以跟我少年时代的任何时刻联系起来的任何公认为真实的思慕。”亨伯特对弗洛伊德及其徒子徒孙的攻击,就这样贯穿始终。只要一提及精神分析学说,他的嘴角就会浮起轻蔑的微笑。
3
不管怎么样,亨伯特的渊博已经得到充分的确认。事实上,他的涉猎范围远远超出我们已经论及的范围。或者换一种表述,《洛丽塔》一书与数以百计的诗歌、小说和戏剧文本构成山穷水尽、柳暗花明的互文关系,筑起了一座富丽、幽深而缭乱的复义大迷宫。亨伯特回忆起,有一次,洛丽塔钻出汽车站在雨中,“用一只幼稚的手把紧贴着胯裆的连衣裙的裙褶扯扯松”,就暗引了罗伯特·布朗宁的韵文戏剧《皮帕经过》。当亨伯特谈及他和洛丽塔住过的数不清的汽车旅馆,他就会发问:“你记得吗,米兰达,另外那个‘极端时髦的’、有着免费赠送的早咖啡和流动供应的冰水、不接待十六岁以下儿童的强盗窝。”这里袭用了洛克《塔兰台拉舞》的起句和叠句。后来,洛丽塔消失了,亨伯特需要有人陪伴和照料,他很快就在灯蛾酒吧认识了里塔。后来他记得,那是“五月里一个堕落的夜晚”,天啦,这简直是对T·S·艾略特《老年》一诗中那个名句的直接引用:“在堕落的五月,山茱萸和栗树,这些开花的叛徒。”我们还发现,他曾以歌德《埃尔柯尼希》为典展开过叙述,并且模仿过布格尔戏剧民歌《勒诺尔》中勒诺尔及其鬼情人联袂骑驰的妙文,——由此可见,他不仅仅熟读英国诗人和美国诗人,而且熟读德国诗人。事实上,《一千零一夜》、柯勒律治、普希金、易卜生、福楼拜、契诃夫、奥尼尔、刘易斯·卡罗尔、基尔默、波特、佩罗、米尔恩、罗·路·史蒂文森……他们全都参与到《洛丽塔》的意义空间建设中来了。只不过,透过这些一晃而过的互文,我们并非次次都可以看出亨伯特对这些文本和作者的态度,也就是说,不是从所有的互文中都能够掘出一小筐洛丽塔诗学。
4
现在要牵涉出一位剧作家,大家都知道,我指的是奎尔蒂。这是小说中的人物,而非历史上的人物。此人按照通常的做法,引诱洛丽塔,玩弄洛丽塔,将洛丽塔置于众恶之墅。然后,他就消失了。亨伯特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他。这个狡猾的家伙,当他看到亨伯特掌心那把油亮的手枪,立即仿效吉卜林的《订婚人》,现场胡诌了一句诗,“女人就是女人”,试图软化亨伯特的复仇之心。事实上,奎尔蒂并非诗人,而是一个剧作家,写过悲剧、喜剧、幻想剧,热衷于越轨性行为,“被称作美国的梅特林克”,——由此可以看出亨伯特对梅特林克和剧作家的态度。就是这个剧作家,在临死之际,他也没有忘记与亨伯特套近乎,“我们都是老于世故的人,不管在哪一方面——两性关系、自由诗、枪法”,可是这个一点也不管用,亨伯特扣动了扳机。
反过来讲,既然亨伯特讨厌剧作家,那么奎尔蒂就必须是一个剧作家。
5
除此之外,我们并非没有注意到泛指意义和本体意义上的洛丽塔诗学。
小说开篇第十一行,我们眼前就跳出了这样一条提醒:“你永远可以指望一个杀人犯写出一手绝妙的文章。”这是什么意思?亨伯特弄死了奎尔蒂,他是一个杀人犯,但是,他还是一个叙述者。他要我们把目光从杀人犯移到叙述者上来:杀人非要事,叙述很成功,两者不矛盾。我们很快就会相信:他果然作了精致的回忆。继续读下去,相左的观点出现了。亨伯特狂热地迷上洛丽塔,黑兹太太反而成了一个障碍。有一次,亨伯特甚至想到过弄死黑兹太太。就像是诅咒的应验,黑兹太太——她的名字叫夏洛蒂——很快就出车祸死了。亨伯特虽非凶手,但是做贼心虚,他为自己辩解道,“诗人从来就不杀人”,希望可怜的夏洛蒂呆在永恒的天堂,在沥青、橡皮、金属和石头的炼金术中千万不要恨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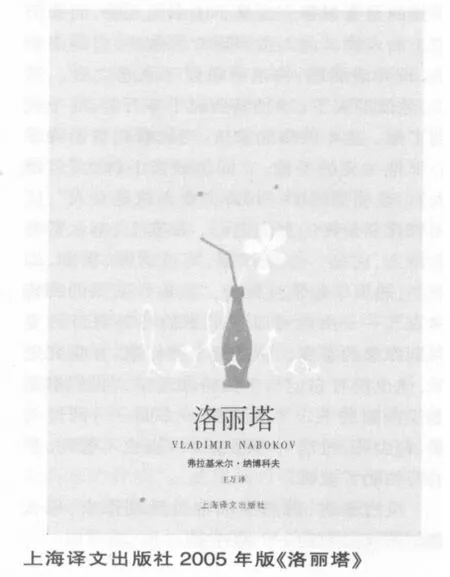
那么,叙述者亨伯特,诗人亨伯特,他到底喜欢什么样的诗?上文已经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里可以进一步清晰化。“我悄悄穿过的那些温和朦胧的境地是诗人留下的财产”,这个可以说明亨伯特的意境观;“她的凌空截击和她的发球就像结尾的诗节和三节联韵诗之间那样密切相关”,这个也许可以说明亨伯特的格律观:他就这样同时兼爱象征主义意境和古典主义格律。
刚才谈到,亨伯特将洛丽塔打网球的动作和姿态比作一种民歌的建行法和用韵法,可以这样说,在亨伯特的眼中,两者都是不朽之物。让我再次来到故事的结尾,亨伯特自知大限将至,但是他仍然清晰地列举出他和洛丽塔可以共享的一切不朽之物:欧洲野牛、天使、颜料持久的秘密、艺术的庇护所,当然,还有预言性的十四行诗。
亨伯特知道洛丽塔不爱诗,也不读诗,但是他仍然坚持做一个顽固的诗人,而且一厢情愿地将洛丽塔视为诗之化身。在这个问题上,亨伯特宁愿骗自己,也不愿意忍气吞声地迁就洛丽塔。
6
可是,亨伯特并不存在。
他只是一个“叙述的叙述者”,或是一个“被叙述出来的叙述者”,常常在叙述与被叙述之间穿梭往来。这个小说人物,在多大的程度上与小说作者纳博科夫相吻合呢?或者这样说,纳博科夫在多大的程度上对亨伯特的叙述进行了干扰?这个叙述学的千古难题,再次摆在我们面前。
一些证据显示,纳博科夫认为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逝水年华》的“前一半”是“二十世纪散文中四大杰作之一”——注意,是前半,还是散文——这个态度与亨伯特颇有几分相似。另外,纳博科夫曾断言,并非所有的俄国人都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他的,大都因为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而不是一个艺术家。而纳博科夫,他十分“厌恶文学神秘主义者”。这个成见,导致亨伯特“露出了一丝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狞笑”。还有,纳博科夫认为,凡·高是一个二流画家,所以《阿尔的女人》就出现在黑兹太太的门厅,——很显然,黑兹太太既非纳博科夫喜欢的人物,亦非亨伯特喜欢的人物。至于纳博科夫的弗洛伊德观,那是再明显不过,他多次自称与弗洛伊德的“巫术”存有“宿怨”。种种迹象表明,在诗学的直接表述和不经意的间接表述上,叙述者甚至就是作者,亨伯特甚至就是纳博科夫。这一点,还可以找到一些外围信息的支撑,比如,两者都从法国来到美国,都对美国汽车旅馆留下深刻的印象。
纳博科夫曾说:“我的亨伯特这个人物是个外国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除了性早熟女孩这一点之外,还有许多事情我与他的看法也不一样。”这个话值得玩味。关于马克·吐温的一则幽默故事讲道,有一次,他说,一些国会议员是婊子养的,激起了议员们的愤怒,于是他改口说,一些国会议员不是婊子养的。这个故事给了我们解读纳博科夫此语的另外一个角度。纳博科夫所谓“性早熟女孩”,亦即亨伯特所谓“性感少女”。纳博科夫用一个冰冷的术语取代了亨伯特那热烈的赞语,借此表明两者嗜爱之异。但是我很怀疑纳博科夫的诚实,他这样说,是不是置亨伯特于不顾,转而从道德上为自己开脱呢?我不相信,一个不是亨伯特的人,能够写出如此刻骨铭心的亨伯特;一个没有性感少女情结的人,能够写出如此活色生香的洛丽塔。
退一万步说,即便在性感少女这个问题上,作者与叙述者真有不同的观点,那也仅仅意味着,对于但丁、彼得拉克和爱伦·坡,两者可能会分别给出不同的赞赏理由。
由此可见,洛丽塔诗学其实就是纳博科夫诗学,或者说,洛丽塔诗学其实就是纳博科夫对亨伯特的强加。
7
现在回到纳博科夫。
1899年,纳博科夫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1919年流亡德国,后来进入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法国和俄罗斯文学。1922年开始在柏林和巴黎的文学生涯。1940年移居美国,1955年出版《洛丽塔》。1961年迁居瑞士。1977年病逝,墓碑镌文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作家”。
这个镌文不一定得到过纳博科夫本人的首肯。因为,他不光是作家,还是诗人,曾先后出版过《串珠集》、《山路》、《1929-1952年诗集》、《诗歌与问题》等多部诗集。他有一首诗,说从天堂回来,找到了旧屋子,哭泣的门,蔚蓝小窗户上的一团蒲公英,卡累利阿桦木沙发,以及玻璃下面蝴蝶的家,然后他写道,“我将再度成为尘世的诗人:桌子上摊开了练习簿”,——由此可见,当纳博科夫被公认为杰出的作家时,他自己,也许更愿意做一个静悄悄的诗人。
纳博科夫的诗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爱情、湖泊、太阳、月亮、云朵、梦幻,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明喻。毫无疑问,这些诗不具有那个时代所迸发出来的现代性特征。我有个观点,任何一部文学史都是风格正变与风格奇变的交替史,二十世纪初现代主义的勃兴就迎来了新一轮的奇变期。纳博科夫的诗滞后一步,挽留了十九世纪正变期的一些重要特征;但是他的小说,无疑乃是奇变之奇变:充满了倾斜、跳跃、诡异、迷醉、白热化、神经质、异想天开和无暇他顾,设置了大量两人化的、不足为外人道的意义死角。到了今天,用我们饱受现代主义洗礼的眼光来看,他的小说甚至比他的诗更像诗。
倒是小说人物亨伯特的那些游戏之作,具有二十世纪的某些特征。我们不会忘记,亨伯特曾经把洛丽塔在拉姆斯代尔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名单——里边有多少性感少女啊——视为一首诗。洛丽塔,当然,也就是“多洛蕾丝·黑兹”,前后两个同学,前面的“罗斯”和后面的“罗莎琳”,都是“玫瑰”之意,亨伯特就把她们称之为洛丽塔的“玫瑰护卫”。这张普普通通的名单,立马就被亨伯特“创造成”一首诗,——这真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做派。当然,在整部小说中,亨伯特还曾写下数首诗歌,或是诗歌片断,一边唐突前贤,一边泄露自我。比如,他所写下的“冯·库尔普小姐”片断,就是对T·S·艾略特《老年》一诗若干行的剪拼。还有“圣徒,的确!当褐色皮肤的多洛蕾丝”片断,则是对布朗宁《西班牙修道院中的独白》一诗第四节的戏拟。值得注意的还不仅仅是亨伯特这种游戏精神,他有两首较为完整的诗,让他可以被称作诗人。一首是为奎尔蒂下达的韵文判决书,他要求奎尔蒂大声朗诵一遍,然后就枪毙了这个朗诵者。另外一首,是在此前,他弄丢了洛丽塔,住在魁北克一家疗养院里,在那儿度过了那年冬天余下的时光和第二年春天的大部分时光,期间完成的韵文寻人启示。那真是绝妙的文字,充满了甜蜜、猜忌、嫉妒、痛苦、寂寞和悲凉,大量具体可感的物象,比如汽车、棕榈成荫的海湾、自动唱机、磨损的牛仔裤、破了的圆领运动衫、名叫“绿日”的古老香水、亮着灯的铺子、短袜和蒙的灰色目光,点点滴滴,滴滴点点,撒落在全诗的每一个角落,让这种无计可消除的爱情获得了清晰可辨的独特徽记。除了这种历历在目的细节感,还有那心如死灰的结尾“,余下的只是铁锈和星尘”,让人过目难忘。对此,亨伯特自己也不免有几分得意,他说,“用精神分析法来看这首诗,我发现它真是一个狂人的杰作”,——他一边赞美自己,一边再次揶揄弗洛伊德。很显然,这则韵文寻人启示,正是典型的“只写给一个人”的诗。只写给一个人,这种想法如此彻底如此决绝,以致于此诗终于可以写给任何人。这正是写作的坦途。
可是,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亨伯特并不存在。亨伯特之诗事实上都出自纳博科夫之手。然而亨伯特之诗真是纳博科夫之诗吗?相似的问题是,薛蟠之诗,抑或林黛玉之诗,难道真是曹雪芹之诗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不好回答:那个“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的作者,真是“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的作者吗?从某种角度讲,曹雪芹只是一个代笔者。纳博科夫也是如此:他只是亨伯特的代笔者。亨伯特的角色心理和身份特征,对纳博科夫形成了严厉的规定: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只能模拟亨伯特的想法来写。如此,这些诗,就成了亨伯特对纳博科夫的反强加。奇妙的是,纳博科夫的写作居然藉此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我们当然已经发现,这些诗比纳博科夫本人的诗更具深情和快感,更加自由和开放。代笔者纳博科夫,就这样轻易地洞穿了个我写作的层层束茧,转瞬之间发生蝶变:亨伯特之诗原本不过是游戏之作,结果意外地上升为别开生面的美学创造。
8
洛丽塔诗学的叙述学分层到此结束。这笔糊涂账,还将继续给我们带来烦恼。谁的洛丽塔?这将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乐趣永远来自于计算,而不再是答案。
——《洛丽塔》的叙事心理学解读
——《洛丽塔》的成长小说解读
——论《洛丽塔》中亨伯特的自由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