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离婚老娘舅”们
陈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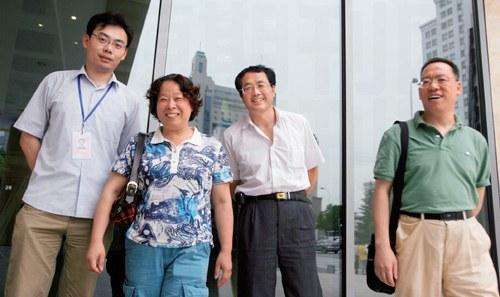
由退休民政工作人员、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们组成的上海特色“离婚劝和”队伍,负担着超出自身的任务和期许。
几乎没有任何预兆,黄锦英听见办公室门外传来一阵争吵,声音由小渐大。
她走出门去。门外一对三十多岁的男女——女人涨红了脸,男人昂着下巴,攥住一只橘黄色皮包争夺不放。还有一位妈妈模样的妇女打着电话,手指与嘴唇都在颤抖:“110吗?有人要诈骗在(普陀)区婚姻登记所”。
黄锦英心里明白大半,这又是一对为协议离婚吵架的夫妻。她上前拉开两人。
这里是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婚姻收养登记中心,黄锦英在此工作近20年,见惯大场面。三年前,她退休后被返聘为“离婚劝和”员,专门从前来办理离婚的夫妻中辨别冲动型、情绪型离婚,劝其和好。
而这对夫妻似乎没有劝和的希望。半年内,他们因吵架打过7次110;争抢的是皮包里的一万元分手费。末了,丈夫提出,妻子必须归还他的礼物——一枚戒指和一只MP3。
听到归还MP3,黄锦英从心底里有点瞧不起这个男人。但她还是主持局面,让双方在她的见证下分割财物。点完钱、签完字,两人一前一后出了门。
“你看,多快的事情。时钟滴答一两分钟,夫妻就变成陌生人了。”黄锦英转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做了个双手合拢又分开的姿势。
冲动离婚引发的服务
“我自己想想,还真的有点像老娘舅一样。”黄锦英说。
在上海语汇中,“老娘舅”指舅舅,母亲的弟兄。过去的大家庭,遇上兄弟分家、妯娌吵架等纠纷,常会请出老娘舅主持公道。渐渐地,有威信、有亲和力、善解争端的热心人都被称为“老娘舅”。
她曾遇上一对来离婚的老年夫妇。老头气鼓鼓的,进门便说:“现在我扬眉吐气了!”
细细一问,老伴一直嫌弃他做的菜太咸,年轻时觉得不是件大事,退休后越来越难以忍受,几次挑剔后老头回了嘴,两人大吵一架,早上买完菜后就来办离婚。
“你这么多年都忍耐过去了,还差这几年么?”黄锦英哄着已经78岁的老头,“哎呀呀,你就下辈子不要跟她做夫妻啦!”
周围人笑起来。老头绷紧的脸放松了,想想觉得难为情,拉着老伴又要走:“算啦,回家回家!”
这是黄锦英最快、最成功的一次“老娘舅”式劝和。她在离婚登记窗口旁有一间从档案室隔出来的小办公室,但她很少坐下,只是像街坊邻居一样,在大厅里和不同的夫妻搭上几句和气话。有愿意说下去的、情绪不稳定的,再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详谈。
在《婚姻登记条例》正式施行的2003年10月1日,黄锦英还是普陀区民政局婚姻收养登记中心的负责人。早先,这个条例叫做《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自从 “管理”一词引退,行政权力的干涉在新条例中消失,手续全面简化,离婚率也从此上扬。
这一年,黄锦英发现来离婚的夫妻多了。她记得的一个数字是,《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后的2004年,区里协议离婚登记量比2003年增长了37.8%。而在2003年以前,全国协议离婚数只是平均每年递增5%~6%而已。
2006年的一天下午,她接待了一对父母。这对老人得到消息,女儿女婿在当天上午办理了离婚手续。小夫妻俩前一天傍晚还在老人家里吃了饭,像往常一样回到家。不料,当天深夜,孩子尿床大哭,小夫妻俩谁都不愿起床照管,大吵一架愤而离婚。
当他们来办离婚时,婚姻登记员自然无从知晓这对年轻小夫妻的故事——他们甚至不记得这对夫妻了。
“你们这样太轻率了!如果你们帮我们劝一劝的话,他们也许就不会离婚了。”确定女儿女婿真的离婚后,老人重复着这句话。这话深深触动了在场的普陀区民政局局长曹道云。
2006年3月,在曹道云的主持下,中心在婚姻家庭健康咨询工作室中辟出一角,放下一张办公桌、一块指示牌,请来一位退休的妇科女医生,“离婚劝和”工作室便正式成立了。
之后,松江、浦东、闵行等上海各区陆续跟上。到目前为止,全上海18个区县都有类似的工作室或组织提供这一服务,专门工作人员约有五六十人。
从“难离”到“闪离”
31岁的心理咨询师王美萍,两年前加入上海市松江区“离婚劝和”工作队伍。
只要当事人有情绪、只要愿意倾诉,就有可能劝和。如果双方都是初次结婚,希望则更大。当然,也有考虑成熟、理智分开的夫妻,遇到这种情况,王美萍可能在简单沟通后便放弃努力。比如,她看到一对夫妻的离婚协议书,附有财产分割的详细清单,除了电视机、冰箱等大物件,还有一条是,“卧室窗帘布属装修时附送,留给男方。”
夫妻之间竟能算得如此决绝清楚,王美萍暗暗吃惊。她把这件事当作新闻告诉了工作室的另一位全职工作人员,63岁的退休律师封秋全。不料,封秋全笑了,连说不稀奇不稀奇,“稻谷多少斤、蚕豆多少斤,大碗三个、小碗六个,都是我写过的离婚协议。”
退休前,封秋全在松江区小昆山镇政府法律事务所工作了整整25年。上世纪80年代,小昆山镇有15个村,每村8个大队,只要一个大队打来电话,说队上哪户人家吵架了、闹离婚了,他便骑着自行车到村民家里实地调解,“不过人们离婚都羞答答的,说出‘离婚这两个字感觉比登天还难。”
1980年,实施了3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进行了首次修改,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条件。改革开放后,离婚数量持续增长。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封秋全代写的协议离婚书变多了。有的村民,甚至在烟盒子撕下的锡纸片背面写上离婚协议书,请他查看。
而那时的离婚,亦远不如今天便捷。
2003年前,沿用近9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办理离婚需要单位、村委会或居委会的介绍信,从审核、登记到发证要1个月的工作期。此外,离婚协议中没有房产的一方,还需要写明离婚后的居住地与户口迁移地。更复杂的是,接收离婚人的第三方,还得带上户口本、房产证,到婚姻登记单位来签字。
黄锦英记得,有不少花白头发的母亲,被离婚的女儿扶着,哆哆嗦嗦地在协议上签字。倘若找不到户口迁移地,便不能办理离婚手续。为了这些繁琐的手续,一些离婚夫妻在登记中心拍了桌子,“是不是要死给你们看,我们才能离婚啊?”
还有介绍信的公章问题。普陀区规定,离婚者所持的介绍信应有处级单位的一级章。可是,单位越来越多,登记员无法辨明级别,也会引来争吵。最后,还是普陀区发了文件,将处级单位名称和公章要求一一列出。
“现在想想,这些个证明真的是无所谓的”,黄锦英说。1999年,上海一个处级单位的党委书记来离婚,听说了介绍信的公章要求后,沉默半晌。接着,他找到黄锦英:“介绍信我完全可以自己开出来,但是我不想这么做——因为这是我个人的隐私,和单位没有关系。”
这位党委书记最终没有办离婚。但他的这段话让黄锦英第一次意识到婚姻的个人权利。
起初,上海市大多区县的婚姻登记中心还没有服务窗口。同一个房间里,一天办结婚,一天办离婚。接着,工作间分开了,但这边的新人听着登记员的声声“恭喜”,背景音却是隔壁离婚夫妇的争吵哭泣。现在,结婚登记大多设置成开放敞亮的服务窗口,而离婚登记则在房间里再隔出一个个小间分开办理。
2001年,上海市还规定,办理结婚登记时应进行颁发结婚证书仪式,对颁证室面积、背景、颁证员服装胸卡等都做出细致规定。后来,有的区县还会特邀德高望重的金婚夫妇,为新人颁发结婚证。
而对于离婚,进入21世纪后,程序愈来愈简便,状况却愈来愈复杂。
有人带着第三者来离婚。妻子在哭,丈夫在写离婚协议。丈夫身后,一个年纪相仿的中年妇女指点着财产分割,“这套房子给她,这套你留下嘛好咧”
有夫妻俩在上班路上发生争吵,一气之下直接将车开到了婚姻登记处,“离就离,谁怕谁?”而争吵原因竟然是,开车的丈夫过路口时抢了黄灯,妻子责怪他不懂得安全第一,丈夫却郁闷妻子不理解送她上班迟到的担心。
因夫妻沟通障碍而离婚的,在上海市松江区2010年3000多对离婚夫妻中,占到44.4%。这是王美萍所在松江区离婚劝和心理咨询室的统计数据。其中,夫妻之间因琐事冲动离婚的不在少数。其次是婚外情,占总数的21.8%;其他则是因赌博、产权纠纷、经济压力等原因导致的离婚。
最近几年,与共和国同龄的封秋全有点想不通,“有人离婚就像来结婚似的。”
两个年轻人在他面前商量着,要写离婚协议书。男生抖着腿,女生紧挨着:“你不是说给我30万的嘛?”
“好好,给你30万。”
协议书写完,手续办好,两人又搂着出了门:“离了,咱们去吃顿饭纪念一下吧?”
封老师把这件事当成新闻告诉王美萍,王美萍也笑,连说不稀奇不稀奇。
王美萍身为80后,理解同龄人好聚好散的新观念。2007年,一位上海男孩与旅游时偶遇的女孩在46小时内结婚、100天离婚的典型“闪婚”“闪离”,到如今有了更多的现实样本。
专业人员登场:从劝和到疏导
关于上海年轻人的闪婚闪离,32岁的社工俞嘉华是从网络中看到这些信息的。他是上海市浦东新区社工协会的工作人员。2009年,社会协会成立睿家婚姻家庭项目组,与浦东新区民政局合作,进驻市民中心婚姻登记处,2010年6月起正式为前来离婚的夫妇提供免费服务。他由此成为“离婚劝和”队伍中的一员。
俞嘉华没有民政局的制服,也没有单独的工作室,只是流动在前来办理离婚手续的夫妻们中间,微笑着与他们打招呼:“你们好!我是家庭社会工作者。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他得到的大多数回应,是沉默、摇头,或是简短的拒绝。还有人反问“社工”的意思。
俞嘉华拥有社会工作硕士学位,在德国一所新教高等应用大学获得。在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社会工作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社会工作者分为青少年社工、移民社工、养老社工、家庭社工等多个门类,其中,家庭社工常常成为德国夫妻发生家庭矛盾时的沟通者。
他曾在德国移民局的一处外国移民家庭咨询工作站实习。一对夫妇,因为儿子初中毕业后的职业选择有了矛盾。意大利父亲想让儿子学汽车修理,德国母亲希望儿子将来做厨师。他们找到工作站,一套职业倾向测试题最终解决了这次分歧。
“现在国内有多少夫妻会觉得,现在我们有问题,要找婚姻家庭咨询?人们只知道有居委会干部,不知道有社会工作者。”这一年中,理解并愿意与社工谈话的夫妻只有499对,只占前来离婚夫妻的十分之一左右。
有人说他们也是“老娘舅”。俞嘉华是上海人,印象中那些热心快肠的调解员们,大多年事已高、见过世面,凭着人情与阅历,像居委会干部似地解决问题,甚至有情感上的偏袒和倾向。
他回答说:“我们不是老娘舅,我们是中立的社会工作者、婚姻家庭辅导师。对夫妻双方的行为不作评判,只是对他们的状况提出建议,共同探讨。”于是,他更愿意定义自己的工作性质为“婚姻危机干预”而不仅仅是“离婚劝和”。
“也许沟通了很久,他们还是要离婚。没有关系。更重要是让他们先明白一些东西,明白婚姻不是游戏,而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对今后有成长。不然,婚离得不明不白的,以后又结又离,这样是不好的。”
如今,除了浦东新区,普陀区也计划将“离婚劝和”工作室更名为“离婚疏导”工作室。
除了专职社工的加入,2007年6月,松江区民政局每年拿出6万元,与区内首家心理咨询工作机构——松江区心理咨询协会合作,在婚姻登记管理所开设“劝和”心理咨询工作室。松江也是上海市第一个将心理咨询引入离婚劝和的区县。
当然,这里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心理咨询室。比如,心理咨询师应面向咨询者45度角坐下,以观察对方的身体语言,而在这里,因为地方小,两只灰色布艺沙发只能面对面摆放着,而另外两只沙发,则并排着挨在一起。
“我们想,肯定有很多夫妻在跨进这里前,已经很久没有肩并肩地坐在一起了。”这是王美萍特意为离婚劝和做的安排。
在这两只紧挨着的沙发上,有前来离婚的夫妻将初识的美好一一说给她听。可能刚一开头,听着的男人会比诉说的女人更早流下泪来。
“离婚劝和”服务推出的五年多来,上海不同区县都有不少成功案例。然而,在离婚率节节攀升的社会背景下,这个成功率仍然微小。2010年在上海各区县,咨询协议离婚的夫妇有4636对,经过劝和,有1338对当场表示不离婚了。但是这一年上海的离婚数字,是37738对。
今年6月初,民政部公布的全国民政事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共有46.5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平均每天有5000多个家庭解体,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7.1%。其中,北京、上海及深圳位列离婚率前三位。
“以前不知道,我们做的其实不只是离婚劝和,还有很多人是要来跟你说心里话的。”黄锦英曾经接待过一位单独前来的中年妇女。四个多小时里,女人讲如何与老公相遇相爱、老公先下岗后创业升为副总、两人交流越来越少的故事一股脑全说了出来。她穿着一件圆领汗衫,脚上是拖鞋,尽管只有51岁,看上去却像是“在菜场里买菜的老太太”。
“看你今天到我这里来的这身衣服,我就敢断定,问题就出在你自己身上。” 黄锦英以过来人的经验指点,“第一件事,要打扮自己。下次你来见我,要让我眼前一亮。第二件事,不要再摸老公口袋,看老公的手机,不要总是怀疑他。”
最终,这位妻子挽回了丈夫和家庭。
“作为婚姻登记机关,我们实际上是在最后一道防线上建起一道篱笆墙。” 上海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处长周吉祥说。由婚姻登记工作人员、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和其他志愿者等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们组成的上海特色“离婚劝和”队伍,事实上正负担着超出自身的任务和期许。正如上海睿家社工服务社主管文雨所说,“中国人如今真正需要的,是走进企业单位、走进学校和课堂的婚姻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