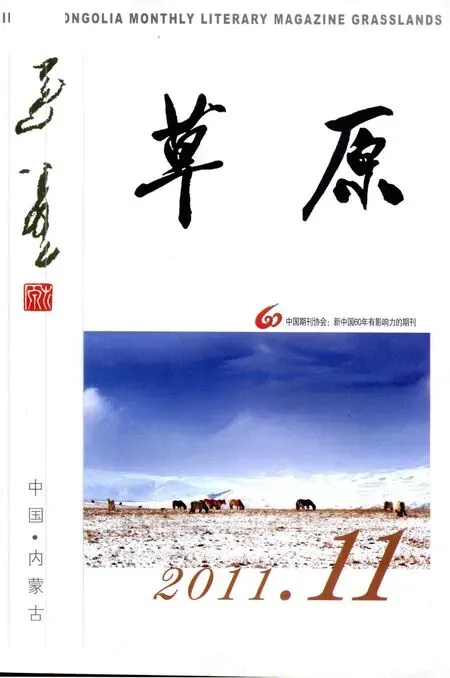最后的土地
□王玉涛

苞米油绿油绿地长在地里,每棵苞米的腰上,都挂着鼓鼓囊囊的苞米穗子,看一眼心里就舒坦。
地里其实没有什么活计要干,垄沟里连一棵草都寻不着,可范老大还是每天天一亮就下地,中间吃上一口饭就急匆匆地再回到地里去,好像地里种的不是苞米,而是金子。
村里的人早就不下地了,许多人家开春连地都没有种,就那么让它荒着。村里的人,上了点年纪的,吃过饭就在树底下闲聊。年轻的,有的出去打工,有的闲逛,更多的是玩,当然不白玩,现在有钱了,哪家都有个百十多万,不玩干什么?还有几户早早买了小车,呼呼啦啦地满大街跑,要么就拉着老婆孩子出去旅游。
只有范老大种地,老伴劝,儿子劝,女儿劝,谁劝也不好使。一开春,他就早早地把地蹚了,没有人给他浇水,机井属于被占的地,电线都给掐了。但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一场及时雨下来,小苗呼呼地往外长。瞅着那小苗,范老大见谁跟谁说,长到七十多岁,这么好的墒情真不多见。土地是啥?土地就像娃娃,你疼它,护着它,它就健健康康地长身体。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范老大懂得这个理。
腰里的手机响了,不用看,不是儿子就是闺女。每天打电话劝他,地别要了,把钱领回来进城享清福去。儿子在城里把楼房都给他买好了,宽敞亮堂,开车把他和老伴拉过去,老伴一看就相中了,老东西,你不来,我来!我一会儿就去办手续,把钱拿回来!你敢!要来你自己来,钱你别动。地,就是我的闺女儿子,我不卖!
可话是这么说,你说不卖就不卖?这是政府项目,要建经济开发区,又不是一家一户的事,影响全局呢。范老大说,我有合同,二轮承包合同,五十年不变,这才几年啊!
手机又响。响就响。范老大犯了倔劲,把手机扔在草地上任它自己唱。他掏出烟来,卷了一支,眯着眼看他的庄稼。看着看着,看见老爹从地里走了出来……
买地那年,老疙瘩十一,娘正有病。老爹几次要领她进城看病,娘就是不肯,说去看病买地的钱就没了。谁知道,地买回来了,娘却没了。娘连一次也没进过自己家的地。还有,埋葬娘的那天,爹还戴回来一顶富农帽子。村里人笑他,想地都想疯了,啥时候了,还买地,省吃俭用,攒了一顶富农帽子!可爹却不后悔。范老大知道,他爹的后半辈子,就和这块地连在了一起,想分也分不开。即便后来地归了公社,他仍把这块地当成自家的,就是进城憋一泡屎,也要老远跑回来拉到这块地里。
也许是命里注定,这块地和范家有着不解之缘,分产到户时,生产队事先定好抓阄定地块。抓阄的前一天晚上,范老大在爹的坟前坐到天亮,心里所有的期望都是抓到这块地。在他颤抖着手展开纸条,看到了正是他所希望的这块地时,竟然一下子瘫在地上。
手机又响了。不接!所有和土地承包有关的手续都在他的身上带着,只要他不去,谁也领不出钱来。范老大就不信,他不签字,有谁敢毁他的地!
还有三两天,苞米就熟了,就可以满满地烀上一大锅,老伴一辈子就好这口,有时候在梦里吧叽嘴,醒了还说,这青苞米真香!范老大笑他,你就是受穷的命,有了苞米、大葱大酱就知足。城里的孙子也喜欢,烀好了,先给孙子送去。左邻右舍呢,尽管看他们把这么好的地撂荒着招人来气,但也要送点。还有孙全,过去那可是个好庄稼把式,每次耪地,他们俩都是摽着膀子干,谁也没服过谁。可自从政府征地,他屁颠屁颠地把钱领回来,还到处显摆,这辈子头一回见着这么老多钱!腰里有了两个臭钱,老家伙就不学好,优哉游哉地像个二流子。不给他吃,就让他馋着!
范老大想象着一大锅黄澄澄的烀苞米,心里美滋滋的。自己种的苞米,自己用大锅烀熟,捞出来就吃,那股香味,给御宴也不换!范老大眯起眼睛,仿佛已经闻到了烀苞米的香味。
想孙全,孙全就来了,这个老东西,拿了征地款,一天三顿小酒,小脸红扑扑,哪还像个庄稼把式!
孙全坐在他身旁,从兜里掏出一盒“红梅”,递给他一支。范老大瞥了一眼,没接,掏出烟口袋自己卷了一支。说,你那玩意,价钱好,不是正味。
孙全笑了笑:“老大,你有福气,儿子、闺女都在城里当官,听说,一百多平米的楼房都给你买好了。”
范老疙瘩说:“那玩意太高,不接地气。”
孙全说:“这是潮流,早早晚晚都一样。就像死了一把火烧成灰,不是你想不想烧。”
范老大说:“死了的事我管不着,活着,我就得种庄稼。”
孙全说:“你种庄稼,不让毁地,可把你儿子的前程给毁了。”
范老大说:“他当他的官,我种我的地,我碍着他啥了?”
孙全说:“你是放着明白装糊涂,这么大一片开发区,为啥别人家的地都毁了,就你家的地没毁?还不是你家有人?”
范老大没想过这一层。
孙全说:“听说这回换届,就因为你赖着这块地,你儿子怕是要下去了。”
范老大问:“有这事?”
孙全说:“这事村里人都知道,都这么说。”
孙全走了,范老大觉得脑袋有点迷糊。他摇摇晃晃想站起来,拱了两拱竟然没站起来。再坐下,心里就乱糟糟的,好像心里有好多话要说。想着想着,眼泪就下来了。他抓起一把青草,放在鼻子底下使劲闻,是一股略带苦涩的清香味,范老大在这草地上奔波了一辈子,脚底下一天不踩着这草,走道都不踏实。可这里马上要变成高楼大厦了,到了城里,星星点点的也能看到草,可那草娇贵,怕踩,也没有这野草的清香味,别说喂驴喂马,喂兔子都不吃。
太阳高高地挂在头顶上,晒得人有点头晕。他想站起来回家吃饭,重要的是要找个人说说心里话。和谁说?只有老伴。可使了使劲不但没起来,反倒一头倒了下去。躺在热得发烫的土地上,心里好像一下子舒服了,他骂自己,真是贱命,就是离不开这土地。迷迷糊糊地,他就做起有一搭没一搭的梦。
醒来时,已经是在城里的医院里。范老大一眼看到了孙子,他伸出三个指头说:“再有两三天,地里的苞米就熟了,到时候爷爷给你送来。”儿子、老伴赶紧把脸扭了过去。
迷迷糊糊地他又回到自家那块地,油绿油绿的一大片,苞米果然熟了。他掰下一穗,剥开苞米皮,用指甲一掐,苞米粒里就流出牛奶一样的白浆。他捋捋肥厚的苞米叶子,捏捏圆乎乎的苞米穗子,嘴里念叨着,这是他这辈子见到过的最好的庄稼。
这时,一阵轰隆隆的响声惊醒了他,一大片蝗虫似的推土机开过来,没等他躲开,推土机就从他的身上碾了过去。他就舒舒服服地躺着,任凭推土机一辆一辆从身上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