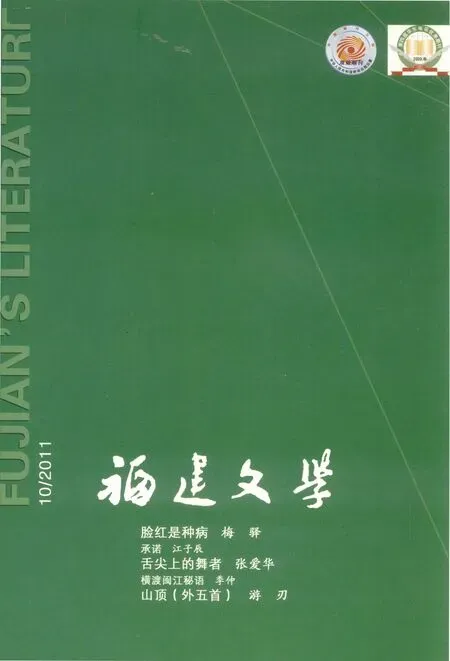复活了一段闽人历史 展示了一场民俗盛宴——绿笙长篇小说《永安笋商》读后
莱 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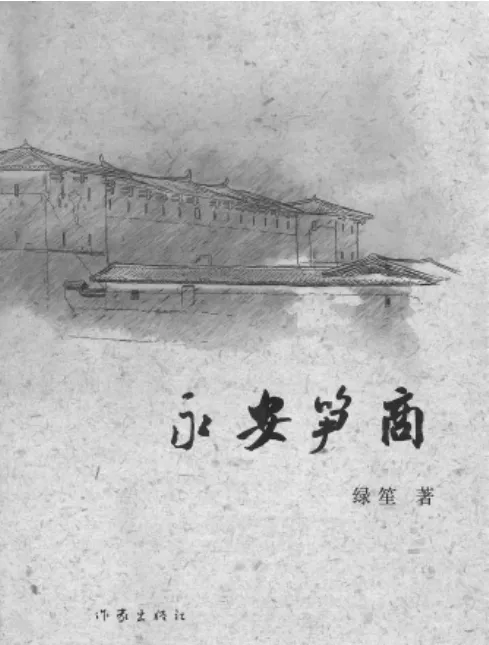
通读完这部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的40多万字长篇小说,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永安笋商》复活了一段重要的闽人历史,集中展示了福建母亲河上游的沙溪民俗。
这段复活的历史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福建抗战前后的普通人物画卷。绿笙通过塑造池家两代笋商、描绘笋帮公栈一批笋商命运变迁来复活这段历史。在福建近代历史上,省会所在地有过两处,一处是福州,一处是永安。永安成为福建省会,是由于日本入侵,福建省政府的内迁。主人公池加林在福州的爱情单纯以及在永安的爱情复杂化,揭开的是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理念;笋商们从窝里斗到一致对外投身抗战,揭开的是舍弃商家利益维护国家利益的精神。《永安笋商》从这种个人命运的微妙变化中展现出国家与民族的精气神,立意崇高,这其实也是受命文学与作家个人思想风貌的巧妙结合。假如仅仅就这样把如此宏大的主题给喊出来,《永安笋商》可能就会成为一只简单的传声筒,绿笙的可贵在于,他并不正面描绘笋帮公栈的整体层面,而是剖开了笋帮公栈之中池、姜两派对立笋商的命运变迁,以人物内心的冲突来组织世事的变迁,以人物性格的演化来推进这段历史。绿笙的可贵还在于,以志书与学术方式展现的永安抗战文化被他以文学的手法进行了活灵活现的表达,永安抗战文化是全国抗战文化之中为数不多的重要代表之一,至今,文学界对它的具体传达还是少见的,《永安笋商》的这种描绘,使历史具有了文学的生动性,使文学具有了历史的厚重感。最重要的是,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历史再现,而是民族气节的揭示。
读《永安笋商》,仿佛是在品味民俗盛宴。绿笙在这部长篇小说里集中了大量的沙溪流域的风土人情,随着情节的演绎,一种又一种的民间传说和特色习俗逐一呈现,石马、旌鼓舞、燕子窝、太保公、黄石仙师、公平石……闽中西部鲜为人知的民俗在《永安笋商》中引人入胜,使整部小说变成了一簇民间传说的活化石。这样一种对神秘的沙溪流域文化遗产的描绘,是通过揭秘讨笋与贩笋的现象展开的。绿笙的聪明就在这里,他不是单纯地将笔触局限于笋的范畴,而是以笋为媒,串起这一带的民俗与历史事件;通过大量的神秘民俗与历史事件,烘托闽笋的神秘。在这样的彼神秘与此神秘的相互呼应中,小说的文学性得到了美妙的抒发。值得注意的是,假如仅仅收罗大量的民间传说加以堆砌,绿笙就可能平庸成一台复印机,对民俗与传说的简单复制是作家的绞刑台,绿笙的又一次可贵就在于,他对这些神秘民俗的解读是带有文明价值取向的。比如,他对太保公的大量描绘,有一副楹联很有画龙点睛的出彩,那就是沙溪流域众多太保庙可见的楹联:“为人奸邪对我烧香何用,做事刚正见吾不拜无妨。”还有小说中展现的一系列有关笋的生动民谣,倡导的都是正义与勤劳。正是这样的文明价值取向,使众多的民俗与传说在《永安笋商》中产生了健康的审美效应。
《永安笋商》是第一部三明本土作家描写三明本土文化的长篇小说。从《永安笋商》,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同类小说的创作启迪,就作家如何化解素材而言,我感到以下三个意识是值得具备的:
第一,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谁都知道,生活是创作的来源,忠实于生活是文学的基本准则。但是,照搬生活并不能产生优秀的文学作品。作家的本质才华绝对不是仅仅从语言上表现的。如何从浩瀚如海的生活中选择成功的创作素材?这才是检验作家创作才华的本质所在。对素材的嗅觉,是作家的首要才华。就绿笙《永安笋商》的创作而言,其实也是来自他的生活。绿笙在童年时期就接触闽笋,这是他写作闽笋的生活基础,再加上创作前期的大量采风,绿笙有了很好的生活来源。但是,闽笋产地众多,闽笋事件繁杂,写怎样的闽笋呢?这就有一个取舍了。永安笋干在历史上有“福建八大干”之一的名誉,上世纪九十年代永安又获取了国家级“笋竹之乡”称号,加上抗战文化,选择永安笋商为创作素材,显然比起选择其他更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基于这样的素材形成的小说,一旦得到认可,小说作品对于闽笋特别是永安笋竹产业的品牌传播功效,那是显而易见的,文学作用于生活的功能也就可能得到更好的印证。我以为,作家不能仅仅停留在有感而发。作家要善于在自己的感觉与社会公众的关注之间找到共同点,要善于对那些能够推动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素材产生感觉。假如费神于那些与大众不关痛痒的题材之中,那么,下的写作功夫越多,精神与体力的浪费也就越大。
第二,源于历史而鲜于历史。
文学本来属于虚构范畴,小说的基本文学特征就是建立在虚构基础之上的。而当下世界文学发展中有一个普遍热点,那就是非虚构文学包括非虚构小说的写作。许多国家的文学研究资料表明,在媒体化的年代,非虚构文学的写作对于彰显文学功效有着强大的力量,是大众阅读的广泛需要,而如何在非虚构文学中兼顾真实性与文学性,则是创作能力的体现。历史题材的创作就是置于这样一个真实与虚构的坐标之中展开的,既要尊重历史又不能受困于历史。那么,作家应当怎样处理好这对矛盾呢?从《永安笋商》来看,这是一部取材于历史事件的小说,作品中的时间与地点都是真实的,绿笙在这里的历史再现老老实实地照搬了史料;而对于人物与事件,则有许多无从考证之处,其实这类写作是有一个不成文的准则的,那就是主要人物与重大事件不能虚构,否则就有歪曲历史之嫌,但是,史料没有记载的具体细节和场景却需要虚构,没有这样的虚构就没有文学性,绿笙聪明地做了虚构泼墨,使历史复苏。这是创作历史小说需要有机把握好的一个度。我以为,复活历史的催生剂是作家的想像力,入乎历史之内又出乎历史之外,使陈年往事变得鲜活。
第三,源于民俗而优于民俗。
世界各地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数是从文学作品中保存下来的,文学留住了民俗的生命又从民俗中得到了滋养。在过去文学西化的横向移植中,不少作家曾经一度沉迷于哲学式的精神高蹈,仰视意识流的高空,以致无法俯下身子关注足下的文化土壤。其实,那是一种文学异化。即便在西方,对本土文化的关注也是很受重视的。令众多中国作家很不服气的诺贝尔文学奖,那些获奖理由的陈述也有相当内容是针对了作家对本民族文化的精妙叙述。中国文学传统其实也是一条人文关怀的历史长河。当然,作家发出的声音确实只是个人的声音,甚至十分微弱,但是,作家一旦深入民俗之后再发出的声音却会更加洪亮与亲和,民俗会让文学更加精彩。就我个人阅读而言,《永安笋商》对民俗与传说的描绘比人物性格的描写更加吸引我,我惊讶于那些神秘的民俗竟然得到这样精彩的再现,精彩的不单单是民俗内容的细腻叙述,还有着作者入情的理解。我认为,作家的文学境界是饱含着思想的美,不少小说家都在追求构筑一个自己的特色世界,把笔触伸进民俗有利于这样的追求。只是,民俗之中沉淀下来的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作家要用自己的思想去剪裁它们。作家不能成为民俗的俘虏,作家应当成为民俗的主人,要让民俗在作家的笔触中得到新的生命,这样的民俗才是文学意义上的民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