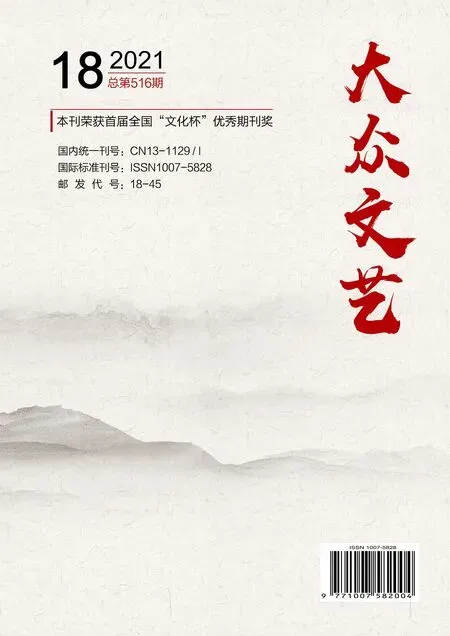试探谭盾音乐的三反
黄建龙 (温州大学 浙江温州 323000)
谭盾,作为一个深受当代世界文化影响的作曲家,他的音乐不仅涵盖了诸多的元素,并且发展为一种“综合的文化语言”,这也使他的音乐成为新旧音乐文化交锋的争论焦点。笔者认为,当一个人对朝夕相处的传统文化有着很深厚的感情与成见时,势必他会做出常人所认为的离经叛道的事情。而谭盾恰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论是他音乐中的文化色彩还是音乐色彩处处都恰如其分地体现出这一特征。本文笔者将分别从谭盾音乐的反传统创作手法、反传统表演方式及反传统音色选择三方面来对其音乐的离经叛道进行探求与解读。
一、反传统创作手法
由于谭盾的音乐创作手法新颖,因此他的作品问世不是广受好评就是饱受非议,也正是因其反传统的创作手法,他的作品也被归类为“新音乐”。笔者认为,谭盾的这种“新音乐”创作手法并非是偶然的,因为从20世纪以来新音乐的不断诞生及更替的过程来看,它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谭盾的创作最突出的是创新,一般而言创新的根本是创作观念的更新,而谭盾创作观念的更新则是其音乐创作区别于传统创作手法的根本所在。在谭盾看来“生活就是艺术,艺术就是生活”,他把音乐作为一种纯粹“声音”的艺术,更注重自然音的运用,从而打破了传统的种种规范和原则。[1]换言之,谭盾的音乐除他的独具特色创意外,他的思维方式实际是利用了反向思维进行的复古式实验,也就是所谓的反传统而又不失其传统精髓。创作观念的新追求必然要求创作手法的改变,而谭盾音乐创作手法当中最凸显的还当属蒙太奇手法中的拼贴与对位。
1.拼贴
拼贴手法在谭盾的音乐中是较多使用的重要技法之一,主要是将各自独立的不同音乐材料交错或重叠地结合在一起的创作方式。拼贴的材料通常来自不同作曲家、时代、风格、体裁的音响复合体。[2]虽然拼贴手法是一种世界通用的传统作曲技法,但是被谭盾拼贴后的音乐效果却与传统有着很大的反向弹力。如其创作的《鬼戏》当中运用的巴赫钢琴曲与中国民调《小白菜》,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乐曲拼贴在一起,但二者旋律走向依次下行,每一个乐句也都由高而低,体现了一叹再叹的主题内容,所以在旋律进行方式和情感色彩等方面有着天然的亲和力。笔者认为谭盾的拼贴并非是要传达某种具有特定象征的传统意义,他的拼贴只是为求音乐的创新、冲突及烘托音乐氛围的一个效果。如其作品《九歌》中拼贴进去的《十面埋伏》就是为了恰当地表现战争的肃杀氛围,而此处的拼贴也因此造就了戏剧的亮点。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谭盾有些材料的拼贴过于随便。
2.对位
谭盾曾坦言,他“喜爱巴赫的对位法,不仅是音符对音符的对位,而且也是语言对语言,意象对意象,文化与文化的对位。”[3]于是在他创作的作品中表达出了许多不同的对位现象,这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其音乐中为何会出现拼贴的原因。对位原本是一种写作技术,归属于技术范畴,但谭盾在作品中极大地拓宽了其内涵,使对位远不止是一种技术,而是被置于一种新的语境之中,成为一种观念“对话”的代名词。[4]在谭盾的音乐作品中,对位中的对比因素不再受限于旋律线条,而是扩展到节奏、节拍、速度、织体等音乐要素的各个方面。从其创作的《水乐》《纸乐》及《鬼戏》等作品中可以得出:音乐各声部之间纵向上结合比较自由,不协和音的运用遍布各处,调性也十分自由,这些看起来似乎都是较为普遍的反传统创作手法,但结合其音乐却都又能很清晰地看出其对位手法明显突破了传统的种种规范与原则。
二、反传统表演方式
如果按传统音乐会的标准来要求谭盾的话,那么也就不会出现所谓的“谭卞之争”。1一直以来传统的表演方式给观众大多是单声单向,而在谭盾的音乐表演方式中大多是给观众以多声多向,充分展示了音乐的多维性、立体性以及流动性。当然,这也正是谭盾手法的高明之处:用反传统表演方式把音乐延伸至空间性、视觉性和互动性三方面,其创造的新格局让音乐不再局限在传统的演出形式与特定音乐场所。
1.空间性
为了使音乐更富空间流动性,谭盾把音响空间观念加以拓展,不仅把剧场的布局、灯光运用纳入其创作之中,并且在演奏者的移动方位上也特别讲究,这也就是谭盾独有的散布乐队。如其作品《鬼戏》中,表演者在剧场的四周添设了7个演奏位置,其中4个在台上,有3个散布在台下观众之中,如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其剧场布局把观众围成了一个圈,但是表演者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在这7个位置台上台下来回的移动,并且从表演者移动的路线中又可得出谭盾作此布局的目的:“完成一个由剧场的四周(散)—中心位置(聚)—剧场的四周(散);形成一个大圆到小圆再到大圆的收拢扩散的循环,最终实现仪式音乐形式与西方弦乐四重奏的形式变换”。[5]笔者认为谭盾作此布局的目的不止于此,谭盾真正要呈献给观众的是:使其音响空间呈现出忽远忽近、忽上忽下的立体化效果,音乐则表现出行云流水般的流动性特征。
2.视觉性
传统意义上的音乐表演大多数是在观众的听觉上大作文章,而谭盾则是运用反向思维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法:让每一场音乐会的表演既有听觉上的感受,又有视觉上的享受。眼睛之所以在白天能看的很清晰是因为我们的眼睛感受到了光线,而谭盾恰巧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其音乐表演中灯光的运用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如其作品《鬼戏》中,谭盾使用了类似皮影戏的手法,让表演者在幕布后面演奏,同时又与幕前的演奏者交流,再加上与灯光调节相配合,于是产生了“阴阳对话,人鬼交流”的效果,这无疑是给了观众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当然,在视觉性方面做文章并不只是在灯光的运用上,谭盾还有意识地在多媒体、器乐及服装等多方面赋予了不一样的视觉冲击力,在此笔者将不再一一赘述。
3.互动性
众所周知,传统意义上的音乐表演只有舞台上的演员是动态的,而台下的观众几乎是静态的,这样的表演让观众与演员之间隔着一堵墙。但是谭盾的音乐表演让这堵墙不推自倒了,在他的音乐表演中不仅增加了演员与观众间的互动性,并且让观众感觉到自己被娱乐的同时也自娱了一把。这样的互动性在谭盾1992年为散布乐队、两个指挥及现场观众而作的《乐队剧场Ⅱ:Re》作品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作品中全曲的核心材料只有一个“Re”音,通过反复哼唱“Re”音,构建起了一个新的音乐文本体系。其中,谭盾还根据西藏喇嘛念经的形式自编了一个“Hong Mi La Ga Yi Go”的“六字经”,要演员和观众采用藏戏念白的方式集体念诵这“六字经”,整部作品的演出到结束几乎都是互动的。[6]这样的音乐表演不正是跨越了传统的标准界线而达到了音乐的“反”效果吗?
三、反传统音色选择
谭盾把音乐作为一种纯粹的“声音”艺术,更注重自然音的运用,因此在音色的选用上,谭盾根据每件乐器的特性出发,大多使用某一些特殊演奏法,并将不同乐器的演奏方法互相渗透,以便达到挖掘出乐器更多潜力的目的。笔者认为在谭盾音乐中反传统音色的选择可从器乐与声音两方面来探讨。
1.器乐
谭盾在传统的器乐音色选择上主要在打击乐器方面凸显其“反”的一面。在打击乐器中,他大大扩大了常规交响乐队中打击乐的编制,大量引进了一些色彩特殊的、乐队不常用的打击乐器,他还利用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常见的一些事物加以改造利用来获取新音源,有时甚至还自制或与他人合作来发明一些乐器。在演奏方面,谭盾也并未墨守陈规,而是大胆地改变了传统乐器的常规用法或者独创性地运用不同乐器的组合来丰富音乐的色彩性。如运用弦乐器在极高音区的演奏,箫的花舌音,笛子的双音,扬琴的滑音奏法等,此时具体的音高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对音响色彩性的追求,强调这种富有弹性的撞击所带来的力度和音色的变化与对比,并且通过此手法产生了“旧器新声”、“一器多声”的音响效果。[7]
2.声音
在谭盾的音乐中,应用了多元化的声音素材,因此也引进了“整体声音观念”这一概念。所谓“整体声音观念”是指“音响不是建立在音阶的观念上,而是建立在全部声音的基础上的”。[8]从此概念中即可得出谭盾音乐的“反”面。声音色彩的运用,除前文中提到的通过改变乐器演奏方法获取新音色外,谭盾总是从平常生活中的声音里寻找突破口,并且总是适当突出那些具有自然特征和日常生活特征的音响。如其创作的《鬼戏》中的水锣通过弓子与锣的摩擦和改变浸入水中的多少产生一种类似于揉弦的效果,而两种手法的结合又产生一种尖锐、刺耳的音响效果,制造出一种鬼怪、梦呓的意境;作品《纸乐》中的纸通过用嘴吹和一端固定另一段摆动及撕纸三种方法使其发声;再如其创作的《地图》中的石头通过敲打或摩擦石头的不同位置,或者改变口腔的大小和与石头的距离改变音高与音色。无一例外的是这些都充分显示出谭盾音乐中声音素材的多元化源于日常生活,同时也印证其音乐的创作观念:“艺术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艺术”。但从他的作品中又能折射出这样一种音乐“反”现象:打破了传统乐音材料的局限,大量使用自然之声、噪音等声音材料,甚至包括无声,由此拉近了音乐与生活的距离,使音乐的表现力获得了空前的拓展。
结语
谭盾音乐风格的多元化与他多元的人生体验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多元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观造就了其音乐的“三反”,也造就了其音乐的离经叛道。笔者认为,谭盾音乐之所以既能引发轰动的效应又能引来众多非议,并不是毫无征兆的:一方面是因为他创作中反向思维进行的复古式实验,给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同时也给传统创作带来了新方法新尝试;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音乐给还处于古典音乐审美的中国音乐爱好者来了个跳跃式的前进,这使得音乐爱好者在古典与新潮之间少了一个过渡,自然而然也使他们的审美落差感暴涨。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何会出现在国外谭盾的音乐广受好评与赞赏,而在国内却褒贬不一的现象。虽不能说谭盾的音乐创作尽善尽美,但是在他音乐的“三反”中体现的创新精神远远超越了其作品本身的意义,并为作曲界的创作提供了全新的理念。也可以说谭盾音乐的三反其实是在传统音乐文化基础上的创新与拓展,用谭盾自己一句具有辩证意味的话讲就是“古得不能再古的东西,同样也是新的不能再新的东西”。
注释:
1.2001年,北京电视台的谈话类节目《国际双行线》播出了卞祖善和谭盾的访谈,两人因在音乐观念问题上发生冲突,谭盾当场离座拂袖而去。谭、卞二人的冲突公开曝光,引发了一个卷涉艺术界、新闻界和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谭卞之争”。
[1][8]杨和平.《谭盾歌剧研究》[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2][3][4][5] 侯太勇.从《鬼戏》看谭盾创作中的解构与重组[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01期.
[6]石峥嵘.谭盾音乐的巫化倾向与现代巫术思潮[J].艺海,2009年第1期.
[7]孙谊.浅谈谭盾民族器乐作品的创作手法[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5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