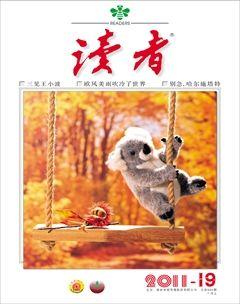我们的青春长着风的模样
潘云贵
过了很久,我才听出树上的蝉声还如当初一样的清晰。那些旖旎时节的花雨流经我们的生命,像极了一阵风,从多年前那面长满苔草的墙壁拂过。
那一行粉笔留下的字迹,细小得如同张开的翅膀,迤逦而来。
夏天又到了,我喜欢六月所带来的一切。那些芬芳的花草气息,丰沛的雨水,白衣少年的身影,单车,教室,卷子,铁栏窗,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符号海洋,都被回忆的脚趾柔软地踩响。请允许我不转过身来,不让你觉察到我的不舍是那么紧紧地贴在脸庞上。
阳光沿着记忆的旧址返回,这是通往过去的唯一途径。
南方的五月,台风还没入境。学校颇不情愿地让出三天的节假日给我们,而各科老师亦是没忘帮我们打包一沓的卷子、讲义,白花花的纸张铺天盖地地在我们的心里翻江倒海。而我自小便是不入流的那类,执意不想错失这般可供自己喘息的机会,所以趁母亲不注意时便从小门溜到院里。庭院里种满了合欢树,树下摆满兰草和各种枝叶奇形怪状的盆栽。台阶两侧有一口花纹大瓷缸,里面是长于卵石缝隙间的莲荷,通常会在初夏一场突袭的暴雨过后开出清淡的花,浅红粉白,点缀得婷婷碧叶有了泼墨而出的风韵。池边的岩壁上,蜗牛静静地蠕动,恰若时间放慢的脚步。
记得年少时,自己常常趴在花草丛中,闻着三七、薄荷草的香气,无邪地旁观着这方可以四处长出唐诗的世界。“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残云收夏暑,新雨带秋岚。”父母那时拿出自制的甘草凉粉,一边教我诵读,一边用白瓷小勺细细舀出,一口一口喂我。时光惬意得似乎一辈子都拥有这样的幸福与欢喜。但入学后,这样的日子渐少。白鸟衔起翠枝柳叶远飞天涯,桃花下的马匹一夜之后迷途于江湖,我的好时光彻底被突如其来的高三掐断。放学回家便早早吃完饭,然后躲进近乎密闭的卧室里,对着案几上成堆的教辅看上半天,且翻看着翻看着便开始昏睡。偶尔有剩余时间,自己也懒得出门,僧侣一般临窗独坐。薄暮里,夕阳一点一点斜落,硕大鲜红的身子,像我们不知何时被人摘走的果实。
纽扣经常说,这样下去我们迟早会疯掉的。纽扣是我最爱的朋友,因他的眼睛和小脸一般圆,我便给他取了这外号。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手里的纸飞机已经折好,并被他漂亮地掷出窗外。它承载着少年忧伤与渴望的梦,似乎在天穹下飞了好远好远。“它会飞往天边去看普罗旺斯的花季吗?”我问。纽扣没说话,圆圆的眼睛看了看我,然后把头埋低,低到再也无法返回的时光里。
恍惚间光阴已被碾成一地碎银,当自己试图将它全部捡起的时候,新的时间又撒落了,无尽得像条河流。五一假期简简单单地结束,我又回到了透明的自己。我愈加不习惯在文字、公式、ABCD中游离,那张冷淡、孤独、不安又机械的面孔,我不喜欢。高考的深潭日渐扩大它的容积,而立体的自己悄然间竟被压成了平面。
我不喜欢Mr.林让我们花掉一整节早读课限时做完人手一份的《英语周报》,不喜欢学习委员每天来催促自己上交作业时甩出的眼神,不喜欢不断被延长的晚自习时间,不喜欢黑板左上角的“倒计时”从三位数瘦成两位数,不喜欢老班满怀危机感地宣告高考即刻到来的消息。朝西的天空不再蔚蓝,朝东的门总有匆匆的脚步进进出出。时间以流沙的速度前进,我们拉不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纽扣笑着说:“我们是不是像傻瓜,被人掌控了一切而什么都不知。”我点点头,想起岛崎藤村曾在《银傻瓜》中写道:“世界上,不管哪个地方,总有一两个傻瓜。”小纽扣,什么时候我们竟然这么甘心地变成傻瓜了呢?纽扣又笑了,然后拉着我从教室后门溜出。
那时离高考仅剩二三十天,我们依旧不谙世事,依旧在操场上疯跑,大声地叫喊,依旧从图书馆里借来卡夫卡和卡尔维诺的书籍,在凌晨一两点的台灯下孜孜不倦地读,依旧在晚自习时趁着老班不注意翻墙出校。那时保安大叔常在后面紧追不舍,我们则大汗淋漓地笑着,又拐弯到便利店买来雪碧,当啤酒一样大口大口灌下。很多岁月流淌出的细节生长成繁密的枝丫,排列出好看的形状,悬挂着铃铛一样的花,然后微风穿过了我们的胸膛,温暖的时光镶嵌出水晶般的圆。
高考前的一段时间,每晚睡前必听的一首歌是《最初的梦想》。范范的声音很动听,有一种玻璃光亮似的质感,穿透了夜间的层层雾水后依然清冽。我喜欢这样的时光,它让我感知到自己的存在。白昼里,我们茫然地游弋在光的骗局中,重复的是一天天相同的疲倦与对未知的恐惧。而夜,是从不熄灭的烛火,只燃烧着冷静的黑,让我们思考,把我们和这世界精确地重叠到一起。在音乐对耳鼓密密的低语中,夜亦成了一个耐心的听者,让我们卸下积蓄的泪水与彷徨。寂地在《踮脚张望的时光》里说,荡气回肠,是为了最美的平凡。而我们的梦想也应是荡气回肠的,或许到最后结果只是平凡,但我们已经在实现的过程中为自己真正活过了一回。
雨水扰人的六月,高考伴着入境的台风如约而来。所有的船帆都做好最后靠岸的准备。我亦忘不了那雨声磅礴的两天,白衣少年悲欣交集的哭泣声像朵朵小花连缀成片。
那段时间里,父亲为了陪我,放下那个时节田间繁忙的农事。考试的两天里,他都坚持在凌晨四点起来搭五点去市区的车,晚上又跑到车站去赶末班车。夜色里总会见到他跑得缓慢的背影,在城市路灯下渐渐变成一幅模糊的线描,洇着湿雾,无尽的苍凉压在我的心底,阵阵疼痛。
父亲始终在校门外静静地等我。每考完一科,周边总会有父母着急询问自己子女考试的情况,而父亲在涌动的人流中只保持着一贯的沉默。八号考完最后一科英语的时候,大雨下得更为猛烈,就像人激动或者释然的情绪。我像被掏空内脏一样恍惚地冲出校门,在喧哗的人群里艰难行走,迎面听到有人喊着我幼时的小名——小航。是父亲沙哑的声音。他一只手撑着淡蓝色的雨伞,一只手递来一瓶消暑的花茶。“走的时候,怎么不拿伞?”他问。我笑着说:“嫌麻烦。”父亲摸了一下我的头,执意撑着伞,并不断把伞倾向我。我看了看此时的父亲,头发不知不觉间已经苍白稀疏,曾经透着锋芒的眼神被岁月磨得平淡。那天的雨一直下着,滚落到手心,却是暖的。
那一天,被时间借走的自由、欢喜与爱重回我们的手上。
那一天,大雨没有浇灭花朵恣情吐出的鲜红色彩,那些停靠在花草上的蜻蜓把翅膀扑成闪光的徽章,蝉声清晰而悦耳。
那一天,我们曾经执意要穿越的城池、山峦、河道、海洋、平原和边界,渐渐展开宏伟的地图。
那一天,我们开始真正地长大。
很久以后,我还记得到校领取通知书的时候,纽扣又像往常一样把我从庞大的人流中拉出。我们走到废弃的墙垣边,身旁的蒿草丛中停息着几只粉蝶,摇摇晃晃的树影间它们彼此相拥,像岁月里那道深刻的吻在风中飘动着。纽扣拿出粉笔,在苔草遍布的墙壁上写下一行字:我们的青春,是一阵风,那么快地到来,那么快地消散。
小纽扣,这阵风里有我们最美好的记忆,它们穿过了树梢上稀薄的烟云,让我们看到花开花谢后的圆满。
飘忽的花香中,我们是虔诚的看花人,站在时光的边缘,等着回忆一点一点明亮。
(柳青摘自《美文》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