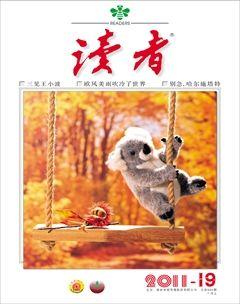高手们
周凌峰
我问过许多实习生,有时间能不能帮我做做校对工作。回答几乎无一例外:这活儿太没技术含量了,想学点更实用的招数,比如选题策划、采访技巧、编辑秘诀等。
这多少让我有些失望。我看过他们编出来的稿件,勉强能达到文通字顺的标准,可是一涉及专有名词,就往往错得离谱——我很奇怪,为什么就没人去翻翻工具书,哪怕使用百度也成啊,这不都是校对的基本功吗?
我想起了我师父,他就是一位校对高手,人送外号“天下第一校”。在遇到他之前,我根本不信校对还能校出花来。前人说得好: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所以,能把错误率降低零点零几个百分点,已经是阿弥陀佛了,要想完全不出错,怎么可能呢?后来,我才领略到他的“恐怖”之处:我的每一封邮件,他几乎都能找出错误来,要么是错别字,要么是分段不够准确,或者标点符号使用不到位。平心而论,我不是个粗心大意的人,可要想不被他抓住小辫子,太难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篇两百字的稿子。两百字,计入标点的话,在Word文档中也就五行而已,可他逼着我修改了不下十遍,从标题到标点,足足磨了四五个小时。
有人看不下去了,劝他:“不就一篇稿子嘛,犯得着这么较真吗?”
他倒是想得通:“不这么磨,怎么提高?”
我差点崩溃。接着,师父又给我下了一个任务:不管写什么稿子,都在两百字内解决。
那段时间,两百字成了我写作的核心标准。一篇评论稿,从引用相关报道,阐述基本事实,直至展开讨论,再加上个人意见,要想“随心所欲不逾矩”,还真不是个轻松活儿。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把能想到的招儿都使上了,就差没用文言文写作了。我的邮箱里留下了一堆以“两百字”为题头的稿件,不消说,很多都是被打回来修改的。慢慢地,我理解了他的良苦用心:这样的约束,能让人在短时间内养成精准使用文字的习惯。
师父只是我见过的众多爱较真的人之一。
我曾经接过一个棘手的活儿,去采访一位“不太好伺候”的著名教授。
有关这位教授的传言很多,先期接触过他的同事告诉我,这位教授有“三不为”:一不参加集体活动,二不接受媒体采访,三不兼行政职务。他甚至连照相都没时间,他们学校网站上的“学人介绍”一栏,挂的还是他十年前工作证上的照片。
好在有热心的师长帮忙,我和教授联系上了。他没有传说中那样难以亲近,只是提了一个要求:“你采访我可以,但不要问那些小儿科的问题。你能不能先读一读我的书?这样交流起来更顺畅一点。”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他研究的领域正是我比较关注的,他的著作我也曾拜读过一些,这不算很为难。可第二天教授将书单发来之后,我还是吓了一跳:这是开给他门下研究生的书目啊!截稿日期一天天临近,我只能抛开手头的工作,窝在图书馆一本一本啃下去,读书之余,还顺手做了些札记,算是意外收获。
结束了这段苦读之后,我把拟出的问题和札记一起发给了教授。教授很快做了答复:所提问题太过宽泛,不易作答,还请再考虑考虑。我做的札记中有一处引文出错,他也做了订正,并特意指出,札记有些模棱两可之处,说明我还没有读懂,应该参看某些著作,接下来,又是一列书单。
我又回到了图书馆,就像卡夫卡《城堡》中的主人公那样。原来的目的已经不重要,我只是想弄明白,要完成这次采访,到底还要经受哪些煎熬。
让我完全没想到的是,最后的采访过程波澜不惊,问题大致还是那些问题,教授很认真地做了答复。我纳闷了:“其实您完全可以在一开始就接受采访,为什么要让我绕上这么大一个圈子?”教授笑了笑:“你如果没有读我的书,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就完全不一样了,又怎么可能和我平等交流呢?”这一瞬间,我几乎有种错位的感觉,好像教授是记者,我才是他精心培养的采访对象。
每逢遭遇困难,我总会回忆一下这些“恐怖”的经历,借此给自己打气。我尊重这些爱较真的人,他们看似偏执,其实只是在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一条再平凡不过的准则:敬业精神。
(常宝军摘自《青年博览》2011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