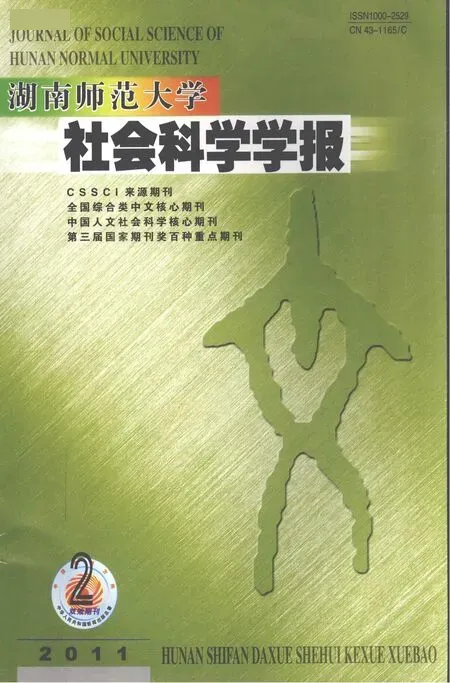“怕”与“畏”的思与诗
——《狂人日记》的海德格尔式思考
吴 康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 沙 4 10081)
“怕”与“畏”的思与诗
——《狂人日记》的海德格尔式思考
吴 康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 沙 4 10081)
海德格尔将此在的生存描述为非本真的与本真的两种样式:前者称为沉沦,沉溺于世;后者则是从沉沦中超脱出来,回归本身,回归最本己的能在。沉沦的现身情态是“怕”,后者的现身情态即是“畏”。畏乃是此在实现其两种存在样式转换的“别具一格”的展开状态。海氏详细论述了畏与怕的种种存在关联,畏于“无”中启示出“有”(此在之本真能在)的复杂情形。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以文学的或诗的书写映证了海德格尔关于怕与畏的思考,小说始于狂人就近生存的莫名的怕,就怕而展开生存之思,思及世人的“吃人”心思,思及一部民族仁义道德遮蔽下的“吃人”历史,思及这部历史残忍的吃人方式。这样就使狂人深陷于“无”的存在境域中了,亦使狂人于无中看到了“有”,看到了本己能在的“真的人”,从而发出他朝向现代的“呐喊”来。这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畏的展开状态。
怕;畏;无;个别化;思;“吃人”;“呐喊”
海德格尔在其思想名作《存在与时间》的前半部分主要探讨“此在的生存论建构”,依此在的日常存在情形展开,分别从“世界之为世界”、“共在”、“此之在”方面进行描述。描述首先展示的是此在实际的被抛境况,海氏说:“寓于上手事物的存在,共他人的存在,都同样源始地属于在世;而在世向来是为它自己之故而存在。但这个自己首先与通常是非本真的,即常人自己。在世总已沉沦。因而可以把此在的平均日常生活规定为沉沦着开展的、被抛地筹划着的在世。”[1](P210)然而,在此标示为“沉沦”的展示中,此在存在的另一情形——最本己的能在本身——尚未得到揭示。海德格尔尝试地探问:“在此在之中有没有一种有所领会的现身情态,可使此在别具一格地对它自己展开了呢?”也就是说,“必须在诸种最广泛最源始的可能性中寻找一种处在此在本身之中的可能开展”[2](P211),从而使海氏所寻求的此在生存论建构从整体上摆到明处。而这种“有所领会的现身情态”、“这种处在此在本身之中的可能开展”就是“畏”,“畏”乃是此在“别具一格”的展开状态。畏作为此在存在的可能性之一,连同在畏中展开的此在本身一道,将为鲜明地把握此在源始存在的整体性提供现象的基地。由此,海氏展开了对“畏”的思考。
一、“畏”作为此在别具一格的展开状态
畏的分析以沉沦为出发点,沉沦意味着:此在消散于常人中,消散于所操劳的“世界”中,所谓“消散”,即此在在它本身面前逃避,在本真的能够自己存在面前逃避。而畏则能够把处于这种“逃避”中的此在本真的能够自己存在、即一种本真的能在彰显出来。
海氏认为,“畏”作为此在的现身情态总与“怕”密不可分,“这两种现象多半总是不分的,是怕的东西被标识为畏,而有畏的性质的东西则称为怕”。[1](P214)那么,怎样对怕和畏作出区分呢?怕被标示为沉沦的现身情态,所谓此在在它本身面前“逃避”即是“基于怕而在怕所开展的东西面前‘退缩’”。海氏论及,怕之所怕总是源于一个世内的、从一定场所来的、在近处临近的、有害的存在者,它具有威胁的性质;而“在怕所开展的东西面前‘退缩’”即是此在在它本身面前退缩。而这并不是说此在从世内存在者那里退向自身,恰恰相反,却是此在要逃到世内存在者那里去,消散沉溺于其中。退缩意味着:此在处于与世内存在者紧密联系的生存情态的怕中,它忘记了自身。
如此看来,怕总牵涉具有威胁性质的世内存在者,而畏却远远超出了这一点,它牵涉于此在的整个在世生存。海氏说:“畏之所畏不是任何世内存在者。因而畏之所畏在本质上不能有任何因缘。凡有害之事都是从一定的角度看来对被威胁者的一种特定的实际能在有害,但畏之所畏者的威胁却没有这种特定的有害之事的性质。畏之所畏是完全不确定的。”“凡是在世界之内上手在手的东西,没有一样充任得了畏之所畏者。在世内被揭示的上手事物和现成事物的因缘整体本身也一样无关紧要。这个整体全盘陷没在自身之中。世界有全无意蕴的性质。”[1](P215)海德格尔在此无非是说,畏之所畏者乃是此在的整体存在状况,并非牵涉于具体的某事某物,其威胁并不具有特定的有害之事的性质。这是畏与怕的区分。
既然“这个整体全盘陷没在自身之中,世界有全无意蕴的性质”,那么,畏的显著特征即是“无”。海氏称畏的“威胁者乃在无何有之乡”,这是畏之所畏的特征。但“无何有之乡”并不意味着虚无,“而是在其中有着一般的场所,有着世界为本质上具有空间性的‘在之中’而展开了的一般状态”。[1](P215-216)这种无之所以并非虚无,乃是因为它贯穿于此在的所有存在境况,贯穿于此在空间性的“在之中”的一般场所和一般状态,它确乎无处不在。故此,海氏说:“它已经在‘此’——然而又在无何有之乡;它这么近,以致它紧压而使人窒息——然而又在无何有之乡。”[1](P216)这些描述无非表明,畏是指向某种整体存在处境的,乡者,处境也;无何有之乡,无一不在那种处境中呈现,然而所呈现的又只是无。“它紧压而使人窒息”,乃是此在于此处境中所深深感受到的这种无处不在的无的紧迫与压力,此在无法脱身与逃遁。因而在这个意义上,畏之所畏就是世界本身,“如果无,也就是说,如果世界本身,把自己提供出来作为畏之所畏者,那么这就等于说:畏之所畏者就是在世本身”。[1](P216)“世界”、“在世本身”都意味着此在的整体存在处境。
然而,在此整体的具有彻底之“无”的性质的畏中却又蕴含着这样的意义:“在畏中,周围世界上手的东西,一般世内存在者,都沉陷了。‘世界’已不能呈现任何东西,他人的共同此在也不能。所以畏剥夺了此在沉沦着从‘世界’以及从公众讲法方面来领会自身的可能性”[1](P217)。“无”虽然意味着此在在其寓世存在中找不到任何有意义的东西,整个世界似乎都沉陷了,它走到了生存的绝境,但这同时就是说,此在处在了一个生存的转折点上,“畏剥夺了此在沉沦着从‘世界’以及从公众讲法方面来领会自身的可能性”,这样就使此在有可能从沉沦于世中解脱出来,不再按“常人”的“公众讲法”来领会自身的可能性,而回归到一种依其自身领会自身的可能性。这就是,畏从“无”中启示出“有”,归属于此在本身能在之“有”:“畏把此在抛回此在所为而畏者处去,即抛回此在的本真的能在世那儿去。畏使此在个别化为其最本己的在世的存在。这种最本己的在世的存在领会着自身,从本质上向各种可能性筹划自身。因此有所畏以其所为而畏者把此在作为可能的存在开展出来,其实就是把此在开展为只能从此在本身方面来作为个别的此在而在其个别化中存在的东西。”[1](P217)这样,畏导致了此在的生存转折,畏把此在拉回到自身,拉回到自身的能自己存在,不再按公众讲法来领会自身,而是按其最本己的能在来领会自身,向各种可能性筹划自身。如此地向自身能在的筹划即是此在的“个别化”,使此在从共在的平均可理解性中凸显出来,从常人中挣脱出来,成为了自己。
海氏认为,这正是此在的自由:“畏在此在中公开出向最本己的能在的存在,也就是说,公开出为了选择与掌握自己本身的自由而需的自由的存在。畏把此在带到它的‘为……’的自由存在之前,带到它的存在的本真状态之前,而这种本真状态乃是此在总已经是的可能性。”[1](P217)自由乃是此在的存在的本真状态,它是从此在的非本真状态中争而后得的,建立在此在个别化的能在中,实现于畏的现身情态中。这样,此在便处于“真”的(或真理的)澄明之境中了。
这即是海氏所描述的畏作为此在基本现身情态的展开状态。现身情态表明“人觉得如何”,而在畏中,人觉得“茫然失其所在”。“茫然失其所在”意味着此在现身于畏中所特有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无与无何有之乡”,海氏又把这种状况称之为“不在家”。海氏在《存在与时间》中曾一再论及,此在的“在之中”是“缘……而居”,“熟悉于……”,常人加固了这种状况,把此在稳固在安定的、不言而喻的平均日常生活的“在家”状况中。但是在这里,畏却使此在从其消散于“世界”的沉沦状态中抽身出来,将此在作为在世的存在个别化了。唯此,此在才会深感于它已陷入了无与无何有之乡的“不在家”状态。“不在家”是对畏之所为畏的另一表述,即深感于整个世界都沉陷了,世界有全无意蕴的性质。
从此,我们就能更清楚地从现象上看到处于沉沦状态中的此在所逃避的是什么了:“不是在世内存在者之前逃避,而恰恰是要逃避到这种存在者那儿去。操劳消失于常人,以便可以在安定的熟悉状态中滞留于世内存在者。”“沉沦地逃入公众意见之在家状态就是在不在家状态之前逃避,也就是在茫然失所之前逃避。这种茫然失所寓于此在中,即寓于被抛而在其存在中交托给了它自己的在世的存在。这种茫然失所经常紧随着此在,而且即使不曾明言却也实际威胁着它日常消失于常人中的状态。”[1](P218)海氏描述的正是怕的生存境况,此在在日常的“在家状态”中,总是常处怕中。但海氏一再强调:畏与怕并非两种并列的生存样式,而应是同一种生存状态的转换,怕中总含有畏,怕亦可转变为畏,同样,畏中亦含有怕,畏亦可回复于怕。一般说来,此在总是首先被抛入沉沦状态的怕中,而后才可能有畏的发生;此在总是先处在安定的“在家”状态中,而后才会深感其“不在家”状态。诚然,怕并不必然转变为畏,此在往往常处怕中,“实际上,茫然失所的情绪即使在生存上也多半仍然未被领会。而且在沉沦与公众意见占主导地位的时候,罕有‘本真的’畏”。“‘本真的’畏”乃是此在少有的罕见的情形,在此意义上,畏是怕的一种生存变式。
但是,我们却绝不能将畏视为一种后起于怕的生存样式,畏作为此在本真能在的现身情态,从一开始就植根于此在生存,因为此在究其实质是朝向能在的生存,“畏作为基本现身情态属于此在在世的建构,这种本质建构作为生存论结构从不现成摆着,而是其本身总存在于实际此在的一种样式中,也就是说,存在于一种现身情态中”[1](P219)。这就是说,在任何此在的实际生存样式中,在任何此在的现身情态中,都具有本真能在的畏。因此,“畏暗中总已规定着在世的存在,所以在世的存在才能够作为操劳现身的寓于‘世界’的存在而害怕”。唯其如此,畏与怕简直不可分离,“怕是沉沦于‘世界’的、非本真的而且其本身对这些都还昧而不明的畏”。海氏强调的是,畏固然是此在所罕有的生存情态,但怕中总含有畏,只是惯常为常人所涣散、所遮蔽罢了。唯此,此在若要走向自己的本真能在,实现个别化的自由,就必须去蔽,回归自身,实现从怕向畏的生存处境的转折,这一转折并非是转向别处,而就是回归到原本的本真能在上来,使自己的本真能在崭露出来。
这就是海德格尔所探讨的“‘畏’作为此在别具一格的展开状态”,在对于怕的超越中,畏造就了此在的个别化,“这种个别化把此在从其沉沦中收取回来并且使此在把本真状态与非本真状态都作为它的存在可能性看清楚了”。“这些基本可能性显现在畏中,一如依其本身显现,毫不假托世内存在者”。[1](P220)
二、《狂人日记》的海德格尔式思考
海德格尔这一番关于怕与畏的哲思确乎使我们感到有些玄乎,难明究底,但我们却可更真切地从鲁迅的文学表述、从近乎诗的表述中得到确证。这就是他震世骇俗的小说创作《狂人日记》。
小说开篇的描写即是从狂人生存感受的“怕”开始的,怕始于狂人的就近生存,始于从世内存在者那里所感受到的威胁。他怕什么?世人古怪的眼光;众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最凶的一个人张牙露齿的笑。这一切使狂人“从头直冷到脚根”。这不是怕吗?而一伙小孩子铁青着脸对他的议论与仇视更使狂人彻骨心寒,因为如此的怕滋生于尚未成人的后代,怕延展至了将来。这样,狂人从周围世界中感到的是世人对他莫名其妙的敌视和难以名状的仇恨,这些使狂人“怕”得“纳罕”、“伤心”。“怕”得“纳罕”且“伤心”亦即非同寻常的怕,这之中便含蕴有“畏”的因素了,即海氏所说的周围世界整个地都沉陷了,世界有全无意蕴的性质。
因此莫名的“怕”,引发了狂人寻根究底的“思”(生存之领会),怕之所怕缘何而生呢?即狂人所谓的“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狂人的思首先指向“他们”——世内存在者,那些给知县打枷过、给绅士掌过嘴、给衙役占了妻子、给债主逼死了老子娘的人们,为什么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他们是被奴役、被压迫的一群,但他们为何不向奴役者、压迫者反抗,而反而仇视狂人呢?狂人从他们古怪的言行中思得:那是因为在他们的心里皆藏着一个“吃人”的心思。他们也有“吃人”的可能:街上的女人打他儿子,眼睛却盯着狂人说:“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家里的人”都装着不认识狂人,把狂人当鸡鸭关起来,准备宰割了吃。狼子村的佃户说,大家打死村里的一个大恶人,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从此种种行径,无不显露出那个“吃人”的心思,他们既是被奴役者,同时也是参与吃人者,他们是“青面獠牙的一伙”。狂人从深寓于怕的思中洞见到了世人的吃人本质:“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2](P424)这原本是一个可怕的吃人的社会。
然而他们的吃人,是真吃吗?确乎不是,所显露的不过是一个吃人的“心思”。这样古怪的“心思”又缘何而生呢?狂人再度深思,从他现今所处的生存进而思及这部民族的生存史:“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狂人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2](P425)这乃是狂人生存之思最伟大的发现,一部书写着“仁义道德”的冠冕堂皇的历史其实质却是罪恶的“吃人”的历史,仁义道德将吃人的历史深深地掩埋或遮蔽起来了。狂人或鲁迅是历史的伟大解蔽者,谎言的揭破者,这正是“他们”成为“青面獠牙的一伙”、心藏“吃人的心思”的历史根源所在。从此也更深层地揭示出狂人起初为何说他“怕得有理”,他为何“怕”得“纳罕”且“伤心”。这里所表述的当然已是“畏”了,狂人无异已置身于畏中,因为“在畏中,周围世界上手的东西,一般世内存在者,都沉陷了。‘世界’已不能呈现任何东西,他人的共同此在也不能。所以畏剥夺了此在沉沦着从‘世界’以及从公众讲法方面来领会自身的可能性”。显然,已经揭破专制社会伦理道德“吃人”本质的狂人,已经无法再像他人那样地沉沦于世,已经无法再按照“公众讲法”(伦理道德)来领会自身的可能性了。世内存在者对他而言皆已沉陷,世界已不再具有任何意义。这即是狂人由怕至畏的转折,狂人的觉醒,他精神的“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正是狂人深寓于思的由“怕”至“畏”的转折揭示出他从“发昏”到“精神分外爽快”的觉醒。
由此,狂人再度深思了仁义道德的“如何”吃人,乃是中国历史生存最奇异的吃人方式:“他们的方法,直捷杀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祸祟。所以大家连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最好是解下腰带,挂在梁上,自己紧紧勒死;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2](P427)。这正是鲁迅称之为“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没有血腥味的吃人。封建统治者与他们所标榜的“圣人”将自己的统治意志言说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伦理规范——礼教制度,然后通过数千年的“教化”灌输到民众中去,在历史的过程中积淀为笼罩一切的社会心理结构,铸成特定的国民人格。这样,民众既为外在的社会伦理所制约,为普遍的社会舆论所谴责(在他们的心里都潜在着一个“吃人的心思”);又为内在的道德人格所戕害,最终只能走向自我摧残的生存境地。小说揭示出仁义道德吃人方式的极度残忍,狂人喻为“只会吃死肉的”鬣狗“海乙那”,它常跟随在狮虎等猛兽之后,吃它们所吃剩的动物的残骸,“连极大的骨头,都细细嚼烂,咽下肚子去,想起来也教人害怕”[2](P427)。如此的怕是朝向整个民族历史-现实生存的,狂人缘何不怕!缘何不怕得有理!
况且,如此的吃人生存贯穿于所有的人群,大哥可以吃他的兄弟——狂人“我”,而我,“也未必无意之中不吃我妹子的几片肉”,“我”也是有“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他如“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2](P429)从此展示出狂人对这部吃人历史的整体否定,同时也显示出寓于此历史中的狂人极度沉重的“怕”。怕并非源于某人某事某物,而是源于全部整个的生存,怕无处不在,也即“世界”、“在世本身”,源于表面“仁义道德”实质上“吃人”生存的有理性。如此的怕当然也即是畏了,畏的“威胁者乃在无何有之乡”,“它已经在‘此’——然而又在无何有之乡;它这么近,以致它紧压而使人窒息——然而又在无何有之乡”。鲁迅所书写的狂人这种刻骨铭心的怕难道不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畏的“紧压而使人窒息”的在世感受吗?难道不正是畏之所具有的“无”的性质吗?“畏之所畏为世界之无”,“我生存于其中的世界向着无意蕴沉降”[1](P390)。无意蕴便是断了与生存世界的联系,陷于无家可归(“不在家”)的状态。这正是狂人当下所处的生存境况,他处于与生存世界的整体对立中,况且这样的存在情形使他无处脱逃,唯有于“怕”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思。
这样,畏同时就标明了此在生存的临界点、转折点,它所面临的并非是“虚无”,而是从“无”中启示出将来的“有”,否则便不能称其为畏了。从无方能到有,这就是另一样生存的可能性——能在:“畏把此在抛回此在所为而畏者处去,即抛回此在的本真的能在世那儿去。畏使此在个别化为其最本己的在世的存在”。“畏在此在中公开出向最本己的能在的存在,也就是说,公开出为了选择与掌握自己本身的自由而需的自由的存在。”畏于无中启示出有,正如狂人的于“怕”的深思中看见了“他”,见到了“真的人”。这样便在狂人面前开敞了一片新的天地,使狂人有了发昏与醒觉的区分,同时亦才有可能使狂人跳出他的此在生存,去反思民族的曾在历史,洞见其“吃人”的奥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对于狂人之“怕”的存在之思的展示即相应于海德格尔对于“畏”的存在论思考,文学之思与哲学之思交融为一。我们可以从此展开诗与思的对话,作为小说的文学之思与作为哲学的存在之思相应而至,狂人的“怕”与海德格尔哲学的“畏”同根而生。这样,一旦当我们于“怕”的存在情形的开敞中去运思时,民族生存的真理就悄然而至了。
唯此,正是基于狂人的怕,从“他”——“真的人”——的发见所到来的不仅是寓于此生存的狂人对曾在历史整体否定的思,而且同时是一部于现今所延展的现代历史的到来。这便是现代启蒙,即鲁迅所谓的“呐喊”,朝向未来能在的“真的人”的呐喊,于当今之畏中呼之欲出。这样便有了狂人深置于“梦”的自我批判,对以“大哥”为首的众人的启蒙的“劝转”,以及荡气回肠地对历史与现实的“吃人”生存的揭露。虽然狂人的呐喊对深度沉沦于世的人们并无丝毫反响,虽然狂人最终仍被冠以“疯子”的名号而重复置于黑暗之中,但他的呼喊仍旧不绝于耳:“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2](P430-431)“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2](P432)
这一旷世的呐喊,源自对狂人就近生存刻骨铭心的“怕”的感受,源自对一个极度昏噩残忍的吃人世界的深刻洞见,因而具有穿透时空的生命力;如此的呐喊,更在于对未来时代的预见,一个异样的现代似乎将从此呐喊声中到来。这无异就是欲“把此在抛回此在所为而畏者处去,即抛回此在的本真的能在世那儿去。畏使此在个别化为其最本己的在世的存在”。“呐喊”“公开出为了选择与掌握自己本身的自由而需的自由的存在”。这正是鲁迅“呐喊”的本义所在:“是故其声出而天下昭苏,力或伟于天物,震入间世,使之瞿然。……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大之觉近矣。”[3](P23-24)毋庸置疑,“呐喊”的目的即在于造就此在的个别化,实现此在个别化的自由,回归其本真的能在。在此,这两位思想大师确实是殊途同归了,归于最本己能在的个别化的自由。
因此,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对狂人的“怕”的生存状况的书写确乎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畏’作为此在别具一格的展开状态”。畏造就了个别化,“这种个别化把此在从其沉沦中收取回来并且使此在把本真状态与非本真状态都作为它的存在可能性看清楚了”;对狂人而言,在深寓于怕的沉思中,他既看清楚了沉沦于仁义道德“吃人”的民族历史的非本真状态的生存,同时也看清楚了朝向“真的人”的最本己能在的本真状态的现代生存。“救救孩子”的呐喊虽然深含绝望之音,但所呼唤的并非仅仅寄希望于后代那样的一种愿望,而是朝向未来“真的人”的呼唤,对最本己能在的呼唤,心对心的呼唤,唤起的并非是古老的幽灵,而是现代新生。然而不幸的是,时至今日,我们却尚未真正听懂,或只是蓄意遮蔽地佯装听懂,漏听了其本真的生存内涵,使我们今日仍深陷“无我”、“无谁”的荒漠生存中。唯此,鲁迅对于“怕”的文学书写又确乎要比海德格尔关于“畏”的哲思更具震撼力,因为他所展示的并非只是此在的一般生存建构,而是处于一个民族历史转折期中的具体此在惊心动魄的生存呼唤,这个具体此在只能被目为“狂人”。
[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M].北京:三联书店,2000.
[2]鲁 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鲁 迅.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Abstract:Heidegger describes“the existence”in the real and unreal styles:the former is called the sink,which means the indulgence in the world;the latter is detached from the sink in it,which means returning to itself and to most of the can own.Appeared sinking modality is“Fear”,the latter coming out modality that is“Reverence”.But this Reverence exists in two styles to achieve its transformation,“unique”in the expanded state.Heidegger discussed in details the association of all the reverence and the fear,and the complex situation that reverence reveals“there”from the“no” (that is,the truth of this can be in) .Diary of a Madman,written by Lu Xun,reflected the Reverence and the Fear of Heidegger’s thinking in literature or poetry writing.The novel begins with the nameless madman living nearby fear,conducts thinks on living under fear,and analyses the“cannibalism”mind of people,the thought and a nation under the Cover of virtue and morality“cannibalism”of history,the thought and history of this cruel way of eating.This allows the madman to be trapped in“no”existence in the realms and also to see this already in the“real people”from“no”,and thus send the modern“Screaming”.This is what Heidegger called the Reverence of the expanded state.
Keywords:fear;reverence;no;individualized;thinking;“cannibalism”;“The Scream”
(责任编校:文 一)
On“Fear”and“Reverence”in the Expression of Philosophizing and Poetry---Diary of a Madman in Heideggerian Thought
WU Ka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I106.2
A
1000-2529(2011)02-0109-04
2010-08-10
湖南省高校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面向‘在’的思与诗:海德格尔与鲁迅的比较研究”(10K037)
吴 康(1954-),男,湖南益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