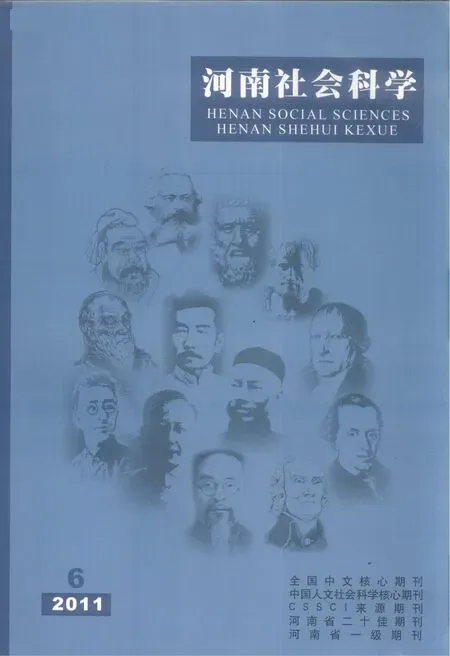互文视域下的文化意象翻译
顾建敏
(河南大学 民生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互文视域下的文化意象翻译
顾建敏
(河南大学 民生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一、文化意象的互文性
文化意象并不是孤立的语言符号,它在本质上具有互文性。根据互文性理论,任何一个文本的构成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这就意味着,文化意象同样是由文化意象的语言符号及其文化所指之间依存联结构成的,是语言符号和文化意义化合而成的结果。文化意象的互文本质揭示了文化意象在特定的文化话语空间中的参与价值,反映了文化意象及其语言符号、知识代码和文化表象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文化意象的互文性源自其存在的文化母体,同一切其他互文关系一样,必须将其置于它所赖以生存的文化母体中予以考察[1]。“互文性”概念的提出者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艺批评家克里斯蒂娃指出,一个文本总会与别的文本发生某种形式的关联,总是处于该民族的哲学、宗教、传统、习俗、传说等所构成的文化体系之中,同时又与世界上别的民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由于所属文化圈的隔膜,互文性的关联往往不为其他文化体系中的人们所熟悉,从而成为翻译中的“超语言因素”,构成理解与交际的障碍。可见,文化母体约束了文化意象的互文性,但文化意象的“互涉”、“互为释义”从广义上讲,不只是存在于语内文本和文化内,由于人类经验的普遍性,文化意象的互文性可扩展至人类文明的母体中,并以其文化特色构成对其他文化母体的吸引和渗透,使文化意象跨越语际文本和文化成为可能。
文化意象由物象和寓意两个部分组成。物象是形成意象的客观事实,是信息意义的载体;寓意则是物象在一定语言文化环境中的引申意义。意象的功能是指在不同的语境中,以具体来表现抽象,以已知或易知来启迪未知或难知。如苏轼在其著名的《前赤壁赋》中用形象的语言写道:“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其中,蜉蝣这种朝生暮死的小昆虫是汉语言读者所熟悉的文化意象,诗人在此用这种独特的意象来比喻人生的短暂和人的渺小,体现了诗人独特的创作风格和高超的艺术水平。由此可知,文本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文字符号,还包含了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语言之外的因素。因此,要把语篇的互文置于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将文化内涵、意识形态和知识结构融入一种互文关系,让译文保持原文风格,再现原文艺术魅力。
二、文化意象的互文性和翻译的关联性
翻译是文化交流的工具,担负着帮助人类沟通思想感情、传播文化知识、促进社会文明的神圣职责。翻译不仅是语言层面的语码转换,更是一种传播文化信息的跨文化转换。从某种程度上说,语言符号的转换只是翻译的表层,而翻译的实质则在于文化信息的传播。因此,要将源语中的文化意象深刻、贴切地传递给译语读者,译者必须洞察英汉语言的文化特征及其差异。要再现互文性文本中蕴涵的民族特色文化,译者既要传达文化意象的信息意图又要传达其交际意图。换句话说,要体现源语文本的互文意义就需要保持源语文化母体的约束作用;而要使译语读者接受源语文化意象,又需要借助译语文化母体的约束机制来弥补翻译中的文化亏损。文化意象的互文性因此成为文化意象翻译的关键。在翻译过程中,文化意象的互文性首先是一种内互文性,对源语文化来说,这种内互文性是开放性的;对译语文化而言,它却是封闭性的。翻译中文化意象互文性的实现在本质上已体现出不同文化间相互影响、借鉴、参照的关系,同时将文化意象互文性对译语文化的封闭性转变为开放性。
依据关联理论,任何言语交际都是以认知关联为基础的,翻译的本质是一个对源语进行阐释的动态的明示—推理过程。关联辖制语篇,语篇服从关联,但语篇给关联提供推理的基础和操作的依据。由于人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环境都是动态的,译者尽可能根据话语的内容去识别源语交际的意图,并把它传达给译语接受者,而译语接受者也在自己动态的语境内对文化意象进行详细的阐释。译者和译语接受者推理时所依据的是最佳关联性,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不可能有严格意义上的对等,翻译的首要目的在于传达原作的意图。译者首要的任务是达到翻译的效度和信度,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接受者的期待相吻合,在保证传达原作意图的前提下,译语语篇应力求在语旨、语义、语形诸方面向原语语篇趋同,使所译的文化意象囊括所有相关的文化内涵。
由于源语文本读者对本国文化的熟悉程度超过对异国文化的了解,在分析和理解源语所代表的文化时,往往受本国文化模式和观念影响,受个人文化素养的限制。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与作者进行着跨越时空的对话,进行着基于源语文本的取舍与再创造的活动,常常经受源语文本多元意义的“磨难”。这一多元的意向性活动在无限庞大的文化意象网络中相互作用,翻译也就得以在众多文本的互相指涉中完成。
三、文化意象互文性与翻译策略
(一)“异化”、“归化”策略
异化与归化是两个相互关联的翻译策略,可以视为传统上所说的直译和意译的概念延伸,但这两组概念又不完全等同。直译和意译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在语言层面来处理形式和意义,而异化和归化则将视野扩展到语言、文化和美学等层面,从而突破了语言因素的局限。韦努蒂认为,归化法是在翻译中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源语文本符合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而异化法则是在翻译中采取民族偏离主义的态度,接受源语文本的文化价值观,把读者带入源语文化情境[3]。因此,异化和归化的核心理念是立足于文化大语境下的价值取向,而不拘泥于语言层面的价值取向。通俗而言,异化法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源语读者习惯的表达方式再现原文本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译入语读者靠拢,采取译入语读者习惯的译语表达方式重构原文本的内容。
(二)跨文化转换策略
文化意象的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而且要密切注视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处理的好坏,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无论在英语中,还是在汉语中,都有不少文化特色浓郁的词语,特别是许多成语、谚语、俚语、方言,文化内涵尤其丰富。翻译这样的词语,应该本着一个总的原则:一方面要尽可能传达源语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又不逾越译入语文化和译入语读者可接受的限度。即从互文角度出发,把翻译的语言转换过程置于源语文本和译入语文本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考虑社会文化互文因素,尤其是意识形态传递的互文等效。译者究竟采取何种翻译策略,这是由译者自身尤其是他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所决定的。具体说来,可采取如下翻译策略:
1.移植
一般说来,带有异域文化特色的表达方式往往都是些形象化语言,保留住原文中的形象化语言就等于为中国读者保留下了了解西方文化的机会。同时,新鲜意象的不断引入,也有利于提高汉文化对异域文化的解释和消化能力。对于英语中文化内涵丰富的词语,凡有可能,应尽量采取保留形象的移植译法。例如:英语成语teachapigtoplayona flute,文化意象近似汉语的“对牛弹琴”,但直译成“教猪吹笛”,就会使中国读者感到耳目一新。不过,由于英汉语言文化的差异,有时候仅仅采用直译法还不能完全达意,还要注意吃透原文的意思,表达时切忌生搬硬套,以免引起歧义。
2.借用
英语中有不少表达方式在意思和形象上同汉语的表达方式非常相近,或非常相似,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借用这些相似或相近的汉语现成表达方式来传译。如:Likefather,likeson——有其父必有其子,Habitis secondnature——习惯成自然。这些英语习语跟后面的汉语习语可谓“形同意同”,将它们拿来互译,可以说是形神兼备,通顺流畅。如果非要采取生搬硬套的移植法,把上述习语译成“父亲什么样,儿子什么样”、“习惯是第二天性”,其结果不是生硬拗口,就是令人费解,远不及借用法来得自然流畅。另外,英汉两种语言中还存在“形异而意同”的表达方式,也可以借用现成的表达方式来互译。例如:haveanaxetogrind——别有用心,Greatmindsthinkalike——英雄所见略同。
3.意译
互文性的文化意象处理关键在于运用意象的语义唤起读者的想象力,使其更能感受到源语文化意象的异域情调。在文化意象的翻译中,译者在受到译语社会文化差异的局限时,不得不舍弃原文的字面意义,以求译文与原文的内容相符和主要语言功能相似的意译法。如:“在农村,特别是比较偏僻落后的农村一些年轻人还不得不忍受包办婚姻的陋习。”译成:“InChina’smoreremoteandbackwardruralareas,someyoungpeoplestillhavetosubjecttocorruptpracticesof forcedmarriages.”原文本中的“包办婚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带有鲜明的历史烙印,对现代西方读者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事物。如果直译成arrangedmarriages,就难以表达出包办婚姻的强迫性和当事人的无奈感,因而造成原文本文化意象的信息损失,阻碍跨文化交流。因此,可以紧扣原文本的精神实质,将“包办婚姻”意译为“forcedmarriages”。
总之,语言的文化意象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浓厚淡薄之别。从本质上说,异域文化包括文化意象的翻译就是使所理解的意义置于一个新的文化语境中被人理解,这种文化意义必然以一种新的方式在新的语言世界中发生作用。这种联想与源语的文化内涵或多或少有某些重叠,但仍然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而译者必须考虑的也正是这种源语的文化精神与译入语文化精神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虽然并不影响译者理解互文性篇章的基本语义,但难以克隆出文化意象的原始意义,即用同等形式完整地再现出文化意象的互文性,因为文化意象赖以生存的母体结构已经改变,译者重构的文化意象只是一种可能近似的再现。
文化意象互文性是一个语篇载入文化和文化载入语篇的互动过程。文化意象翻译将文化意象的封闭性和开放性结合起来,同样是一种互文活动。通过文化意象互文性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那种含而不露的意识形态意义及其文化内涵的关系。在汉英翻译过程中,意象的处理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意象处理是否得当,直接影响到翻译的成功与否。对文化意象的把握能够加深译者对互文本的认识,并改进其翻译策略。无论是直截了当地传递还是曲达其义地改写,这种互文关系都是由译者所操纵,都摆脱不了译者对文本及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互文性的把握。从互文性角度来解读翻译过程中的文化意象必然会给翻译研究带来新的启发,它既能帮助学者更好地认识翻译活动,也能提高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处理文本和文本外因素的能力。
[1]黄念然.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J].外国文学研究,1999,(1):16.
[2]JuliaKristeva.互文性研究[M].邵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3]Venuti,Lawrence.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M].London&NewYork:Routledge,1995.
2011-08-01
顾建敏(1958— ),女,河南范县人,河南大学民生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宋淑芳
(E-mail:hnskssf@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