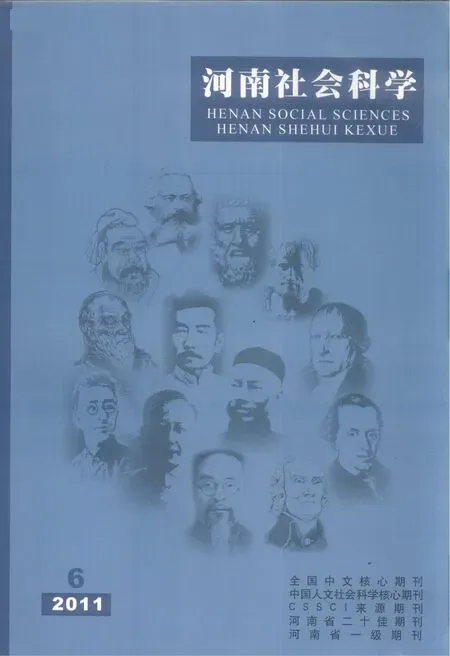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紫色》
吴良红
(淮阴工学院,江苏 淮阴 223002)
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紫色》
吴良红
(淮阴工学院,江苏 淮阴 223002)
艾丽丝·沃克在小说《紫色》中展示了男性与女性、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三个阶段:分裂、缝合和完整。在分裂阶段,自然和女性受到父权制的共同压迫,其压迫的根源是二元制思想。到了缝合阶段,女性开始觉醒、自然开始报复人类,这两种变化最终导致了男性思想的觉悟。这其实是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矛盾缓和并逐渐走向和谐共存的过程。在完整阶段,女性完成从被压迫走向独立的转型、男性开始尊重女性和自然,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即将形成。沃克正是通过揭示黑人妇女和自然在重重压迫下的生存状态来唤醒黑人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探索缝合破碎灵魂以实现完整生存的途径,作品表达了渴望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艾丽丝·沃克;《紫色》;生态女性主义
艾丽丝·沃克(AliceWaiker)是美国当代文坛最富盛名的黑人女作家之一。沃克在其作品中主要关注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下的黑人女性,深入她们的内心世界,展示她们的彷徨、无助、觉醒和反抗,并以此成为黑人女性的代言人。沃克本人也曾说过:“我全部心思都放在了我的人民的精神生存上了。”[1]她的成名作《紫色》一经出版就获得普利策文学图书奖、国家优秀图书奖和全国图书评论奖,并成为美国黑人文学的里程碑。
国外评论家对《紫色》的评介涉及其主题意义、妇女主义思想和文化身份等多个方面。如彼得·普雷斯科特(Peter Prescott)评论《紫色》中的主题包括恐惧、爱的补偿、卑劣的谋杀等许多方面;而贝尔·胡克斯(BellHooks)则认为,对《紫色》的阅读,“超越了种族、阶级、性别和文化的界限”[2]。其他评论家分析了该小说的艺术形式,如叙述策略、书信体格式和语言特征等。自20世纪80年代沃克访问中国以来,国内开始了对其作品的研究,并呈方兴未艾之势。国内评论家对《紫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妇女主义在小说中的体现方面,如王晓英教授认为,沃克妇女主义的灵魂是对人类完整生存的追求。还有一些评论分析了小说中的人物、主题和艺术形式等。总的来说,国内对沃克作品的研究还亟待进一步开发。
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和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迎来了鼎盛时期。生态女性主义分析了生态危机和性别歧视的根源,其核心观点是“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性的关系”[3]。这种关系就是父权制世界观。生态女性主义不仅批判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还批判男性中心主义(androcentrism),其目的是建立一个男女平等、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社会。近年国内外学者都开始注意到沃克作品中的生态思想,但研究还有待深入和系统。本文将《紫色》中男性与女性、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三个阶段——分裂、缝合和完整,认为沃克的作品不仅深入探讨了黑人女性的生存状态,更表达了她对人类和自然和谐共处、完整生存的意愿。
一、分裂——女性与自然:父权社会的牺牲品
(一)女性遭受虐待
生态女性主义先驱厄斯特拉·金认为:“自然被客体化、被征服,成为了与统治者有着本质差异的‘他者’。女性在男权社会等同于自然,同样被客体化、被征服。在这种意义上,女性和自然成了最原始的‘他者’。”[4]生态女性主义者在研究后发现,对女性的剥削和自然的主宰都是西方男性统治的结果,也就是说,女性和自然都是父权制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牺牲品。在《紫色》中,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最初处于分裂状态,女性和自然被看做父权制统治和征服的对象,处在社会的边缘。
小说中的黑人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不仅遭受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还在精神上深受男性中心主义思想的毒害,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甚至包括身份和个性。作为父权制和男性沙文主义的牺牲品,黑人女性在精神上遭到男性中心主义思想的牢牢控制。根据传统的西方文化思想,女性通常被认为是被动、柔弱、劣于男性的。黑人女性的境况更糟,她们一无所有,男性为了牢牢掌控她们的命运,剥夺了她们的各种权利。在《紫色》中,非洲奥林卡的妇女整日在地里劳作,却不拥有家里的财产。没有金钱维持生活,她们只能依靠男性生存。此外,黑人妇女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小说女主人公西莉并非唯一一个早早辍学的黑人女性。在奥林卡,男孩去上学,女孩只能在家做家务。由于男性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他们害怕女性获得这一力量之后会找出男性政权体制后的真相并最终威胁到他们的权威,因此男性想方设法阻止女性接受教育。除此之外,黑人女性没有话语权,处在失语地位。父权权威迫使女性保持沉默,这样男性的罪行才得以隐藏,他们对女性的剥削才得以继续。通过以上手段,男性达到了在思想上掌控女性的目的。因此,小说中的黑人女性相信她们生来就是卑贱的,她们天生就该忍受一切苦难。而这种精神折磨实际上构成了她们最大的不幸。在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压迫之下,她们背负着任何其他人都不愿承担的重负,在父权制下扮演着任劳任怨的“骡子”的角色。她们失去了身份,甚至失去了自我。她们的地位正如伏波娃在《第二性》中所概括的:“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the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subject),是绝对的(the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other)。”[5]不言而喻,女性在男性社会中没有独立的身份,是无法逃脱成为男性玩偶身份的。
(二)自然遭遇的破坏
在西方文化中,自然一向被认为是理应被压迫和被征服的,而自然资源理所当然应该为人类服务。事实上,人类对自然的这种态度可以追溯到圣经。据圣经记载,上帝在创造世界万物时说道:“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土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6]人类陶醉于自己的力量肆意以毁灭自然为代价来发展工业文明,最终导致了世界性的生态危机。生态女性主义者致力于探索这一危机的根源,并得出结论:人类对自然的统治思想根源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沃克在《紫色》中向读者展示了非洲山村奥林卡和其他地方遭受人类蹂躏后的状况。
奥林卡是位于非洲的一个宁静的山村,人们居住的地方“就是有许多树,密密麻麻的树,树中有树,层层叠叠的,而且很高大……还有葡萄树、蕨类植物以及小动物和青蛙等”[7]。在这里,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处、相依相存,生活在和谐与宁静之中。但是白人筑路工人在一夜之间打破了这种和谐,奥林卡成为白人殖民主义者的领地,田地被占用,茅草屋被铲平,大叶树被砍光……白人殖民统治者旨在种植橡胶树取代原有的大叶树林来把这里变成橡胶工业的总部。生态平衡因此被彻底破坏,动物无处可栖,当地人被迫逃离家乡。而白人在现代文明的面纱下,成功地占领了这里的生物,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事实上,奥林卡并不是唯一遭受厄运的地方,当聂蒂和桑莫尔在回英国途中遇到白人女传教士多丽丝·拜因斯时,拜因斯告诉他们,战争的迹象遍布整个非洲和印度,树木被砍伐用来建造船只和制作家具,土地被种上人们无法食用的植物,动物被宰杀供人食用,毛皮被制成衣服,骨头被做成装饰品……
(三)女性与自然的天然联系
生态女性主义者卡伦.J.沃伦认为,对女性的剥削和对自然的压迫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事实上,女性和自然作为生命的赋予者,存在着特殊的象征关系。由于女性与自然之间具有紧密联系,所以她们更容易接近自然、理解自然。在遭遇欺压时,女性往往会走入自然寻求力量和安慰;而在开心时,她们也想引起自然的共鸣。基于这一事实,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构成了她们对抗父权社会和赖以生存的主要策略。
《紫色》中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首先体现在女性与树木的关系上。在许多文化中,树木常被比喻成无私的奉献者。沃克在小说中也强调了这一观点:“我们跟它们(动物们)的联系至少像我们与树木之间的联系一样亲密。”[8]西莉把树木当做一种精神安慰,每当她被殴打时,她会“让自己像木头一样”[7],她会告诉自己:“西莉,你是棵树。”[7]在孤立无援的绝境中,西莉只能希望自己像树木一样,没有思想,没有感情,树木成了她痛苦时最大的安慰。同样,莎格对树木也特别偏爱。对她来说,树木也有感情,应该受到保护。
除了树木以外,奥林卡的茅屋也象征着女性与自然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聂蒂的描述中,“学校的茅屋是方形的……而我的茅屋是圆的,有墙,还有个用屋顶大叶子树叶铺成的圆顶”[7]。众所周知,方形代表着法规和制度,而圆形则是自然、和平和舒适的象征,因此圆形对女性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奥林卡茅屋的主要建造者是女人们,男人只是偶尔帮帮忙,而铺放茅屋顶上的树叶更是女人的专利。奥林卡女性对茅屋的圆形设计和热爱表明了她们对自然的深厚情意。
女性和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还体现在她们共同遭受男性的压迫与统治上。“欧洲世界观的父权主义核心是一种文化恐惧,即害怕自然和女性的创生能力,如果不受文化父权们的管辖,将会是混乱无序的、席卷一切的。”[9]因此,二元制价值观和价值等级思维应运而生,二元制思想把所有的事物分为对立的双方,如男性和女性、人类与自然、思想和身体等。在每一对中,前者优于后者,对后者拥有合法的统治权。毋庸置疑,二元制思想造成了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和自然成为男性统治对象的现状。沃克断定,要结束对女性和自然的压迫与统治,人们必须超越父权社会二元制的概念思想。
二、缝合——人类的觉醒和自然的报复
(一)女性的觉醒
小说中,黑人女性间的姐妹情谊帮助她们逐渐意识到思想解放的必要性,开始了解她们本该知道的事实和拥有的权利,而奴隶制和男性中心主义下的集体生活方式是黑人女性产生姐妹情谊的重要条件。在男性的残暴压迫下,黑人女性往往寻求其他女性的安慰和帮助,姐妹情成为黑人女性反抗残酷剥削和提高觉悟的重要途径,为她们提供了支持和力量。
以西莉为例,最初在遭受精神和肉体折磨之后,她会通过给上帝写信来寻求安慰,上帝在她心目中的形象是:“……又大又老又高,灰色的胡子,身上白白的。他穿着白色服装……”[7]在她看来,上帝高大英明,充满智慧而且善恶分明。因此她把所有的困惑、忧虑甚至秘密都告诉上帝,相信上帝终究会解救苦难中的人们。所以当索菲亚被投进监狱时,她首先幻想上帝的救助。最后在其他女同胞的指点下,西莉最终明白其实上帝根本不存在。可以说,对上帝的正确认识是黑人女性思想解放的第一步。在姐妹情的帮助下,西莉还学会了欣赏自己的女性美,了解到人的基本权利和做真正的自我的必要性,完成了思想的嬗变。在莎格的鼓励下,西莉不再相信自己一无是处,当得知阿尔伯特藏起了聂蒂所有的信件时,一向对丈夫言听计从的她决心离家去孟菲斯市自谋生路。面对阿尔伯特的冷嘲热讽,西莉最终觉悟过来:“我很穷,我黑乎乎的,我也许很丑,又不会烧菜……不过,我还活在这个世上!”[7]这掷地有声的话语正是西莉醒悟后的独立宣言和决心反抗父权制的女性宣言。现在她开始寻求和男性平等的权利而不是男性的怜悯。可以断定,西莉的巨大变化代表了黑人女性思想的巨大进步。
(二)自然的报复
正如苏珊·格里芬所说:“他本该知道他的行为会遭到报应的……我们常说每个行动都会对其本身造成后果,现在报应来了。你砍光了树木,就肯定会发洪水。”[10]大自然从来不受人类愿望和理智的束缚,它有自己的节奏、法则和生命,所有凌驾于自然意志之上的人类努力都是苍白无力的。人类对自然的不断剥削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自然的反抗,小说中奥林卡人不幸成了自然报复的对象。
对奥林卡人来说,大叶树是保护他们的救星。但是为了经济利益,酋长曾一度下令人们砍掉大叶林来种植经济作物。很快,他们遭遇了暴风雨:茅草屋被吹倒,许多人发高烧甚至死亡。在雨停后,他们立刻重新种植大叶树来弥补过失,这次灾难使奥林卡人深刻意识到自然神圣不可侵犯。然而在白人殖民主义者破坏森林的生态系统后,奥林卡人再次遭到了自然的报复。“他们病的病,死的死,比例惊人。”[7]可悲的是奥林卡人要为白人的罪行承担后果。
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环节,人类总是把自己放在统治者的位置上,扮演着剥削者和破坏者的角色,这就最终导致了生态系统的恶化并使之处于崩溃的边缘。人类如果不停止破坏自然的恶行,最终必将会被自然毁灭。
(三)男性的觉悟
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剥夺了男性内在的自由和仁慈,带给他们的只是无爱的婚姻。女性逐渐兴起的反抗和自然的报复促使男性仔细思考整个局势,只有当他们认识到对女性和自然的罪行之后,他们才能抛弃男性至上的思想从而达到自我愈合的目的。沃克在小说中安排男性人物最终改变了对女性和自然的态度从而获得了精神的解放。这一安排也表达了沃克对男性最终觉醒的希望。
首先,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导致男性转变的主要因素。在小说中,西莉离家之后,阿尔伯特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把自己锁在房子里不让任何人进来。西莉的出走促使他下意识地进行沉思,思考过去对西莉的种种暴行、西莉作为女性对他的价值以及西莉走后自己生活的变化。最终他得出结论,女性也拥有自己的尊严,理应被爱和平等地对待。终于,他抛弃了传统的男性中心思想,并且开始尝试一些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所有这些变化都证实他经历了一次重生,成为一个自然人。
其次,真爱也促使了男性思想的觉悟。比起父亲阿尔伯特的变化,哈泼的转变可以说是他与索菲亚之间真爱的结果。起先,哈泼与索菲亚的婚姻生活非常和谐,索菲亚在地里干活,哈泼负责打扫房间、做饭。虽然这种做法违背了传统家庭模式,但他们自己却感觉很惬意。然而迫于外部压力,哈泼也开始设法控制索菲亚。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无效努力之后,他最终放弃了要控制妻子的想法,并且意识到不能控制妻子并不是一种耻辱。哈泼的这一改变使他赢回了索菲亚的爱,最终走向精神的解放。
再次,自然的报复是促使男性转变的导火索。面对生命的威胁和家庭的缺失,男性最终意识到善待女性和自然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男性的发展和成长也是沃克本人偏爱《紫色》的原因之一。
三、完整——走向完整的生存
(一)女性从被动走向独立
身体和精神的自由是一种对自然的反映,这种反映使人们在生态意义上重获自由和创造性。《紫色》中的女性人物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获得了经济独立,继而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成为独立的个体,不再依附于男性,最终从被动走向独立的生活状态。
女权主义者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指出,女性要想做真正的自己,首先要拥有自己的房间,每年有500镑的收入。拥有工作和经济独立对女性来说是获得独立身份的首要一步。小说中的许多女性通过经济独立获得了解放,西莉和玛丽·阿格尼斯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孟菲斯市,西莉偶然发现自己有做衬裤的天赋,于是开了家专做衬裤的裁缝店。对西莉来说,做衬裤本身就是对父权制的一种挑战,因为在父权社会中做衬裤向来是男性的专利。西莉是个天生的设计师,她知道如何把衬裤做得经济漂亮,展示人们的特点。通过开店,西莉显示了自己的艺术天赋,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情感,丰富了物质和精神生活,开始走上一条成为一名完整而独立女性的道路。而玛丽·阿格尼斯在莎格的指引下,不仅学会了作曲,还敢于在众人面前演唱。歌唱一方面成为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另一方面也给了她勇气和自信。终于玛丽通过努力成为一名职业歌手,获得了他人的承认,改变了隐形人的身份,成为一名拥有工作和进取心的新女性。
经济独立还使西莉和玛丽获得了物质解放,她们逐渐品尝到了独立的胜利果实并最终实现了自我价值。她们成功地证实了她们是拥有自我身份、充满自信、不容忽视的女性。
(二)男性尊重女性和自然
小说中的男性在觉醒之后开始尊重女性和自然,主要体现在开始向女性学习,并试图理解女性和自然方面。
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黑人男性发现他们从女性身上学到了许多知识。通过改变对家务活和农活的态度,男性开始尝试做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此外,男性还学会了关心和爱护身边的人。通过亲身劳动体验,男性开始理解劳动的真正含义,并在此基础上理解女性。阿尔伯特学会了缝补这一细节表明他已经抛弃了过去有关女性不如男性、男性比女性更有价值的错误思想。他愿意与女性一起共同劳动。小说中男性的转变还体现在他们对自然的尊重上。西莉走后,阿尔伯特以全新的目光看待自然,开始了内心的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田地里的劳作表明了他开始了更加接近自然的尝试。在自然中劳作使他平静下来,使他有机会思考过去与未来。正是自然帮助他摒弃了男性至上的思想。在旷野中,他感受到了平和的精神的升华。他开始收集象征自然的贝壳,倾听贝壳中海浪的声音使他听到了大自然的天籁之声。他收集贝壳的行为实际上体现了他对自然的尊重。很明显黑人男性的自我改变促进了他们与女性和自然的关系的和谐,完整的生存已指日可待。
(三)理想化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实现
人类与自然共存是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放弃信仰上帝的西莉和聂蒂一起贴近自然并最终治愈了她们的精神伤痛。西莉的最后一封信是写给亲爱的上帝、星星、树林、天空、人们和万物的,可以看出,此时此刻,万物已经融为一体,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黑人和白人之间没有界限,没有歧视,平等共存。奥林卡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对他们来说,大叶树叶是保护他们远离自然灾害的救星。他们在村庄被占领后,选择加入居住在丛林中的“森林人”,拒绝为白人工作或是接受白人的统治。他们走向自然怀抱的举动表明他们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重建。
与此同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小说中男性对女性的尊重无疑促进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此外,白人与黑人之间也开始了合作。在小说的结尾,西莉雇佣了白人在她的店里工作。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白人和黑人开始和平共处,相互合作。在此基础上,男性与女性、白人与黑人之间建构了和谐平等的关系。
综上所述,只要人类学会放弃种族压迫,停止对自然的剥削,抛弃二元制的概念思想,善待自然、地球和整个宇宙,生态女性主义者倡导的理想的和平世界就一定会实现。
四、结语
身为生态女性主义者,沃克从未停止对种族和父权制度下牺牲品的关注,她始终在为一切物种的平等权利而奋斗。她确信,艺术可以拯救人类。小说《紫色》就是一例。在这部作品中,她竭力抨击人类中心主义和父权制思想。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沃克不仅关注黑人女性的痛苦和艰辛,同样也关注黑人男性的疾苦。她的伟大不仅在于她对男性暴力和女性遭受虐待的关注,更在于她坚信压迫者可以被改变,这也是她对父权制的理想。
沃克追求的是男性与女性、黑人与白人以及地球上所有生物之间的和谐共存。她在西莉的书信中表达了这一观点:阻止人变成蛇的唯一办法是接受这一事实,即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孩子,都是妈妈的孩子,不管他长成什么样子,举止如何。虽然小说结尾的幸福结局带有乌托邦色彩,但它却表明沃克对世上万物理想共存状态的渴望,也说明人类仍需数代人的艰辛努力才能使这一和谐社会的梦想得以实现。
所以说,《紫色》不仅仅给读者留下了文学和艺术的震撼,还给读者提供了思考现实的无限空间。由于环境在日益恶化,生态平衡已被打破,各种毁灭性的灾难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物种正在灭绝,人类的生存受到了威胁。此时正是人类停止破坏环境、保护自然的关键时刻,而这一切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必要前提。
[1]JohnO’Breien.“Interview”[A].Gates,HenryLouis,Jr andK.A.Appiah,ed.,AliceWalker:CriticalPerspectives PostandPresent[C].NewYork:Amistad,1993.331.
[2]Hooks,Bell.Writing the subject:Reading The Color Purple[A].HaroldBloom,ed.,AliceWalker,Modern CriticalViews[C].New York:ChelseaHousePublishers,1989.16.
[3]普伦·斯普瑞特耐克.生态女性主义建设性的重点贡献[J].国外社会科学,1997,(6):62—65.
[4]KingYnestra.“TheEcologyofFeminismandFeminism ofEcology”[A].Judith Plant,ed.,HealingtheWounds:The Promise ofEcofeminism[C].San Francisco:New SocietyPublishers,1989.21.
[5]伏波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6]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M].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2003.
[7]艾丽斯·沃克.紫色[M].杨仁敬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
[8]Walker,Alice.TheUniverseRespond-Or,HowILearned We can Have Peace on Earth[A].David Landis Barnhill,ed.,AtHomeontheEarth:BecomingNativeto our Place-A MulticuralAnthology[C].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9.301.
[9]查伦·斯普瑞特耐克.生态女性主义哲学中的彻底的非二元论[A].法尔克,等.冲突与解构:当代西方学术术语[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64.
[10]Griffin,Susan.WomanandNautre[M].SanFrancisco:HarperandRow,1978.
I106
A
1007-905X(2011)06-0162-04
2011-08-10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项目立项课题成果(2010SJD750017)作者简介:吴良红(1973— ),女,江苏宿迁人,淮阴工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责任编辑 姚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