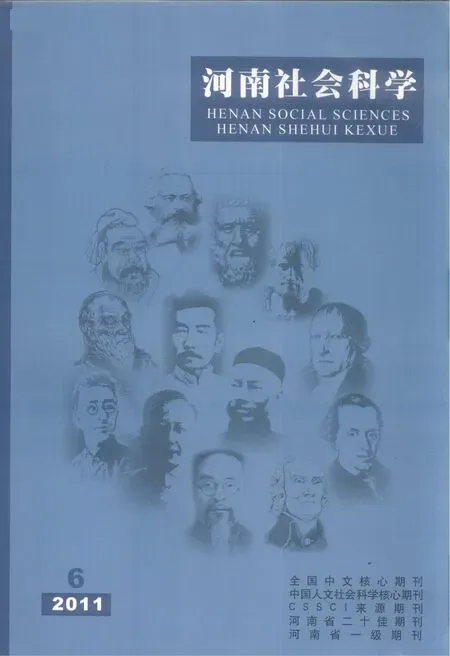1912—1937年间华北的贫民教育援助政策研究
赵宝爱
(济南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1912—1937年间华北的贫民教育援助政策研究
赵宝爱
(济南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教育援助政策。各界积极兴办慈善学校以救济贫寒失学的儿童,或捐助资产,或为慈善学校提供运转资金;面向贫民以及所收养的贫民等开展职业教育,实施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谋生的能力;设立奖学金和贷学金等以鼓励贫寒学生的升学深造,促进社会公平和造就国家建设人才。
民国;华北;慈善;教育
民国时期,社会救济理念日渐积极,教育援助风气大兴,诸如儿童的就学、青年人的深造以及成年人的学习和技能训练等都纳入了救济的范畴。1912—1937年间华北的教育援助政策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慈善学校的创办、职业培训以及清寒学生的深造资助等层面。本文拟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就这一时期的教育援助问题略加探讨[1]。
一、贫儿就学的满足
创办慈善学校、满足贫寒家庭子女的求学需求历来是民间善举之一,到民国时期,慈善学校的发展表现为数量显著增加、运作模式比较新颖以及经费来源渠道相对多元等。
(一)积极兴办慈善学校
明清时期,华北几乎各州县都设有私立或官办的“造就贫寒子弟”的义学,如山东德县,在清代屡屡奉文“以公款设学教授贫民子弟”[2]。相对于庞大的城乡少年儿童来说,义学在满足多数贫民子弟的教育需求方面更多的是象征性和点缀性的。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后,愈来愈多的社会团体和民间人士本着“救人救彻”、教养兼施的思想从事贫民子女的教育援助活动。一是宗教慈善机构把教育纳入救济的范围。道院组织(与世界红万字会属同一系统)认为教育“为立国之大本”,故在免费教育贫民子女方面可谓不遗余力。1933年,世界红万字会掖县分会成立后随即附设了平民小学,招收60名清寒子弟入校学习,“不收学费”且免费供给笔墨书籍和体育服装等[3]。二是公共机构在慈善学校的创办中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1921年10月,河北清苑县警察机关在原四处贫民半日学校的基础上,改组设立了两处小学,其中每校附设一初级班,“救济贫寒失学儿童”,非但不收学费,且还免费供给文具和书籍等[4]。三是部分营利机构也成为慈善性学校的主体。如青岛华丰纱厂既坚持“以营利为目的”,也主张义利兼顾,兴办子弟学校[5]。四是宗族和社区仍是慈善学校的兴办主体。民初不少宗族仍延续了兴办学校、教养本族子弟的传统。山西永济县黄旗营村的周氏家族集资举办了“周氏义学”,专门来教育本族的子弟[6]。
(二)创新学校教育模式,减少贫民子女的就学困难
各界还积极探索慈善学校的运作模式,以求尽力兼顾不同贫苦儿童的谋生和就学需要。一是针对贫寒家庭子女平日多“帮助家庭力作”的实际情况,创设贫儿半日学校和露天学校等非全日制学校,灵活安排授课时间,以解决贫儿学习和劳作的矛盾,其中北京地区这类学校较为可观。1916年,京师警察厅在京城创办了60余所“贫儿半日学校”,以“补助学校教育,救济失学儿童”,儿童每天学习3小时,其中可资造就者则送入公立学校继续深造[7]。除此之外,青年会等社会服务团体也在京城各地创办了一些露天学校。二是慈善救济机构附设给学校。近代民间慈善组织往往兼顾教养并举的救济原则,以“养成健全良善之国民”,如北平私立龙泉孤儿院附设有教务部(初级小学一至四年级),对院内所养孤儿及院外平民儿童等施以“国民基础教育”[8]。三是设立临时性的慈善学校,救济灾童等。1920年北五省旱灾期间,清华大学在河北唐县山南庄设立灾童学校,招收周围6个村的70余名灾童在此学习及做游戏等,使灾童学校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乡村小学[9]。
(三)学校经费来源多元化
慈善学校多不收学费甚而免费供给学生一些学习用品等,这固然降低了贫苦家庭儿童求学的成本,但筹集经费、维持学校运转成为办学者必须面对的首要难题。一是慈善机构的赞助。济南道院小学免费接收学生实施教育,其经费均由该院拨付,1923年学校运转经费1075元均来自于该院的资助[10]。1924年,河北晋县人曹自琢捐地60亩、价值洋2200余元,以所收地租作为东周头村曹氏义学办公经费[11]。二是政府及民间的资助。慈善学校虽主要由民间人士和机构所办,但同样需要官方的一些补助,如香山慈幼院自设立之日起就获得了中央政府的经费补助,北平私立龙泉孤儿院小学校每月获得北宁铁路局补助20元[8]。社会捐助则是学校资金的重要来源,1887年西方传教士在北京所设立的启明瞽目学校(1921年改名为启明瞽目院),其年经费5000余元均来自于社会各界的捐助[12]。三是设立专门的教育基金。鉴于很多学校缺乏生息资产,学校经费困难,1932年,熊希龄乃捐洋26万余元、银6万余两,在北平设立“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以息金来资助部分学校的运作[13]。
不过,多数慈善学校既无基金也无可供出租的田产、房产等,为缓解经费压力,只好采取开源与节流并举的措施,如呼吁社会捐助和政府补助,借用乃至不用校舍、动员教师和青年学生参与义务教学活动等,但仍经费匮乏,维持数年即宣告解散者为数不少。
二、职业技能的训练
这一时期,社会各界还把援助延伸向了职业教育领域,以提高广大平民和贫民的知识道德素养,培养其职业技能,最终实现发展社会经济、改善民众生活、造就合格的国民和公民的宏大目标。
(一)提高贫民的职业技能
清末民初,民众生活艰难,游民渐多,各界逐渐意识到,贫民生活全赖职业,贫民技艺培训“亦为国计民生之本”。其一,设立贫民工厂,借助工厂的形式对贫民实施职业技能训练。近代贫民工厂不在于营利,而是工读合一的技能培训机构,即寓习艺于生产,属于慈善和救济的一种。如河南夏邑县就把发展工艺和家庭副业等列为改善民生之“急务”,积极筹设贫民工厂,生产日常用品,招收贫民入厂习艺[14]。其二,对院内收养贫民施以“适当之职业教育”。清末以降,愈来愈多的救济机构把开展职业技能训练列入了救济的范围。天津妇女救济院就曾设立了刺绣、缝纫、理发等班,聘请专职教师向所收养妇女传授技艺,使其习得一技之长,出院后能够独立生活或谋生等[15]。其三,院内收养儿童的职业技能培训。孤儿和灾童历来是社会的弱者和救济的对象,民国时期的诸多慈善机构出于“造就健全国民”以及成年后“服务社会之能力”的考虑,除了文化传授和职业训练外,也注重正确道德观念的培育,出院后“不致流为废人”。如香山慈幼院既注重职业技能训练,又灌输正确的职业观念,使其能够深刻体悟“好好读书,好好劳动,好好图自立”的道理,并能够自立于社会、造福于社会[16]。该院坚持以近代工艺来训练生徒,倡导农业本位的职业思想,附设了各种农场,让学生定期前往实习等。
(二)训练专门职业人才
一些慈善机构开始探索把扶助对象的谋生和职业的社会需求结合起来,以提高救助的针对性,真正实现从“治标”到“治本”的转型,其中香山慈幼院无疑最为成功。该院除了向儿童传授基本知识和生活技能外,还试图培育较高层次的女性职业技术人才,提高女性的职业竞争力。1922年创设了女校师范部,对本院女子等实施师范教育,既可以满足社会的师资需求,又可扩大本院女生的出路。从1923年到1933年间,该院毕业生290余人,其中多数在基础教育领域从事服务工作[16]。另外,设立保妇养成班,培养慈幼专门人才。长期以来,各慈善机构等所雇乳母等均未受过何种专业训练,缺乏科学的保育知识,其照看婴幼儿不过是基于一种女性和母亲的本能。设立保姆看护妇训练所,从小处言之,关系到婴儿的健康成长问题;大而言之,则关系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前途。为此,该院招收寡居、离异或年龄稍大的未婚女子等入院学习儿童卫生、保育等专业知识,并开设婴儿教保园来提高其实际技能。经过一年的训练和实习后,她们或进入上海、济南和青岛等城市的托儿所充当保育员,或到一些富人家庭做高级保姆等[17]。
当前主流手机浏览器均支持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具备访问WWW站点的功能。系统以当前流行的移动互联网手机作为设计标准,设计与普通PC端一样的WWW服务站点。
三、勤苦学生升学的资助
民国时期,学历文凭成为获得某些公共职位的基本条件,资助贫寒青年深造就成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改变底层子女命运的重要途径。
(一)设立清苦奖学金
相对而言,中等和高等教育成本高,中产家庭尚不堪重负,贫寒家庭更是无力负担,其子女被迫放弃深造的机会,即使幸运入学也可能面临着被迫中途退学的无奈。为解决清寒学子的生活和学习困难,南京政府在1931年的《中国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就曾规定,各校要设奖金学“以奖进品学俱优、无力升学之学生”。1929年,山东省教育厅就把设立免费学额和奖学金制度列入教育行政规划之内。1931年,河南省教育厅出台了《省立师范学校及高中师范科优秀贫寒学生奖学金规程》和《河南省立中等学校贫寒学生免费及奖学金规程》等文件,分别按照甲、乙两类标准发放奖学金以奖励清寒学生;1935年,《河南省立中等学校贫寒优良学生奖学金规程》规定对豫籍初级、高级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中品学兼优的贫寒学生,分别按甲、乙、丙三等标准给予奖学金[18]。此外,一些慈善机构和民间人士等也设置了奖学金,鼓励清寒学子深造。1924年,河北榆次县公民杨润霖独自捐款4000元,发商生息,将息金作为全县贫寒大学生补助之费[19]。1933年,香山慈幼院为鼓励本院学生继续深造,拟定了中学和大学升学奖学金章程,凡升入初中、高中和大学的学生,每年每名分别给予奖学金180元、220元、240元[16]。
总的来说,多数奖学金政策特别强调了申请者的贫寒和优秀两个基本条件,但若操作起来就会发现,贫寒标准实际上比较模糊,且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有关机构很难判断学生申请资料的真实性。在学生看来,奖学金其实偏重于成绩,为获得奖学金,满足虚荣心,选课时难免倾向于选择那些容易通过且获得高分的课程。而且,不管家庭是否贫寒,只要学习成绩符合条件,有的学生就会积极争取,以至于真正清寒笃学之士反不能从中受益。
(二)实施清寒学子贷学金政策
贷学金是公共教育机关及社会团体等为救济升学的贫寒学生而提供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一种制度。这一时期,华北地区的贷金来源渠道有三个:其一是教育管理机构的列支。民国时期,各级地方政府也创设贷学金资助本地清寒学子的深造,如河北省各县专门设立了贷学基金委员会来办理学生的贷金问题,山东则规定原春秋祀孔祭品费改充贫苦学生升学贷费之用。1930年,河南省教育厅为扶植本省“优秀贫寒生进学起见,特设助学贷金”,决定每年筹集贷金经费2万元,1936年度,该省曾列支国内大学贷金16300元[20]。其二是民间慈善组织所筹集。1926年,香山慈幼院担保向香山农工银行借款4574元,贷给院内外学生升入大学者,至1935年,受助学生达107人之多[16]。其三是学校、师生的捐助。1927年,山东六中及该校毕业生为资助“优秀寒俊学生求学起见”乃捐助基金设立了“山东六中同学助学会”,贷给本校升入大学学生[21]。
应该说,贷学金兼顾了教育资助中的公正和效率目标,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问题。一是各地贷金数额差距过大。“视经费之多寡和环境之需要”是各地贷金数额确定的原则,但各省乃至同一省内各县份间的贷金数额差距还是非常显著的,如山西贷学金来自于省政府,生均所贷额度较高,如1920—1928年间留学金陵大学、协和医学院者每学年可贷280元[22];山东贷学经费由各县筹集,生均所贷额较低,但受益人数多,如济宁县规定大学生每人每学年仅能贷50元,名额为8人[21]。二是公平性问题。考虑到求学成本的不同,各地贷学金发放标准常常有省外与省内学校之别,有的地方规定只有国立和省立大学的学生才有资格申请,就读于私立大学者则被排除在外。三是贷学金名额问题。各地贷金总额有限,难以做到应贷尽贷,只有出现缺额时,才能依次递补。如,河南省教育厅规定本金每收回满200元才能增加贷金生1名,造成了候补者过多的局面[20]。四是贷费偿还问题。为保障学生毕业后能够分年偿还贷金本息,多数贷金机构既规定申请贷金要选定本地殷实铺保等,也兼顾了其偿还能力。如山西省规定,贷金生应自毕业第一年起,在7年内偿清,但到1929年,尚有部分学生未按时归还1920年的贷款,影响了贷学金的循环使用[22]。
四、结论
综上,到1937年,华北各省市均逐步建立了贫民教育救助体系,受益人数增加,且援助的主体、形式和内容都较为丰富。
首先,教育援助主体和目标呈现出多元化的结构特点。且不说社会“有力者”或出资或筹资从事教育援助行动,就是青年学生等也以志愿服务的形式参与其中。正是因各界的普遍参与,教育不再是一种培养少数精英的活动,而是愈来愈大众化和平民化,贫苦家庭的子女等受教育的机会大增。教育不再是实施社会教化的载体以及培养顺民的工具,而是使贫民及其子女能够适应团体生活、摆脱奴性、提升尊严,成为合格的国民。
其次,教育援助形式表现出多样性和开放性。在定位上,各界既坚持了教育援助的福利性、平民性和精英化,也不断地探索和创新教育援助的形式,针对不同阶段、不同受教育群体的实际状况来开展救济活动,力图更加贴近贫民阶层的实际生活和需要,把免费、半收费以及贷款等结合起来,以便让更多的贫民及其子女等获益。在义务教育阶段,教学组织形式十分灵活,既有全日制的慈善学校,又有半日学校、露天学校、短期学校等;在职业教育方面,既借助了学校形式来教授知识,又借助慈善机构和贫民工厂等传授生产和谋生技能。
再次,教育援助内容的丰富性和时代性。传统的义学在教学内容上以儒学为主,主要是传授一些文化知识。民国时期,教育援助不仅在于创办慈善学校,满足儿童的知识学习、陶冶情操及强身健体等需要,而且更侧重于职业和生存能力的培养。民国时期,中国的工业经济现代化有了初步的发展,工业化和技术变迁等对普通劳动力的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产技术、劳动技能及生活技能等从民间言传身教到正式教育体系中,教育救济也逐步向职业培训领域延伸,贴近民众的实际生活和社会需要,从而把“教使自养”提高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总之,民国华北的贫民教育援助活动已扩展到教育的各个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华北教育资源短缺的状况,保障了贫民及其子女的受教育机会,提高了谋生和自立的能力,促进了贫民子女的向上流动和社会的公平,有助于提高国民素质、造就社会人才,同时也拓展了社会救济的视野,丰富了社会救济的内涵。
[1]赵宝爱.略论近代山东的慈善教育事业[J].济南大学学报,2010,(5):44—48.
[2]李树德,等.德县志[Z].1935.
[3]刘国斌,等.四续掖县志[Z].1935.
[4]金良骥,等.清苑县志[Z].1934.
[5]青岛华丰纱厂特刊[Z].1937.
[6]永济县志编纂委员会.永济县志[Z].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7]朱有谳.中国近代学制资料·第三辑下册[Z].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8]私立龙泉孤儿院小学校[J].时代教育.1933,1(6):162.
[9]附录:唐县清华灾童学校[J].清华周刊.1921,(218):37—39.
[10]济南道院小学校十二年度简明报告书[J].道德杂志,1923,3(4):9.
[11]专载:河北省捐资兴学褒奖一览表[J].河北省政府公报,1934,(23-24):41.
[12]启明瞽目院[J].时代教育.1933,1(6):160—161.
[13]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史料[A].陈乐人.北京档案史料[C].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68—86.
[14]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五四前后的河南社会[Z].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15]宋蕴璞.天津志略[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
[16]北京市立新学校,北京香山慈幼院校友会.北京香山慈幼院院史[M].1993.
[17]关瑞梧.解放前的北京香山慈幼院[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55—165.
[18]本省规程[J].河南省政府公报,1935-01-22,(1233):2.
[19]国立北平大学关于河北蓟密滦榆两区贷学金问题与医学院、法商学院等来往函[Z].北京市档案馆,J24-1-161.
[20]河南省教育厅河南教育年鉴编辑委员会.十九年度河南教育年鉴(上编)[M].1931.
[21]山东省济宁县教育局贫苦学生升学贷费简章[Z].北京市档案馆,J29-3-363.
[22]本省法令[J].山西教育公报,1929,(286):16—19.
K26
A
1007-905X(2011)06-0142-03
2011-08-2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08JA770018);济南大学学科方向团队项目;山东省高等学校国内访问学者项目
赵宝爱(1967— ),男,山东东平人,济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访问学者,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史研究。
责任编辑 宋淑芳
(E-mail:hnskssf@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