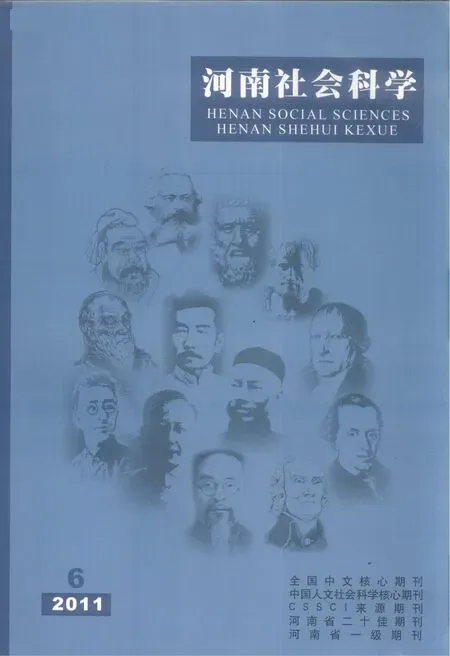论当代中国辩证逻辑研究的历史发展
张建军
(南京大学 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93)
论当代中国辩证逻辑研究的历史发展
张建军
(南京大学 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93)
辩证逻辑研究是我国当代逻辑学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在该学科的学科属性及一系列基本问题上仍存在着广泛的争论,并形成了诸多不同学派与研究进路。系统总结我国辩证逻辑研究的历史发展,在当前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文革”前的辩证逻辑研究基本上限于苏联学界所设定的“问题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辩证逻辑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两方面都获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七大主要研究进路,即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比较研究进路、范畴理论研究进路、科学方法论研究进路、非经典逻辑研究进路、现代逻辑与逻辑哲学新成果的辩证审视进路、应用研究进路、思想史研究进路。但与演绎逻辑及归纳逻辑相比,当代辩证逻辑研究尚未获得成熟形态,一些基本问题尚待进一步探索与澄清。辩证逻辑的发展既要鼓励各种研究路径的“百花齐放”,又要提倡路径之间的深度互动与争鸣;同时,应进一步拓展国际交流的广度与深度。在“问题导向”的多学科、多视角合力攻关研究已成为学术研究主旋律的时代,加强跨学科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发挥各种研究路径的解题功能,是当代辩证逻辑研究的生命力之所在。
当代中国逻辑史;辩证逻辑研究;问题域;研究进路
辩证逻辑研究是我国当代逻辑学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与辩证哲学研究具有十分密切的关联,辩证逻辑研究在我国一般哲学研究、科学哲学与科学方法论等研究领域也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进展,同时,在该学科的学科属性及一系列基本问题上也存在着广泛的争论,形成了诸多不同学派与研究进路。自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复杂性演化科学的长足发展和解决逻辑科学一系列前沿难题的现实需求的推动,国际逻辑学界的相关研究也获得了新的重要进展,这不仅体现于欧陆学界辩证逻辑研究传统的新的演进,而且体现于英语世界辩证法与辩证逻辑研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复兴。因而,系统总结我国辩证逻辑研究的历史发展,在当前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本文拟在简要考察辩证逻辑研究的历史背景和“文革”以前我国辩证逻辑研究状况的基础上,对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辩证逻辑研究的主要进路给予系统考察与评述,以期推动相关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
一、辩证逻辑研究的历史背景
众所周知,自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我国的逻辑学研究受到苏联学界的深刻影响,辩证逻辑研究更是如此。因此,评述当代中国辩证逻辑研究,需先做一些历史背景说明。
当代辩证逻辑研究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哲学密切相关,但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公开发表的著作中,并没有使用“辩证逻辑”这一术语。关于辩证逻辑的研究对象,经常被征引的是恩格斯在其哲学名著中的如下两段著名论断:
“在以往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①
“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②
比较这两个论断不难看出:第一,与黑格尔《逻辑学》不同,恩格斯这里使用的作为学科名称的“逻辑”一词,仍指“形式逻辑”。第二,恩格斯这里使用的“辩证法”概念不是指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辩证法(他和马克思认为那已经是广义“实证科学”的研究对象,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实践的那样),而是与“形式逻辑”相并列的“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关于思维过程及其规律的学说”,不过不是作为实验心理学意义上的关于思维的经验科学,而是作为“纯粹思想领域”的“辩证法”学说,因而后人将这样的学说称为“辩证逻辑”,亦属顺理成章之举。但需要强调指出的一个文本事实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公开发表的文字中,除了引用和指谓黑格尔的《逻辑学》之外,他们所使用的“逻辑(学)”一词都是明确指谓“形式逻辑”的。这是他们与黑格尔的一种自觉区分。马克思与恩格斯从没有否认形式逻辑在人类理性思维中的作用,在自己研究与论证实践中也熟练地加以运用。这一点还体现在他们对归纳与演绎在理性思维中的互补作用的辩证把握上。恩格斯曾就此强调:“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③正确把握演绎与归纳的关系,也是正确理解它们与辩证逻辑之相互作用的一个关节点。而“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这个要求不但适用于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当然也适用于辩证逻辑。不过,结合他们自己的成功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更为强调的是对祛除黑格尔神秘色彩之后的“辩证法”的把握之必要性与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后来的列宁都曾提出了在黑格尔工作的基础上建构科学形态的辩证逻辑的任务,但他们只是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指导思想,并没有真正实现这项工作。须知,马、恩、列视域中的“形式逻辑”只是传统形式逻辑,加之受黑格尔在“绝对理念”统摄下贬低形式逻辑思想的影响,他们并未考虑到形式逻辑被赋予新的生命而获得长足发展的可能,也没有注意阐明形式逻辑与所谓“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严格区分。这一点不应苛求于先贤。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哲学背景之一,黑格尔哲学的“反形式逻辑外貌”,在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使得辩证法和辩证逻辑研究与现代逻辑发展长期脱节(直到近年才有所改观),极大地限制了辩证逻辑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发挥。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巨大遗憾。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未公开发表的手稿文本中,迄今只发现一处使用了“辩证逻辑”这一术语(这也是历史上“辩证逻辑”这一术语的首次使用),即:
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不像后者满足于把各种思维运动形式,即各种不同的判断和推理的形式列举出来和毫无关联地排列起来。相反地,辩证逻辑由此及彼地推出这些形式,不把它们互相平列起来,而使它们互相隶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④
这段文字来自《自然辩证法》手稿中一段札记。从上下文可以看出,恩格斯这里说形式逻辑把判断和推理的形式“毫无关联地排列起来”,并不是指形式逻辑没有自己的理论系统,而是指形式逻辑并没有使用“流动范畴”考察判断与推理的“辩证关联”。他用“摩擦是热的一个源泉”、“一切机械运动都能借摩擦转化为热”、“在每一情况的特定条件下,任何一种运动形式都能够而且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转变为其他任何运动形式”这三个判断为例,用“个别”、“特殊”与“普遍”的辩证范畴理论说明三者之间的“辩证”关联。这种辩证分析,当然与运用形式逻辑工具的演绎与归纳分析居于不同层面,但毋庸置疑的是,演绎与归纳分析提供了这种辩证分析的前提条件。
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苏联学界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反形式逻辑”思潮,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相互拒斥的思想成为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主流思潮,《自然辩证法》(于20年代末被编辑出版)中的上述论述被看做是马克思、恩格斯拒斥形式逻辑的根据,而他们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对相反观点的明确宣示与说明却遭到了冷遇。直到40年代末期,“形式逻辑”才获得艰难的“平反”,但作为现代形式逻辑的数理逻辑仍然被批判,这种局面在苏联直到60年代才得到根本改观。历史的不幸在于,唯物辩证法与辩证逻辑恰恰是在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较大规模地从苏联传入我国的,其所携带的“彻底地反形式逻辑”的外貌,对我国逻辑学和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负面作用,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历史背景。
通过“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之关系”的讨论,苏联学界在辩证逻辑的研究对象与基本性质上逐步形成了三大学派的观点:1.科学形态的辩证逻辑就是唯物辩证法本身,只不过要更加凸显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思维方式与思维方法的一面;2.辩证逻辑是关于思维辩证法的学说,与自然辩证法及历史—社会辩证法相并列;3.辩证逻辑是关于辩证思维规律、形式与方法的学说。在辩证逻辑的学科性质上,也形成了是哲学不是逻辑、是逻辑不是哲学、既是哲学又是逻辑三种不同观点的交锋,从而与当时关于“数理逻辑”的学科性质的三种观点(是数学不是逻辑、是逻辑不是数学、既是逻辑又是数学)的争论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同时,各学派也在努力建构辩证逻辑学科体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二、“文革”前辩证逻辑研究概况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我国的辩证逻辑研究与讨论基本上限于苏联学界所设定的“问题域”。其中,苏联的几部代表性著作,在我国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有些著作被相继翻译出版。影响较大的有罗森塔尔著《辩证逻辑原理》(马兵、马玉珂等译,1962)、阿里克塞也夫著《思维形式的辩证法》(马兵译,1961)、柯普宁著《作为逻辑的辩证法》(郑杭生等译,1965)。苏联以及东欧学界的一些相关研究论文也被大量翻译发表。我国学界关于辩证逻辑的讨论也在此基础上相应展开,其中,《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辩证法、逻辑与认识论的统一》(1959)、且大有编《辩证逻辑参考资料》(两卷本,1959)等,在讨论中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
与苏联学界相应,这一时期我国学界关于辩证逻辑的研究对象与学科性质的讨论也大致分为三个学派:一是认为辩证逻辑就是唯物辩证法,或者说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方面。这构成当时我国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并写入了艾思奇、李达、孙叔平等编写的哲学原理教材,在逻辑学界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有李志才、杜岫石等;二是认为辩证逻辑的对象就是思维辩证法或者思维形式的辩证法学说,这是上列三本苏联辩证逻辑著作的观点,展开来说,就是罗森塔尔所述“辩证逻辑是运用辩证方法去研究思维和认识,是这一方法的一般原则在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领域中的具体化”、“辩证逻辑的主要任务,是要指出如何才能在概念、范畴、判断、推理等等的逻辑中表现客观存在的运动”⑤,这种观点,也成为当时我国学界大多数辩证逻辑研究者的主流观点;三是认为辩证逻辑就是关于辩证思维的规律、形式与方法的科学,其代表有江天骥、且大有、章沛等,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又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辩证思维形式是与形式逻辑研究对象迥异的“辩证概念”、“辩证判断”、“辩证推理”,另一派则与前两派一样反对这样的观点,而主张辩证思维形式是对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的辩证把握的逻辑刻画。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存在上述学派分野,但各派都十分重视“辩证思维方法”的研究,就“归纳与演绎相统一”、“分析与综合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特别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展开了富有新意与启发价值的深入研讨,并遵循柯普宁著作的范例,开启了辩证逻辑研究的科学方法论维度的系统探索。
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辩证法)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学界“逻辑大讨论”的首要问题,并贯穿讨论的始终。经过长期论证,基本澄清了“形式逻辑”在科学思维中的基础地位及其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差异,但由于讨论的参加者大多尚未掌握作为现代形式逻辑的数理逻辑工具,讨论的水平受到了限制,这表现在用“初等逻辑”与“高等逻辑”来把握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仍构成当时多数讨论参加者的主导观念上。
周礼全是讨论参加者中少数具有深厚的现代逻辑与分析哲学背景的学者之一。他以一个逻辑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与敏锐的洞察力认识到:苏联和我国,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就流行着对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错误看法,其根源都来自黑格尔的《逻辑》。黑格尔在《逻辑》中本来就说了不少糊涂话。后来某些人又变本加厉地宣传这些糊涂思想。……要纠正和清除这些关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错误思想,就必须深入研究亚里士多德的矛盾律思想和黑格尔的《逻辑》。因为亚里士多德的矛盾律思想是形式逻辑的根本原理,黑格尔的《逻辑》则是辩证逻辑的主要经典,而且这两者又是互相牵扯的⑥。本着这一认识,周礼全于1954年至1957年花费大量精力获得了《论概念发展的两个主要阶段——由抽象概念到具体概念》、《亚里士多德论矛盾律和排中律》和《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三项重要成果。其中,第一项成果于1956年由《哲学研究》连载,并于1957年出版;第二项、第三项成果当时虽没有出版,但印行了不少征求意见本,在学界有重要影响。这些系列成果系统澄清与体现了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分析风格的辩证法与辩证逻辑研究是否可能、何以可能的问题。
我国现代逻辑事业的奠基人金岳霖在其后期思想中放弃了其前期的狭义逻辑观(只承认演绎逻辑是逻辑),而转变为接受包括辩证逻辑在内的大逻辑观,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关于形式逻辑的逻辑真理之“普适性”的思想。在形式逻辑获得“平反”之后,苏联、东欧与我国学界曾就“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即逻辑真理的客观基础)问题展开了多方研讨与争鸣,先后提出了逻辑真理反映客观事物的“相对稳定性”、“相对独立性”、“质的规定性”等多种观点,其中尤以“相对稳定性”说占主导地位。由此说还派生出了形式逻辑只适用于把握事物的量变阶段,只有辩证逻辑才适用于把握事物的质变阶段的观点。然而,在金岳霖看来,这些观点只是在表面上承认形式逻辑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实质上还是对形式逻辑的排斥与否定。因为形式逻辑的逻辑真理之所以是逻辑真理,恰恰在于它们以“穷尽可能”为特征,在于它们的普遍有效性,也就是在思维中的普适性。倘若认为思维中有逻辑真理并不适用的领域,则逻辑真理之普遍的规范性就无从谈起,也就等于否定了逻辑真理。显然,这个问题不解决,使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不相互拒斥而且相辅相成的诉求是难以真正达到的。这是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上最难解开的一个理论“死结”。经过长期探索和反复钻研,金岳霖终于找到了解开这一理论“死结”的通路:逻辑真理虽与其他所有科学真理一样具有反映性,但它所反映的既不是其早年所说作为“纯存在”的“式”,也不是处于永恒变化发展中的客观事物的任何局部状态或局部阶段的属性,而是反映“客观事物的确实性只有一个”这样一条“相当根本的客观规律”。这条规律并不与任何其他规律(包括唯物辩证法的规律)相冲突,同时,又是任何其他规律成立的必要条件。他于1962年在《哲学研究》发表的长篇论文《客观事物的确实性和形式逻辑的头三条基本思维规律》,是在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背景下,运用“反映性与规范性相统一”的认识,对形式逻辑的逻辑真理的普适性思想的系统阐发与辩护。把握确实性也绝不与思想认识的过程性、发展性相冲突,“认识的深入是撇开现象的确实性,深入到本质的确实性,撇开偶然的确实性,深入到必然的确实性,撇开支流的确实性,深入到主流的确实性……认识总是要由浅入深的,但是,无论浅也好深也好,认识总是要反映对象确实性的”⑦。正因为如此,人们要获得关于客观事物的任何方面、任何阶段的正确认识,都必须保持思想认识的确定性。由此决定了人类思想认识中一条基本的反映规律:“只有确定的思维认识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确实性。”按照这个规律,为获得正确的认识,我们就必须研究在思维(包括辩证思维)全过程中(而不是局部过程中)维护思想确定性的条件,寻找保持思想确定性的规范来克服不确定性,这就是逻辑真理及由之决定的逻辑规范之所由来。该文尽管主要是就矛盾律、排中律和同一律立论的,但根据金岳霖关于“三律”在整个演绎逻辑大厦中的基本性的一贯认识,上述结论自然可以推广到所有逻辑真理。金岳霖本人也做了这样的推广⑧。这项被晚年金岳霖称为平生“最得意的”三篇论文之一的成果,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相辅相成关系的把握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逻辑讨论中所获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三、新时期辩证逻辑研究的主要进路
正如周礼全在20世纪90年代初所指出的:“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辩证逻辑的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许多辩证逻辑的研究者不满足于停留在对辩证逻辑的某些原则的空洞讨论上,已开始比较扎实地研究辩证逻辑的具体内容。有些辩证逻辑的研究者根据自己对辩证逻辑的理解,正在试图构造或已经构造了他们的辩证逻辑体系。这些情况不能不说是一个可喜的进步。”⑨这段话可作为对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辩证逻辑研究的恰当概括。彼时,学界既探讨了辩证逻辑的对象、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辩证逻辑与哲学的关系等老问题,也在思维领域的基本矛盾、辩证逻辑的基本规律、辩证思维的形式与方法等诸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富有启发价值的学术新见,同时也探讨了辩证逻辑研究进一步发展的不同路径⑩。经过争论,学界在辩证逻辑研究对象为“辩证思维的规律、形式和方法”上达成了基本共识,但在“辩证思维形式”的性质上仍存在根本性分歧。不同学派均开始了构造辩证逻辑体系的工作,这一时期出现了多部以辩证逻辑命名的专著与教材(详见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逻辑学会辩证逻辑研究会的会员近500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延续80年代的“繁荣”,但辩证逻辑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两方面都获得了新的重要进展。整个新时期辩证逻辑研究的发展,可概括为如下七个方面的主要研究进路。
(一)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比较研究进路
如前所述,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研究,是贯穿于辩证逻辑研究始终的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其实质是两种逻辑类型的比较研究。新时期以来,随着我国逻辑教学与研究现代化事业的发展,现代演绎逻辑和现代归纳逻辑的科学体系逐渐为我国逻辑学者掌握与使用,加之辩证逻辑研究本身的发展,使得这种比较研究获得了新的深度。1992年出版的黎祖交主编《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比较研究》,可视为这种比较研究成果的一种阶段性总结。该书吸取学界比较研究的成果,从概念论、判断论、推理论、论证论、思维方法论、思维规律论等多个角度比较了两门学科的研究历史、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性质以及发展方向。周礼全对其研究结果做了如下三点肯定性概括:“这两门学科无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重点和研究目的等方面都是有所不同的……是具有不同性质的工具性学科,没有低级与高级之分。”“两门学科都是研究思维形式、规律与方法的科学,即都属于逻辑科学。”“两门学科仍将沿着各自的轨道向前发展,继续作为两种互补的思维工具发挥作用。这里没有谁吃掉谁的问题。”⑪这样的两门学科的“互补性”观念,已逐步成为国内辩证逻辑研究的主流观念。
由于辩证逻辑以辩证法的矛盾学说为根本基础,而矛盾律又是形式逻辑的基本法则,也是现代逻辑系统的可靠性研究的基石,因而,“辩证矛盾”与“逻辑矛盾”之差异的辨析,就成为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比较研究中的首要问题,许多逻辑学者(包括不承认存在作为逻辑学分支的辩证逻辑但承认辩证法的矛盾学说的学者)参与了该问题的讨论与争鸣,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⑫。香港学者黄展骥正是通过对中国内地学界有关区分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之争论的考察,把辩证逻辑学界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之关系的把握划分为“鹰派”与“鸽派”,同时把拒斥“辩证矛盾”及辩证法学说的学者称为“形式派”。所谓“鹰派”即坚持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不两立、不相容的立场,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和中国学界的辩证学派为代表;“鸽派”则主张拒斥逻辑矛盾与把握辩证矛盾“并行不悖”,即坚持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可并立的立场,50年代后苏联与中国学界这种观点占据主流。但他也敏锐地注意到,那种认为形式逻辑适用于把握“量变”、辩证逻辑适用于把握“质变”的观点,实际上否认了形式逻辑规律与法则的普适性本质,他将之与同样否认矛盾律之普适性的“次协调(亚相容)辩证逻辑”学派称为“新鹰派”⑬。这种学派划分的意义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肯定。国内“次协调辩证逻辑”的主要代表桂起权欣然接受“新鹰派”的称谓,并指出:“形式派、辩证鸽派、辩证新鹰派、辩证旧鹰派可以排列成一个家族谱系,相邻派别的观点是交叉重叠的。”⑭张建军则进一步提出,以是否坚持所谓两种逻辑的“初等”、“高等”说划界,又可把辩证鸽派的观点分为两类,“一类维护初高等说,强调矛盾律的所谓‘狭隘和初级的眼界’;另一类则放弃初高等说,而把矛盾律的普适性贯彻到底,真正把拒斥逻辑矛盾作为辩证思维的一项基本原则,主张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⑮。他把前者称为“旧鸽派”,把后者称为“新鸽派”,并指出金岳霖、周礼全的观点即属于“新鸽派”。赵总宽则对这种学派划分做出了系统总结:“旧鹰派主张唯一正确的逻辑是唯物辩证法的逻辑,而否认形式逻辑是正确的逻辑,提出用辩证逻辑取代形式逻辑。新鹰派并不完全否认形式逻辑,但主张必须限制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和某些推理规则的普适性,认为逻辑矛盾命题是辩证矛盾命题的特例,悖论命题可以是真命题,主张用次协调逻辑来补充形式逻辑……旧鸽派认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都是逻辑学,不能互相取代,而是二者有类似初等与高等数学关系的两种逻辑学。新鸽派主张形式逻辑主要作用在于排除思维中的逻辑矛盾命题,它普遍适用可能出现逻辑矛盾命题的全部思维领域;辩证逻辑主要作用在于把握辩证矛盾命题。二者是功能互补的两种逻辑学。”⑯不难见得,这种学派划分,对于把握辩证逻辑研究的现状及其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在以下各个研究进路上的成果,都可看到上述不同学派的立场与背景的影响。
(二)范畴理论研究进路
由前面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辩证范畴理论可视为辩证逻辑研究的“本原”进路。这一进路的发端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形而上学》中的“次范畴”理论及《论辩篇》中的“四谓词”理论,作为对象明确的“逻辑类型”则成型于康德“先验逻辑”及黑格尔的“辩证转换”,后经马克思主义者“祛魅”而明确其科学方向。周礼全曾对这一历史进程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澄清⑰。沈有鼎也曾通过对“思维形式”的多重语义的澄清,明确认为“辩证逻辑即辩证的范畴论”⑱。通过文本分析不难看出,前引恩格斯关于作为“纯粹思想的领域”的“逻辑与辩证法”,就是指形式逻辑与辩证的范畴理论,恩格斯经常将二者统称为“理论思维形式”。
新时期我国学界以范畴理论作为主要与核心进路所获得的成果,以冯契的《逻辑思维的辩证法》(1982年内部印行,1996年出版)为首要代表,该书的特色在于,通过对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范畴理论和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传统的互相诠释,勾画了一个以“类”(包括一系列在“知其然”的认识阶段所运用的范畴)、“故”(包括一系列在“求其所以然”阶段所运用的范畴)、“理”(包括一系列在“明其必然与当然”阶段所运用的范畴)的次序作安排的辩证思维范畴体系。在冯契有关思想的影响下,彭漪涟的《辩证逻辑述要》(1986,2000年更名为《辩证逻辑基本原理》再版),《概念论——辩证逻辑的概念理论》(1991)、《逻辑范畴论》(2000),都是在这一进路上所获得的重要成果。李志才也长期致力于范畴理论进路上的辩证逻辑研究,发表了多篇专题研究论文,其成果凝结于所著《辩证逻辑体系》(载李志才主编《方法论全书(1)》,2000)。章沛、金顺福也是范畴理论进路上的两位重要代表,其共同特点是将“概念理论”研究作为辩证思维的主要与核心形式,将其他部分作为其逻辑展开。其成果体现于章沛主编《辩证逻辑基础》(1982)、章沛著《辩证逻辑理论问题》(1985)、金顺福主编《辩证逻辑》(2003)、金顺福著《概念逻辑》(2010)。张世珊著《辩证思维逻辑学》(1988),也是这一进路上另一代表作。两位唯物辩证法专家的辩证逻辑著作即刘景泉著《辩证逻辑概论》(1989)、封毓昌著《辩证逻辑——认识史的总结》(1990),也主要是围绕辩证的范畴理论而撰著的。
需要在此说明的是,本文关于辩证逻辑研究进路的划分及其代表作的例举,都是就其核心研究进路来说的,实际上,许多著作都是多种进路相交叉的,特别是因为范畴理论是历史上辩证逻辑之由来的“本原”进路,辩证逻辑的任何其他进路都需要与这种范畴理论“挂钩”并以此为背景而展开。例如,我国第一部辩证逻辑的通论性著作《辩证逻辑》(张巨青等著,1981),就含有“辩证逻辑的范畴体系”的论述,此后出版的某些通论性著作中也含有关于范畴理论的各具特色的论述,如沙青、徐元瑛著《辩证逻辑简明教程》(1984),赵总宽、苏越、王聘兴著《辩证逻辑原理》(1985)等。
(三)科学方法论研究进路
马克思、恩格斯在改造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创立建立在社会实践论基础上的唯物辩证法的过程中,都特别关注辩证法所固有的方法论功能,倡导用辩证思维方式取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列宁提出“辩证逻辑四原则”(全面性、发展性、实践性、具体性),也是从认识与思维方法论着眼的。以此为指导思想,苏联和我国的辩证逻辑研究中都有明确的方法论维度。新时期以来,西方学界在现代形式逻辑获得长足发展的背景下形成的当代科学方法论(科学逻辑)研究成果陆续引入国内,而其发展中存在的疑难(如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冲突)也彰显出辩证思维方式的缺乏所造成的问题。我国学者敏锐地认识到,与当代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结合与互动,应当是辩证逻辑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在前述第一部通论性著作《辩证逻辑》中,就辟有“辩证逻辑在科学理论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一章。而这一研究路径上的主要成果,凝结于张巨青主编的原国家教委委托编写教材《辩证逻辑导论》(1989)之中。该书是迄今所有通论性著作中与当代科学方法论结合最为密切的著作。此后推出的张巨青、刘文君主编的《认知与方法》丛书(1990、1994、1998分三批出版)中,多部著作可视为在这一进路上深化与拓展性研究成果,如张巨青、吴寅华著《逻辑与历史——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嬗变》(1990),郁慕镛著《科学定律的发现》(1990),金顺福著《科学思维的辩证模式》(1994),梁庆寅、黄华新著《真理——科学探索的目标》(1994)等。梁庆寅著《辩证逻辑学》(1988),是这一研究进路上的另一重要代表作,其中明确地把辩证逻辑视为“科学最一般的方法论”,并给予了系统论证与说明。
有些学者致力于范畴理论进路与科学方法论进路的相互结合,突出显示了辩证范畴理论面向当代科学理论的方法论功能。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作是沙青著《逻辑科学方法论论纲》(1995),其基本宗旨是使辩证哲学的逻辑方法论与科学方法论相结合,以达到辩证理性与分析性理性的统一,以便逐步形成一种适应现代科学发展的逻辑科学方法论。金顺福、汪馥郁主编《辩证思维论》(1996),也是在同样路径上所获得的另一重要成果,其中建构了以辩证范畴理论为轴心的辩证思维“一般模型”和关于非生命世界、生命世界、社会领域、精神世界之科学研究的“特殊模型”。
苗启明系统考察了在辩证逻辑的研究对象上的长期争论,提出以往在辩证逻辑之名下实际上有三门不同的学科,即“哲理逻辑”(大体相当于前述辩证范畴理论)、“思维辩证法”(包含于许多辩证逻辑的通论性著作之中)以及“辩证思维方式论”。他称后者为“狭义辩证逻辑”,以辩证地系统地把握对象的辩证性与系统性的辩证思维方式为其对象。其成果集中体现在《辩证思维方式论——狭义辩证逻辑》(1990)和《辩证逻辑的发展与分化》(1991)等著作之中。其“狭义辩证逻辑”可视为一种特殊的方法论维度上的探索。
(四)非经典逻辑研究进路
致力于“范畴理论研究进路”和“科学方法论研究进路”的学者,在辩证逻辑的学科性质上,大多数赞同“既是逻辑又是哲学”的主张,这也是“文革”前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新时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鉴于现代演绎逻辑最终从哲学怀抱中独立出来获得长足发展的历史事实,有些学者认为,作为“逻辑科学形态”的辩证逻辑,也应是不属于哲学的逻辑理论,而其真正的成熟形态,则是辩证逻辑的形式化理论。以现代演绎逻辑的观点看,这属于致力于建构与经典形式逻辑不同的一种特殊的非经典逻辑研究进路。
赵总宽是这一研究进路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将辩证逻辑的发展分为两大阶段:一是从哲学到逻辑科学,二是从非形式化的逻辑科学到形式化的逻辑科学。前一个方面的划分标准是以思维辩证法研究为主体,还是真正以辩证思维的形式结构及其规律为主体;后一个方面的划分标准为是否达到现代逻辑的形式化要求。以这样的标准,上面列举的张巨青、彭漪涟、梁庆寅等人的著作被列入“哲学形态”;而上列章沛、沙青、赵总宽、张世珊、苗启明等人的著作与下列著作一起,被列入“非形式化的逻辑科学形态”,它们是:李世繁著《辩证逻辑概论》(1982),马佩等著《辩证逻辑纲要》(1982),李廉著《辩证逻辑》(1982),张智光著《辩证逻辑》(1985),于惠棠著《辩证思维逻辑学》(1989),章沛、李志才、马佩、李廉主编《辩证逻辑教程》(1989)等⑲。考察这些“逻辑科学形态”的著作不难发现,它们在“辩证思维形式”的理解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其中大多数著作也包含了“思维辩证法”的内容,有些作者本来就是前两种研究进路的代表人物,而且许多著作仍明确把辩证逻辑称为逻辑与哲学的交叉学科,并没有完全独立于哲学的明确诉求。但这样的分类在研究进路的比较研究上是具有启发价值的。
马佩也长期致力于辩证逻辑的“逻辑化”工作。他依照与赵总宽类似的标准把辩证逻辑研究流派划分为“哲学派”与“逻辑派”,而其本人长期致力于独立于哲学的辩证逻辑探索,其系统成果体现在《辩证思维研究》(1999)和《辩证逻辑》(2006)之中。他的研究是非形式化的,但他表示支持辩证逻辑的形式化工作。他认为多值逻辑、模糊逻辑等异常逻辑均属于辩证逻辑的形式化,但这个观点未能得到多数学者(包括同一进路上的学者)认同。
桂起权明确主张辩证逻辑是一种“特殊的非经典逻辑”,因而也致力于辩证逻辑的形式化工作。但他也同时重视并积极参与了前两种进路上的工作,并认为这样的工作与形式化工作可以相得益彰。他认为当代“次协调逻辑”(又译为“弗协调逻辑”、“亚相容逻辑”等)是辩证逻辑形式化的主要阶梯与基本途径。他的有关辩证逻辑形式化及其相关哲学背景的讨论体现于《次协调逻辑与人工智能》(2002)。近年,杨武金亦得出了“弗协调逻辑是哲学辩证法等一切不协调理论共同的逻辑基础”的研究结论,并在其专著《辩证法的逻辑基础》(2008)中给出了系统论证。
郑毓信、林曾主张“辩证逻辑是一种非形式化的哲学逻辑”,认为辩证逻辑的产生本来就是以与形式逻辑不同的方式发展起来的,辩证逻辑需要将自己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规律精确化,但追求形式化并不是必需的。他们在《数学、逻辑与哲学》(1987)之中对此做了论证。金顺福则认为,辩证逻辑的形式化应当探索,但不是研究辩证逻辑的重点,从总体上说,迄今搞辩证逻辑的形式系统的条件尚不成熟,当前的研究重点首先是搞清楚辩证思维的内在结构和机制。其观点的系统论证及对某些形式化成果的评论集中在《辩证逻辑》(2003)之中。针对这些观点,致力于形式化方向的学者则对辩证逻辑形式化的必要性、可行性、既有成果与发展路径做了多方面的辩护与新探。
桂起权等所代表的是辩证逻辑形式化的“弱纲领”,即一种特殊的“变异型”非经典系统,这也是当代英美学界探索辩证逻辑形式化的主要进路。而赵总宽的《数理辩证逻辑导论》(1995)所代表的是辩证逻辑形式化的“强纲领”,即一种特殊的“扩充型”非经典系统。我国学者(如柳昌清、罗翊重、张金城等)构造的其他辩证逻辑形式化系统大多属于后者⑳。
(五)现代逻辑与逻辑哲学新成果的辩证审视进路
新时期以来,我国逻辑学界开启了逻辑教学与研究现代化、与国际逻辑研究接轨的历史进程,同时,我国逻辑学与相关学界也有不少学者运用辩证法与辩证逻辑理论考察现代逻辑与逻辑哲学理论所获得的新成果,从而构成了辩证哲学与现代逻辑互动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
美籍华裔著名逻辑学家王浩,曾力图运用辩证法对现代形式逻辑所使用的基本方法——形式系统方法的哲学性质进行思考研究,他借鉴列宁关于思维的“隔离性”的论述,提出了如下重要见解:“当我们把形式思维与辩证思维加以对照的时候,我们想的是比获得结果(这些结果能在给定的形式系统中写出)广泛得多的某种东西。说得更恰当一点,它或多或少相应于抽象思维,或者更广泛地说,它被看成是下述一种思维:这种思维并不充分具体地抓住实在的情况。如果我们这样广义地理解形式思维,那么我们甚至会佯谬地说:在每一时刻我们只能形式地思维,而辩证法的本质在于认识到这一点,而且自始至终地力求更好地逼近全部实在情况。”㉑1977年王浩在回国演讲中对此加以宣讲,并得到沈有鼎等学者的支持,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学界也产生了对现代逻辑及逻辑哲学的诸多重要成果与问题展开辩证分析的成果。张家龙在《公理学、元数学与哲学》(1983)一书中,考察与论证了“公理学的辩证本性”的问题;他在现代逻辑发展史的考察中也多次强调了现代逻辑成果的辩证性质,如他曾就塔尔斯基的形式语言真理理论指出:“在语言层次的链条上,对象语言与元语言的对立统一关系构成了链条的本质,它们的阶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由此决定了可否在元语言中定义真值等语义概念,所以,语言层次论具有辩证法的精神。”㉒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是现代逻辑辩证本性的典型体现,其对于深化与发展辩证哲学与辩证逻辑的价值得到了学界高度关注,学界就此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朱水林考察了哥德尔在证明该定理的过程中所体现的辩证思维方式,表明哥德尔“既重视形式的逻辑思维,也重视直觉的超限思维,并且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双方,既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对立,更强调它们的联系和转化,正是这种朴素的辩证思想,促使他攀上了科学的高峰”㉓。郑毓信则对哥德尔后期关于“集合的迭代概念”的研究进行了辩证分析,揭示出“在关于集合的直觉与抽象的公理化集合论之间所存在的并非是一种单方面的‘保证’关系,而是一种既对立、又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㉔。徐利治、朱梧等运用辩证法关于有限与无限的对立统一理论长期探索数学无穷观的逻辑基础,徐利治提出了兼容与统一潜无穷与实无穷的“双向无限”概念,并用于连续统结构等问题的研究,其有关辩证分析体现在《数学方法论选讲》(1983)和《论无限——无限的数学与哲学》(2008)之中;朱梧则在致力于“无限与有限的对立统一”的逻辑刻画中,始终专注于相容性问题的探索,先后提出了“中介逻辑”和“潜无限数学系统与重建实无限数学系统的构想”,论证了其强大的解题功能,其成果凝结于《数学基础概论》(1996)和《数学与无穷观的逻辑基础》(2008)之中。
当代逻辑悖论研究的辩证分析,在推动我国辩证逻辑事业的发展中起了特殊的作用。杨熙龄首先引入了国际学界具有自觉的辩证逻辑视角的次协调逻辑学派关于悖论的研究,并阐述了其本人关于悖论的辩证性质的认识,对国内有关研究有开启之功,其思考体现于《奇异的循环——逻辑悖论探析》(1986)一书。一些著名的辩证逻辑专家如马佩、沙青、赵总宽、桂起权等都发表了有关悖论的辩证分析的研究成果。尽管在悖论的基本性质上存在争议,有些学者的观点也发生了改变(如桂起权正是通过悖论研究由明显的“新鸽派”观点转变为“新鹰派”),但大家都认为逻辑悖论是连接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研究的一个“关节点”。郑毓信在其系列论文与著作中提出了逻辑悖论“实质上都建立在对于对象辩证性(过程性与完成性的对立统一)的片面化与形而上学化之上”的观点,其系统论证体现于他与夏基松合著的《西方数学哲学》(1986)。张建军在关于逻辑悖论研究的系列成果中,也始终贯穿了辩证分析的视角,提出了合理的解悖方案均可“辩证重建”的观点,并论证了其方法论功能㉕;他建构了集合论—语形悖论、语义悖论、认知悖论、合理行动悖论与辩证的存在论、真理论、认识论、行动论的对应关联,为公理化集合论及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的“非特设性”进行了辩证哲学辩护,论证了当代悖论研究之发展体现出“固定范畴”向“流动范畴”的转变,及其对当代分析风格的辩证哲学与辩证逻辑研究的启发机理。其研究成果凝结于《矛盾与悖论新论》(1998)和《逻辑悖论研究引论》(2002)之中。
(六)应用研究进路
如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所强调的,当代以系统科学为代表的一系列“横断科学”和以认知科学为代表的“大科学”的产生,进一步确证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辩证思维方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显示了辩证逻辑所可能具有的重要应用价值。在上面所列举的各种进路的研究成果中,都有在这方面的应用价值的探讨。此外,在非形式化研究和形式化研究两方面,都出现了多维度、多领域的应用研究成果。其中,与现代管理理论相结合的探究,形成了系列成果,其代表作有汪馥郁著《辩证逻辑和管理工作》(1986)和《管理者的思维工具——辩证逻辑》(1987)、苏越著《立体思维与管理工作》(1989)、张智光主编《管理决策逻辑》(1990)、王宁湘著《辩证逻辑与管理思维》(2007)等。非形式化的辩证逻辑应用研究的著作还有侯树栋、丁士峰著《辩证逻辑与军事工作》(1989),苗启明主编《辩证思维方法及其应用》(1993),贺善侃著《辩证逻辑与现代思维》(1996)等。形式化方向应用成果的代表性著作有桂起权等著《次协调逻辑与人工智能》(2002)、柳昌清主编《渗透逻辑及其应用》(1998)等。思维创新方面的逻辑应用机理研究,引起了我国学者的高度关注,其中具有自觉的辩证逻辑视角的著作有黄顺基、苏越、黄展骥主编《逻辑与知识创新》(2002),郁慕镛、张义生主编《逻辑、科学、创新——思维科学新论》(2002),张义生著《求解思维的逻辑》(2009),汪馥郁主编《企业发展与创新思维》(1997),楚明锟著《现代管理与创新思维》(1999)等。张巨青等著《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方法研究》(1998)、张桂岳主编《邓小平理论的逻辑研究》(1999)、陶文楼主编《邓小平理论与创新思维研究》(2001),亦均具有明确的辩证逻辑应用视角,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新近出版的王习胜、张建军著《逻辑的社会功能》(2010),则以“辩证求‘和’——条件链上的动态平衡”为题,专章论述了辩证逻辑的多领域应用价值。在研究论文方面,辩证逻辑的应用研究则涉及更为广阔的领域㉖。
值得指出的是,近年,辩证逻辑研究受到我国人工智能学界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不但尝试运用辩证逻辑思想解决当前人工智能研究中的一系列瓶颈问题,而且试图借此推动辩证逻辑研究本身的发展。其中,何华灿领衔的“泛逻辑”研究团队所取得的相关进展最为突出。
(七)思想史研究进路
思想史研究进路在辩证逻辑学科建设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但与其他研究进路相比,逻辑学界在这一进路的成果较少,尚未形成合力攻关性质的系列性、持续性研究成果。除各种通论性著作对辩证逻辑思想史的简要论述外,主要的代表性成果除周礼全于20世纪50年代完成的《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于1989年正式出版外,尚有陶文楼著《辩证逻辑思想简史》(1984),蔡灿津著《辩证逻辑史论纲》(1986),李廉著《周易的思维与逻辑》(1994),且大有著《马克思的辩证逻辑思想研究》(1998),彭漪涟著《冯契辩证逻辑思想研究》(1999)等。罗翊重著《东西方矛盾观的形式演算》(三卷本,1998)包含了比较丰富的思想史研究内容。沙青、张小燕、张燕京著《分析性理性与辩证理性的裂变——二十世纪中国逻辑思想论争的历史反思》(2002),对20世纪30年代与五六十年代中国学界围绕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关系的两场论战,进行了系统简明的梳理与深刻独到的剖析,得出了如下基本结论:一种现代化的辩证逻辑“无论是作为逻辑还是整体论方法最终都不能离开现代逻辑和数学的手段,更不用说把二者对立起来”;“辩证理性与分析性理性在分析性之精确前提下的有机统一”,既是科学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要求,也是当代辩证哲学与辩证逻辑研究所应担负的历史使命。晋荣东在《逻辑何为:当代中国逻辑的现代性反思》(2005)一书中,辟“辩证逻辑的论辩术”专章,系统考察了辩证逻辑与论辩术的历史关联及其在论辩术的当代复兴中所可能发挥的作用。最近,我国学者注意到当代西方“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运用现代模态逻辑工具对辩证法与辩证逻辑进行“分析性重建”的努力㉗,为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维度。
不难看出,与演绎逻辑及归纳逻辑相比,当代辩证逻辑研究尚未获得成熟形态,一些基本问题尚待进一步探索与澄清。比如,对于金岳霖曾着力澄清的“逻辑规律”与“思维规范”的区别与关联,学界在关于“思维(形式)辩证法”与“辩证思维形式”的长期争论中,并未给予足够重视。与此相关,科学方法论进路、非经典逻辑进路与范畴理论进路之间的互动关联,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互动关联,辩证逻辑与现代逻辑及逻辑哲学间的互动关联,都缺乏持续性、系统性深度研究。因此,辩证逻辑的发展既要鼓励各种研究路径的“百花齐放”,更应提倡路径之间的深度互动与争鸣;同时,应进一步拓展国际交流的广度与深度。在“问题导向”的多学科、多视角合力攻关研究已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旋律的时代,加强跨学科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发挥各种研究路径的解题功能,是当代辩证逻辑研究的生命力之所在。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②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
③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6页。
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1页。
⑤罗森塔尔:《辩证逻辑原理》,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71页。⑥《〈周礼全集〉自序》,载《周礼全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⑦金岳霖:《客观事物的确实性和形式逻辑的头三条基本思维规律》,《哲学研究》1962年第3期。
⑧参见张建军:《论后期金岳霖的逻辑真理观》,《学术月刊》2005年第9期。
⑨周礼全:《〈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比较研究〉序言》,载黎祖交主编《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比较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⑩参见金江文:《关于辩证逻辑讨论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国逻辑学会辩证逻辑研究会编《辩证逻辑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⑪周礼全:《〈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比较研究〉序言》,载黎祖交主编《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比较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⑫参见张建军:《如何区分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讨论评述与刍议》,载《矛盾与悖论新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曹祖明:《辩证矛盾与逻辑矛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⑬参见黄展骥:《“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并行不悖吗?——辩证法的“鹰”、“鸽”两派》、《辩证派、形式派“平分秋色”》,载《矛盾与悖论新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⑭桂起权:《再论矛盾、辩证法与逻辑》,《人文杂志》1996年增刊。
⑮张建军:《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之辨——兼评黄、马、邓、桂之争》,《人文杂志》1998年第3期。
⑯赵总宽主编:《逻辑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12页。
⑰参见周礼全:《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57页。
⑱沈有鼎:《论“思维形式”和形式逻辑》,载《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⑲参见赵总宽主编:《逻辑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299页。
⑳辩证逻辑形式化成果的最新评述可参见桂起权:《对我国辩证逻辑的历史发展之浅见》,《武汉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㉑王浩:《数理逻辑通俗讲话》,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㉒张家龙:《数理逻辑发展史——从莱布尼茨与哥德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5页。
㉓朱水林:《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94页。
㉔郑毓信:《数学哲学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
㉕参见张建军:《悖论的逻辑与方法论问题》,载《矛盾与悖论研究》,黄河出版社1992年版。
㉖参见桂起权:《2005:辩证逻辑正在向深度和广度拓进》,
《河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㉗参见张建军、曾庆福:《关于“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2010年第12期;曾庆福、张建军:《埃尔斯特“现实矛盾”思想解析》,《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B81
A
1007-905X(2011)06-0044-08
2011-08-07
张建军(1963— ),男,河北沧州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所长,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 吕学文
(E-mail:dalishi_sohu@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