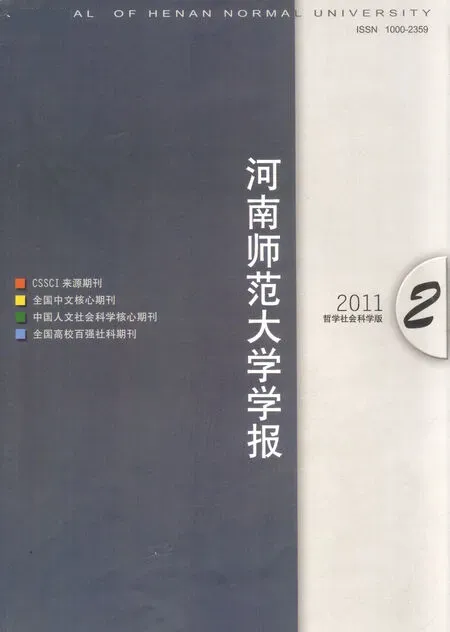人本法律观下的刑事诉讼犯罪嫌疑人权利群
李 贵 扬
(吉林大学 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人本法律观下的刑事诉讼犯罪嫌疑人权利群
李 贵 扬
(吉林大学 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刑事诉讼中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在与办案机关的关系、与其他社会成员社会角色的对比、自身权利义务轴失衡等三个层面存在不平等性。为消除犯罪嫌疑人不平等地位可能对其产生的不利影响,需要赋予相关权利以进行平等化矫正,这些权利包括底限人权、受限权利、派生权利。要实现由该三项权利构成的权利群,以人本法律观为主导的观念转变和以人权为主导的权利意识的生发就显得尤为重要。
人本法律观;底限人权;受限权利;派生权利
以人为本已经成为影响当下刑事司法实践的重要理念。在人本法律观下,“人是法律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法律之源”[1],在犯罪嫌疑人问题的研究中,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人本”的学说,深刻理解犯罪嫌疑人“人”的属性,深刻理解法律以人为依归的观念,对于重塑犯罪嫌疑人权利、实现刑罚目的、保证犯罪嫌疑人免受非人处遇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一、“犯罪嫌疑人”解读:从“犯罪”主导到“人”主导
犯罪嫌疑人这个称呼的出炉彰显了法治理念的进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十数年的实践似乎证明,犯罪嫌疑人所代表的“无罪推定”理念仅只是书斋之中、学者之谈的理念,还远没有成为为广大司法实践者所接受、能够顺行于司法实践的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观念的东西是最难改变的,一旦形成就具有历史延续性。对于司法实践者,根深蒂固的“罪犯”观念禁锢了“无罪推定”理念所内含的以“犯罪嫌疑人”为“人”的要求。于是,“犯罪嫌疑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犯罪—嫌疑人”的结构而不是应该的“犯罪嫌疑—人”的结构,前者明显倾向于“犯罪”主导型的思维:司法者思维一端是犯罪,一端是嫌疑人,遵循的依然是有罪推定的老路,这就导致在实践中各种围绕程序正义设计的制度流于形式主义。后者则使犯罪嫌疑人在他与“犯罪嫌疑”千丝万缕的关系没有理清之前,始终具有一个“人”的资格。犯罪嫌疑人始终具有“人”的资格,是其能够获得平等处遇的根本前提。勒鲁认为:“平等是一切人类同胞所具有的权利,这些人同样具有知觉、感情、认识,他们被置于同等条件下:享受与他们存在的需要和官能相联系的同样的财富,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支配,不受控制。平等被认为是一切人都可以享受的权利和正义。”[2]283如果司法者能够合乎理性地将犯罪主导型的思维模式改造为“人”主导型的思维模式,即思维一端为“犯罪嫌疑”,另一端为“人”,那么实践中恐怕也就会少了很多犯罪嫌疑人遭遇非人待遇的事例。考虑到这种思维转变存在的成本投入、破案压力等实践障碍,我们认为需要将“稳定压倒一切”与“以人为本”进行折中,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先行推行观念转化教育,观念的转换对于广大司法干警来说,实际上是符合中央“以人为本”的号召的。“犯罪—嫌疑人”的思维模式向“犯罪嫌疑—人”的思维模式的转变,是展开权利探讨的前提性设定,也是使权利探讨不至于沦为空谈的现实路径。
二、犯罪嫌疑人地位的三重不平等
如果以蕴涵着平等观念的“犯罪嫌疑—人”的逻辑结构来审视犯罪嫌疑人的地位,则该地位具有不平等性。卢梭认为,阐明了“人是怎样从一种状态进入另一种状态的”[3]问题,就可以找到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现象产生的原因。鉴于此处的不平等所意指为犯罪嫌疑人与办案机关地位的不平等,同时也包括与正常社会成员相比处遇的不平等,所以在案件发生之时,如果犯罪嫌疑人尚未被控制,那么此刻尽管立案、侦查工作或已展开,但是犯罪嫌疑人尚未在第一种意义上出现不平等状况,而在第二种意义上,此时的犯罪嫌疑人可能正在做出虚假掩饰,或者正在逃避追捕,或者正在毁灭罪证,这些使其难得有正常社会成员的生活自由,但是此刻该种自由的丧失,完全是基于其内心自愿,并不能认为是与其他社会成员产生了不平等。犯罪嫌疑人从“平等状态”进入“不平等状态”,在笔者看来是犯罪嫌疑人被控制之后,此时最大的特征,便是国家权力对犯罪嫌疑人现实地起了作用。该种公权力对犯罪嫌疑人的作用,传统地表现为犯罪嫌疑人承担了强制“配合”义务,而未从这种义务的承担中获得应有的权利。这就导致了犯罪嫌疑人在前两种意义的不平等之外,还遭受了第三种不平等,即:犯罪嫌疑人本身权利义务轴的失衡。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可以表示为以零为起点向两个方向延伸的数轴,权利是正数,义务是负数,正数每延长一个刻度,负数也一定延长一个刻度,而正数和负数的绝对值总是相等的[4]。该关系式适用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所以犯罪嫌疑人所处的不平等状态,并不能必然导致出其权利的丧失;对于其配合义务的承担,则可以获得相应的权利延展。同时,国家权力对犯罪嫌疑人所起的作用具有暂时性。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限制只能在为了更高的社会价值目标的意义上才可以获得正当说明,而且仅只是暂时性说明。在正当说明正当化的构成中,必然要赋予犯罪嫌疑人特定的防御权,因为此时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限制还无法从权利本身找到正当化事由,如果说在更高社会价值目标的指引下,犯罪嫌疑人呼吁“无辜”是一种无效主张的话,那么就必须赋予犯罪嫌疑人足够的防御权,一方面使得权利义务轴获得平衡,另一方面可以避免犯罪嫌疑人因主张无辜而陷于底限人权被剥夺的另一种无辜。底限人权、受到限制的部分权利、派生的防御权,这三者便构成了处于不平等状态下的犯罪嫌疑人能够获得平等处遇、进行平等对抗的“权利群”。该权利群的价值是使处于不平等状态下的“人”获得平等的武装,在手段上保障犯罪嫌疑人最终权利状态的确定。
三、犯罪嫌疑人权利群的构成
(一)底限人权
所谓底限人权,即人在任何境遇中都应该享有的权利。底限人权可以大致等同于“基本权利”。底限人权是宪法中确定的每个人本来就有的权利,这些权利先于国家而存在,它们不是国家意志的产物。自然法理论是最早对人权进行分类的理论。所谓先于国家的人权,指的是不依赖国家而成立的人权,这些权利就是卢梭论证的人人生而平等的那些人权。这些人权在进入文字表达和法典中的时候,因其对国家的无关性,而可直接称为使人成其为人的人权。那些基于国家而产生并因国家的存在而成立的凡行使时必与国家发生联系的人权,则因其对应着国家政治,其权利不称人权而称公民权[5]。底限人权指称的就是这样一种“先于国家的人权”,它的存在不依赖国家,宪法对它的规定只是一种确认而并非创造,底限人权的享有主体是“人”而不是“公民”,这种权利的享有仅因权利主体的消亡而丧失,其正当性由天赋人权予以说明。
底限人权在刑事诉讼权利群中属于“原权利”,是实现刑事诉讼被羁押人平等地位的根本保证。在现代关于人权最通行的“自由权、政治权、社会权(生存权)、请求权、平等权”分类体系中,哪些属于底限人权即“原权利”呢?“平等”是笔者所欲贯穿行文始终的最高权原,也即最高原则,亦即在笔者看来,“平等权”是高于其他四项权利的,处于统领的地位。在剩下的四项权利中,有没有属于“原权利”即底限人权的呢?由于在笔者看来底限人权是由“人”享有的、属于“先于国家的人权”,那么这种人权便不包含公民权在内。基于“公民权”基础而进行的划分虽然不能反映“底限人权”,但是内含了“底限人权”的要求。最明显的表现是“人身自由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这是现行宪法对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规定。人身自由权是由具有人身权利的公民享有的宪法权利。宪法的该条规定可以从反面解读为“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可因特殊情况受到侵犯”,但是受到侵犯的仅仅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而作为“公民”人身自由权利基础的“人”的“人身权利”是任何时候都不可以侵犯的,这些人身权利包括健康权、人格权、名誉权等。首先一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的明文规定,对于人权的侵犯是违反宪法规定的行为,应该承担不利后果。其次,在关于国家和公民的权力、权利范围的法理上,对于前者,遵行的是“法无明文即禁止”的原则,对于后者遵行的是“法无明文即自由”的原则。宪法规定的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可以在一定情形下被侵犯,但是作为“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基础的“人”的“人身权利”是没有规定可以被侵犯的。对进入刑事诉讼领域的被羁押人而言,其“人身自由权利”已经被部分剥夺,但是诚如勒鲁所言,如果说司法对他们是公正的、不偏不倚的,那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们都是人[2]23。
(二)受限权利
在20世纪末叶,有学者提出“权利本位”的理念并且逐步在法理学界获得广泛的认可与支持。权利本位观认为,权利是法哲学的基石范畴[6]335,那么同样地,权利也是部门法学的基石范畴。于是我们认为,在刑事诉讼领域,在理解被羁押人的特有属性时,应该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思维从阶级斗争主导下的“义务本位”模式转化到法治理念主导下的“权利本位”模式。在权利本位模式下,“本位一词不过是基础、根源、出发点和逻辑起点的意思”,“义务在实质上是权利的引申和派生物,当立法者发出禁令,要求人们承担某种普遍的义务时,只有当它是从权利中被合理的引申出来的,它才能成为一种合理的存在”[7]。权利本位观为我们正确理解被羁押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提供了指引。
在确立了“犯罪嫌疑—人”的构架和权利本位两个理论前提下,我们探讨被羁押人的“受限权利”,其着力点在于“权利”而不在于“受限”。受限权利的享有主体不同于“底限人权”,其主体为“公民”。在阶级斗争的痕迹渐行渐远的当代,对待犯罪嫌疑人已经不可用“敌我”的两分法简单划分,因为无罪推定的法治原则提醒我们,在未经生效判决确认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被认为有罪。所以,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侦查阶段乃至包括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在内的整个未定罪阶段中,其社会权利仅仅处于一种不确定或者说待定的状态,而受限权利则是这种状态的常态显示,处于该种状态下的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受限权利是一种“公民权利”而不是“人”的权利,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在没有被定罪量刑之前,仍然应该受到一种变通的公民处遇。因此受限权利既是犯罪嫌疑人权利不确定状态的表征,也是其公民身份的表征。
受限权利的正当性可以从犯罪嫌疑人与所被疑之罪的关系中获得说明。犯罪行为是“反社会的行为”,犯罪嫌疑人既然被疑有“反社会行为”,那么即使仅为证明其清白的目的,暂时被动放弃其部分社会权利或者被限制其部分社会权利也是有正当理由的。犯罪嫌疑人受到限制的权利包括:部分自由权、部分政治权、部分社会权。该些权利从表现上看属于“社会人”意义上人享有的权利,即公民享有的权利。而犯罪既然是“反社会”的行为,那么“社会人”意义上的权利即公民权利受到限制也有其内在正当性。
受限权利为什么是权利而不是义务?首先,以“权利”作为考量被羁押人权利义务关系的逻辑起点,可以更好地申明其被“限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被羁押人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只能接受羁押场所提供的三餐等诸如此类的限制,其合理性在于保证被羁押人的生存权和健康权,亦即被羁押人的权利是该种限制的来源;其必要性则在于保证被羁押人的“公民地位”[8],以致最终达到权利义务状态的明朗化,亦即法院的有罪或者无罪判决。其次,被羁押人享有的受限权利是一种“无可选择的权利”,虽然在“不可选择”上它具有和义务相类似的特性,但是其本质仍然是权利。米尔恩在区别“可选择的权利”与“无可选择的权利”时论述道:无可选择的权利与义务究竟有何区别?如果无可选择的权利的享有者除了接受之外别无选择,这是不是说他有接受的义务呢?不过,区别还是有的。这就是:无可选择的权利在本质上具有被动性,权利人并未被要求去做什么,他纯属某种待遇的受益者,而别人负有给予他此种待遇的义务。由于其他人员负有给予他的义务,严格说来,他是有资格得到此种待遇——也就是说,有权享有它[9]。米尔恩在此处给出了一个极好的思路,即,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其享有的“受限制的权利”虽然“除了接受之外别无选择”,但是这一别无选择的权利具有被动性,犯罪嫌疑人并未因享受该权利而被要求承担相应的义务;更为重要的是,侦查机关具有给予犯罪嫌疑人该种“别无选择的权利”的义务。简言之,对于侦查机关,从承担义务的视角审视,对于犯罪嫌疑人,从享有权利的视角审视。这就使得犯罪嫌疑人享有的“受到限制的权利”不至于被看成一种“义务”,同时又对侦查机关强大的侦查权力进行了限制。再次,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的义务包括:如实回答的义务,即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承受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传等强制措施,接受侦查人员的讯问、搜查、扣押、检查等侦查行为;不能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毁灭证据,等。总的来看,犯罪嫌疑人的义务属于“配合义务”,同时也是一种“拟制”义务,这种拟制义务有如下几个构成要素:承担该义务的前提是有证据表明该人可能与案件有所关联,该义务的承担是在更高的价值目标下才被允许,该配合义务必须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加给该人,该配合义务不得对该人的实体权利造成不必要影响。这些义务的获得,并不等同于自由权、政治权、社会权等的丧失,而仅仅是暂时受到了限制。在权利本位观的指引下,在受到限制的权利中,限制的因素实际是国家强制力的因素,在事态尚未清晰的前提下,国家权力与公民的权利应该处于一种张力中,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只在足以保证权利义务最终能够明朗的范围内有其正当理由,该意义下的限制并不能等同于剥夺。受限权利并不影响查明犯罪是否为犯罪嫌疑人所为以及犯罪嫌疑人最终的刑事责任问题。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享有受限权利是承认其平等的“公民地位”,从而不将其排除在社会之外的重要保证。
(三)派生权利
在笔者的分类体系中,犯罪嫌疑人作为“人”所享有的“先于国家的权利”属于底限人权的范畴,犯罪嫌疑人作为“公民”享有的自由权、政治权、社会权属于“受限权利”,而对由于进入刑事诉讼领域而获得的其他权利,笔者将其归为“派生权利”,即请求权。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犯罪嫌疑人拥有的派生权利有:辩护的权利、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申请回避的权利、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的讯问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的权利、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权利、核对笔录的权利、侵权控告权、获得赔偿的权利等。
在笔者看来,这些派生权利是为了矫正国家权力涉足私人领域之后可能会出现的不平等而产生的,其性质是请求权。按照罗尔斯的观点,这些派生权利属于“正义原则受到侵犯时反对侵犯的权利”,之所以能够援引正义原则,一是由于处于羁押状态下的犯罪嫌疑人“对他人的平等自由不构成直接威胁”,二是因为犯罪嫌疑人具有“自我保存”的权利[10]。这些派生权利设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平等对抗,而这种平等对抗的权利在罗尔斯那里是具有正义性的。
派生权利对于平等的意义一是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平等武装以便实现与国家的平等对抗,二是实现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轴的平衡。在权利本位论者看来,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力服务于权利,权力应以权利为界限,权力必须由权利制约[6]396。在权利对权力的制约方面,底限人权和受限权利是不容再破坏的,对于权力形成“硬制约”;而以“请求权”为实质的派生权利则成为对于权力的“软制约”,以规范权力的合法运行。对于犯罪嫌疑人本身的权利义务轴来说,当其具有配合调查、回答讯问、接受强制措施等义务时,相应的权利也必然要获得延展,以达到权利义务轴的平衡,而辩护权、申请回避权、申请取保候审权等则保证了权利义务轴的平衡,这种平衡也最终保证了犯罪嫌疑人在与国家对抗中的平等。
四、关于权利意识的问题
如果说犯罪嫌疑人的底限人权和受限权利的实现主要依靠国家对个人的尊重,那么犯罪嫌疑人的派生权利的实现则主要依靠其自己的主张。耶林说道,不管是国民的权利,还是个人的权利,大凡一切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都准备着去主张权利[11]。而主张权利前提是要求知道权利。“知道权利”便是指称人们的权利意识问题。在具备了一定的制度设计的前提下,是否能够产生“国家尊重犯罪嫌疑人的底限人权和受限权利”,同时犯罪嫌疑人“对于自己的派生权利懂得主张”的结果,皆在于当事方的“权利意识”。
权利意识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其特殊之点在于,它是主体对自身主体性的肯定意识,是对主体间自由方式的规则意识,同时也是对主体间交往规则的正义意识。因此,概括说来.权利意识是主体对自身在主体间交往中根据正义的规则所应当享有的自由的意识[12]。那么办案机关和犯罪嫌疑人的关系,是主体之间的关系,还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我们可以看看罗德雷的论述:人类之间的不人道行为只有在施虐者或行刑者能够否定其受害人的人性时才会发生……在孤立的案件中,一个人以上述方式对待另一个人可能是精神变态的行为。但是,当这样的行为成为一种制度化的行为时,那么起作用的就是别的东西了:受害者被视同一种物体,他们被非人性化并且必须被非人性化。这是看待“敌人”的传统的、必然的方式。不管是什么群体,必须剥夺其成员作为人的固有尊严,以便动员其余的人来反对他们[13]。在“阶级斗争”模式下,人被“敌我”二分,被羁押人被作为敌人来对待,自然就失去了“主体”资格,也就很难产生一种只有“主体”才可能产生的“权利意识”,从而受到“刑讯逼供”等“不人道”的待遇也就有了观念基础。随着宪法对“人权”的总括性规定,以及权利本位观念的接受与推行,犯罪嫌疑人最终必将现实地获得主体地位,从而使“权利意识”获得生发,在制度保证其平等权利的条件下,能够真正使其由合法权利构成的权利群和谐一致地获得实现。
[1]李龙.人本法律观简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4(6).
[2]皮埃尔勒鲁.论平等[M].王允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4.
[4]徐显明.公民权利和义务通论[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65.
[5]徐显明.人权的体系与分类[J].中国社会科学,2000(6).
[6]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7]郑成良.权利本位论[J].中国法学,1991(1).
[8]林劲松.刑事诉讼与基本人权[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46.
[9]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M].夏勇,张志铭,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115.
[10]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14.
[11]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M].胡宝海,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1.
[12]常健.当代中国权利规范的转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43.
[13]奈杰尔·S.罗德雷.非自由人的人身权利[M].毕小青,赵宝庆,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5.
[责任编辑孙景峰]
OntheRightsofCriminalSuspectsinCriminalProceedingsintheViewofHumanistConceptofLaw
LI Gui-yang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The inequality of detained suspect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exists in three aspect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se-handling organ and the suspects,comparison of the other members of society,unbalance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shaft.Coping with the possible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suspects,related rights including lower quartile human rights and restricted rights and derivative rights should be endowed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equality.In order to realize this objective,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stablish humanistic legal concept and to set rights consciousness which led by human rights.
humanistic legal concept;lower quartile human rights;restricted rights;derivative rights
D925.2
A
1000-2359(2011)02-0136-05
李贵扬(1980-),男,山东胶南人,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基础理论研究。
201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