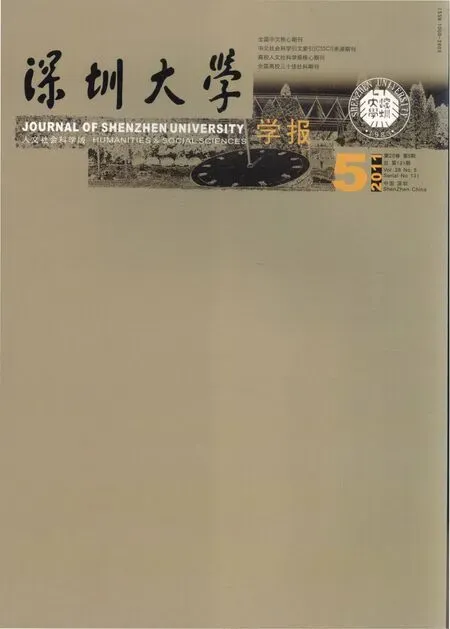论S·拉什迪后殖民语境下“象”的思维——以《午夜之子》为例
梅晓云
(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一个经常为评论家所指出的现象是,在后殖民文学中,往往形成对比性的“意象”:东方/西方,混乱/秩序,嘈杂/安静,分裂/统一,黑暗/光明,神话/科学……,作家借这些意象表达出他们的文学思想和社会批判。作为后殖民文学家的拉什迪则表现得更为复杂而多样,且往往刻意突破二元思维而造成多元的或模糊的寓意,形成丰富的、色香味声俱全的画面感,以至于有评论说拉什迪的小说有“三D”效果。无疑,作家特异的想象力是早就为评论家们所惊叹的,在笔者看来,甚至拉什迪的文学思维还常常是涵超语言的,可以说,拉什迪有一种“象”(image)的思维。作家在《午夜之子》[1]中曾明确说道:“思想以画面呈现的机率,跟仅透过语言象征是一样的”[2],此处的“画面”一词是pictorial,但与image含义相近,后者往往译为“形象”或“意象”,不仅有物质性的“象”,也含有精神性的“意”。文学作品里用语言构造的“画面”(pictorial),其实都含有某些意义,都是某种程度的image,而不只是纯粹物质性画面,拉什迪这里的“画面”(pictorial)其实就是“象”(image)。《午夜之子》中有极为突出的多种“象”——语象、物象、味象、声象、色象等,它们共同构成作品呈现思想的画面,正是这些各别的“象”,造成拉什迪小说突出的文学特色,形成后殖民文学意象,表达出作家深刻的思想。
关于“象”的理论问题,国内文学批评界已形成多种认识①。什么是“象”?与“象”有关的概念究竟其内涵如何界定?在中文语境里,如何解决对应的外语形式?汉语文献里极多的关于“象”的界说以及概念如物象、事象、气象、想象、境象、兴象、意象……等等,可否用来讨论外国文学作品?或者反过来说,外文的相关词如pictorial,image,icon,甚至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ideality,ideal nature②可否用来讨论中国的诗歌或小说?我们分析的对象是拉什迪这样的以英语写作的作家和作品,而我们这里的分析却是中文的思维并表达为中文的陈述,读者也主要是在中文的语境里来理解,更进一步说,我们——中文写作者和阅读者——即使是进入英语思维,也难以完全切近拉什迪的文学世界,因为他还带有印度文化背景并且涉及乌尔都语、印地语、梵语等多种语言及其概念的南亚文化脉络。本文并不一般地讨论“象”的文艺美学理论,而只是企图在具体分析中表达自己的认识,当然,也会引述其他学者的论述,以建立自己的概念脉络,从而产生自己的解释合理性。
一、《午夜之子》里的语象
《午夜之子》是一部英语小说,但在文本中涉及到多种南亚语言,这种拉什迪式的英语和南亚其他语言共同形成非常特别的语象,这些语象写作帮助作家完成其思想表达和社会批判。我们认为,语象是由声音和字符构成的存在,在阅读中,其声象(某种语言话语的声音)、视象(某种语言文字的图形)和义象 (某种语言语词的意义联想或暗示)共同构成语象,按一般语言学理论,作为书面语的文学作品,其语象应该都有这三个方面的涵义。有人论证了一个语象的三维状态,可以进一步启发思考:1.能指词的音响结构作为物质实体保存下来;2.所指显明的意义转换成存在的世界图像;3.能指词约定的所指转化为“存在视象”[3]。在此,本文作者所规定的语象概念所含之声象、视象和义象都一定程度地可以涵入这个三维结构中,更进一步说,这里实际上存在着语言本身的“象”与语言所形成的“象”两个层次,即:语言的存在视象与其所形成的世界图像,它们相关,却又不同。拉什迪对英语的拼接、关联、变形、戏仿、破碎、自我相关、语义的扩充、暗示和有意模糊所造成的非常特别的语象,主要是第一层的“象”,在阅读中同时表达为声象和视象,如《撒旦诗篇》中的“易不拉欣”/“亚伯拉罕”(Ibrahim/Abraham),“马洪德”/“穆罕默德”(Mahound/Muhammd),在阅读中,其发声相近,其符形亦相似,正是这种相似、相近引出第二层的“象”,即由义象关联带来的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冲突的“世界图像”。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圣人,穆圣为穆斯林教众高度尊崇,而马洪德在西方十字军的字典里意思却是“魔鬼”。在此,语象关联和语义暗示正是其造成巨大的文化误读效果的手段,伎俩虽小,效果却大,可以说一切与《撒旦诗篇》有关的冲突,都与其创造的特别语象有关,拉什迪自己的文学遭遇也与此有密切关连。
在《午夜之子》中,语象指涉和表义极为复杂,作家可以自造特别的字词,以表达某些意涵;可以运用关联产生语义联想;可以采取形似或声似的方法来造成效果;可以巧妙地切割字词造成破碎感等等,形成了拉什迪式语象,甚至生成拉什迪式英语,更重要的是,这些语象形成了作品的风格,也表达了作家深刻的思想。作品里为表达非常重要的“大鼻子”,拉什迪就生造了几个字,如proboscissimus这个字结合了proboscis(长鼻子的)与hippopotamus(河马),意思是大鼻子中的大鼻子,作品里的英格利丽说,这样的鼻子上面可以开马路[1](P7);而cyranose这个字结合了cyrano与nose,cyrano是人名,即17世纪的法国军人兼剧作家cyrano de Bergeras,其人以大鼻著称,后来19世纪的新浪漫主义剧作家艾德蒙·罗斯坦创作了中译名为《大鼻子情圣》的剧本并拍成了电影④;而nose是鼻子。cyranose这个拉什迪自创的英语词,可以译为“西哈诺鼻”,其语象(包括声、形、义)可以给人许多联想:外公的大鼻子在小说中意味深长并遗传给了撒利姆,在印度传统里长鼻子象头神伽内什也是文学神。在西方传统里,大鼻子是性能力的象征,大鼻子暗示着既擅文且多情,作品里撒利姆正是这样。而且他们一家人都与大鼻子有关:“在阿吉兹身上代表大家长风范,但在我母亲身上它显得高贵而有点压抑,在我小姨翡翠身上,它是势利眼,在大姨艾丽亚身上代表知识分子,在我哈尼夫舅舅身上,它是一个不成功天才的道具;穆斯塔法舅舅用它做二流角色的嗅味器;……”[1](P8-9)。然而有意味的是,这个大鼻子的午夜之子长大后却是性无能的,其深意颇值究诘,因为无论在古代或现代文化里,“性”都象征着创造力,性无能即是创造力的丧失,这使我们想到同是印裔英国作家的V·S·奈保尔在他的印度三部曲里“湿婆停止了舞蹈”的慨叹,而湿婆大神正是性力神。又比如在人物的名字上,拉什迪认为:“我们的名字里蕴藏了我们的命运。生长在一个名字不像西方那么毫无意义的地方,名字不仅仅是声音而已,我们也被我们的头衔所害”。[1](P396)主人公的名字“撒利姆”(Saleem)的含义是“健康、安全、完整”,而事实上他的生活不仅充满危险,他的身体也布满裂痕;他的姓氏“撒奈伊”(Sinai),按叙述者所言,蕴藏有波斯智者伊本·锡纳(Sina)、月神辛(Sin)和蜿蜒而行的蛇(S,像蛇一般曲折……蜷曲在这名字里)[1](P396)的丰富内容,同时也与《旧约》中的启示与不毛之地“西奈”(Sinai)同名,这其中深含着历史深处的信息,联系小说中不断强调的“连接模式”,其深意很值得进一步探究。拉什迪认为名字具有“无法抵抗的力量”[1](P457),所以在这部作品的人名、地名上下足了功夫,如阿达姆/亚当(Aadam/Adam),既是主人公外公和他的孙子的名字,也赋予了《圣经》中人类始祖的联想,而他(外公)也正是这部作品的起点人物;伊薇/夏娃(Evie/Eve)也是如此,有语义的叠加扩充。小说里的贫儿湿婆与印度教主神之一的湿婆神(Siva)同名,代表毁灭与性力,他以膝盖善战,外号“种马”,私生子无数,其情人帕华蒂(Parvati)也巧妙地与湿婆神的妻子雪山女神同名。而地名在这部作品里也是极尽语言魔法,“S”这个字母“像蛇一般曲折”,凡与此有关者,都奇怪地发生关联:地图上的“南方”(Southern)/月神“辛”(Sin)/中东的“西奈”(Sinai)/主人公“撒利姆·撒奈伊”(Saleem Sinai)/作者“萨尔曼”(Salman)等等,“S”还意味着历史大势,在作家认识里,南亚历史上但凡从南方北上没有不失败的,暗喻着拉什迪的历史观。在书里书外关系上,也往往借助语象类似、同构等方法造成特殊效果,如:扎法尔(Zafar),既是作品人物名字,也是作家儿子的名字,发生小说与现实的关系;楚飞卡尔(Zulfikar),既是撒利姆小姨父的名字,也是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里·布托的名字,前者是小说里的巴基斯坦将领,后者是国家领导人,语言互涉能使读者引起某些联想;方块/钻石(diamond/diamond),以西方的扑克牌喻言印度地形,一语双关,在作家意识里,印度是一颗比例不佳、品质粗糙、颇似西方玩物的“钻石”[1](P256);“午夜之子联盟”M idnight Children’s Conference/“大都会童子军俱乐部”Metro Cub Club/“午夜秘密俱乐部”M idnite-Confidential Club的英文简写都是M.C.C.[1](P586),体现了魔幻现实与真实现实的“摩耶”(梵语:Maya,幻象)。其他如语词的变异,民间成语的运用等,都有刻意的表达:舅舅家门牌上的“fly”,原来是一种“剔骨除肉的缩写”,指的是“家人”(Fam ily),而“穆斯塔法一家人确实就如同神话中切掉头的苍蝇,那么被践踏、那么像昆虫、那么无足轻重”[1](P506);“汤匙”与“拍马屁”同构(Chamcha/Chamcha),是民间成语中的戏谑语言[1](P507);乌尔都语的 “老头”/梵语的 “佛陀”(buddha/Buddha),发音相同,以历史的佛陀“在与不在”的摩耶(幻)联系着现实的撒利姆不在而在、在而不在的难免被擦掉的宿命[1](P454)。作家非常了解语言魔法的力量,他自己其实就是笔下那个高明的 “弄蛇人”(snake charmer),玩弄英语就如弄蛇人般令人眼花缭乱,惊叹不已。在谈到英语写作是否适用于印度主题的表达的争论时,拉什迪曾明确表示:“我们不能简单地按照英国方式使用英语;它需要为我们自己的目标重新使用。……征服英语也许就是实现我们自身自由的过程。”[4]他甚至技痒难捺,把欧洲著名宫殿名字如“无忧宫”、“凡尔赛”、“白金汉”等套在殖民地印度的建筑上,当然不只是为了玩弄语言技巧,而是有着深刻寓意。以上这些语象,是由声音、符形、意义构成,声象(语言声音)、视象(文字符号)和义象(语言含义)形成多层结构,正是这个结构唤醒了读者的记忆和心理表象,并产生评价性认识。
二、《午夜之子》里的物象
物象是语象的一种,它由实体名词形成,其表达的对象有具体物质性,由于它也是语象的一种,因此有声象、视象、义象的综合象,它经过了作者的选择和意义注入,经过能动的综合,也就当然有一定的“意”,有思想、情感指向。《午夜之子》中最突出的物象有“剪洞的床单”、“酱菜坛”、“红药水”、“银痰盂”、“洗衣篮”等等,甚至成为小说章节的题目。这几个物象符号若以蕴含的思想份量来看,以“红药水”联系殖民地屠杀、以“银痰盂”暗喻文化传统、以“洗衣篮”体现人物心理等,虽然很有特色,却在思想意义和创作特色上不如前两个物象那么重要。拉什迪在这部反映后殖民思想的作品里,极其强调 “破碎”、“空洞”、“裂缝”这一类意象,在作家看来,不仅印度国家是破碎的,文化是破碎的,甚至人物也是破碎的,从历史到社会,从外部生活到人物内心,到处都是空洞和裂缝,“被掏空”的感觉无处不在,而头脑“就像一颗被吸空了的鸡蛋”[1](P456)。在《羞耻》、《摩尔人最后的叹息》、《她脚下的土地》等小说中,他往往用破碎的镜子来表达这类意象,而在《午夜之子》中,则是“剪洞的床单”。撒利姆的外公阿达姆·阿吉兹行医中爱上了瞎眼地主的女儿娜芯,他的“爱情”是从破碎的床单中一点一点形成的,他以及他的家人的人生从此与破碎的床单发生了关联:外公身上的“窟窿”、撒利姆身体的“裂缝”、大地上的可怕开裂、母亲为爱上新夫而去重新“发现”他的身体各部分、妹妹贾米拉在床单的破洞后唱歌等,无处不在的破碎和精神的分裂,都是中了“床单的魔咒”,“被剪洞的床单注定一辈子过支离破碎的生活”[1](P153)。拉什迪自己曾经说,1001个午夜之子也就是1001个“破碎的自我”,撒利姆能听见自己身体里的裂缝咔擦咔擦地在扩大。有意思的是,撒利姆出生时总理尼赫鲁的贺电把这些午夜之子比喻为“我们大家的镜子”,“是古老印度的最新继承者”,而这面镜子却是破碎的,岂非是“我们大家的”、也是“古老印度的”难逃宿命?所以无论是破碎的镜子还是剪洞的床单,都是作家用来表达自己后殖民思想的重要物象符号。
《午夜之子》有浓厚的历史小说意味,也是现实政治史诗,但作家的历史观不是以思想文本的形式而是以令人印象深刻的物象符号来传达的,“酱菜坛”在这里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布拉根萨酱菜场的老板是撒利姆儿时的保姆、当年制造调包事件的助产士玛丽·沛蕾拉,作为小说的倾听者和参与者的帕德玛则是这家酱菜场的女工,酱菜气味不仅成为他的童年记忆,而他最后的归宿也在酱菜场。可以说,酱菜坛子的多次出现绝不是闲笔,它带有浓重的思想痕迹,也与他的“嗅觉伦理学”关系密切。在这部小说里,拉什迪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酱菜历史观”,他认为通过“将时间腌渍”起来的方法可以“使历史酱汁化”[1](P594),30个酱菜坛子,就是作品的30章,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含义,每个章节都腌渍妥当,好比他的另外一部作品《羞耻》中妇人手织的十八条围巾也各有自己的内容一样。作家说,“一切都必须记录,然后加以腌制”[1](P505),但 “还没有发生的事不能腌渍”,有了历史原料后,按照“特殊配方”,“在里头惨杂回忆、梦想、观念……”,这样制成的“酱菜版历史”当然也会有扭曲,“技巧在于,调制口味到某种程度,但不能使它完全变样,更重要的是赋予它形状与形式——也就是说,意义。”[1](P596-597)在这个过程里,撒利姆被掏空、干涸、腌制成历史的木乃伊,小说《午夜之子》成为了“酱菜版历史”。而在这个思想的表达方式里,“酱菜坛”这个物象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午夜之子》里的味声色象
本文作者认为,在文学作品里,味象、声象、色象,如同物象概念一样,也都是语象的下属概念,由一定的语象表达,但更复杂。如前所论,物象是由实体名词形成的,有物质性,而嗅味、声音、颜色却不具有实体性,它们是某物的性质而不是某物本身。味象如何可能?味而有“象”,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问题,它当然与味觉、嗅觉甚至触觉有关,还是包含有温度觉、痛觉等多种感觉的复合的生理、心理反应,可以说,物象是高度凝聚的,物与象一致,而味象、声象和色象则是弥散的,象大于引起象的物。问题是,“味”在文学作品里如何有“象”?同样,它也是语象的一种,由某词(组)引起,比如“望梅止渴”,梅之酸味、酸引起的生理反应、梅之颜色性状以及“望”和“止”的心理动作等,共同形成了包括有生理反应和心理活动的“象”,即味象。这个象与物象的不同在于,它没有实体性,因为“酸”只是“梅”的性质,不是“梅”本身。而声象也与味象类似,没有实体性,物理学上的声象,是指声音振动波的振动模式在人的头脑里形成的声音表象,由于声音随生随灭的性质,所以声象只是对声音感觉痕迹的追忆所形成的 “象”——表象。文学作品里声象概念的提出,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由本来有声音的语象构成,又用来描写声音,结果出现了双层声音,即前文所论之语言本身的“象”与语言所形成的“象”两个层次。色象,也是语象的一种,同样是不具实体性的象。色象在文学作品里,是由语词引起的感觉记忆,即某物之色的表象,不是面对某物时的感觉。总之,味象、声象与色象,都是语象的下属概念,是语象的一种,这些不同的象互相勾连、互相影响、互相叠压、纠缠、配合、协调,形成了所谓“象的网络”,好比是作品里强调的声色嗅味的通觉,造成了极复杂的文学意象,在《午夜之子》里,这个复杂的象的网络有着鲜明的表现。
读拉什迪的作品,最突出的阅读感受,就是仿佛进入了一个色、香、味俱全的文学酱菜场,事实上《午夜之子》写的也就是一个与酱菜场的气味密切相关的故事,1001种色香味以及与人生、世界和感情有关的东西全被 “整齐地收纳在我一格格的心灵空间里”[1](P415)。拉什迪极为敏感,也极擅运用这些味象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或文学构思。我们知道,撒利姆是一个大鼻子的、嗅觉特别灵敏的午夜之子,鼻子功能倘在,他就是午夜之子,失去鼻子功能他就回到了现实,鼻子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异能:“我闻得到的,贾米拉都唱得出。真理、美、幸福、痛苦,各有各的香气,我的鼻子都能分辨。”他知道“情绪的香味”,能嗅出危险和快乐,聪明或愚蠢,建立了自己的“嗅觉的通则”,发明了“嗅觉伦理学”,甚至把听觉、嗅觉、味觉形成一种特异的统觉,“脑袋在百味杂陈中团团转”:煮沸的内裤与报纸油墨的气味是蓝色的、旧家具与屁的气味是深咖啡色的、汽车与坟墓的气味是灰色的;他还以重量为气味分类:纸张是蝇量级的、肥皂清新气味的身体是羽量级的、汗水和夜女王的花是轻中量级的、焖羊肉与脚踏车机油是轻重量级的,而愤怒、香薄荷、背叛与粪便则是重量级的,他认为道德的本质与气味的善恶之间无比微妙的层次有很深的关系[1](P412-416)。在这部作品里,食物的气味与人物的心理也设计为某种强烈的情绪关联,因为“菜里吸饱了它们创作者的人格”:阿米娜吃顽固的烩鱼羹和决心的番红花饭菜;掉包的护士玛丽把内心的罪恶感及恐惧调进她做的饭菜,能引起食者不安;母亲在儿子洗澡水的甜美檀香味中找到冒险冲动……[1](P178)。正如詹姆斯·哈里森所言,“可敬的母亲”、阿米娜、玛丽和撒利姆等在烹饪上的强制性技能汇集在一起,为小说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支配性隐喻[5]。而绿色芒果酱在作品里显得尤为突出,蚂蚱绿的芒果酱是撒利姆挥之不去的气味梦魇,疾病高烧中忘不了,生活危机中少不了,回到童年生活的孟买,一瓶绿色芒果酱的气味差点没使撒利姆激动得晕过去!气味与记忆有密切关系,瓶子上的标签使他回忆起开启自己人生和同时将结束自己人生的布拉根萨酱菜场,“从此历史与族谱相遇”,在这里他与帕德玛定情,改变他人生的玛丽是酱菜场主人,一部色香味俱全的酱菜版历史就此展开和结束。[1](P590)可以说,《午夜之子》里浓烈的味象弥散着印度生活的痕迹,并成为作品构形的重要力量之一。
而作品里的声象,同样也表现得丰富迷人,一方面作品可以说是众声喧哗,一方面某些声音又深含寓意,正如许多评论家所惊讶的,作家对现代音乐非常熟悉,在此拉什迪也自负地展现了他的丰富知识。流行电影的插曲声,欧美现代明星的歌曲声,外公的口哨声,婚礼上的歌声,群众集会的欢呼声,电台广播的声音,猴子嚎叫的声音,清真寺呼拜塔上的招祷声,叫卖小贩的拨浪鼓声,占卜师的咒语声,印度教神圣的诵诗声,蒙巴顿方案的时钟滴答声,火车声汽车声脚步声,枪声炮声飞机声,节奏如打雷的乌尔都语声,孟买城市老歌声等等,这些丰富的声音既可以是一般背景声,也可以是为表达特殊意义而设计的声音,它们共同形成庞杂的巨大声象。而与作品思想内涵有密切关系的是三种歌声的声象,即小威利·温基的歌声、妹妹铜猴的歌声、护士玛丽的歌声,其所以重要,乃是因为这些声象具有特别的思想含意。
小威利·温基是一个与吉卜林作品里的人物同名的流浪艺人,他卖艺、调笑、奏手风琴,被人取乐子,像是威尔弟的歌剧《弄臣》里可怜的利戈莱托。他的生活很糟糕,妻子死于难产,儿子不是自己的,老婆与麦斯沃德私通他至死也不知道。他唱道:“小威利·温基是我的名,唱歌混饭吃我最行”,作为“午夜之子”的父亲,温基唱着殖民地时代的旧歌,却受着后殖民地时代的新苦,气喘、弱视、最后得了喉癌,直到他的嗓音变得像是被老鼠咬坏的西塔琴,以至完全失声 (第162-163页)。熟悉印度文化脉络的读者,完全可以在真切声音表象的意义上理解“被老鼠咬坏的西塔琴”的声音和温基得了喉癌后发出的沙哑歌声,这个基于记忆的表象其实是由语词形成的声象,它成为作家表达思想的手段。
妹妹铜猴后来成为走红歌星贾米拉,她的歌也有特别的意义。这个自小乖戾的女孩有许多怪癖,喜欢烧鞋子,能听鸟兽语,猴性十足,但令读者没有料到的是,她后来居然出落得好似“绝世奇葩”,摆脱了瘦巴巴野丫头的青涩,不仅有着令人羡慕的歌唱天才,而且成为一个高鼻杏眼金发的美人儿,这一切变化,却都是做歌星的功效:“她的歌声飘到窗外,交通也沉寂下来,小鸟停止了交谈,对街的汉堡店忽然关了收音机,满街的人都停下脚步,我妹妹的歌声在他们身上流过……”[1](P409)。这个按传统不能在陌生人面前露脸的少女只能在一幅剪了洞的床单后唱歌,可是她的命运却与所谓国家命运密不可分,被称为“国家之音”、“神的夜莺”、成为“国家最新受宠的女儿后”[1](P410),变成了“涤清人类灵魂的武器”,甚至自言“总统的意愿就是我心中的声音”[1](P412)。她在前线为士兵唱歌,成为收音机里爱国主义的符号,却在印巴战争中因为发现战争的荒谬和谎言并公开斥责战争发动者,此后两天“就从地球表面消失了”[1](P509)。这个可爱女孩的悲剧乃是因为她的歌声而罹难,其中深意正在于说出真象还是信守谎言?这在书中的世界是会要命的。
而保姆玛丽·沛蕾拉的歌声仿佛是谶谣:“一生没有不如意,想做什么都可以”[1](P496)。玛丽本是产科护士,作为基督徒的她却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大事:她把撒利姆与湿婆两个午夜之子调了包,引出了无穷的故事。但作者这样安排却不仅仅是出于故事效果的考虑,而是蕴有深意:基督教(玛丽)、伊斯兰教(撒利姆)和印度教(湿婆)的关系在这三者之间展开,玛丽安排了撒利姆和湿婆的关系,就犹如英国处理了南亚事务。这个被算命的拉拉姆称为“双头孩子”的午夜之子,也同时被与历史拷在一起。在印度现实里,印度教与伊斯兰教正是这样互相楔入,难以分开,而这对文化上的兄弟却打得不可开交,为什么?作家没有明说,却在玛丽的调包行为里暗示了全部原因:现代印度是欧洲的产物,印度被调了包,成为了一个畸形的国家。玛丽的歌:“一生没有不如意,想做什么都可以”,却正是撒利姆们的反谶,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他们的人生很不如意,作品在最后点明:“想做什么都可以,是最大的谎”。[1](P600)
在《午夜之子》里,“色象”的形成绝不是简单的背景或闲笔,比如作家刻意写到的“红药水”与“鲜血”,其实这个红色意象正是对当年英国殖民者阿姆利则大屠杀的抗议;作家还多次写到“蓝色”,这既是克什米尔的天空的颜色,也是欧洲殖民者麦斯沃德的蓝眼睛,还是耶稣基督的蓝眼睛,撒利姆外公和撒利姆的蓝眼睛,印度教大神克里希那的蓝色皮肤等[1](P129-148),这些蓝颜色的意义也值得研究者分析。最有意思的是撒利姆诞生的时刻[1](P143):忽然间一切都变成黄色与绿色,房间是黄色墙壁和绿色家具,产妇的皮肤变绿,眼白泛黄,墙上的时钟分针是黄色的,秒钟是绿色的,午夜庆典的焰火是黄色的火箭,绿色的烟花,男人穿黄色的衬衫,女士穿绿色的纱丽,地毯也是黄绿色的,医生带着黄昏色调的温柔说话,“婴儿终于在想必有同样颜色的产道里开始下降”。这些黄色、绿色、白色,其实就是印度国旗的颜色:黄色是宗教人士法衣的颜色,也是英雄们的颜色;绿色代表信心与生产力;白色则代表着真理和纯洁。这个色象正是作品寓意的表现,作家说过,撒利姆是国家的象征,午夜之子们的命运也就是现代印度的命运,在此,色象的创造成为了表达思想的符码。
文学写作中“象”的思维,是涵超语言的,所谓“涵”,是说这些“象”还须以语言来形成;所谓“超”,是说“象”的思维超越了纯语言思维,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思维样式。拉什迪式的“象”的思维创造了“象”的网络,形成了“象”所表达的文学世界,借此,他表达了自己的后殖民文学思想和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
注:
① 可参见赵毅衡《新批评》、陈晓明《本文的审美结构》、蒋寅《语象 物象 意象 意境》、黎志敏 《语象概念的引进与变异》。
② 参见克罗齐《美学原理》,朱光潜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70页。
③ 参见蒋寅 《语象·物象·意象·意境》(《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一文引陈晓明论述的观点。
④ 参见张定绮译《午夜之子》第8页注。
[1]萨尔曼·拉什迪.午夜之子[M].张定绮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
[2]Salman Rushdie,Midnight’s Children (New York:Avon Books,1982)262.
[3]蒋寅.语象·物象·意象·意境[J].文学评论,2002,(3):73.
[4]Salman Rushdie.Imaginary Homelands[M].London:Granta Books,1991.17.
[5]James Harrison.Salman Rushdie[M].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2.58.
——六必居酱菜制作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