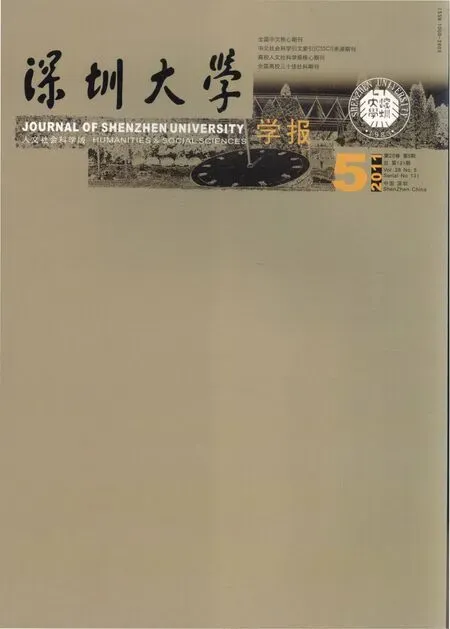多元化的拉美文学与拉美文化
李德恩
(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089)
20世纪60年代的拉美“文学爆炸”使拉美文学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新篇章,作家辈出,佳作迭现,形成盛况空前的繁荣局面。如果说拉美文学各种流派在各个不同时期还有它们各自的发展轨迹,历史也留下了它们的印痕。但在“文学爆炸”,尤其是后“文学爆炸”时代,各种文学流派共时同存,呈现出文学多元化的趋向。
全球化的文化多元化解构了二元文化的对立,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企图控制、主宰他国文化已不可能,那种引领世界文化潮流一枝独秀的西方文化已成为历史。各国文化的相似性使不同文化共同发展,从而使各国文化得以交流、融会。但有人认为,西方后现代和后现代文化思潮使人觉得世上再无客观标准可言,将使本国的主流意识失控,民族凝聚力丧失,似乎曾经横行世界的西方中心主义霸权话语卷土重来。这种骇人听闻的言论,除了对西方文化满怀恐惧外,表现出对本国文化缺乏应有的自信和抗衡能力的脆弱,面对西方文化竟然失却了判断力,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没落情绪。果真是这样,这个民族将像《百年孤独》中的家族一样,“一百年处于孤独的世家绝不会有出现在世上的第二次机会”。
拉美文学的发生和发展离不开它的宗主国西班牙,可以说早期的拉美文学是西班牙文学在拉美的翻版;拉美文学又是法国文学在拉美的延续,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便是在法国超现实主义影响下萌生的。然而,拉美现代主义(现代派)和魔幻现实主义摆脱了西、法文学的羁绊,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阴影,使拉美文学成为具有强盛生命力的文学大军。
但是西班牙征服者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即使在拉美各国独立以后这种影响也依然存在。西班牙殖民者声称,要在印第安人的庙宇上建立起天主教的教堂,形象地刻画了西班牙殖民者在拉美的战略:剑与十字架。用剑征服印第安人的肉体,用十字架统治印第安人的灵魂。剑使印第安人沉默了,不过时而也爆发反对殖民者的骚动,如著名的图帕克·阿马鲁起义。然而,十字架却始终未能矗立在印第安人的灵魂上。在拉美,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便有殖民者的教堂。在建筑教堂时,印第安的能工巧匠,在哥特式的尖顶或文艺复兴的圆拱大门的教堂里掺入了印第安人的风格——更甚于欧洲巴洛克的 “印第安巴洛克”。教堂的建筑线条是西班牙式的,而它的装饰却是印第安式的。对此,艺术史家是这样解释的,西班牙美洲的殖民地艺术远非西班牙形式在一个新世界的纯粹移植,而是在许多方面对立的两种文明的组合。
这两种文明的组合首先在人种的混合上表现出来。西班牙人去美洲探险的目的有三,其中之一便是对黄金、奴隶和女人的贪婪。为此,西班牙王室曾颁布谕旨,使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通婚合法化,以满足征服者的欲望。“1514年1月14日谕旨规定:印第安男人和女人有与任何人结婚的完全自由,印第安人、我们王国出生的人或在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都不得加以阻挠。”[1]据说阿隆索·德奥赫德是第一个把印第安妻子带回欧洲大陆的。后来,伊莎贝尔女王准许西班牙人把印第安妻子带回西班牙或者这个王国的任何省份。西班牙王室还多次颁布谕旨,赞许西班牙人和土著人通婚。这一方面是出自西班牙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不得已的措施。所以,西班牙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种族偏见和排他主义的可能性,他们在新大陆比较容易和印第安人融合。英国人在对待印第安人的态度上和西班牙人截然相反,他们采取种族灭绝政策,在北美的土地上重演白人间的斗争,建立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这并不等于说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混血是完美的、和谐的,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恰恰相反,这种混血对印第安人来说是一种灾难,印加和阿兹特克地废墟便是西班牙人毁灭印第安文明的历史见证,史诗《阿劳加纳》(1596)是西班牙人屠杀印第安人的生动写照,西班牙神父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的《印第安毁灭简述》(1552)是殖民者在拉美种种暴行的记录。墨西哥著名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在他的论著《孤独的迷宫》中称这种混血是强制的、暴力的,但毕竟是另一种文化的种子打在这块大陆上,为古老的印第安文化带来了新的血液。
“欧洲流浪的灵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他们与这块土地上的印第安人混血后又与后来的黑人结合,拉美国家独立后又与欧洲移民通婚,在血液、五官和肤色上与他们原先的民族已毫无相通之处了。这个新兴的民族超越了种族的个性,形成了拉美“新的精神”,塑造了拉美民族的特性。在文学艺术上则表现为各种文学流派、风格的共存。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秘鲁的印加·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出两种种族基因所起的作用,他的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是印第安人。他深谙克丘亚语和西班牙语,一生著有多部作品,《王家述评》是他的代表作,这部作品确立了他在拉美文学史上的地位。他写这部作品的目的是:“普遍介绍我的国家、同胞和目前并不富裕的民族”“第二,写这部作品的目的和动机是纪念(体面地、至少适度地)英勇、伟大的西班牙人。他们以勇敢和军事科学为上帝,为国王、为自己战胜了那个富饶的帝国……”,“写这部作品的第三个原因是充分利用时间,不在悠闲中浪费光阴。”[2]正如作者所说,这部作品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印加帝国昔日的荣耀;西班牙征服者的“伟绩”。无疑,还叙述了印第安人被奴役的过程。西班牙人的征服和印加帝国的毁灭,这一事实本身便是水火不相容的。《王家述评》使不同质的、敌对的文明巧妙地统一和平衡。人的相似性多于人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文化中的表现可以从每个集团的文化历史中得到证明。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差异,在这两个“集团”的融合过程中都顽强地表现出来,首先在事物认识上的差异:西班牙人把印第安人抽烟看做吸未烧透的木柴;印第安人则不明白人与马竟能连为一体,人还能从马上下来,一分为二!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同样反映在建筑、文学、雕塑、音乐上,在语言上尤为显著。在拉美大陆,西班牙语并不是印第安人自己的语言,用土著语言还是征服者的语言来创作文学作品,这一直是缠绕拉美作家的问题。语言不仅在于表达,而且涉及文学题材的趋向,后来印第安小说的盛行正是这种趋向的发展。随着印第安文明的泯灭,这种差异逐渐缩小,但也未销声匿迹。
印第安人的信仰、习俗、意识形态与当时文艺复兴后以理性主义作为判断、衡量实物标准的欧洲文化大相径庭,他们把现实看作梦幻,梦幻便是现实,亦梦亦觉,生活在神话的世界中。无意识、下意识、直觉、幻觉,甚或迷信是他们解释自然变故的思维方式。虽然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在意识和心理上存在着差距,这种差距甚至是不可弥合的,但在某些方面却有着奇特的相似之处。“黄金国”“青春泉”是印第安人梦幻中的现实,但西班牙人从印第安人的这种现实中找到了自己的梦。他们在新墨西哥印第安人集结的地区里,证实了中世纪有关“黄金国”的传说。佩德龙·马丁在给庞波尼奥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写的:“令人赞叹的房子,庞波尼奥。人们在地面上找到了本地的粗金沙,这些金沙是这样的重,以至于都不敢说出口来。人们还找到250盎司的金沙,还想找到更大、更多的金沙。土著人得知我们非常看重黄金后,用手势向我们指点。”从希腊、罗马到中世纪骑士们梦寐以求的“青春泉”、“长生不老水”在美洲的比米尼泉和佛罗里达河发现了这些圣水,据古巴和埃斯帕尼奥拉的印第安人说它可以使老人恢复青春。西班牙人在美洲找到的欧洲神话的归宿,哥伦布认为《创世纪》提及的天堂之河是美洲的奥里诺科河,柏拉图的阿特兰蒂达存在于美洲。两种不同文化的不同神话在美洲的土地上不谋而合,所不同的是欧洲人带着宗教的神秘主义来到这块大陆,他们看到的是与欧洲迥然不同的事实、乌托邦的事实。而印第安人生活的神奇事实,正在逐渐演变成真实的事实,神话的空间变成可计量的地理空间。总之,物质的宇宙将出现在梦幻和神秘的果核之中。
印第安人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和欧洲人的理性思考,在拉美处于同一时空。“美洲是不同时期共存的大陆。在这块大陆里,20世纪的人可以向四世纪的人伸手,可以像如同没有报纸、没有通讯的居民伸手。比这个时代更近的1850年的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同时存在。”[3]不同时代的人可以在拉美找到共同的语言,理性与非理性,现实与非现实同时并存。因此在拉美,历史不仅仅是理性的思索、现实的反映,而且是更深层次的非理性和非现实的表达。“我们生活在历史里,创造历史。当我们生活在历史里的时候,我们是这样解释历史的:我们每个行动都是一种符号。我们生活的历史是一部作品,在这部可见历史的作品里,我们应该读到不可见历史的变形和变化。”(奥克塔维奥·帕斯语)“可见历史”与“不可见历史”的综合,外在的“符号”和内在的“变形和变化”的统一形成了拉美文化的思维结构。
在文学上,反映这种思维结构的便是具有拉美特色的魔幻现实主义和“神奇现实”。现实主义通过人们的活动——符号,客观地描述现实的外部形态,谱写一部“可见历史”、有形的历史;魔幻作为印第安人的深层意识,存在于不同地区、不同部落的印第安人的神话、传说、信仰、礼仪之中,是“不可见历史”、无形的历史。大自然的变化无常,神秘莫测,捉摸不定,影响了印第安人的心理和精神活动。在印第安人的心目中,无生命的自然是一部有生命的史诗,这是印第安人魔幻意识形成的重要因素。这种 “可见历史”与“不可见历史”,危地马拉著名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称之为“真实现实”与“魔幻现实”。此外还有第三种现实即融合“真实现实”与“魔幻现实”的印第安人现实。魔幻现实主义确实与印第安人的原始思维有着直接的关系,印第安人以想象来思考问题,看不见发展过程中的事物,而把事物带到另外的领域。在那些领域里,现实的东西消失了,出现了梦幻;在另一些领域里,梦幻的事物又变成了可能触摸的和可见的事实。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阿斯图里亚斯的《玉米人》便是各种因素的混合体,现实与梦幻,人与大地在小说中并举;源于玛雅——基切的史前文化和现代民间日常的生活方式并存。在印第安人神话中,人是用玉米做的,《波波尔·乌》、拉美人的《圣经》关于玉米的传说在拉美广泛流传。因此,玉米在印第安人的世界里是神圣的,是人赖以生存的粮食。小说的根本冲突在于玉米的神圣化和玉米的商品化的矛盾,为吃而种植的玉米是玉米人神圣的粮食,为出售而种植的玉米意味着玉米人的饥饿。这关系到印第安人的生存、人与自然的平衡,如果失去这种平衡,印第安人将面临种族灭绝的危险。
如果说阿斯图里亚斯的《玉米人》反应了印第安人的“第三种现实”,古巴卡彭铁尔的《这个世界的王国》则阐述了他的文学主张——“神奇现实”。卡彭铁尔在访问海地时发现,每一步都能找到神奇的现实,那种神奇现实的存在和有效,不是海地所特有的,而是整个美洲的财产……“神奇现实”与“第三种现实”所不同的是它是现实的延伸,地理、历史和社会诸因素的综合;它是建立在日常经验的基础上的,来自大自然和周围的事物,但剔除了事物表层的功利和实用,发掘其奇特的一面,从而激发人的想象力。神话中的集体无意识,现实与历史的交融而产生的变化,都丰富了现实的神奇,从而使神奇自由地流动,打破过去与未来、现实与想象、开放与封闭之间的界限。阿斯图里亚斯和卡彭铁尔创造的魔幻现实主义、“神奇现实”开拓了拉美文学改革和创新的道路,这既涵盖了我们时代的经验,又是对人的潜意识的探索。
美洲是世界的未来,是一种新文化的焦点。魔幻现实主义和“神奇现实”是否能全面反映“世界的未来”和“新文化的焦点”呢?事实上,拉美文化的未来和焦点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并非 “世界的未来”和“新文化的焦点”所能包容。主观的想象、抽象的梦幻、乌托邦的幻想、人文的客观现实的对立构成了当今拉美文化的特点。要消除这两者的对立,只有通过文学手段才能实现,因为文学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艺术,可以冲破理性和非理性、现实和非现实的界限。拉美文学之所以有今天的繁荣局面,是由于拉美文化所形成的现实和作家对现实认识上的深化所致。
在拉美文化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非洲文化,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没有非洲文化的加入,今日的拉美文化又当别论了。“1502年,第一批非洲黑人进入了拉丁美洲。三年后,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答应把黑人当做商品大量输入美洲。除了西班牙、葡萄牙外,凡拥有船队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和荷兰都干着贩卖黑奴的勾当。这种贩卖黑奴的买卖大约持续了四个世纪。”[4]据保守统计,输入拉美的黑奴大约有2000万,仅牙买加一地就贩入了61万黑人。由于拉美的气候、土壤、自然与非洲相似,黑人很快就适应了拉美的环境;他们性格开朗、外向,易于克服精神和身体的痛苦,在拉美这块土地上扎根,并与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混血的第一代后裔联姻,这种联姻的直接结果便是黑人的信仰发生了变化,产生了一种宗教调和的现象,与异教的神灵半同化了。
非洲文化和欧洲文化的交融如印第安文化和欧洲文化的结合一样经历了矛盾和斗争。加勒比地区,随着西班牙势力逐渐被美国、法国和荷兰所取代,实行以非洲黑人为主的奴隶制度,而当地的印第安土著文化处于被消灭的状态。因此在加勒比地区,白人的欧洲文化和黑人的非洲文化是主要文化。这两种文化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本土文化——克里奥约文化,但本土文化绝不同于非洲文化,因为它植根于加勒比岛国的生活和自然,是岛国自身发展的产物,虽然仍保持着非洲的习俗和某种部落文化,尤其在圭亚那、苏里南、法属圭亚那内地的森林地区。
19世纪末,加勒比地区和安第斯国家掀起了一场文学运动,研究非洲的风俗和文化,斥责所谓黑人低下、非洲没有文化的言论。英属安第斯国家的杰出诗人克劳德·麦基的诗歌强烈地表达了对非洲的思念,对欧洲奴役黑人和歧视他们文化的愤怒。牙买加马库斯·加维的《回归非洲》直接从非洲不同地区的音乐和歌谣中汲取灵感。这些作家用不同的方式表示了他们对欧洲文化的不满,但并不等于说他们要重返非洲,或把非洲文化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加勒比地区和黑人集中的国家(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巴西),恰恰相反,他们更热衷于本地的克里奥约文化。曾创作诗歌《土地,松和鼓》的厄瓜多尔作家奥尔蒂斯对非洲事物颇感兴趣,但不愿回归非洲,也不模仿非洲作家的创作模式,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巴西,尽管非洲的影响在巴西非常强大,但巴西黑人和混血种人感到自己是地道的巴西人,而不是非洲人。
秘鲁著名思想家、文学评论家马里亚特吉曾说过,印第安文学在只有印第安人能够自己创造它的时候,才算来到了。黑人文学也是如此,在条件成熟时,它便应运而生了。克里奥约文化始于16世纪后半叶,反映这种文化的加勒比文学也因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参差不齐。随着各国民族的形成,这种差异尤为明显。20世纪初,苏里南、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和某些英语国家(牙买加、圭亚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巴巴多斯、格林纳达)的文学都显示了它们的个性。加勒比各国的文学朝着各自方向发展的同时,一种强烈的认同趋向也平行地发展。这种认同趋向不仅表现在作品的人物、风俗和自然景象上,更重要的是反映在作品的题材上,反殖民主义小说,反奴隶制度小说、反独裁小说,如马提尼克作家雷内的《巴托乌阿拉》、埃梅·塞泽尔的《鲁瓦·克里斯托夫的悲剧》、古巴作家卡彭铁尔的《这个世界的王国》。因此,加勒比文学既有该地区各国文学的特殊性,又有普遍性。真正代表黑人声音的是古巴诗人尼古拉斯·克里斯多弗·纪廉,在他的三部诗集《松的旋律》、《松戈罗—科松戈》和《西印度公司》中,非洲的战鼓在古巴抒情诗中开始轰鸣。纪廉的诗是非洲的,是流行于非洲北部的歌谣。诗歌的语言是古巴亚鲁巴黑人的方言,诗歌的节奏是非洲音乐的节拍,并掺杂着西班牙的文化。古巴真正的黑人小说是米盖尔·巴尔内特于1968年在哈瓦那出版的《逃亡奴隶的自述》,这部小说中一个104岁的老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奴隶的生活、非洲舞蹈的起源和巫术。
智利伟大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曾说过“我,历经沧桑”,如果用这句话来形容拉美文化,既贴切,又实在。拉美文化历经500年,可谓沧海桑田,在那里有印第安人的呻吟,也有非洲黑奴的呐喊,拉美文学不正是在呻吟和呐喊中从昨天走向今天的吗?
[1]Anderson Imbert,Enrique.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hispanoamericana,México,Fondo de Cultura Económ ica,1961.
[2]Henríquez Urena,Pedro.Las Corrientes literarias en la América Latina,México,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1987.26.
[3]Carpentier,A lejo.Tientos,diferencias y otros ensayos,Espana,Plaza&Janés Editores,1987.66.
[4]Collazos,Oscar.Las vanguardias en América Latina,Barcelona,Ediciones 62 S.IA.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