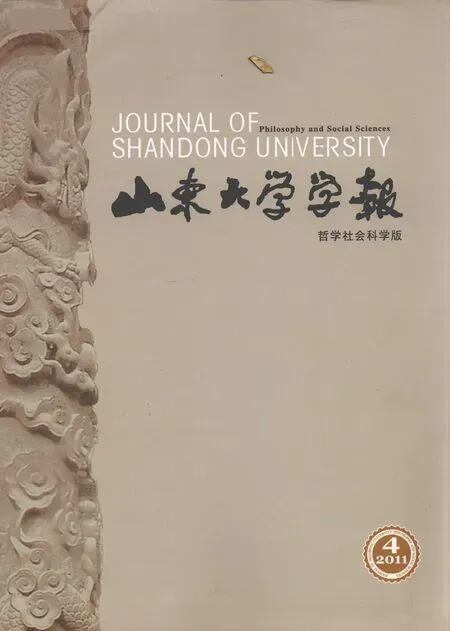孟子“以意逆志”的语义学诠释——基于修辞理解角度
丁秀菊
东汉以还,众多学者对孟子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进行了注释、疏解,但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观各家之说,他们“分歧的焦点在于对‘文’、‘辞’、‘志’、‘意’等几个关键词及其之间关系的理解不同,而共同的毛病则在于缺乏对原词词义的清晰界定以及对两处例子示范意义的准确理解”。①周裕锴:《“以意逆志”新释》,《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6期。的确,“文”、“辞”、“志”、“意”是准确理解孟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关键,而“逆”更是关键中的关键,因为“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只是“以意逆志”的铺垫,在逻辑上是应被排除的;而“以意逆志”乃“是为得之”的必备前提和重要保证。那么“逆”当怎样理解?是迎取、测度、钩沉抑或其他?本文拟从修辞理解角度作一阐释,以期对“以意逆志”的语义内涵作出完整、准确的理解。
一
“以意逆志”语出《孟子·万章上》,原文如下: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
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②朱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以下引文,版本同。
孟子通过对“以文害辞”、“以辞害志”的否定,突出、肯定了“以意逆志”的必要与必须。“以意逆志”建立在“以文害辞”、“以辞害志”被排除的基础上,那么我们首先应弄清“文”、“辞”、“志”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先秦时期,“文”与“辞”都呈现多义性:“文”可作文字、文章、文献、文学、文采、文饰等讲,“辞”则具有诉讼、口供、文辞、言辞、语辞、卦辞、爻辞、推辞、责让等意义。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它们具有不同的意义;但在语言表达层面,“文”、“辞”与“言”、“语”等又具有相同的意义或作用,尤其是“言”与“辞”,有时甚至可以无条件地换用,如孟子自己曾两次同时运用了意义相同的“言”与“辞”,一次是《孟子·万章上》:“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一次是《孟子·公孙丑上》:“何为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而在“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文”与“辞”并不处在同一层面上,它们与“志”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层层递升的语义关系,即“文”→“辞”→“志”。孔子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①《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言”用以表“志”,反过来就是说,“志”是由“言”、“辞”来表达的。
众所周知,所有“言”、“辞”均由字词构成。“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②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375页。对此,清代著名语言学家段玉裁也有精辟分析。他说:
词,意内而言外也。有是意于内,因有是言于外,谓之辞。……意者,文字之义也。言者,文字之声也。词者,文字形声之合也。……词与辛部之辞,其义迥别。辞者,说也。……犹理辜,谓文辞足以排难解纷也。然则辞谓篇章也。词者,意内而言外,从司、言。此谓摹绘物状及发声助语之文字也。积文字而为篇章,积词而为辞。孟子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词害辞也。”③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29-430页。
根据段玉裁的分析,有学者认为,“‘文’就是文字,也就是词(word);‘辞’就是篇章(text);而‘志’就是诗人的志向,即创作意图(intention)。由于‘词’(即‘文’)是‘意内而言外’,因此‘文’有其意义,同理,由‘文’积成的‘辞’也有其意义。这样,三者之间的递进关系应是,由文字之义组成篇章之义,由篇章之义显示作者之志。”具体到“不以文害辞”中的“文”与“辞”,又说:“这里的‘文’不必仅限于个别的字眼,而应理解为整篇‘辞’(text)中的一部分,可以是词,也可以是词组(words)甚至句子(sentence)”。④周裕锴:《“以意逆志”新释》,《文艺理论研究》2002第6期。这就值得商榷了。“文”既然是文字也就是词,又何以再为词、词组或句子呢?还有,“辞”仅指篇章吗?《汉语大辞典》:“篇章,篇和章,泛指文章。”事实上,书面文章为“辞”,口头话语也是“辞”。话语有长有短,可以是句子,可以是句群,可以是段落,也可以是篇章。可以说,只要能完整地表达一个意思、一种思想的话语,都是“辞”。如“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中的“辞”就指句子,而“何为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中的“辞”则指话语。由此可见,“不以文害辞”中的“辞”绝不仅仅指篇章。
“辞”具有篇章修辞的功能。这是因为,字、词、句虽是三个不同的语言结构单位,但在具体的语言表达中,言与意并不时时统一、处处一致,许多时候存在“辞面”与“辞里”离异的情形,尤其是运用了一些特殊的表达手段如隐喻、暗示、象征、夸张、双关、婉曲等以后,言辞话语总是表面为一种意思,背后还隐藏着一层意思,即言外之意。话语的表面意思、字面意义,只要通过语言材料的组织形式——字、词、句就可以直接获得,如“你来啦”,“我去吧”,“今天上午下雨了”等所表达的意思一目了然;而话语的深层含义、言外之意,有时通过一个字、一个词(如夸张)、一个段落表现出来,有时则蕴藏在整个话语的背后,需要接受者悉心体察、认真领悟方能得出。成语“朝三暮四”,字面意义是早三晚四;而考察其出处可知,它真正表达的是“反复无常”的意思。“你是萍……凭——凭什么打我的儿子?”⑤曹禺:《雷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98页。面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周萍,母亲鲁侍萍欲上前相认,又对周萍打自己弟弟鲁大海的举动深感气愤,所以叫了一声“你是萍”,又马上以谐音字掩饰:“凭——凭什么打我的儿子?”纠结、矛盾、痛苦、愤恨、失望而又无可奈何,种种感情交织其中,溢于言表。再如:“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⑥张籍:《节妇吟》,见马茂元选注:《唐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从诗句字词来看,这首诗描写了一位节妇不为利诱、不为势屈的情形;而从诗的副题《寄东平李司空师道》看,这首诗其实是写给当朝权贵李师道的。李师道凭借手中权势,想笼络官吏文人,张籍不愿为他所用,故借诗回答。张籍以节妇为喻,委婉含蓄又态度坚决,柔中带刚,恰当得体。等等。“辞表”与“辞里”的离异,不仅使话语产生了“言此意彼”、“言近指远”的言外之意,而且起到了贯通文脉、塑造人物、结构全篇的作用。
从表达角度看,作者欲表达的“志”是主观的,具体文、辞表达出来的“志”可以是话语的字面意思,一目了然,一听便知;也可以是话语的言外之意,藏之“辞”后,细审方知,具体要依表达者表达时的心境、环境、能力、水平而定。而从理解角度看,“志”是客观存在的,接受者理解话语必须从其语言组织形式——字词、句子入手,考察话语表达的具体语境,考察表达者的思想感情、心境情绪、立场态度、身份地位等各方面因素,结合自己的知识、经验等进行多方面、全方位的分析、综合,然后作出正确、合理的判断。正如著名学者钱锺书先生所说:“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虽然,是特一边耳,亦只初桄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辞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derheme neutische Zirkel)者是矣。”①钱锺书:《管锥编》(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7页。由此我们可以判定,“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中的“文”指文字或词,“辞”是包括句、段、篇章在内的语辞(话语),“志”是表达者通过“文”、“辞”所欲表达的思想感情、意志倾向、观点态度等主观意图。孟子“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的意思就是,解说诗歌者,不要因为一个字或一个词的表面意思而曲解了整句话的意思,也不要因一句、一段、一篇的意思(表面意思)而曲解了作者所欲表达的主观意图。
二
在古代,“意”与“志”具多义性,在表示心意、情志方面,二者可互训。但在“以意逆志”中,“意”与“志”则有着明显的区别。从孟子与咸丘蒙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以意逆志”承续上文而来,省略了言说主体“说诗者”,而“以”主要引介动作行为所凭藉的工具、方式,那么“意”自然不可训解为动词“测度”,也不能表示古人之意或表示文本中客观存在的意义,而当指“说诗者”之意。而“说诗者”所欲“逆”的“志”,实际上同时承载了作者所欲表达之“志”与作品实际表达之“志”。当然,这个“志”主要通过具体的“文”、“辞”呈现出来。作者所欲表达之“志”与作品实际表达之“志”二位一体,或立场观点,或思想观点、情感倾向,或情趣兴致,与“说诗者”之“意”显然不同。至于“意”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从接受者对修辞文本的理解、阐释过程中一窥究竟。
作为被接受的对象——修辞文本,映入接受者眼帘的或进入接受者大脑的,首先是具体的词句。接受者需通过自己的知识储备,先弄清词句,弄清词句所表达的字面意思,继之查考表达者创作表达时的时代文化背景,查考表达者的身份地位、思想观点、立场态度、情感倾向等,运用自己的学识修养去认识、领会话语蕴含的意义,最后得出自己的见解、判断。与言说表达不同的是,言说表达是一个正向的组词成句、缀段成篇的过程,是信息的编码、建构过程;而理解接受则是一个反向的解词释句、还原话语的过程,是信息的解码、解构过程。也就是说,在表达过程中,作为被表达的对象,“志”隐“辞”后;而在理解过程中,“志”已是客观存在,“意”在“辞”后。理解、阐释的过程就是使接受者的“意”与被表达的“志”融合为一、由已知而未知、“推陈出新”的过程。所以作为理解、接受的主体,“说诗者”说诗实际是对诗句意旨的还原与再创造。而“说诗者”在说诗时既要有对事实材料的客观考证,又要有“说诗者”主观感受的参与。对事实材料的客观考证,可为理解、阐释的客观、正确提供一定的保证;主观感受的积极参与,可赋予理解、阐释以创造性和独特性;而主客观的交融贯通则为理解、阐释的全面与准确奠定了基础,是“得之”的必备前提和重要保证。由此看来,“意”作为“说诗者”主观方面所具有的东西,它既包括“说诗者”对作品本身的认识感受,也包括对作者身份地位、学识修养、心境情绪、创作背景、创作动机、创作角度、倾向态度等的认识感受,包括对已有理解、阐释材料的分析把握(也有学者认为,如此,“意”负担过重。事实表明,在古代,正是这样,才有“微言大义”“言简意丰”之说)。最后,“说诗者”从个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立场角度、价值取向等把“意”与“志”融合在一起,从而得出有别于他人的认识和结论。所以,不同的“说诗者”有不同的“意”,用不同的“意”就会“逆”出不同的“志”,“意”是“逆志”的前提,怎样“逆”、从什么角度“逆”、“逆”的广度与深度,既是“得之”的关键,也是“说诗者”个人知识结构、认识能力等的彰显。千百年来众多学者对“以意逆志”的不同理解、阐释,就是一明证。
关于“逆”字,学者们或训为“迎”,或训为“测度”、“钩考”。《说文·辵部》:“逆,迎也。从辵,屰声。关东曰逆,关西曰迎。”“迎,逢也。”“逢,遇也。”可见,“逆”、“迎”是区域用语,是一个方言词(汉扬雄的《方言》亦收录,可证),且二者可互训,是相逢、遭遇之意。孤立地看,“逆”之本义自然可以如此解释,但在具体话语中也如此理解未免机械了些。若训“逆”为“迎”,诚如周裕锴教授所言:“孟子是在谈《诗》的阐释方法问题,如果把‘以意逆志’解为‘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那么‘迎取’仅仅意味着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心灵接触,理解和解释还未开始,所以不能说‘是为得之’。真正的理解和解释有待于‘测度’和‘钩考’。”①周裕锴:《“以意逆志”新释》,《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6期。朱熹虽训“逆”为“迎”,但他还说:“今人观书,先自立了意,后方看书,牵古人言语,入做自家意思中来。如此,则是推广得自家意思,如何得见古人意思?须是虚此心,将古人言语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杀向何处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长进处。且如孟子说《诗》,要‘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又说:“逆者,等待之谓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来时,且须耐心等,将来自有来的时候。他未来,其心急切,又要进前寻来,却不是‘以意逆志’,却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牵古人言语,入做自家意思中来,终无进益。”②黄宗羲:《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50页。由此看来,理解话语时接受者的“以意捉志”不足取。同样,接受者被动地等待己意与作者之志的遇合③尚永亮、王蕾:《论“以意逆志”说之内涵、价值及其对接受主体的遮蔽》,《文艺研究》2004年第6期。、忽略接受者的主动参与,也不足取。可见,朱氏训“逆”为“迎”有失全面。
《玉篇·辵部》:“逆,度也。”《周礼·地官·乡师》:“以逆其役事。”郑玄注:“逆,犹钩考也。”④《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13页。基于此,有学者认为“以意逆志”中的“逆”为“度”、“钩考”。“度”乃测度,“钩考”犹钩沉,旨在探索深奥的道理或考证佚失的内容。若依此训解,由此“逆”出的结论势必会有层级深浅的区别。具体地说,仅“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会使“逆”浮于表面;若只注重“测度”,理解、接受则会耽于主观臆测;若仅是“钩考”,又会使得理解、接受滞于逻辑实证。事实上,在具体的话语理解中,任何人、任何时候都需要“测度”和“钩考”,但这并不能成为训“逆”为测度、钩考的可靠依据。
训“逆”为测度、钩考,因过于注重接受者的主动性和事实材料的客观性,会使理解、接受偏于一隅,并由此忽略了“逆”的另一特质:反向性。《周易稗疏·数往者顺》:“自上而下谓之顺,自下而上谓之逆。”《尔雅·释言》郝懿行义疏:“逆对顺言,故有拒意;逆以迎言,故有逢遇之意。”就是说,反其道而行的都是“逆”。就话语的建构与解构来说,表达者的建构系统是“志→文→辞”;与之相反,接受者的解构系统是“文→辞→志”。孟子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所揭示的正是这样一种系统。
“以意逆志”的阐释方法提醒接受者不要为修辞文本的字面意义所蒙蔽,要通过对作者创作背景、创作角度、创作动机、处境心绪等的了解和把握,通过对修辞文本有关信息的认识和分析,辨识文本的修辞技巧,领会其言外之意,自觉地为修辞性话语遮蔽进行解蔽,否则会闹出“周无遗民”的笑话。在与咸丘蒙的对话中,孟子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和“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句用的是修辞上的夸张手法,但对诗句的修辞艺术显然已有充分认识。事实表明,接受者不仅要对运用了夸张手法的诗句“以意逆志”,对运用了其他修辞手法或所有具有言外之意的话语都应“以意逆志”。理解张籍的《节妇吟》,如仅拘泥于字面意思,就会把它当作一首描写节妇情志的诗;用“以意逆志”的方法去读诗,就会真正理解张籍以诗明志、婉拒李师道的用意。再如李商隐的《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象征、比兴、暗示等多种手法的运用,使得意象迷离惝恍,意境朦胧隐约;而庄生梦蝶等典故的巧妙运用,则使得诗情蕴藉深远。所以接受者对它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以为是爱情诗,有的以为是咏瑟诗,有的以为是悼亡诗,有的以为是自伤身世诗等等,众说纷纭。①张宝石:《“解诗”与“用诗”》,《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三
从接受者阅读理解的解构系统出发解说“逆”的意义,更合乎孟子的原意,也更符合孟子“以心揆心”的思维方式和“知人论世”的行为方式。
《孟子·告子上》:“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口对于味道,有着相同的嗜好;耳对于声音,有着相同的听觉;眼睛对于容色,有着相同的美感;心对于义、理,也有着相同的感受。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种“以心揆心”、“推扩此心”,在思维方式上,同“以意逆志”有着内在的一致性。②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15页。换句话说,“逆”就是一种典型的“以心揆心”、“推扩此心”。
孟子注重“以心揆心”,而“以心揆心”是建立在知人论世基础上的。孟子曾自豪地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所谓知言,即“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之所以能够知言,是因为“诐辞”、“淫辞”、“邪辞”和“遁辞”表现出了人们的普遍心理,具有一定的共性,这与《周易·系辞下》所言“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③[唐]孔颖达:《周易正义》下,余培德点校,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715-716页。是一个道理。“言为心声”。要知言,首先要知人。孟子在论述交友之道时说:“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④《孟子·万章下》。孟子提倡这种交友方式,也是因为彼此间有共同点,容易沟通。尚永亮、王蕾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肯定孟子的“知人论世”于文学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指出:“‘知人’的核心在于了解作者的心理和人格,即他的思想情感、性格气质、理想追求和艺术修养等有关因素;‘论世’的核心在于了解促成作者人格建构的客观原因,即时代、社会、思潮、风尚等及其给予作者的影响。”并认为,“依此法则循序渐进,顺藤摸瓜,是可以获致对‘作者’之‘志’的较准确的把握”。⑤尚永亮、王蕾:《论“以意逆志”说之内涵、价值及其对接受主体的遮蔽》,《文艺研究》2004年第6期。这与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说的“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⑥王国维:《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见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69-170页。有异曲同工之处。通过其世考察其人,通过其人推求其志,这是理解与诠释之正途。这不仅适用于文学的理解,同样适用于其他表现形式的话语理解。可以说,“知人论世”是“以意逆志”的必须。
另外,对“逆”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同样离不开对孟子“以意逆志”语出背景的考察。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盛行,在政治外交等场合均要求吟咏《诗》中的诗句,通过赋诗、用诗委婉、含蓄地陈述己意。而“春秋之后,周道滞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⑦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1页。,从而出现了“赋诗断章,余取所求”⑧《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之弊端:或不解诗意而断章取义,或有意割裂诗句而引之,有的甚至故意歪曲而用之,等等。针对此等混乱局面,孟子提出“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的主张,有意识地加以纠正。“说诗者”既然不能“以文害辞”、“以辞害志”,停留于文、辞的表面,那么就要深入进去,用自己的知识、经验、体会及逻辑分析与判断能力,去考察、探求作者的本意、目的或所欲达到的目标,从而实现对作者之志的把握。就接受者对作者、作品的了解、把握而言,他绝不是被动地等待,而是主动地探求;在探求过程中,他也绝不会盲目地、毫无根据地进行主观臆断,而需要先做一番精密、细致的调查研究。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⑨鲁迅:《题“未定”草》(七),载《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425-430页。接受者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用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等去探索、寻求作者之志,而不同的接受者具有不同的年龄、性别、职业、身份、知识修养、经验体会等,对同一个接受对象他们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感受,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论。鲁迅先生在谈及《红楼梦》时曾有精辟论述。他说,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①鲁迅:《〈绛洞花主〉小引》,载《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45-146页。不单是命意,人们对《红楼梦》的其他方面也有纷纭奇异的认识,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理解的千奇百态是客观事实,如何理解完全有赖于接受者个人的素养和能力。由此可见,孟子用一“逆”字,是如何精当地概括了“说诗者”的说诗过程的。
中国古典解释学告诉我们,正确而可靠的话语理解方法是“自下而上”阅读分析法与“自上而下”阅读分析法相结合的“上下推求”法。“自下而上”,由字词而句子,由句子而篇章,逐步考察,层层推进,从而获得对话语整体意义的理解;“自上而下”,从社会文化背景和话语的系统性出发,首先“知大体、识大局”,然后由篇而章,由章而句,由句而字词,逐步解决疑难,澄清模糊,进而获得对全句的完整理解。前者主要凸显了文本话语的首要作用,后者则着重凸显了解释者的能动作用。既充分依据话语本身,又充分发挥解释者的能动作用,综合运用这两个因素,就能如愿完成对话语的完整理解,实现对话语信息的整合与建构。如果偏于一端,就会失于全面:仅依据话语本身,得出的结论就会流于片面;仅依据解释主体,就会先入为主,流于主观臆测。②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77-279页。孟子“以意逆志”的“逆”,涵盖面广,表现力强,恰恰包括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个方向的解读过程,当可用现代语词“推求”对应之。
另外,与测度、钩沉相比,推求一词也更合乎人们的理解、接受过程,它涵盖了接受者理解、接受的全过程,从已知到未知,从主观到客观。而测度,则主要侧重于接受者的主观推测,钩沉更多侧重于事实材料的搜集,又偏于客观。孟子提倡“言近而指远”,而且善于“言近旨远”。孟子的“以意逆志”是一种重要的阐释原则和方法,它开启了人们理解言语作品的思路,并由此使学界产生了一大批有价值、有影响的著述。当然,此法的正确使用有赖于解读者实事求是的态度。接受者如果缺乏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缺乏必要的逻辑实证,融入太多的主观臆想成分,就会曲解话语,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