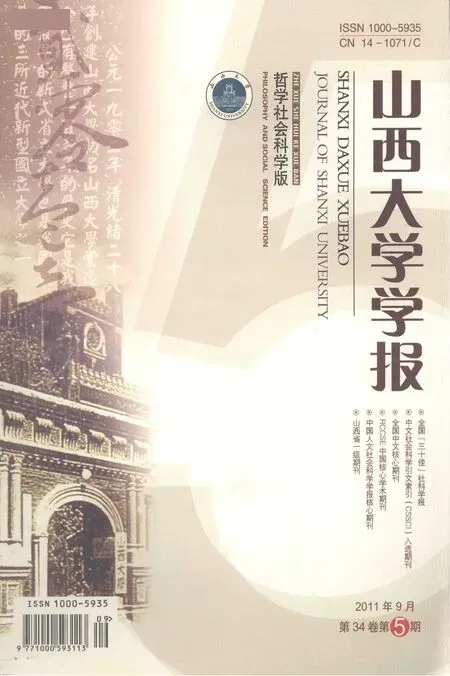论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以构建统一调解制度为视角
赵银翠
(山西大学法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
论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
——以构建统一调解制度为视角
赵银翠
(山西大学法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
法治的局限性、民事纠纷的复杂多样性、行政职能的广泛性等决定了行政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我国现行法规范关于行政调解协议效力的规定却不明确,影响了行政调解制度功能的发挥。从立法政策学的视角来看,行政调解效力制度的完善应以构建统一调解制度为基本出发点,区分不同类型的行政调解,并赋之以不同的法律效力。属于自治型行政调解的,其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效力;属于裁断型行政调解的,由行政调解机关制作的行政调解书一经当事人签收,即具有执行力。
自治型行政调解;裁断型行政调解;效力
在价值日益多元、纠纷日益多样的现代社会,法律的有限性与诉讼的程式化导致人们转而寻求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而调解以其便捷、低廉、灵活、尊重当事人意愿等特征日益成为人们颇为青睐的纠纷解决方式。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大量纠纷不仅仅是利益上的冲突,而且包含着价值上的对立,采取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成为保持社会关系的和谐与平衡的一种更加适合的制度选择。[1]36而行政调解,在现代社会背景之下,随着行政机关管理职能的不断扩张与深化,以及人们对行政的依赖不断增加,日益成为现代社会一项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我国的行政调解机制一方面继承了我国传统社会“和为贵”基础之上的行政调解传统,另一方面在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之下,又融入了新的内涵,在承认利益对立的前提下平衡各方的利益关系,使个体利益之间、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达到一种大致的平衡。由行政机关对其职权范围内出现的民事纠纷进行调解,“具有依靠专家判断、对纠纷当事人有权威性影响力、效率高、成本低,以及可以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积累政策经验等优势”,“不仅对一方当事人要求解决的纠纷给与事后的处理,还往往以一般的预防侵害发生的意识,对没有暴露出来的纠纷也进行积极的事前干预”,[2]83也可以使主管部门察觉到问题发生的根源,从而消除隐患,避免类似纠纷再次或反复出现。由于行政调解具有诸如此类的优势,因而能够发挥其他纠纷解决机制无可替代的功能,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制度设计中,由于行政调解的效力不明确,如何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也存在诸多疑问,直接影响了这一制度功能的实现。据悉,国务院法制办已经就行政调解立法开始进行研究。①“莫于川教授率领课题组圆满完成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委托的‘行政调解立法研究’课题”,载于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52772,2011-6 -25 最后访问。本文拟以构建统一调解制度的立法政策学为视角,从行政调解的双重结构、类型划分等基本理论的分析入手,通对借鉴其他民事调解协议的效力制度,为确定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提供理论依据与制度借鉴,进而为完善我国的行政调解制度提供理论支持。
一 行政调解的双重结构及其类型划分
(一)行政调解的双重结构
行政调解,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对其职权范围内发生的民事纠纷,以法律、政策、人情常理、公序良俗等为依据,居中进行沟通、调停、提供意见甚至调查事实等方式,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从而解决民事纠纷的行政事实行为。
目前学界对行政调解的理解存在两个倾向:一种倾向是强调民事纠纷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另一种倾向是强调行政调解机关的裁断作用。这两种理解均有失偏颇,笔者认为,应当将行政调解视为一个过程,视为所有行政调解程序参加者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行政调解机关与当事人之间的纵向关系,也包括当事人之间的横向关系,在对行政调解进行分析时,既不能过分强调行政调解的纵向关系,也不能过分强调当事人之间的横向关系,才有可能完整揭示行政调解的内涵。具体而言,对行政调解内涵的理解,应从行政调解的双重结构,即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性与调解机关的行政作用性两方面入手加以把握。
1.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
行政调解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体现了当事人的主体性和自治性。民事纠纷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行政调解机制的核心,是行政机关介入民事纠纷的正当性基础。意思自治在行政调解机制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当事人是否选择行政调解解决纠纷取决于当事人的自主意愿,即使在法律明确规定行政调解为行政裁决或诉讼的前置程序的情况下,当事人虽然在程序选择权方面受到限制,但依然可以以拒绝调解的方式体现其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自由;其二,当事人在选择以行政调解作为纠纷解决方式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调解协议的形式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取决于当事人的自主意愿。行政机关在调解过程中的作用在于促成当事人合意的形成,而不是用调解机关的意志来代替当事人的意志,行政机关不得强制当事人接受调解。
2.调解机关的行政作用
尽管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构成了行政调解的基础性结构,但是,在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行政机关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行政调解中,行政机关从始至终介入民事纠纷解决过程,居中沟通、调停,为当事人提供公共政策、法律依据、相关专业知识,甚至就事实真相进行调查,提出解决方案与建议等,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从而解决民事纠纷。虽然这种行政作用因行政机关介入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正是由于行政机关的调解作用,才促成了民事纠纷的有效解决。
(二)行政调解的类型划分
行政调解的双重结构决定了行政调解的独特性。行政调解是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基础的纠纷解决方式,但又不同于完全的当事人自治式纠纷解决方式,而是在行政机关主持下,由当事人根据自己的合意达成调解协议。在调解过程中,由于行政机关介入民事纠纷的深度与强度不同,从而会对调解的性质与结果产生不同影响。“调解的结果经当事人双方同意或合意,类似于契约,而调解过程则类似于在第三者的帮助或主持下展开的契约的交涉过程。第三者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可强可弱。如果其作用越弱或仅仅停留在促进信息交换的程序,调解所达到的结果就越接近于契约的性质,第三者解决纠纷的正当性较明显地建立在当事人的合意之上。而随着第三者作用的加强或增大,如不仅提供解决方案还施加种种压力迫使当事人接受的话,则调解的结果就带有了更浓的‘裁决’色彩。”[3]27因而,根据行政机关介入民事纠纷的深度与强度不同,大体上可以将行政调解分为自治型行政调解与裁断型行政调解。
所谓自治型行政调解,是指在行政调解过程中,民事纠纷当事人起主导作用,而行政调解机关居中进行劝告、提供专家意见、阐明法律政策等,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是否达成调解协议并签订调解协议书。例如,根据《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7-11-3)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对合同争议进行调解。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受理调解申请后,其对当事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最后如果调解成立的,由双方当事人应当签署调解协议,或者签订新的合同。①参见《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7-11-3)第10、第11、第15、第19条。在调解过程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进行实质审查,不调查取证,调解协议最终由当事人进行签署,而不是由调解机关签署。由此可以看出,在合同争议的解决过程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调解只是起到居中促成作用,调解协议的达成以纠纷当事人为主导,因此,此类调解可归入自治型行政调解。
所谓裁断型行政调解,是指在行政调解过程中,行政机关积极主动调查取证、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甚至提出调解方案,在此基础上由民事纠纷主体决定是否达成调解协议,如果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经行政调解机关审核并制作行政调解书。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2005-8-28)第9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2006-1-23)进一步规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的规定,对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以及其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应当本着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依法尽量予以调解处理。……同时,为确保调解取得良好效果,调解前应当及时依法做深入细致的调查取证工作,以查明事实、收集证据、分清责任。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书,交双方当事人签字。”该解释强调了公安机关应依法进行调解,强调了公安机关在行政调解中“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义务,明确了如果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公安机关应当制作调解书等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在调解过程中,公安机关对能否达成调解协议以及调解协议的内容有很大的决定作用,因此,可以将公安机关所作的治安纠纷调解归入裁断型行政调解。
二 现阶段有关行政调解协议效力的规定及相关理论
关于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现行法规范的规定并不明确、统一,其基本的制度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其一,行政调解协议无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履行的,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2005-8-28)第9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规定将达成并履行调解协议作为不予行政处罚的法定情节予以规定,而调解协议本身并无法律约束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对方当事人应以民事争议为由提起民事诉讼。《道路交通安全法》与《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办法》也作了类似规定。①《道路交通安全法》(2007-12-29修正)第74条规定:“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办法》(1997-11-3)第20条:“调解不成立或者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告知当事人根据仲裁协议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其二,行政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应当履行,但调解协议的性质以及不履行调解协议的法律后果不明确。例如,《电力争议调解暂行办法》(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2005-3-28)第25条第2款规定:“电力监管机构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应当履行。”《民间纠纷处理办法》(司法部,1990-4-19)第16条规定:“……调解书自送达之日起生效,当事人应当履行。”
从上述这些规定可以看出,现行实定法规范要么回避对行政调解的效力作出规定,要么含糊其辞,对其法律效力的性质语焉不详。实定法规范不明确,理论界与实务界也未形成统一观点。目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关于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调解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该观点认为,“行政调解是非权力性质的调解,其效力依赖双方当事人的自觉履行。即便当事人达成协议,也可以反悔。当事人反悔的,调解书不发生依靠国家公权力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也有学者以1997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办法》的规定为例加以说明,认为该办法第20条的规定“间接表达了行政调解协议允许当事人反悔的意思。”[4]220
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调解具有合同效力。其理由是调解协议与和解协议具有同质性,和解协议具有合同效力,因而行政调解协议作为调解协议的一种当然具有合同效力。[5]100-103有的人民法院在实践中也持这一观点。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年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七部分第9条规定:“就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或者一般人身损害赔偿,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在公安机关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后,一方反悔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保护起诉权。但不能证明在订立协议时具有无效或者可撤销情形的,应认定协议有效。”该规定明确了行政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虽然没有阐明该法律效力的性质,但从内容可以看出,其认为行政调解协议与当事人的和解协议具有同样的效力,即具有民事合同的效力。
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调解协议效力应高于一般民事调解协议的效力。其理由是行政机关是具有公权力属性和中立地位的第三方,其调解具有较高合法性、合理性和规范性,由行政机关主持所达成的调解协议的效力理应高于一般民间调解协议。同时,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对行政调解协议效力的定位,应与具体制度与程序相联系,在专门调解机制与附带调解机制中应有所不同。[6]174-184
目前法规范关于行政调解协议效力的规定不明确、不统一,相关理论研究也不足以为行政实践与司法实践提供有力的指导,导致了行政调解机制的虚置与行政资源的浪费,而行政调解协议具有明确的法律效力是行政调解机制有效运作的前提,因此,行政调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必须首先从制度上明确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现行民事调解协议的效力制度上获得相应的制度经验。
三 其他民事调解协议效力制度对行政调解协议效力制度的启示
与行政调解协议效力的法规范不明确、不统一的现状相比,其他民事调解协议的效力则有较为明确的法规定。鉴于行政调解协议与其他民事调解协议具有一定程度的同质性,因此,对其他民事调解协议效力的分析可以促进我们对行政调解协议效力的理解,并进而为明确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提供制度借鉴。
(一)其他民事调解协议的效力
民事调解的种类很多,大体上可将其分为正式的民事调解与非正式的民事调解。正式民事调解是当事人通过寻求法定的调解机构对民事纠纷进行调解。在我国,正式的民事调解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与法院调解等调解机制。非正式民事调解是指当事人在正式民事调解机构之外寻求其他第三人对民事纠纷进行调解,包括各类协会、人民团体、个人、所在单位等进行的调解。非正式调解机制之下当事人就其纠纷达成调解协议的,如果调解协议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应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具有民事合同的效力。而正式调解机制之下所达成的调解协议的效力如何,则取决于立法者的制度选择。现行法规范根据调解协议(书)的不同性质,设定了不同的效力制度。下文就正式调解机制之下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法院调解书、仲裁调解书的效力进行分析。
1.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
人民调解协议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的调解下,当事人为解决民事纠纷而达成的明确其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关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国务院,1989-6-17)与《民事诉讼法》(1991-4-9通过,2007-10-28修订)的规定并不明确。直至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02-9-16),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与效力才得以明确。该司法解释第1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
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人民调解法》(2010-8-28)关于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规定虽然在表述上不同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但基本上确立了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法律制度。根据该法第31条、第32条的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当事人之间就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关于调解协议所具有的“法律约束力”的性质,笔者认为,这一法律约束力指的就是民事合同意义上的法律约束力,其理由有二:其一,《人民调解法》将人民调解协议视为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调解协议;其二,当事人之间就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的,应当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解决争议,当事人无权拒绝履行调解协议,亦无权变更或者撤销调解协议。
2.人民法院调解书的效力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在作出判决之前,对于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对当事人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亦可自行和解,并达成和解协议。对于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予以确认并制作调解书。①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4]12号)第4条。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②参见《民事诉讼法》(1991-4-9通过,2007-10-28修正)第9、第89、第91条。调解协议生效后一方拒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持民事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③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15号)第15条。由此可以看出,由人民法院制作的调解书具有相当于民事判决的效力,其一经生效,即具有既判力,当事人必须履行生效的调解协议,否则,另一方有权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3.仲裁调解书的效力
民事纠纷当事人选择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仲裁庭在作出裁决前,可以先行调解。当事人自愿调解的,仲裁庭应当调解。根据《仲裁法》(1994-8-31)的规定,“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或者根据协议的结果制作裁决书。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在调解书签收前当事人反悔的,仲裁庭应当及时作出裁决。”④参见《仲裁法》(1994-8-31)第51、第52条。由此可见,当事人在仲裁裁决前达成调解协议并由仲裁庭依法制作调解书的,该仲裁调解书具有与仲裁裁决书同等的法律效力。
(二)其他民事调解协议的效力制度对行政调解协议效力制度的启示
上述三类正式民事调解从性质上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当事人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之下进行的调解;另一类是当事人在审判机构或者仲裁机构的主持下进行的调解。对于前者,由于作为调解主体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群众性组织,其调解活动不涉及国家公权力的运用,因而可以称之为自治型调解;而对于后者,由于作为调解主体的是国家审判机关以及法律授权的仲裁机构,可以称之为裁断型调解。由于民事调解的类型不同,与之相应的调解协议的效力也不同。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效力;而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并由人民法院制作的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效力;在仲裁机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并由仲裁机构制作的调解书与仲裁裁决书具有同等的效力。这一制度安排区分了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对在不同救济机制之下达成的调解协议赋予了不同的法律效力,这一思路对于我们思考行政调解协议效力的制度设计具有参照意义。
四 统一调解制度视角下的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
由于我国调解机制众多,对行政调解协议效力的制度安排,应在法制统一的原则下,考虑与其他调解制度之间的协调性与一致性,在此基础上体现行政调解的独特性。如前所述,行政调解具有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与调解机制的行政作用的双重结构,而在此基础上对行政调解所作的类型划分,正好与上文民事调解的类型划分相契合,笔者认为,从构建统一调解制度的立法政策学的视角出发,立法者可以借鉴其他民事调解协议的效力制度,对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作出明确、统一的制度安排。
在自治型行政调解中,当事人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具有民事合同的效力。因为在自治型行政调解过程中,行政调解机关所起的作用体现为向当事人解释法律与政策、提供专家意见、进行劝导等,纠纷的解决由当事人自主决定。当事人在此基础上缔结的调解协议,其效力不是来源于行政调解行为,而是来源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来源于当事人交涉性的合意。对于当事人之间的相互承诺,应承认其具有合同的效力。合同一经成立,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应当依法履行调解协议。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其履行调解协议。如果另一方认为调解协议无效或者可变更、可撤销的,应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其无效或者变更、撤销调解协议。
在裁断型行政调解中,由行政调解机关在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上制作的行政调解书,一经当事人签收,即具有执行力。在裁断型行政调解中,行政机关有义务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在此基础上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是否能达成和解。如果当事人就纠纷达成合意的,由行政机关根据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制作行政调解书。因此,尽管裁断型行政调解书是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基础,但该调解书同时也反映了行政调解机关的意志。行政调解机关制作的行政调解书,经双方签收后,具有执行力。当事人一方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只要不存在明显违法情形的,人民法院应予执行。①笔者认为,不应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行政调解书的权力,而应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借此可以通过执行过程中审查程序,审查行政调解是否存在明显违法的情形,从而避免行政调解作用的滥用。如果一方认为行政调解书存在无效或者违法情形的,则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司法程序确认行政调解书无效或撤销行政调解书。
[1]季卫东.调解制度的法律发展机制——从中国法制化的矛盾情境谈起[M].易平,译//强世功.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36.
[2][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M].王亚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83.
[3]王亚新.纠纷、秩序、法治——探寻研究纠纷处理与规范形成的理论框架[M]//清华法律评论:第2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27.
[4]崔卓兰.新编行政法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220.
[5]赵石麟.行政调解协议的合同效力探析[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5):102-105.
[6]范 愉.行政调解问题刍议[J].广东社会科学,2008(6):175-185.
(责任编辑 魏晓虹)
On the Legal Validity of the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ng the United Mediation Mechanisms
ZHAO Yin-cui
(School of Law,Shanxi University,Taiyuan030006,China)
The limitation of rule of law,the complexity and variety of civil disputes and the extensiveness of administrative function decide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solving civil disputes.The uncertainty of the legal effectiveness of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in present statutes affects the function of i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islative policy,the improvement of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mechanisms should be based on constructing the united mediation mechanism,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s and endowing them different validity.The agreements made by parties ha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ivil agreements in the autonomous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and the agreements made by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have the effectiveness of enforcement in the arbitrary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the autonomous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the arbitrary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validity
D912.1
A
1000-5935(2011)05-0111-06
2011-06-10
山西大学校科研基金2007年人文社科项目“行政过程中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0709058);2008年万权律师事务所委托课题“行政调解制度研究”
赵银翠(1972-),女,山西寿阳人,山西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比较行政法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行政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