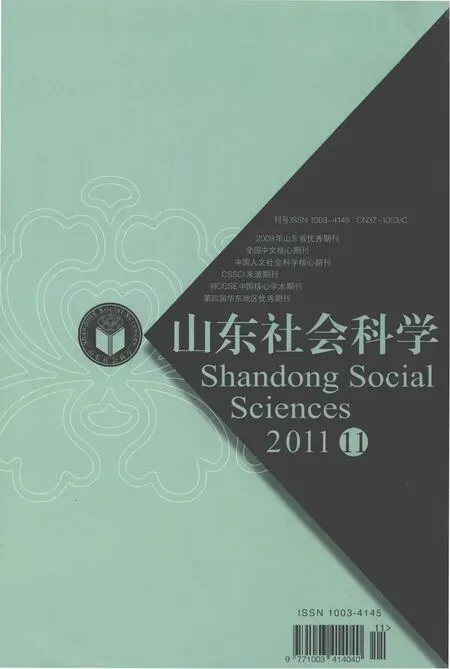论科学证据对常识证据的超越
刘振红
(安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河南安阳 455000)
论科学证据对常识证据的超越
刘振红
(安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河南安阳 455000)
科学证据克服了常识证据的表象性、模糊性等缺陷,是对常识证据的超越,但超越并不意味着科学证据可以替代常识证据,更不意味着常识证据退出了诉讼舞台。当前,在诉讼实务中,人们优先使用的仍是常识证据,科学证据只是作为常识证据的补充而排在第二位。美国比较法学家达马斯卡教授的“科学将会将经验常识从事实认定中彻底清除”的观点有所偏颇。
科学证据;常识证据;超越;经验
“在我们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①[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86页。科学已经成为人们把握世界的主要方式,它日益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司法裁判活动而言,越来越多的重要事实只能通过高科技手段查明,事实认定越来越依赖于科学证据。美国比较法学家达马斯卡教授预言:“随着科学在日常生活的各项事务中持续不断地证明自己最适合担任最终裁判者的角色……它会将经验常识从事实认定中彻底清除。”②[美]米尔吉安·R·达马斯卡:《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制度》,吴宏耀、魏晓娜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科学证据真的能够完全取代常识证据吗?如果不能,那么在事实认定过程中,它们又各自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一、依附于日常经验的常识证据
常识是人类世世代代日常生活经验的累积,是人类生存的重要手段,它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常识最本质的特性是经验性,在此意义上,我们常常把经验与常识连用,称为“经验常识”。常识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对人类的思想和行为起着规定和否定的双重作用,它规范人们怎样想和不怎样想、怎样做和不怎样做。③杨建军:《常识常理在司法中的运用》,《政法论丛》2009年第6期。诉讼行为同样也受常识的规范和制约,比如《周礼·小司寇》记载:“职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这里的“五听”就是对人们日常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生活常识在司法活动中的运用。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和感受:如果一个人说假话,那么一般会表现出言词混乱、面色发红、喘息加重、眼神慌乱等生理现象。依此生活经验,人们便可在司法活动中判断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依靠常识解决纠纷在英美法系中普遍存在。“在英美法传统中,审判最初是解决常规纠纷的手段。原始审判通过把对当地事务拥有知识的个人集合起来的方式裁决恼人的纠纷。纠纷的存在方式是常规知识的组成部分,其解决方式也取决于常规知识。决定疆界、水体使用权或财产权合理保护的地方性常规,是真正意义上的常规,因而为整个社区所知晓。”④[美]罗纳德·J·艾伦等:《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张保生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52页。这种建立在常识基础上,运用常识收集、审查判断的证据,可以称之为常识证据。换言之,一项证据,无论其表现形式是物还是人,如果它的收集、审查方法主要是依赖于人们的经验常识,就可以称之为常识证据。①笔者认为,常识性证据、科学性证据的提法更能准确反映出常识、科学在证据收集、审查判断过程的地位和作用,也能避免证据种类上的混乱。按照学术界的习惯用法,本文仍用常识证据、科学证据的提法。
常识证据具有以下优点:一是主体的大众化。常识是正常人所拥有的知识,它并不为少数精英人士所垄断。人类认识成果通过教育等途径转化为个人的常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个人的受教育史就是浓缩的人类认识史常识化的过程。正因为每个人都分享着常识、使用着常识、贡献着新的常识,所以,人们才能有效地沟通、交流,进而凭借常识对他人行为作出评判并进行预期。这样,即便是普通人也可胜任依靠经验常识从事诉讼证据收集、审查判断等任务。反之,如果否认常识证据主体的大众化,那么陪审团审判作为英美法系事实认定模式的正当性理由就会大打折扣。②达马斯卡教授把其归结为“审判法院的特殊结构、诉讼程序的集中、诉讼当事人及其律师在法律程序中的显著作用。”参见《漂移的证据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5-40页。二是成本的经济性。相对于科学证据而言,常识证据易于获取,不需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特殊经验的专家参与诉讼,不需要为此支付额外的费用,因此,常识证据有利于减轻当事人的经济负担和节约司法资源。三是使用的便捷性。常识内化于人的头脑中,可以随时调用,而不受时间、地点等条件的限制。
当然,依附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常识证据也有其局限性。恩格斯说:“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是极可尊敬的。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惊人的变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某一动物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我们就发现,这有时是极其麻烦的事情。这一点法学家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为了判定在子宫内杀死胎儿是否算是谋杀,曾绞尽脑汁去寻找一条合理界限,结果总是徒劳。”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361页。具体而言,常识证据有以下局限:首先,常识证据不具备精密性、完备性。当代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说:“常识性知识的特征就在于:它既不是明确地系统的,也不是明确地批判的,就是说,既没有把它的所有各个部分同所有其他部分联系起来,也没有自觉地企图把它当做一个首尾一贯的真理体系。”④[美]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85页。其次,常识证据告诉人们的往往是表象,而不是本质。常识虽然“在一定的限制内足够精确,但它很难含有那种对事实为什么是它们被断言的那样的说明。”⑤[美]欧内斯特·内格尔:《科学的结构——科学说明的逻辑问题》,徐向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版,第3页以下。常识更多地让人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比如在“三鹿奶粉案”中,人们凭借常识难以断定“劣质奶粉与胎儿发育畸形或导致婴儿出现大头病这两类现象之间是否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⑥有的学者认为“常识只能作为真的证实标准而不能作为证明标准,真的证明标准只能是命题与科学证据相符合。”参见张继成《论命题与经验证据和科学证据符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再次,“常识有错的概率其实很高,不仅因为时代的变迁,也因为认识的局限。”⑦孟勤国:《常识与事实的距离有多远——关于法国和德国民法典的一个话题》,《法学评论》2009年第6期。这种情况在法学研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武汉大学孟勤国教授经过历史的考察、逻辑的分析,颠覆了民法学界的一个常识,他认为“法国民法典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典型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典型民法典”的观点是错误的,“法国和德国民法典与资本主义的自由与垄断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只是后世民法教授人为地生拉硬扯关系,所谓的常识不过是学术游戏形成的学术垃圾”。⑧孟勤国:《常识与事实的距离有多远——关于法国和德国民法典的一个话题》,《法学评论》2009年第6期。与常识错误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一个人对生活中的常识有足够的认识,并经过自觉的、反复的训炼,就可以规避常识,在他身上看不到常识作用的印记。对此,典型的例子就是惯犯,他们面对讯问可以做到面不改色,依靠经验性的察言观色很难断定他们是否讲真话。第四,常识有其发挥作用的边界,有些法律现象是常识无法解决或难以解决的。比如,犯罪现场遗留的到底是血迹还是红颜色的别的物质?靠经验观察有时是难以确定的。如果是血迹,是否是犯罪嫌疑人所遗留?这个问题就需要鉴定人员通过运用DNA技术的分析、判断,才能作出准确认定。
二、随科学而发展的科学证据
科学证据是近代科学与诉讼相结合、为解决诉讼中的专门问题而产生的证据类型。⑨陈学权认为,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就有古代科技证据制度,但他又认为“古代科技证据主要是以经验性技术占据主导地位”。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科学证据始于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以后。参见陈学权:《科技证据论——以刑事诉讼为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1-93页,第105页。科学是科学证据形成、发展的源泉和基础。离开科学,科学证据的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身识别技术的进步过程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在18世纪以前,虽然已经开始利用人体外貌特征和笔迹特征进行人身识别,但远没有形成科学的体系。进入19世纪以后,由于科学技术在欧洲的长足进步,笔迹鉴定成为了一门科学,出现了人体测量法,同时,指纹也得到了系统的研究。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为人身识别技术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相继出现了足迹鉴定、压痕鉴定、声纹鉴定、唇纹鉴定等新方法,特别是8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DNA技术,带来了人身识别方法的一次新的飞跃,这种生物医学技术向人们展示了异常丰富的个体特征信息。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推动下,人身识别达到越来越精确的程度。此外,诉讼实践的新需要也是科学证据发展的推动力量,这种需要为科学证据的发展指明方向、提出要求,它召唤着把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引入诉讼领域,以解决诉讼中常识证据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尽管科学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学术界对什么是科学证据仍存在不同的认识,代表性的观点有6种之多。①陈学权:《科技证据论——以刑事诉讼为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47页。何家弘教授从解读物证需要科学技术出发,“称物证及其相关的鉴定结论等证据为‘科学证据’”。②何家弘:《中国证据法学前瞻》,《检察日报》1999年9月2日第3版。四川大学张斌博士以“语义结构和证据功能”为分析框架,认为科学证据就是“运用具有可检验特征的普遍定理、规律和原理解释案件事实构成的变化发展及其内在联系的专家意见”。③张斌:《论科学证据的概念》,《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6期。王传道教授认为:“凡是借助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收集到的证据材料以及借助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揭示出其证明价值的证据,都属于科学证据。相反,不是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发现、收集和揭示出来的证据都不属于科学证据。”④王传道:《科学证据在未来司法活动中将大显身手》,《证据学论坛》第4卷,第380-381页。胡锡庆教授认为:“现代科技证据,不是诉讼证据的一种,……是诉讼证据的一个类别,包括:鉴定结论,视听资料,勘验、检查笔录,现场笔录等。”⑤胡锡庆主编:《诉讼证明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通过争论,人们对科学证据的认识逐步深入,并取得了一些共识:一是,科学证据中的科学不仅仅指自然科学,还应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不仅仅指传统科学,还包括新兴科学。二是,科学证据不同于法定证据,二者的分类标准不同。前者以证据发现——收集——提取——审查判断这一运行过程中是否使用科学原理和技术为标准,而后者主要基于证据的表现形式。
笔者认为,在界定科学证据概念时,首先需要作一个拓展性思考,即证据法学为什么需要研究科学证据,这是界定科学证据概念的认识前提。否则,就会陷入纯粹的概念之争。如前所述,在人类诉讼历史的早期,证据主要表现为常识证据,科学证据是近代科学与诉讼相结合的产物,是为克服常识证据的不足而产生的。但在功能方面,科学证据与常识证据都是准确认定事实的手段。证据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2010年7月1日施行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确立了该原则,其第2条明确规定:“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依据。”依据该原则,证据越多越有利于事实认定,所以,证据学对科学证据采取的是欢迎态度,积极吸纳科学研究的成果来解决诉讼中的专门问题。只是出于诉讼效率、政策选择等价值考量,才排除一些证据。由此反思学者们的科学证据概念之争,可以发现很多争论是无谓的,因为缺少争论的前提——为什么需要科学证据?概言之,科学证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获取、解读案件事实的信息;科学证据是准确认定高科技犯罪的案件事实必不可少的证据,缺乏科学证据,高科技犯罪之类的案件难以侦破、难以证明。⑥熊志海、高源:《证据之异化及回归——以证据与证据运用区分为中心》,《政法论丛》2009年第3期。基于此,笔者认为,只要有助于人们认定事实,并在证据收集、生成、质证、认证中采用科学技术、原理与方法,并且不与诉讼效率、政策选择等价值相冲突的证据,都可以称之为科学证据。
科学证据的种类随科学的发展而丰富。开始时科学证据主要是医学与法律相结合而产生的法医学证据,如人身损伤鉴定、死亡原因鉴定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包括测谎仪、声谱仪、枪弹痕迹检验、中子活化分析、DNA分析等各种类型的科学证据相继进入诉讼程序。目前,科学证据涉及的学科已经由法医学扩展至精神病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各门具体科学。科学证据已经成为证据法学与具体科学之间的连接桥梁,并使跨学科研究成为证据法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心理学对证据法学的入侵以及概率论、经济分析、女权主义运动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法的采用,传统的证据法教义性研究受到挑战,证据法学研究呈现出跨学科发展的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证据法学跨学科研究的步伐进一步加快。”①郭金霞:《鉴定结论适用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证据科学文库总序”第1页。与此同时,人们对科学证据的认识也逐步深入。美国关于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的演变历程清晰地说明了这点。在弗赖伊(Frye)案件之前,法庭对专家证言的审查只局限于专家的资格,而不考虑形成其证言的基础理论与方法的可靠性。在1923年的弗赖伊案件中,法庭确立了弗赖伊规则,即“普遍接受的检验标准”。批评者认为,该标准过于保守,会妨碍基于新兴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所产生的科学证据的使用。在1993年道伯特(Daubert)案件中,法庭就不再局限于“普遍接受”,而是提出了从四个方面检验科学证据可靠性的道伯特规则:(1)争议的科学理论或技术能被检验或者已被检验了吗?(2)该理论和技术已经受同行审查和出版了吗?(3)争议技术潜在的错误率是多少?(4)该理论或技术在科学团体中普遍接受的程度如何?在1992年的Joiner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又把道伯特规则往前推进了一步,其判决意见指出,在审查科学证据可采性时,不仅应当审查专家证言依据的科学原理和方法是否源于科学知识,而且还应当审查专家根据科学资料得出的推论或者论证是否科学。判断专家证言可采性的《联邦证据规则》702条在1998年也进行了修订。②国内很多著作和文章在援引该条时称之为“第702条”。这是一个有害的错误,因为依照解读我国法律的习惯,第702条往往意味着在其前面已经有了701个条文。实际上,《美国联邦证据规则》11章总共有67个条文。该条属于第七章中的第二个条文,称之为702条较为妥当。与修订前的条文相比,新条文保留了原有条文内容,即“如果科学、技术或者其他专业知识,将辅助事实裁判者理解证据或裁判有争议的事实,因其知识、技能、经验、培训或教育而具备专家资格的证人,可以意见或其他形式对此作证”。在此基础上,增加“但须符合下述条件:(1)证言基于充足的事实或数据;(2)证言是可靠的原理或方法的产物,并且(3)证人将这些原理和方法可靠地适用于案件的事实”。也就是说,新修订的702条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3个可采性标准,分别为充分性、可靠性和适用性。
三、科学证据对常识证据的超越
每一时代的证据都是其时代的产物,打上了该时代的烙印,反应了当时的生产力状况、社会关系和人们的认识能力。诉讼法学界把证据制度的沿革分为神示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各有其占主导地位的证据,并由此彰显其证据特征。比如,在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前期的神明裁判阶段,与当时生产力落后、人类处于愚昧状态相对应的是,当出现疑难案件时,“人们将神的示意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唯一依据”,③陈光中:《刑事证据制度改革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之探讨——以两院三部〈两个证据规定〉为视角》,《中国法学》2010年第6期。当时出现了水审、火审等诸多神判证据形式。神判证据成为这一阶段的证据特征。而在欧洲中世纪和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口供裁判阶段,人们主要凭借经验常识判断证人证言这一主要证据的真实可靠性。相应地,常识证据成为该时代证据的代表。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广泛传播,科学证据在诉讼中得到了日益广泛的使用,“从血迹、毛发、体液、药物、纤维、指纹、掌纹、皮肤纹及脚足痕迹等物取得之证据(样品),用以判定犯人同一性之精密方法已臻进步,亦可谓已达普遍化之程度”。④黄朝义:《刑事证据法研究》,元照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229页。科学证据成为诉讼证据的当代特征。
科学证据对常识证据的超越主要表现为,科学证据弥补了常识证据的表象性、模糊性、不精确性等不足。这种超越主要是就其功能而言的,并不意味着科学证据完全取代了常识证据。在生活越来越科学化的今天,常识在司法审判中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审判者的头脑并不是一张白纸,而是存在着由大量背景信息(包含常识)所组成的“知识库”。特文宁教授认为:“一个‘知识库’不是由那些业已经过了单独地、实证地检验并且已经清楚明确地作出的命题所组成的;相反,从个人和集体的角度上看,在我们的头脑中都存在着一些错误定义的信息板块,而这些就典型地构成了一个知识库,它是一个容纳了具有良好理由的信息、深思熟虑的模式、逸闻趣事的记忆、影响、故事、神话、愿望、陈腔滥调、思考和偏见等诸多内容的复杂的大杂烩。”⑤参见[加]玛里琳·T·迈克瑞蒙:《事实认定:常识、司法认知与社会科学证据》,徐卉译,《公法》(第四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页。
科学证据对常识证据的超越也不意味着在证据使用的先后顺序方面,人们首先选择科学证据,其次选择常识证据。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面临使用常识证据还是科学证据的选择时,人们首先考虑的是常识证据,除了前文所述的常识证据的优点之外,还有心理学方面的原因。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人们不会舍近求远,置唾手可得的常识证据于不顾而选择费时费力的科学证据。只有在常识证据不能满足认定事实需要时,人们才会使用科学证据。所以,就证据使用顺序而言,科学证据是排在第二位的,是常识证据的补充。另外,科学证据也并非完美无缺。一是,它有时会与效率、公正等诉讼价值目标产生冲突。聘请专业人员就案件中的专门问题进行检验、分析、判段,需要有时间、资金的保障,无疑会造成诉讼的拖延,会使贫穷的当事人无力承受。①拜荣静、王世凡认为,应把鉴定救济纳入法律援助制度,以确保公民在鉴定中不受财产多少的影响而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参见拜荣静、王世凡:《司法鉴定程序法律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页。二是,审查科学证据对事实认定者来讲是件力所不能及的工作。“一方面,事实裁判者因为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而被迫使用专家证言,而另一方面,他们还得对专家证人的证言进行批判性评价,甚至需要他们对专家证言之间的矛盾作出决断。但是,一个连该学科的基本概念都尚未掌握的人,又怎么能够洞悉其中的复杂性,或者对这些‘高级传教士’之间的争议进行裁决呢?”②[美]米尔吉安·R·达马斯卡:《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制度》,吴宏耀、魏晓娜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6页。优先使用常识证据也是很多国家的做法,如澳大利亚在专家证据的可采性方面明确规定的普通知识规则:“只有在专门知识超出陪审团的知识和经验范围时,才有必要聘请专家提供专家证据。也就是说,如果证据所涉及的知识和经验,在陪审团完全有能力作出判断的范围之内,就没有必要聘请专家。”③季美君:《澳大利亚专家证据可采性规则研究》,《证据科学》2008年第16卷(第2期),第149页。《美国联邦证据规则》702条规定了专家证言的辅助规则:“如果科学、技术或其他专业知识,将辅助事实裁判者理解证据或裁判有争议的事实,因其知识、技能、经验、培训或教育而具备专家资格的证人,可以意见或其他形式对此作证。”换言之,并非所有的主题都适于专家证言,“只有承审法官被说服,在一主题上提出专家证言对陪审员(或法官自己,在没有陪审团的审判中)有所帮助时,当事人才准许提出。”④[美]Arthur Bes:t《证据法入门——美国证据法评释及实例解说》,蔡秋明等译,元照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234页。与此类似,英国规定了专家证言的有用性规则,即只有专家证据能为法庭提供实质性帮助时,该专家证言才具备可采性。
汉斯·波塞尔先生在其名著《科学:什么是科学》的“引言”中写到:科学,“已以空前未有的程度与速度控制与决定着我们的生活,渗透与贯穿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铁面无私的法庭上,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圣经》中的上帝提出的律条,亦不是传统力量的约束,而是‘专家们’的一纸鉴定”。同时,他在该书的“结束语”中又指出,“批判是科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设性部分。批判即是对科学中所提出的每一个答案的批判,是围绕着科学所追求的每一个答案的客观性的批判,是科学中对其每一答案的解释与说明的批判,因而是在科学内部进行的批判”。⑤汉斯·波塞尔:《科学:什么是科学》,李文潮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240页。正是这种“内部批判”才保证了科学中的正确结果。⑥波塞尔先生在提出科学的“内在批判”的同时,还提出了“外在批判”问题。参见汉斯·波塞尔著《科学:什么是科学》,李文潮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40-242页。波塞尔先生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把握科学作用的基本原则:科学不是万能的,它有其发挥作用的边界。
今天,科学毫无疑问已成为人们把握世界的主要方式,但它绝不是唯一方式,而是与神话、宗教、艺术、哲学等并存的一种方式。所以,达马斯卡教授的预言有所偏颇,科学证据不可能将常识证据从事实认定中完全排除,正如科学不能完全排除迷信一样,这与科学的普及、人们教育程度的提高不具有必然联系。
D915.13
A
1003-4145[2011]11-0085-05
2011-07-05
刘振红,安阳师范学院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主要研究证据法学、诉讼法学。
(责任编辑:周文升wszhou66@126.com)